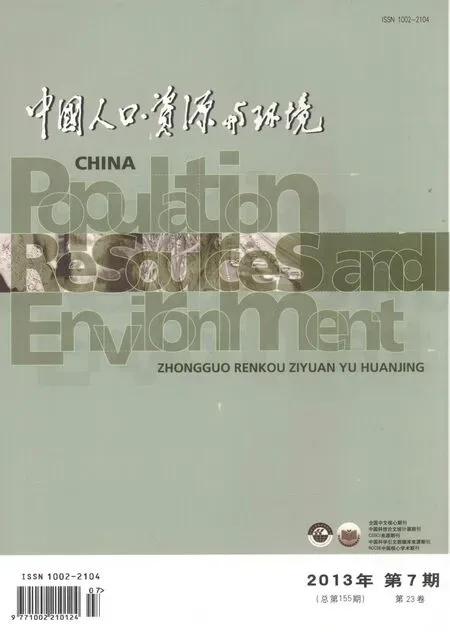國外環境社會系統研究進展
夏 成 甘 暉
(1.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北京100871;2.福建師范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經濟學院,福建福州350007)
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建設的全過程。將環境、社會(包含經濟維度)作為一個系統即“環境社會系統”來進行研究,有助于豐富并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并有望為生態文明建設服務。國外關于此系統名稱的提法有多種,比如社會 -生態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1]、環境社會系統(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2]、復合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3]、人與環境系統(Human-environment system)[4]等。本文除直譯外,其它主要使用“環境社會系統”這一提法。這類研究盡管意義重大,但由于需要多學科的參與和集成,因此難度較大,目前尚處于探索期,還不成熟。本文結合國外此領域的相關進展,本文重點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了歸納。
1 共同演化
共同演化(co-evolution),由兩物種之間的演化擴展到物種適應其生物和物理環境的各種特點時產生的演化[5],其意義在于它將演化生物學和生態學聯系起來。演化的思想已經成為生態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6]。
目前,共同演化的概念已經從生態學擴展至不同種族基因、文化變遷領域[3,7,8]。雖然關于達爾文的進化的基本觀點能擴展到社會、經濟的哪些具體領域及其使用界限仍是目前的爭論焦點之一,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社會、文化演化過程和自然進化過程都有其自身機制,且存在重要的、根本性的差異[5]。Norgaard[5,9,10]提出并初步發展了環境系統和社會系統互相影響、共同演化的思想:環境系統和社會系統是共同演化的,前者影響了后者的文化、價值、科學技術以及社會組織,后者也對環境系統產生影響并體現了環境系統的特點。
文化演化的過程是指從宏觀、微觀層面包含人群在內的各種系統的變化。其方式主要有:通過大規模的生物物理影響;通過有意識地設計文化產品和過程作為選擇力量;故意“操控”基因信息[5]。而自然演化又會在不同的層面、以不同的強度影響文化演化。一些學者已經開始研究文化與自然共同演化的特點及其與技術和社會組織的聯系,以便理解人類的文化如何影響演化的過程和規律,知曉人類的生物性未來[5,11]。
Holling[8]把“pan”和“hierarchy”合成為“panarchy”,暗示了系統演化過程中可能存在不可預期的變化;并通過適應性循環(adaptive cycle)這一概念模型描述了系統的發展、病態和毀滅等不同階段中主體的狀態特征。IPCC的一份報告[12]認為,為了理解社會、制度、技術的演化過程,必須解決以下問題:對新的行為、制度、社會或文化模式的研究;對那些已經發現的(規律)進行試驗;使用各種方法選擇“合適的”或“可取的”變化;使用各種方法普及并固定已經選擇的變化。農業共同演化的研究認為,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是共同演化而非動態平衡,行為的驅動因素可能隨時間演化[13-15]。
當前,不同國家、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全球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壓力。開展環境社會系統演化的動因、機制、途徑等方面的研究,對不同區域邁向生態文明,實現一個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視角。
2 方法論研究
社會系統、自然系統、眾多人造物都具有整體涌現性,因此需要整體性的研究方法。這不僅需要生態學的參與,還需要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技術)的參與[3,4,16,17]。
研究一個系統至少包括三個層次:系統、子系統、包含兩個或以上子系統組成的體系,即suprasystem[8]。層次理論是理解和處理復合分級系統的一種整體性方法;具有等級結構的集成系統比不具有等級結構的、且包含與前者相同元素的集成系統演化得快,還具有更好的恢復力(resilience)[6]。
社會-生態系統具有新的、復合的模式與過程,包括具有閾值的非線性動力學、互相影響的反饋回路、時滯、恢復力、異質性、意外、遺留效應、協同作用等[18]。反饋過程是社會-生態系統的典型特征之一,通過反饋機制導致的持續的交互作用可能使得復合系統遠離平衡[6,18,19]。社會-生態系統是自組織的,個體與系統之間的反饋有可能成為理解制度變革得以產生以及變革結果得以維系的原因[20,21]。系統中的因果關系常常是復合而非線性的;在聯系鏈條中的各個要素中,因果關系可能是循鏈而動,也可能是跳躍的[17]。
就系統優化的方法而言,Ostrom認為〔22〕:環境社會系統研究中,表現出來的主要問題背后的概念結構是一幅崎嶇不平、有著眾多“山巔”和“山谷”的圖景。如果一旦發現了某些山巔就簡單地把潛在的解決方案急劇地減少到幾個“優化的”策略,往往不足以形成富有成效的解決方案,而且,任何提高某個子系統的適應優化程度的過程很可能對提高整個系統的恢復力是不利的[3,22]。在短期內有利于應對全球性變化的治理策略在長期可能是有害的[23]。
在不同學科中,對系統的范圍的定義和使用存在差異;在環境社會系統的研究中,倚靠關于范圍的某種單一視角是不夠的[4],科學研究應該是和實際應用混合在一起而非分離的[17]。
Edward B Barbier[24]認為,必須發展新的方法以獲得生態系統提供各種生態服務的價格。MA[25]使用權衡分析(tradeoff analysis)確定生態服務的價值。Carpenter等[17]認為,在一個相對同質的、博識的社區中使用權衡分析方法,社區容易做出權衡得當的決定,損失容易被補償。
環境社會系統的復合性特點,決定了其研究必須運用多種方法。就目前的研究狀況看,最重要的應該是運用整體性的方法從宏觀上認識、把握環境社會系統。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系統各元素、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包括研究系統物質流、能量流、意識流的方法。研究過程中,定性方法必不可少,而定量方法仍需要較長時間的發展。
3 多樣性研究
研究認為,基因、物種、多樣性正快速下降,景觀日趨同質[17,25]。此外,文化(制度)多樣性也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多樣性提供了多種知識體系和視角以滿足多種社會目標;但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文化多樣性銳減[26]。雖然文化多樣性在短期也可能降低公眾生活的參與程度(例如投票、志愿行為、鄰里信任)[27];但它為人類社會適應環境變化提供了多種選擇空間。在多樣性基礎上,通過實驗、創新、知識分享等過程的社會學習,是在人的維度上建構適應能力和社會-生態系統恢復力的核心過程[26]。由于各地的自然、社會條件的差異,因此不存在適合任何情況的單一制度安排[22,26]。這暗示著在提供環境資源問題的解決方案時文化多樣性是不可忽視的。社會系統的記憶來自個體和制度的多樣性,這些對形成應對變化的系統、構建恢復力、應對意外都是至關重要的[28,29]。地方性的生態知識和實踐是有益的[30]。
地區的差異性決定了開展環境社會系統研究必須尊重多樣性特點。特別是在開展政策研究、實證研究時,必須充分考慮、利用當地的知識和文化。
4 模型研究
Anderies等[31]設計了一個用于分析社會-生態系統魯棒性(robustness)的框架。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魯棒性高(低)的系統的效率通常低(高);但是當遇到外部變化或內部壓力時,前者效率下降速度會比后者慢。魯棒性和恢復力具有類似之處。區別在于,魯棒性是通過表現來定義的,相對容易量化;而恢復力則是指在多大的變化或破壞性的力量作用下系統能保持不變,因此,難以量化。
Monticino等[32]使用多主體模型分析了人類-環境耦合系統對林地利用變化的影響。模擬結果顯示,土地價格以及土地所有者對土地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是土地利用變化的首要驅動因素。
Grant等[33]把自然-人類耦合系統中的人類系統分為6個子系統,其中的經濟、政治、法律3個子系統又和環境系統相聯系。通過模擬運行認為,在環境系統和法律子系統沒有聯系的情況下會發生公地的悲劇。
IPCC的報告提出,由于評估社會、文化和制度變化在經濟和技術發展的作用是困難的,除了在情景分析中以外,當前的知識不允許人類以剛性的、定量的方式來處理社會、文化和制度因素[12]。與此類似,千禧年生態系統評價主要通過陳述相關的科學共識來評價不確定性;只在少數情況下使用嚴格的定量方法[17,25]。
Carpenter等[17]認為,社會-生態系統中集成的、定量的模型并不和已有的概念和定性模型相稱。已有的生態系統服務的模型都是用來處理特定的部門(如農業)或特定的交叉領域(如土地利用變化),而對社會子系統和社會子系統閾值的交互作用的研究很少。涉及演化的數學模型的局限性較大,從模型中得出的結果往往少于定性分析[5]。
在建構定量模型或運用定量模型計算時,采取近似的方式模擬真實世界是不可或缺的過程。由于環境社會系統的非線性、復雜性特點,近似難免導致失真,引起“蝴蝶效應”。因此,一方面應更好地從整體的、定性的角度把握環境社會系統,審慎看待定量模型研究結果的參考價值。另一方面,為盡量避免遺漏重要的因子,有必要在更寬的范圍內考慮可能存在的影響環境社會系統因素。
5 案例研究
Ostrom[22]建構了一個包括8個(一級)變量和若干二級子變量的體系,并用它定性分析了公地悲劇寓言,比較了“流寇”(Roveing Bandits)和“坐寇”(Harbor Gangs)的區別。“流寇”是“打一槍換個地方”,彼此又獨立決策,其造成的后果類似于公地悲劇。“坐寇”根扎于當地社區,建立了可信的規范,可能有利于資源的持續利用。
Lichtenberg等[13]的調查驗證了具有不好的健康體驗的農民傾向于采取防護措施的假設,并發現這類農民也傾向于更少地使用殺蟲劑。具有不好健康體驗的農民包括三類:自己有過、家人有過、知道其他人有過。
Adger等[28]通過分析應對和適應颶風的案例,發現社會-生態系統的許多元素和行動都與人的主體性相關。具體表現為:受災程度通常和政府干預或非正式制度對海岸生態系統的利用規制有關;提高應對災難恢復力的網絡和制度也可以緩沖未來的災害;有效的、多層次政府治理系統在構建適應能力方面十分重要的;由于人類可能對有益于恢復力的要素認識不足,從而導致這些要素被破壞而未采取保護措施;在社會-生態系統中可能有多種機制來應對變化和危機。例如,生物多樣性、功能冗余、空間模式都可以影響生態系統的恢復力;災難性的變化之后,先前的系統的殘余部分(remnant,又稱memory)成為新的社會-生態系統更新和再組織的基礎。
許多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正在下降。為了維持和提高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需要地方性的生態知識(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和實踐。Stephan等[34]研究了與維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管理實踐相關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并調查了生態實踐、知識、經驗是如何被保留和傳播的。關于瑞典市民園地的研究認為(市民園地的含義可以參看文獻[35]中說明),生態實踐和知識是通過模仿、口口相傳、集體儀式、習慣、人造物(文字等)、隱喻、制度等保留和傳播的。此外,通過媒體、市場、社會網絡、合作組織、法律結構等方式或媒介,社會環境也為生態實踐和知識的保留與傳播提供支持[34]。
Olsson等[36]以瑞典南部的濕地景觀治理為案例,分析了環境社會系統轉型背后的自組織機制。在當地各種管護組織和當地政府察覺到地區性的文化和生態價值受到威脅之后,引發了自組織的適應性共管(comanagement)過程。這個轉變包括三個階段:讓系統為變化做好準備;抓住機會窗口;建立新的期望狀態的社會-生態恢復力。
Rescia等[37]通過分析過去45年Picos de Europa地區的環境管理經驗,認為:在保護景觀和實現其他目標時,經濟激勵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同時,為了使得激勵得以成功,也必須考慮到許多社會因素。此外,在設計、執行保護和發展策略時讓目標人群參與是十分重要的。
Janssen等[38]做了更接近于真實世界的實驗。他們把參試人員分成人數相等的小組,分別采取一階段交流或懲罰而另一階段既不能交流也不能懲罰的方式進行對照實驗。研究表明,除非配合以交流,否則對過度使用公共資源的懲罰則是無益的。
Liu等[18]對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6個案例研究顯示,人與自然耦合系統具有新的、復合的模式與過程,并具有系統學的特征。如果由社會科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分開研究這些系統,是不容易發現這些模式與過程的。人與自然系統耦合的動力學受到許多因素影響,且隨著空間、時間和組織單元而變,包括政府政策和本地情勢。
案例和理論研究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一方面,可以運用現有的環境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案例解釋現實世界;另一方面,不斷發掘整理新的案例可以豐富和發展理論。
(編輯:徐天祥)
References)
[1]Austin A,Brewer J.World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lated Technical Problem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72,3:23-49.
[2]Petak W.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The Need for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80,4(4):287-295.
[3]Rammel C,Stagl S,Wilfing H.Managing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A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3:9 -21.
[4]Manson S.Does Scale Exist?An Epistemological Scale Continuum for Complex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J].Geoforum,2008,39:776-788.
[5]Gual M,Norgaard R.Bridging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Coevolution:A Review and Proposal[J].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707-717.
[6]Odum E,Barrett G.Fundamentals of Ecology(5th edition)[M].London:Thomoson Press,2001.
[7]Lalland K, Odling-Smee J, Feldman M. Niche Constructing,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hange.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00,23:131 -146.
[8]Holling C.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Ecological,and Social SystemsAuthor[J].Ecosystems,2001,4(5):390 -405.
[9]Norgaard R. Co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otential[J]. Land Economics,1985,60(2):160 -173.
[10]Norgaard R. Coevolutionary AgriculturalDevelopment[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4,32(3):525 -546.
[11]Giorgos K,Norgaard R.Coevolutionary Ecological Economic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690 -699.
[12]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http://www.ipcc.ch/ipccreports/sres/emission/.
[13]Lichtenberg E, ZimmermanR. AdverseHealthExperiences,Environmental Attitudes,and Pesticide Usage Behavior of Farm Operators[J].Risk Analysis,1999,19(2):283 - 294.
[14]Feola G, Binder C. Towards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Behaviour:TheIntegrativeAgent-centred (IAC)Framework[J].Ecological Economics,2010,69:2323 - 2333.
[15]Rammel C,McIntosh B S,Jeffrey P.Where to Now?A Critical Synthesis of Contempor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of(co)Evolutionary Theory and Discussion of Research Need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logy,2007,14:109-118.
[16]Bodin ?rjan,Crona B.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What Relational Patterns Make a Difference?[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9,19:366 -374.
[17]Carpenter S,Mooney H,Agard J,et al.Science for Managing Ecosystem Services:Beyond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J].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9,106(5):1305-1312.
[18]Liu Jianguo,Dietz,Carpenter S,et al.Complexity of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J].Science,2007,317:1513 -1516.
[19]Walsh S J,McGinnis D.Biocomplexity in Coupled Human-natural Systems: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Editorial)[J].Geoforum,2008,39(2):773-775.
[20]Mayumi K,et al.The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 of Self-modifying Systems: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Post-normal Science era[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57:382 - 399.
[21]Matthews R,et al.Landscape as a Focus for Integrating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Processes[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57(2):199-212.
[22]Ostrom E,A Diagnostic Approach for Going Beyond Panaceas[J].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7,104(39):15181-15187.
[23]Perry R,Ommer R.Introduction:Coping with Global Change in Marin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Marine Policy,2010,34:739-741.
[24]Barbier E.Valuing Ecosystem Services as Productive Inputs[J].Economic Policy,2007,22:177 -229.
[25]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2003.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 Being: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http://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en/Framework.aspx > .
[26]Chapin F III, CarpenterS, KofinasG, etal. Ecosystem Stewardship:Sustainability Strategies for a Rapidly Changing Planet[J].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2009,25(4):241-249.
[27]Putnam R.Unum E Pluribus: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2006 Johan Skytte Prize Lecture[J].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7,30:137 -174.
[28]Adger W,Hughes T,Folke C,et al.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Coastal Disasters[J].Science,2005,309:1036 -1039.
[29]Folke C,Hahn T,Olsson P,Norberg J.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05,30:441 -473.
[30]Daivi R.Social Innovation and Climate Adaptation:Local Collective Action in diversifying Tanzania[J].Applied Geography,2012,33(1):128-134.
[31]Anderies J,Janssen M,Ostrom E.A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obustnes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rom a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Ecology and Society,9(1):18.
[32]Monticino M,Acevedo M,Callicott B,et al.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A Multi-agent-based Approach[J].Environmental Modelling& Software,2007,22:656-663.
[33]Grant W,Peterson T,Peterson M.Quantitative Modeling of Coupled Natural/human Systems:Simulation of Societal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Action Drawing on Luhmann’s Social Theory[J].Ecolog-ical Modelling,2002,158:143 -165.
[34]Stephan B,Carl F,Johan C.Social-ecological Memory in Urban Gardens—Retaining the Capacity for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0,20:255 -265.
[35]http://en.wikipedia.org/wiki/Allotment_garden
[36]Olsson P,Folke C,Hahn T.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the DevelopmentofAdaptive Comanagement of a Wetland Landscape in Southern Sweden[J].Ecology and Society 2008,9(4):2.
[37]Rescia A.,Pons A,Lomba,et al.Reformulating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 a Cultural Rural Mountain Landscape in the Picos de Europa Region(Northern Spain)[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8,88:23 -33.
[38]Janssen M,Holahan R,Lee A,Ostrom E.Lab Experiment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Science,2010,328:613 -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