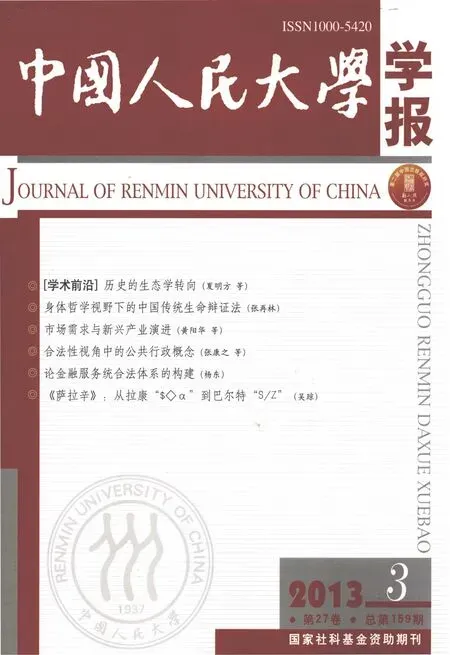馬克思公共性思想初探——基于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比
譚清華
國(guó)內(nèi)哲學(xué)界對(duì)公共性問題的關(guān)注始于20世紀(jì)末,其出發(fā)點(diǎn)與歸宿在于分析和解決政府職能轉(zhuǎn)型、政府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等問題。這是國(guó)內(nèi)學(xué)界一開始就具有的理論自覺。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如何立足于我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在借鑒西方公共性理論的基礎(chǔ)上,提出符合馬克思思想邏輯和立場(chǎng)的公共性理論,一直都是難點(diǎn)。本文試圖對(duì)此做出初步探索。
一、公共性與馬克思思想
雖然馬克思為之奮斗的共產(chǎn)主義本身就包含有 “公共”的意思[1](P293),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對(duì)公共性進(jìn)行明確界定,也沒有像阿倫特那樣試圖基于公共性構(gòu)建一種完整的公共性理論。公共性能夠成為重要的哲學(xué)范疇,要?dú)w功于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正是他們關(guān)于政治公共性、輿論公共性和理性公共性的系統(tǒng)論述,才使得公共性這個(gè)范疇凸顯出來,并為理解和解決當(dāng)代社會(huì)面臨的一些重要問題提供了思路。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duì)公共性的理解是一致的。在阿倫特那里,公共性是一種人與人通過言語和行動(dòng)形成相互聯(lián)系的共存境況,體現(xiàn)了人的存在的世界性、差異性和不朽性。在哈貝馬斯那里,公共性表現(xiàn)為一種意見,這種意見是私人借助于報(bào)紙等媒介形成的,是以批判和監(jiān)督公共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為目的的。而在羅爾斯看來,公共性是指良序憲政民主社會(huì)下公民具備的一種理性推理能力。因此,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對(duì)公共性都有著特定的理解,其提出的公共性理論也是針對(duì)特定問題的。
公共性理論的多樣性,既給我們理解公共性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我們能夠在公共性的差異比較中加深對(duì)問題的理解,又給我們發(fā)展符合馬克思思想邏輯和立場(chǎng)的公共性理論增加了難度。因?yàn)槿魏侮P(guān)于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的論述,其前提都是要回答:馬克思的公共性的內(nèi)涵是什么?它在什么意義上是公共的?沒有這種前提性的回答,或者說,沒有這種與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公共性理論的區(qū)分,所謂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就不是自明的。從理論的具體要求來說,我們首先需要界定公共性這個(gè)概念,而任何對(duì)公共性概念的界定,其實(shí)也意味著對(duì)公共性理論的闡發(fā)。
無論是哈貝馬斯的公共輿論,還是羅爾斯的公共理性,馬克思在早年都曾主張過。在 《摩澤爾記者的辯護(hù)》中,馬克思曾經(jīng)有一個(gè)與哈貝馬斯公共輿論思想一致的主張。這個(gè)主張認(rèn)為,在如何解決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官方利益與社會(huì)整體利益統(tǒng)一的問題上,自由報(bào)刊作為獨(dú)立于私人和官方管理機(jī)構(gòu)的 “第三個(gè)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在報(bào)刊這個(gè)領(lǐng)域內(nèi),管理機(jī)構(gòu)和被管理者同樣可以批評(píng)對(duì)方的原則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從屬關(guān)系的范圍內(nèi),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權(quán)利范圍內(nèi)進(jìn)行這種批評(píng)。 ‘自由報(bào)刊’是社會(huì)輿論的產(chǎn)物,同樣,它也制造社會(huì)輿論,唯有它才能使一種特殊利益成為普遍利 益”。[2](P378)也就是說,馬克思這里也像哈貝馬斯主張的那樣,把自由的報(bào)刊或者說自由輿論視為擺脫利益的特殊性,并使之上升為普遍利益的保障,把報(bào)刊的這種輿論理解為公共性的輿論。可是,當(dāng)馬克思思想逐漸走向成熟,深入到社會(huì)存在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之后,這種求助于輿論公共性的幻想也就被揚(yáng)棄了。因?yàn)轳R克思認(rèn)識(shí)到,這種所謂的公共輿論只不過是構(gòu)成市民社會(huì)基礎(chǔ)的資產(chǎn)階級(jí)利益的訴求,本身就具有階級(jí)性和共同利益的虛幻性。 “馬克思揭發(fā)公眾輿論是錯(cuò)誤意識(shí):它在自己面前掩蓋了作為資產(chǎn)階級(jí)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質(zhì)。”[3](P141)因此,哈貝馬斯的公共輿論思想,僅僅是馬克思曾經(jīng)主張過而后又被揚(yáng)棄的一種思想。這也意味著,馬克思不可能接受哈貝馬斯語境中的公共性內(nèi)涵和理論。
而對(duì)于公共理性的主張,由于馬克思受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理性傳統(tǒng)的影響,曾把國(guó)家和法律視為絕對(duì)理性的實(shí)現(xiàn)和人民自由的保障,從而肯定了理性的公共性。馬克思曾集中闡述了這樣的理性觀:國(guó)家和法都是理性的表現(xiàn),國(guó)家應(yīng)該是 “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實(shí)現(xiàn)”,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而應(yīng)該是普遍的規(guī)范,在這些規(guī)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不取決于個(gè)別人的任性的性質(zhì)。[4](P118)這種對(duì)理性的肯定要求馬克思對(duì)康德的理性學(xué)說進(jìn)行辯護(hù),因?yàn)榭档率堑聡?guó)古典哲學(xué)理性傳統(tǒng)的奠基人。所以,當(dāng)歷史法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胡果自稱是康德的學(xué)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稱作康德哲學(xué)的支脈時(shí),馬克思進(jìn)行了激烈的批判,認(rèn)為 “胡果曲解了自己的老師康德”。[5](P230)可以說,早期馬克思就像羅爾斯一樣,也曾相信理性的公共性,相信國(guó)家和法律就是理性的體現(xiàn)、自由的保障,可是,這種對(duì)理性的信仰隨著馬克思逐漸轉(zhuǎn)變?yōu)楣伯a(chǎn)主義者而受到了批判。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馬克思、恩格斯對(duì)德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的軟弱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反映進(jìn)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其矛頭直指他曾經(jīng)為之辯護(hù)的康德。作為對(duì)康德實(shí)踐理性思想發(fā)展的公共理性主張,馬克思仍會(huì)批判其形式普遍性。
因此,從理論的內(nèi)在邏輯來說,哈貝馬斯、羅爾斯與馬克思的思想秉持的是完全不同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馬克思對(d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是持批判立場(chǎng)的,他正是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huì)內(nèi)在矛盾的基礎(chǔ)上闡明了無產(chǎn)階級(jí)解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這與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是完全相反的。因?yàn)楹笳唠m然不否定資本主義社會(huì)存在各種矛盾,并試圖從自由主義政治傳統(tǒng)出發(fā)就如何在多元化的社會(huì)中達(dá)成共識(shí)進(jìn)行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說明,但是,他們本質(zhì)上都是試圖通過構(gòu)建一個(gè)具有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的憲政體制來化解包括階級(jí)矛盾在內(nèi)的各種沖突,以實(shí)現(xiàn)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長(zhǎng)治久安。正是在這點(diǎn)上,哈貝馬斯和羅爾斯所理解的公共性其實(shí)也僅僅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而已,是與馬克思的主張和立場(chǎng)相沖突的。也是在這點(diǎn)上,阿倫特的公共性主張與馬克思的思想具有更多的 “親近性”,即都對(d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持批判立場(chǎng)。
當(dāng)然,阿倫特與馬克思對(d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批判具有根本的區(qū)別。阿倫特面對(duì)當(dāng)代社會(huì)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不是 “向前看”,而是將視角投向了古代,試圖從古代社會(huì)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差異中找尋現(xiàn)代政治弊病的根源。阿倫特將現(xiàn)代政治的弊病歸結(jié)到勞動(dòng)和勞動(dòng)社會(huì)的興起。因?yàn)樵谒磥恚莿趧?dòng)地位的上升和勞動(dòng)社會(huì)的興起,導(dǎo)致了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繁榮和公共領(lǐng)域的衰落。這樣,阿倫特就錯(cuò)誤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勞動(dòng)和勞動(dòng)社會(huì),而忽視了正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導(dǎo)致了勞動(dòng)的異化,并因此而對(duì)高度肯定勞動(dòng)作用的馬克思展開了批判。她說: “馬克思在把勞動(dòng)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dòng)的時(shí)候,從傳統(tǒng)來看,他并不是把自由的人,卻是把強(qiáng)制的人作為人類來論說的。”[6](P14)因此,阿倫特認(rèn)為主張勞動(dòng)解放本身就是語義矛盾,而勞動(dòng)解放也意味著其失去了政治上的意義。
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阿倫特的公共性思想與馬克思思想在內(nèi)在邏輯上存在的矛盾和對(duì)立,不難理解阿倫特對(duì)馬克思的各種指責(zé)和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誤解基礎(chǔ)之上的批判。在論述公共性思想的三位學(xué)者中,阿倫特是對(duì)馬克思批判最嚴(yán)厲的一位,但她的主張又與馬克思思想最具有 “親近性”,這是矛盾又是事實(shí)。其原因不僅僅在于他們都對(duì)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導(dǎo)致的社會(huì)危機(jī)和弊端進(jìn)行了揭示和批判,而且還在于他們都深入到人的生存危機(jī)這個(gè)當(dāng)代社會(huì)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因而都是立足于人的生存危機(jī)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馬克思揭示了無產(chǎn)階級(jí)這個(gè)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群體的非人的生存危機(jī),并把這種危機(jī)的解決歸結(jié)到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huì)化大生產(chǎn)這一矛盾的克服上,從而提出了一個(gè)沒有私有制、沒有壓迫、每個(gè)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藍(lán)圖。而阿倫特則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huì)里普遍的勞動(dòng)奴役造成的個(gè)體孤寂這種生存危機(jī),以及由此帶來的民主政治的不穩(wěn)定,從而主張恢復(fù)類似古希臘城邦公民政治那樣的公共領(lǐng)域。這種公共領(lǐng)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參與的,而僅僅局限于那些擺脫了勞動(dòng)必然性制約的少數(shù)人。因此,阿倫特的公共性主張從某種程度上說,又是精英主義的,但是她對(duì)公共性的揭示由于是對(duì)包括無產(chǎn)階級(jí)在內(nèi)的現(xiàn)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回應(yīng),因而與馬克思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思想具有 “親近性”。
總之,通過比較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公共性主張與馬克思思想,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的公共性主張與馬克思的思想在價(jià)值立場(chǎng)等問題上存在根本的區(qū)別,很難將他們關(guān)于公共性的界定和主張直接運(yùn)用到馬克思思想中來,雙方屬于不同的理論譜系。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在馬克思的理論主張中就沒有公共性思想呢?筆者認(rèn)為,這需要對(duì)馬克思的思想邏輯和理論主張進(jìn)行分析,只有在全面分析他的思想邏輯和主張之后才能得出可靠的結(jié)論。
二、政治解放與社會(huì)解放
政治解放是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展的結(jié)果,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一大特點(diǎn),也是資產(chǎn)階級(jí)歷史進(jìn)步性的體現(xiàn)。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之前的傳統(tǒng)社會(huì)里,政治領(lǐng)域是受宗教、社會(huì)等級(jí)等非政治因素制約的,甚至在中世紀(jì),財(cái)產(chǎn)、商業(yè)、社會(huì)團(tuán)體和人都是政治的。政治領(lǐng)域與社會(huì)領(lǐng)域具有高度的統(tǒng)合性。政治解放就是要把政治領(lǐng)域從這些社會(huì)因素、身份等級(jí)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完成從政治等級(jí)到社會(huì)等級(jí)的轉(zhuǎn)變,使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等級(jí)差別變成與政治生活完全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私人生活的差別,即形成政治生活同市民社會(huì)的徹底分離。這樣,國(guó)家就宣布了出身、等級(jí)、文化程度、職業(yè)為非政治的差別,宣告了人民的每一成員都是人民主權(quán)的平等享有者。可是,當(dāng)國(guó)家這樣做時(shí),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jí)、文化程度、職業(yè)的差別,而這些差別卻以它們固有的方式,即作為私有財(cái)產(chǎn)、作為文化程度、作為職業(yè)仍然發(fā)揮著作用并表現(xiàn)為國(guó)家的本質(zhì)。國(guó)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shí)際差別,相反,只是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所以,政治解放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分裂,即利己的市民社會(huì)與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國(guó)家政治生活之間的分裂。
這種分裂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局限于政治解放所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因此也構(gòu)成了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的公共性理論的現(xiàn)實(shí)背景。在他們的公共性理論中,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duì)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了回應(yīng)。就阿倫特來說,市民社會(huì)僅僅是為生存的目的而建立起來的相互關(guān)系,是一元的,而政治領(lǐng)域作為人們自由活動(dòng)、展現(xiàn)個(gè)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領(lǐng)域則是多元的。市民社會(huì)的興起是導(dǎo)致政治公共領(lǐng)域衰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她主張將政治領(lǐng)域局限于那些擺脫了生存需要制約的平等的自由人中間。這樣,阿倫特就將政治社會(huì)與市民社會(huì)完全對(duì)立起來,并企圖在政治社會(huì)與市民社會(huì)之間筑起一堵高墻,通過將市民社會(huì)擋在政治領(lǐng)域之外來維護(hù)政治的公共性。與阿倫特這種違背現(xiàn)代自由民主精神的古典政治傳統(tǒng)主張不同,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則從洛克的自由政治傳統(tǒng)出發(fā),首先肯定了市民社會(huì)的自主性和多元性,其次肯定了多元化的市民社會(huì)有權(quán)平等地參與政治公共生活。因此,對(duì)于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而言,問題就在于如何解決市民社會(huì)多元化與政治領(lǐng)域公共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他們都試圖從公共性出發(fā)構(gòu)建一套具有合法性的憲政體制來化解這一矛盾和沖突。這樣,無論是阿倫特,還是哈貝馬斯和羅爾斯,對(duì)于資本主義社會(huì)內(nèi)部的這種分裂,他們的出發(fā)點(diǎn)在本質(zhì)上都是政治的,始終是在維持市民社會(huì)私人自主性的基礎(chǔ)上,主張運(yùn)用政治的公共性來化解市民社會(huì)與政治社會(huì)的分裂。
這一點(diǎn)與馬克思的主張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這種分裂不但造成人自身的分裂,人被分為私人和 “公人”,即一方面?zhèn)€人生活在市民社會(huì)中,作為一個(gè)有著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而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解放使得公共事務(wù)成為每個(gè)個(gè)體的普遍事務(wù),政治職能成為個(gè)人的普遍職能,因此個(gè)人又是一個(gè)公共存在,是一個(gè) “公人”;而且這種分裂還造成公共生活的抽象性,個(gè)體與類的分裂,因?yàn)檎谓夥挪⒉灰允忻裆鐣?huì)的統(tǒng)一為基礎(chǔ),反而是建立在市民社會(huì)利己的私人利益基礎(chǔ)之上。這樣,一方面政治共同體要求人們統(tǒng)一起來,體現(xiàn)了人們生活的普遍性、人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為這個(gè)政治共同體基礎(chǔ)的市民社會(huì)又是一個(gè)利己的領(lǐng)域。在這個(gè)領(lǐng)域里,每個(gè)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實(shí)現(xiàn),而是看做對(duì)自己自由的限制。因此,這種建立在社會(huì)對(duì)立基礎(chǔ)之上的政治公共性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共性,而只能是 “形式的普遍性”。所以,馬克思認(rèn)為,不是政治社會(huì)決定市民社會(huì),而是市民社會(huì)決定政治社會(huì),只有消除市民社會(huì)的分裂才能化解市民社會(huì)與政治社會(huì)的對(duì)立。那種企圖一方面維持市民社會(huì)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政治權(quán)利的公共性來化解市民社會(huì)與政治社會(huì)的分裂的主張,其實(shí)質(zhì)就是以無產(chǎn)階級(jí)的形式上的政治解放來換取其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統(tǒng)治秩序的合法性承認(rèn),從而促使無產(chǎn)階級(jí)放棄解放自身的要求,使得資本主義社會(huì)和資產(chǎn)階級(jí)統(tǒng)治永恒化。
與資本主義社會(huì)之前的統(tǒng)治階級(jí)不同,資產(chǎn)階級(jí)對(duì)無產(chǎn)階級(jí)的壓迫和統(tǒng)治主要不是基于政治的不解放,而是基于市民社會(huì)的內(nèi)部分裂,即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生產(chǎn)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無產(chǎn)階級(jí)的一無所有這一 “純粹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現(xiàn)在的統(tǒng)治不是以 ‘既得權(quán)利’為依據(jù),而是以實(shí)際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為依據(jù),雇傭勞動(dòng)制度不是一個(gè)權(quán)利關(guān)系,而是一個(gè)純粹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7](P131)因此,資產(chǎn)階級(jí)能夠在無產(chǎn)階級(jí)的長(zhǎng)期斗爭(zhēng)中進(jìn)行政治上的讓步,給予廣大無產(chǎn)者所謂 “自由價(jià)值”不等的政治權(quán)利,而對(duì)超出政治解放的進(jìn)一步要求即社會(huì)解放卻以自由優(yōu)先、權(quán)利至上等資產(chǎn)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進(jìn)行反對(duì)。這就說明了,政治解放與資本主義社會(huì)秩序不是相悖的,而是高度統(tǒng)一的;僅僅從一些包括正義在內(nèi)的政治理念出發(fā)去提出相關(guān)措施,無損于資產(chǎn)階級(jí)統(tǒng)治和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那種只是要求政治公共化而忽視通過社會(huì)變革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統(tǒng)一的主張,最終都會(huì)陷入對(duì)資本主義現(xiàn)存秩序的維護(hù)中去,有意或無意地成為資產(chǎn)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俘虜。
這樣,馬克思與阿倫特、哈貝馬斯和羅爾斯之間就形成了立場(chǎng)上的根本區(qū)別。馬克思并不滿足于政治解放形成的抽象普遍性和公共性,他要尋求的是人的解放以及由此所需要的社會(huì)解放。社會(huì)解放的本質(zhì)就是把社會(huì)從資本的支配下解放出來,使社會(huì)成為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里,“每個(gè)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8](P294),“各個(gè)人在自己的聯(lián)合中并通過這種聯(lián)合獲得自己的自由”[9](P119)。也就是說,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并不是個(gè)人之間相互排斥、個(gè)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相互沖突的社會(huì),而是個(gè)人與個(gè)人之間、個(gè)人與聯(lián)合體之間因?yàn)樘幱谝环N自由發(fā)展的相互促進(jìn)中,因而是共享自由發(fā)展的社會(huì)。這種主體間的相互共享性即是公共性。因此,馬克思所主張的公共性,從根本上說,指的就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中普遍存在的相互自由和共享發(fā)展的公共的社會(huì)關(guān)系。
但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實(shí)現(xiàn)并不是自發(fā)的,它一方面依賴于社會(huì)的發(fā)展進(jìn)程,另一方面也依賴于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的歷史主體即無產(chǎn)階級(jí)。就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而言,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并不是應(yīng)當(dāng)確立的狀況,不是現(xiàn)實(shí)與之相適應(yīng)的理想,而是 “那種消滅現(xiàn)存狀況的現(xiàn)實(shí)的運(yùn)動(dòng)。這個(gè)運(yùn)動(dòng)的條件是由現(xiàn) 有的前提產(chǎn)生的”[10](P87)。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基礎(chǔ)存在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發(fā)展中,它通過揚(yáng)棄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而建立。具體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在克服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其他社會(huì)矛盾基礎(chǔ)上不得不進(jìn)行生產(chǎn)社會(huì)化。這種社會(huì)化過程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范圍內(nèi)對(duì)資本主義生產(chǎn)資料私人占有的否定,是向生產(chǎn)資料公共所有發(fā)展的一種過渡形式。就歷史主體而言,無產(chǎn)階級(jí)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的地位決定了無產(chǎn)階級(jí)要解放自身就必須首先消滅資本主義社會(huì),消滅階級(jí)本身。只要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存在,無產(chǎn)階級(jí)作為資本主義社會(huì)存在的前提和結(jié)果也就存在著,并隨著資本主義社會(huì)內(nèi)部矛盾的激化呈現(xiàn)出反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意識(shí)和行動(dòng)。
這樣,社會(huì)化大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無產(chǎn)階級(jí)為了解放自身而推動(dòng)著社會(huì)向消滅資本主義、消滅階級(jí)的運(yùn)動(dòng)方向前進(jìn)就實(shí)現(xiàn)了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意味著,實(shí)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既是一場(chǎng)對(duì)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進(jìn)行改造的現(xiàn)實(shí)運(yùn)動(dòng),又是無產(chǎn)階級(jí)形成階級(jí)意識(shí)和采取行動(dòng),從而推動(dòng)資本主義社會(huì)走向滅亡的過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滅亡和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形成是歷史主客體統(tǒng)一發(fā)展的結(jié)果。無產(chǎn)階級(jí)的意識(shí)和行動(dòng)本身就是推動(dòng)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形成的不可缺少的歷史因素。自從馬克思提出歷史 “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dòng)而已”的命題之后,馬克思就不可能接受一個(gè)沒有無產(chǎn)階級(jí)存在的唯物史觀,更不會(huì)幻想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能夠脫離于無產(chǎn)階級(jí)的意識(shí)和行動(dòng)而以鐵的規(guī)律性自行呈現(xiàn)。這樣,我們就涉及馬克思關(guān)于公共性思想的另一主張,即無產(chǎn)階級(jí)的公共的階級(jí)意識(shí)問題。
三、無產(chǎn)階級(jí)的階級(jí)意識(shí)與政治生活
在現(xiàn)實(shí)中,無產(chǎn)階級(jí)能且只能通過具體的無產(chǎn)者來意識(shí)和行動(dòng)。無產(chǎn)者是一個(gè)個(gè)有著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他的解放只是意味著擺脫無產(chǎn)者的地位,成為其對(duì)立面即有產(chǎn)者。①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關(guān)于無產(chǎn)者 “在本階級(jí)的范圍內(nèi)沒有機(jī)會(huì)獲得使他轉(zhuǎn)為另一個(gè)階級(jí)的各種條件”的論斷,雖然就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條件以及大多數(shù)無產(chǎn)者而言是真實(shí)的,但隨著資本主義國(guó)家普遍實(shí)行社會(huì)福利政策,以及民主政治的發(fā)展和資本形態(tài)的變化,少數(shù)無產(chǎn)者上升為有產(chǎn)者的幾率大大增加了,這對(duì)于無產(chǎn)階級(jí)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就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來說,一些人由于掌握著大量的社會(huì)資源,他們依靠這些資源成為新的有產(chǎn)者,獲得了個(gè)人的相對(duì)解放。而無產(chǎn)階級(jí)則是無產(chǎn)者基于共同的利益和地位組織起來的共同體,它的解放只能通過消滅階級(jí)本身才能實(shí)現(xiàn)。這也是無產(chǎn)階級(jí)與歷史上其他被統(tǒng)治、被壓迫階級(jí)相區(qū)別的地方,是無產(chǎn)階級(jí)與社會(huì)化大生產(chǎn)發(fā)展趨勢(shì)相一致,從而體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jí)歷史優(yōu)越性的地方。無產(chǎn)階級(jí)是由無產(chǎn)者組織起來的,這種組織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yàn)橘Y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造成了無產(chǎn)者在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處于共同的地位和形成共同的客觀利益。其次,就是在與資產(chǎn)階級(jí)合作一起反抗封建勢(shì)力以及接下來反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統(tǒng)治和剝削的斗爭(zhēng)中,無產(chǎn)者對(duì)于自己的社會(huì)地位、共同利益等形成越來越明確的意識(shí)。這種意識(shí),馬克思曾明確稱之為“階級(jí)意識(shí)”[11](P18),后來的盧卡奇在 《歷史與階級(jí)意識(shí)》中對(duì)其進(jìn)行了集中的論述。
所以,無產(chǎn)者與無產(chǎn)階級(jí)之間有聯(lián)系,但也存在重要的區(qū)別,這是客觀事實(shí)。任何忘記這種區(qū)別的做法在理論上和在實(shí)踐中對(duì)于社會(huì)主義發(fā)展來說都是有害的,也容易導(dǎo)致布朗基主義意義上的專政。“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shù)革命家所進(jìn)行的突襲,自然也就產(chǎn)生了起義成功以后實(shí)行專政的必要性,當(dāng)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gè)革命階級(jí)即無產(chǎn)階級(jí)的專政,而是那些進(jìn)行突襲的少數(shù)人的專政,而這些人事先又被組織在一個(gè)人或某幾個(gè)人的專政之下。”[12](P244)因此,布朗基主義意義上的專政絕不等于無產(chǎn)階級(jí)專政。前者是個(gè)人或者少數(shù)人凌駕于整個(gè)階級(jí)之上,是個(gè)人或者少數(shù)人的專制;后者本質(zhì)上是整個(gè)階級(jí)的專政,雖然這種專政需要通過個(gè)人,即通過本階級(jí)內(nèi)部?jī)?yōu)秀成員來實(shí)行,但這些人是服從于整個(gè)階級(jí)的。
無產(chǎn)階級(jí)的階級(jí)意識(shí)對(duì)于形成無產(chǎn)階級(jí),特別是形成 “自為的”無產(chǎn)階級(jí)是必不可少的,是把無產(chǎn)者組織成為階級(jí)的靈魂。在馬克思那里,階級(jí)并不僅僅是一種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人格化,它也是階級(jí)意識(shí)的集中體現(xiàn)。馬克思曾對(duì)法國(guó)的小農(nóng)進(jìn)行過分析。他說,這些小農(nóng)就其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jí)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duì)而言,他們是一個(gè)階級(jí)。但是就他們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lián)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guān)系、形成全國(guó)性的聯(lián)系、形成政治組織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gè)階級(jí)。[13](P677)馬克思強(qiáng)調(diào),階級(jí)不僅是社會(huì)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共同利益的體現(xiàn),也是對(duì)這種關(guān)系和利益的揭示和認(rèn)識(shí)即階級(jí)意識(shí)的體現(xiàn)。就像社會(huì)存在決定社會(huì)意識(shí)一樣,沒有共同的階級(jí)關(guān)系和利益的存在,階級(jí)意識(shí)是無法形成的。反之,只有客觀的階級(jí)關(guān)系和階級(jí)利益,而沒有關(guān)于這種關(guān)系和利益的認(rèn)識(shí),階級(jí)也僅僅是 “自在的”。一個(gè)自在的階級(jí)對(duì)于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分析而言也許是必要的,但是,對(duì)于賦有解放自身使命、從而需要積極參與社會(huì)歷史活動(dòng)創(chuàng)造的無產(chǎn)階級(jí)來說,卻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它還必須上升為 “自為的”階級(jí)。從自在的階級(jí)上升為自為的階級(jí),與把無產(chǎn)者組織成為無產(chǎn)階級(jí)實(shí)質(zhì)上是一致的,其關(guān)鍵都在于無產(chǎn)者形成和發(fā)展階級(jí)意識(shí)。
無產(chǎn)者的階級(jí)意識(shí)并不等同于無產(chǎn)者的個(gè)體意識(shí),二者之間既具有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從二者的區(qū)別來說,無產(chǎn)者的個(gè)體意識(shí)是對(duì)無產(chǎn)者局部性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反映和體現(xiàn),因此具有個(gè)體性。這種個(gè)體性在私有制社會(huì)和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初期都具有利己性特點(diǎn)。而階級(jí)意識(shí)卻不是個(gè)體的意識(shí),而是一種公共的意識(shí)。它之所以是公共的,就是因?yàn)檫@種意識(shí)是對(duì)無產(chǎn)者之間共同社會(huì)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利益的認(rèn)識(shí),是個(gè)體之間相互共享的意識(shí)。從二者的聯(lián)系來說,雖然階級(jí)意識(shí)是公共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脫離無產(chǎn)者個(gè)體意識(shí)的外在的存在。“工人階級(jí)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從它所處的現(xiàn)實(shí)條件中產(chǎn)生的。正因?yàn)槿绱耍@種愿望和意向?yàn)檎麄€(gè)階級(jí)所共有,盡管在工人的意識(shí)中運(yùn)動(dòng)以極其多樣的形式反映出來,有的幻想性較多,有的幻想性較少,有的較多符合于這些現(xiàn)實(shí)條件,有的較少符合于這些現(xiàn)實(shí)條件。”[14](P658)他們每天都生活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每天都會(huì)對(duì)實(shí)踐中的問題和挫折有著或多或少的認(rèn)識(shí)。這些認(rèn)識(shí)就是形成公共的階級(jí)意識(shí)的基礎(chǔ)和條件。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個(gè)體意識(shí)自發(fā)地就能上升為階級(jí)意識(shí),無產(chǎn)者不參與政治就能形成無產(chǎn)階級(jí)。
無產(chǎn)者作為一個(gè)私人,總是生活在具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既受著局部性社會(huì)關(guān)系形成的狹隘利益和直接利益的影響,也受著各種與無產(chǎn)階級(jí)階級(jí)意識(shí)相矛盾、相沖突的落后觀念以及資產(chǎn)階級(jí)意識(shí)形態(tài)的制約。這些影響和制約往往作為重要的因素被包含在無產(chǎn)者不得不生存其間的社會(huì)存在中。這種社會(huì)存在相對(duì)于無產(chǎn)者而言是狹隘的和局部的,是對(duì)無產(chǎn)者意識(shí)形成最直接影響和制約的根源。在它的基礎(chǔ)上自發(fā)地形成的個(gè)體意識(shí)與公共的階級(jí)意識(shí)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幻想和扭曲。因此,無產(chǎn)者要擺脫這種幻想和扭曲不僅需要無產(chǎn)者具有一定的理論批判能力,能夠揭示和認(rèn)識(shí)各種幻想,更需要無產(chǎn)者超越自身的直接的社會(huì)存在,與其他的無產(chǎn)者組織起來形成階級(jí)存在,即形成公共的政治存在。無產(chǎn)者只有通過與其他無產(chǎn)者的交往并且通過其他的無產(chǎn)者才能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自己與其他無產(chǎn)者處于共同的階級(jí)關(guān)系中,自己的命運(yùn)與其他無產(chǎn)者的命運(yùn)是同一的。
所以,階級(jí)意識(shí)作為一種公共意識(shí),是與無產(chǎn)者的政治存在緊密相關(guān)的。馬克思曾經(jīng)指出,雖然經(jīng)濟(jì)條件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勞動(dòng)者,而資本的統(tǒng)治又為這批人創(chuàng)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guān)系,從而使得這批人對(duì)資本說來已經(jīng)形成一個(gè)自在的階級(jí)。但要由這種自在性上升為自為性,即要使無產(chǎn)者克服個(gè)體意識(shí)的種種幻想而發(fā)展出階級(jí)意識(shí),則只有當(dāng)無產(chǎn)者處于政治活動(dòng)中才能實(shí)現(xiàn)。“在斗爭(zhēng) (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聯(lián)合起來,形成一個(gè)自為的階級(jí)。他們所維護(hù)的利益變成階級(jí)的利益。而階級(jí)同階級(jí)的斗爭(zhēng)就是政治斗爭(zhēng)。”[15](P193)很顯然,這里的 “斗爭(zhēng)”不是指單獨(dú)某個(gè)無產(chǎn)者而是指無產(chǎn)者組織起來后針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或者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反抗活動(dòng),它是一種公共的政治活動(dòng)。馬克思這里強(qiáng)調(diào)了,政治的無產(chǎn)階級(jí)與無產(chǎn)階級(jí)的政治,二者是相互促進(jìn)和高度統(tǒng)一的。無產(chǎn)者在階級(jí)行動(dòng)即政治活動(dòng)中形成階級(jí)意識(shí),而這反過來又推動(dòng)著階級(jí)行動(dòng)即政治活動(dòng)和無產(chǎn)階級(jí)的發(fā)展。無產(chǎn)階級(jí)不能離開政治活動(dòng)而抽象存在,無產(chǎn)階級(jí)本身就是政治的存在,任何要無產(chǎn)階級(jí)放棄政治的人都終究會(huì)被他們所唾棄。
[1] 《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哈貝馬斯:《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99。
[6] 阿倫特:《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tǒng)》,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7] 《盧森堡文選》(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9][10][13][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