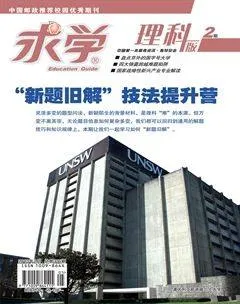拒絕娛樂至死,拒絕娛樂“切碎”
當我要尋找一個動詞,使它足以描述我們所處的娛樂時代對學習造成的劇烈沖擊時,我想到了“切碎”。這是最好的時代,爆炸般洶涌而來的信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豐富體驗;可是,當潮水過境,留下的只是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短暫愉悅的體驗。因此,這也是“最壞”的時代。
你是否早已習慣在自習中將自己的耳朵交付給流行音樂呢?那些讓你深有體會、爛熟于心的歌詞,喚醒著你細碎的、或悲或喜的回憶,于是你的心思飄忽而去,甚至跟著輕聲哼起,卻也早已忘記練習做到哪題。
你是否也會在那些惹人生倦的課上不時掏出手機,打開微博,感受整個紛繁熱鬧的世界撲面而來?你埋下頭,看到某個偶像轉發了一個冷笑話,于是急忙轉發想向整個世界宣告你的興奮和歡樂,至于老師,早已被你遺忘在講臺后。
有時一天喧鬧過后,或許在某個宿舍熄了燈的夜晚,你會埋進被窩在QQ空間里寫上一篇抒懷之作。或極盡搞笑之能事,或彰顯思想之深刻,或盡表詞采之至美,你又讀一遍,然后放下手機微笑著睡去。第二天,從早自習開始,你就不停地刷新著空間,即時與讀者們進行著互動,時間也在這一來一往中悄然流逝。
在如此的生活中,我們如同小水獸攀上了浮萍,開始隨意漂泊,抵達某個娛樂信息的片斷,悲喜不過三秒,又來到下一處……娛樂時代生活紛亂疾捷,甚至來不及對經過的時日匆匆感嘆。
我開始羨慕錢鐘書先生的年代。錢先生是“學術帝”,然而他并非天才。1937年錢先生攜妻女由牛津大學轉到巴黎大學求學,在《我們仨》中,楊絳女士曾如此回憶這一年錢先生的讀書情況:
鍾書在巴黎的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實實地讀書。法文自十五世紀的詩人維容(Villon)讀起,到十八、十九世紀,一家家讀將來。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讀中文、英文,隔日讀法文、德文,后來又讀意大利文。這是愛書如命的鍾書恣意讀書的一年。我們初到法國,兩人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之后,他的法文水平遠遠超過了我,我恰如他《圍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兒都忘了”。
是否因為我們身處信息時代,才使這種切碎感無人能夠幸免?我卻想起了例外,樸樹。九年前他全面告別歌壇,九年的歲月帶走了許多,卻留下了他對音樂的執著。樸樹的音樂有一種內在的超脫之感,它們都關乎夢、關乎愛情、關乎疼痛,卻具有緩慢、沉靜的性質。他用音樂感嘆著“這世界太快了”,從而以他的“慢”去對這世界反戈一擊。在近日樸樹的復出采訪中,有記者發現他保守得令人震驚——“除了拿手機記了個電話號碼外,整個采訪和拍攝期間,他從沒拿出過它,而且它竟然還只是一臺非智能手機。”我看過“樹與花”系列音樂會上海站的視頻,不禁感嘆九年來世界越變越快,而樸樹卻愈發從容、沉靜,以專注拒絕著娛樂時代的切碎。
娛樂至死的時代,我們缺乏的正是沉靜和專注,以及與快餐娛樂相抗衡的慢下來學習的恒心;娛樂至死的時代,誰能逃離,誰就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