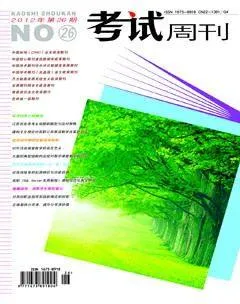送別詩中柳的意象成因簡析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離別,是中國文學中經久不衰的創作母題。送別詩借助于意象的高度情思化,使得其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藝術感染力明顯增強,具有超時空的審美價值。在古代送別詩中,常見的意象有長亭、短亭、陽關、古道、北梁、南浦、芳草、楊柳、夕陽、青燈、美酒等。其中柳意象尤其受到詩人的青睞。
一
柳是送別詩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古代,人們的送別意識極強,無論是科舉送別,還是官場餞別,抑或邊塞贈別,親朋分手,必有隆重熱鬧的餞別場面,而且是有送別必有詩,從帝王將相到白衣士子幾乎都寫過送別詩,據《全唐詩》載,海南一個七歲女孩也能“應聲而就《送兄》一首”。而凡送別詩多與柳有關,古人有折柳言別的習慣。柳意象就成為送別詩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楊柳”一詞早在成書于先秦時期的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已出現了,《小雅·采薇》篇中更有這樣的名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那隨風飄舞的絲絲柳條,就這樣開始牽絆千古留愁別緒。此外,南朝人費昶也有這樣的描寫:“水逐桃花去,春隨楊柳歸。楊柳何時歸,裊裊復依依。”(《和蕭記室春旦有所思》)歷代詩人鐘情楊柳,寄情楊柳,“楊柳”積淀為送別詩中傳達離愁別緒的主要意象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柳”、“留”二字諧音,中國人善于使用諧音表達情感,柳及其相關物的這種諧音便易成為表達情感的媒介,這是古人借諧音“留”住離人之意。由柳而“留”,由“留”而引發人們留別、留思、留存、留戀、留情、挽留等意念。正如劉禹錫所言:“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柳管別離。”于是,柳成了與送行人有關的特殊事物,人們以柳送別、話別,以柳寓離別之苦,經常暗喻離別。“垂絲被柳陌”(盧思道,《贈劉儀同西聘詩》)、“懸絲拂城轉”(岑之敬,《折楊柳》)、“柳絮時依酒,梅花乍入衣”(梁元帝蕭繹,《和劉上黃春日詩》)等都有諧音雙關之意。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在曉風殘月的吹拂映照之下,河邊的楊柳婆娑舞動,一個孤獨的身影在徘徊,別時的傷痛凄苦,別后的長久寂寞,離別之恨和羈旅之愁往復交織,演繹出一幕凄苦的人生悲劇。異地漂泊的游子、天涯獨處的倦客的內心悲愁自然而然地和柳產生共鳴,進而融為一體了。
此外,“柳”還有聚之意。(《周禮天宮》)“柳轂”注疏:“柳者諸色所聚。”(《釋名·釋喪制》)“柳車”注疏:“柳,聚也,眾飾所聚,亦其形僂也。”“聚”也就是留聚的意思。柳還有“團聚”、“聚集”之意,那千絲飛舞的柳枝不都聚集在柳根之下嗎?“傷心路邊楊柳春,一重折盡一重新。”(施肩吾,《折柳枝》)既然留不住親人、情人、友人,那就期待著下次團聚吧。
“柳”多種于檐前屋后,常作故鄉的象征。“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抒發了李白對故鄉的無限牽掛。柳生命力強,隨處可插。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不管是屋前“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陶淵明,《擬古詩》),還是園邊“折柳攀場圃,負綆汲潭壑”(鮑煦,《秋夜詩》);不管是路邊“桃林方灼灼,柳路日瞳瞳”(梁簡文帝蕭綱,《樂府上之回》),還是水邊“柳條恒拂岸,花氣盡薰舟”(梁元帝蕭繹,《赴荊州泊三江口詩》)、“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隋煬帝楊廣,《昔昔監》)都有柳樹垂拂。
柳自春至冬,婆娑起舞,任人攀折,于路邊河畔,房前屋后,目睹了無數世人的悲歡離合,柳枯柳榮之間,送別了無數斷腸之人。“渡頭楊柳青青,枝枝葉葉離情”(晏幾道,《青平樂》)、“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惠洪,《青玉案》),與友人分別于為柳煙所籠罩的長亭路上,豈能不倍感離恨悠悠、離情依依?
二
柳枝又稱長條、柔條、柳絲等,柔軟可挽,與人們殷切期待的情誼久長、永久平安相呼應。詩人寄希望于柳,希望柔弱的柳絲能系住行人,系住親情,系住春色,系住時光,系住青春年華,系住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然而更多的時候,柳枝系不住別離的腳步,“垂楊只解惹東風,何曾系得行人住。”(晏殊,《踏莎行》)“弱柳系船都不住,為君愁絕聽鳴櫓。”(楊炎正,《蝶戀花》)“西域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秦觀,《江城子》)那“弄春柔”、“系歸舟”的絲絲楊柳,牽引出作者剪不斷、理還亂的一腔愁緒,使他終因“不見去年人”而“淚濕春衫袖”。更有“垂柳不縈裙帶住,漫長是,系行舟。”(吳文英,《唐多令》)系得行舟,卻又系不得離人,情景固有不同,詩人的嘆惋卻是同樣的。
三
折柳相贈有“挽留”之意。李賀《致酒行》中就有借“主父西游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表達自己久羈異鄉之苦的詩句。我們今天從詩詞中所看到的用“柳”來表現離情別緒的詩句,其實還要早于這種“習俗”。北朝樂府就有《折楊柳枝》,到了唐代,折柳灞橋、長亭送別更成為一種風俗。其中唐代西安的灞陵橋,是當時人們到全國各地去時離別長安的必經之地,而灞陵橋兩邊又是楊柳掩映,這兒就成了古人折柳送別的著名的地方,如“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后世就把“灞橋折柳”作為送別典故的出處。故溫庭筠有“綠楊陌上多別離”的詩句。“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唐人所作《折楊柳曲》二十多首,大多為傷別之辭,且尤多征人懷念之作。宋代詞人對柳似乎更加鐘情。寇準的《陽關引》可以說是北宋人作的《折楊柳曲》:“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楊柳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隋佚名,《送別》)無法說清楚離人手中那青青的柳枝何時枯槁,但折柳這個動作卻一年一度地重復著。最后升華為一種優雅的傷懷之美,升華為審美傳統中的一個典型意象。
“柳”作為“留”的代名詞,是送別詩中的一個典型意象。那無邊的柳色,碧綠的枝條,如雪的飛絮,無不寄予著人間的離情別緒,無不契合著人間的相思與幽怨。在楊柳的身上,詩人找到了很多對應的本質顯現,千百年來楊柳逐漸積淀成為一個母題性意象,它包含了極大的思想與情感容量,凝聚了先人無數次相似的心理因素與感受方式,楊柳成了詩的化身,情的化身,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集體無意識在送別的驛路中傳承。《風入松》詞云:“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一絲柳”,便牽動一寸柔情;在“萬條垂下綠絲絳”的季節,其離情別緒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