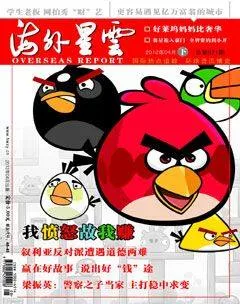敘利亞反對派遭遇道德兩難
2012-12-29 00:00:00歐文.本內特.瓊斯
海外星云 2012年8期

迪拜的一間酒吧內,一位女郎手里端著一杯健力士黑啤。女郎是敘利亞的反對派,在迪拜度周末,抽空到五星酒店來放松放松。女郎身材嬌小、笑容宜人。談起在敘利亞街頭的戰斗,周身上下散發著活力。
酒吧內,坐著許多無精打采、略顯醉意的英國人。他們大多都是男人,一邊喝著威士忌或是啤酒,一邊看超大屏幕上正在轉播的橄欖球賽。在這樣的地方,這位女郎顯得有些鶴立雞群。
她說:“我每天都去抗議示威,但是,我丈夫卻很膽小。”女郎接著說,“他很能自制。我們剛結婚不久。我以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現在……我原本希望能和他共同生活40年,生幾個孩子。也許吧。但是現在,我不能肯定了。我不知道該怎么辦。”
偶爾才看新聞?
再舉個例子。這也是一位到迪拜來旅行的敘利亞女郎。她告訴我:“過去幾個月,我一直在敘利亞,上街參加活動,拍照、上網。幾天前,我到迪拜來,遇到一些住在這兒的敘利亞朋友。我坐飛機來的,所以不知道這段時間發生了什么事。我問他們,他們說,什么也不知道。”
“我接著問,新聞說什么了?他們說今天沒看新聞,因為只是偶爾才看看新聞。他們出來逛街呢。這讓我很吃驚。我在那邊冒著生命危險參加示威呢!我也能呆在這什么也不干!”
她看了看剛剛收到的手機短信,嘆了口氣:“又一個朋友被捕了。”她聳了聳肩,好像這并不怎么重要。但是,她的臉上流露出悲哀和擔心。
母親的葬禮
還有另外一個敘利亞人,沒能回國去參加母親的葬禮。他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寬松的藍褲子。看上去和游客沒有什么兩樣。但是,他是一位流亡的藝術家。他的作品被定性為“反制度”,名字上了黑名單,一在機場露面,立刻就會被逮捕。
我在一家畫廊和他見面。畫廊是一間巨大的倉庫,里面掛著的畫大多是關于槍和士兵的。有一幅畫上面是“三大圣”:奧巴馬、艾哈邁迪·內賈德、本·拉登。
談起母親,他流淚了。他搖搖頭,無法接著說下去,絕望、悲傷地走到了一旁。
現在,許多敘利亞人都在哭泣。
“我選擇向女兒撒謊”
還有一位敘利亞人現在仍在大馬士革活動,但是,他把家人送到了國外。
他頭發花白,身材瘦削,臉上密密麻麻的皺紋,仿佛無聲地刻劃著作為政治犯受到監禁的歲月。
現在,他是一位反對派領導人。他把家人送到了國外,但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3歲的女兒說什么也不想離開大馬士革。他向我講述了說服女兒的經歷。
“我對她說,我們需要辦護照。她問我為什么。我說,也許夏天我們要去度假。但是,她不停地問,為什么其他同學不辦護照、簽證什么的?”
“每一次,我都想出這樣或者那樣的借口。有一次我告訴她,也許是因為其他同學沒錢辦護照、去度假。”
“我向孩子撒謊了。我選擇做一個撒謊的父親,而不是拿孩子的生命去冒險的父親。有時間的情況下,我和女兒在家里坐在電腦前,打開谷歌地圖,我給她看不同的國家,希望能在她心中挑起一點出去看看的熱情。”
“有時候女兒會說,好吧,我真想去這些國家看看。但是轉天早晨,她又改主意了,哪兒都不想去。”
“該走了。女兒必須面對把爸爸留下來的真相。她說,你能受得了、我也能。我們一定要呆在一起。”
“我停下來,想想,我的選擇正確嗎?這對我的國家有利嗎?我能幫助自己的國家、這是不是只是一個幻想?”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是不是選擇了敘利亞人民、而不是自己的家人?”
天生唱反調
最后,再說一位漫畫家。
他告訴我:“1996年,阿薩德還沒當總統的時候,我們見過面。他來看我的畫展。
“有些漫畫讓阿薩德忍不住發笑,特別是那些針對保安的漫畫。當時阿薩德帶著一群保安。他轉過身來對他們說,瞧,這些漫畫拿你們開心呢?你們怎么看?
“阿薩德要走了我的電話號碼。后來,我們經常見面,有時候一星期兩次。他很欣賞我的勇氣。他并不經常聽到反對的聲音,但他希望聽聽我的看法。
“有時候他會到我這里來,有時候我去看他。”
但是幾個月前,阿里·法扎特(A Farzat)畫了一張漫畫,暗示阿薩德像卡扎菲。立刻,法扎特就收到了回報。來找他的那些人拿著黑色的大棒。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使勁打他的手,這樣他就再也不能畫畫了。”
我問:“這是阿薩德直接下的命令嗎?”
他回答說:“我不知道。”
“你還會和他見面嗎?”
“不會了。我天生就是漫畫家。就是要唱反調,和做壞事的當局有不同的看法。這才是我要做的事。”
“醫生說了,再過10來天,我就又能畫畫了。”(編輯/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