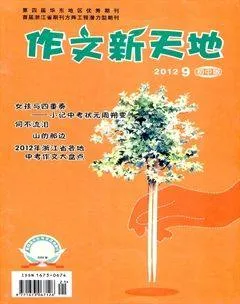九月如初
九月的故事如稻草一樣凌亂。
五年前,我還是一名學生。那個九月的雨天,我哪都沒去,早早便趴在圖書館里尋找世界的另一半棲息地。
彼時,攤開張煒的《我選擇,我向往》,一時間我昏昏欲睡,靜靜地聽著這位善于思考的作家整理著他爬滿蜘蛛網的記憶,我也靜靜地、靜靜地倚在桌沿。
突然覺得《校園的琴聲》是充滿靈性的,校園的樹林總是掛滿詩意的果實,當然,我同樣在校園的邊邊角角中挖掘詩意的琴聲。
而散文呢?仿佛是家鄉的小路,有點熟悉,有點陌生,同時又多了幾分疑惑。
詩與散文本身就沒有鴻溝,我也沒抬舉哪一方,只是寫慣了詩歌,驟然提筆寫散文,像是流浪很多年后的歸家,突然萌發了一種莫名的溫暖。
校園散文是青春的筆調,或許有份叛逆的眼光,但它終歸青春的大海,而屬于散文的那種沉重、沉穩、沉甸甸的目光,且屬于上個世紀的標志,但真正能撼動這個時代的脈搏,非這種目光不可。
張煒先生的目光同樣是穩重的,他善于思索,當然,他善于把思索后的精華融入到文章里,這是他的追求。多年后我像他這樣在小路上撐傘散步時,我仍會感慨于文字的理性,其實這一切平淡如初。
那天從圖書館出來,外面的雨依然下得很大,記得我初到大學的時候,曾寫過一篇關于雨的詩歌:“下雨的時候讓我想起了南方/雨是我家院子上空的繁星/……那是奶奶講的故事/……北方的雨終于落下了,但/雨能打濕的只有眼睛……”
闊別多年后,再次回想起來,同樣是那一份溫存,只不過我不再淋雨,淋雨只會讓我的文字更加潮濕。我打開了傘,在這片北方的雨空中撐起一片云,也就是在這里,在冷冷的風中,淡淡地去想著南方,想著榕樹下倒垂的故事;還有夕陽下石子路上等待我歸來的霜鬢;還有更早之前老去的爺爺肩上的童年。
學生時代的我總疲倦于校園繁雜的事務,更是厭煩世俗無趣的目光,所幸喜歡文字的心讓我去追尋一種平靜。比如獨坐在池邊的石椅上,望著隨風飛揚的柳絮,還有池中羞澀的菱歌;比如提筆在青春的扉頁寫下了《六月詞》,然后投到文學社的雜志里印成墨香;再比如在樺林里,翻開一片片落下的黃葉,翻開一點點平淡的思緒,坐在木椅上,靜靜品讀一闋詞的溫潤,造一方凈土。
那時有很多沖動的想法,時至今日,我依然想用雙手在幽靜的樹林里建造一座小小的瓦屋,在里面住上幾年,平淡地寫著屬于屋內的小小天堂。
突然傳出一首歌,在傘下,是達達樂隊的《南方》:“那里總是很潮濕,那里總是很松軟……”我不想去那傘下探究那汪伊人的秋水,因為我相信她很漂亮,我是指她的心很美。
大學時候,除了用詩來慰藉我的疲倦外,我很少寫日記,更很少用散文的形式來抒發黃昏與露珠的大學生活。或許當時的我想得太多寫得太少,因為在課堂上我總是不時勾畫自己的烏托邦愛情,只是思緒總在世俗的目光中干涸,終究又歸于一種虛無,這些只有詩比較合適表達。
那天的雨下得異常大,我依舊在前行,我多想漫無目的地在雨中走著,想著屬于自己的,雖然是一貧如洗的故事。
瞬間萌生的概念——“逃課”?我很喜歡逃課,因為我把它當成一種青春的叛逆,青春中騷動的事我都愿意去嘗試,不過這次我沒有逃課,逃課是形式上的,逃課也需要境界。或許,當時的我在課堂上看了幾篇文章,寫寫屬于自己的流浪空間,這也是一種逃課,而這種逃課更具有一種高深的境界。當時自己在想:每天重復著這種“逃課”,當不久的將來,達到更深的境界后,將會善于思索、追求平淡、低調而沉穩。
收起了傘,我放下書包,攤開筆記本,提起了筆,計算機老師的目光陷入了暗淡的死寂,而我則深入了思索的綠叢中……
而如今,雜亂寫下這些文字,我仍屬于年少輕狂的時代,我與散文久別重逢,我只是記下屬于自己的故事,這是我繁雜的生活,也是自己一個人的所想、所思。
或許我的文字終究是一種無理的打趣、世俗的塵埃,但她仍屬于我思想的一部分,見證了我那不安寂寞的心,我終將去探索一種超越,像流星一樣,擁有華麗得只屬于記憶、實質卻平淡如初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