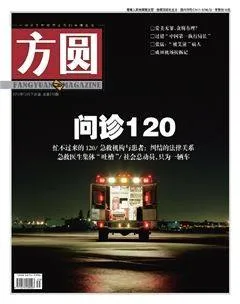成田機場釘子戶抗拆記


日本成田機場事件并不僅僅是“釘子戶拒絕強拆”這一簡單的邏輯,而是在日本戰后經濟迅速發展與社會思潮的復雜背景下,在政府與民眾的不斷反思與訴求表達中,被一個時代所造就的
11月28日,日本千葉地方法院開始拆除成田機場附近的“機場反對同盟”的團結小屋。當天,現場約30名反對同盟的成員進行抗議,聲稱“不允許強制執行”。這一場景再度喚起世界輿論對于成田機場釘子戶幾十年抗爭的關注。
很多人不知道,成田機場的斗爭,持續40多年,浩浩蕩蕩又血雨腥風,稱其為日本戰后最激烈的社會斗爭運動之一也不為過。成田問題,早已經超出所謂釘子戶或者抗強拆的范疇,成田斗爭,伴隨著日本社會的風云變化,起起落落。
興建成田機場
常去日本的人,沒有人不知道東京成田機場。某種程度上,大型國際機場如同國家的名片,一如肯尼迪機場之于美國,戴高樂機場之于法國。
日本東京成田機場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自1978年啟用以來,每天運營的航班將近370次,接待的旅客人次和處理的貨物數量都堪稱世界第一。如果是起降的高峰期,你會看到,這邊的飛機尚未完全飛起,那邊的飛機已經進入跑道,著陸飛機是否滑出導航路尚未確定之時,起航的飛機已經開始滑行。從經濟效益上講,機場的利用率高當然是件好事,但是,一旦發生意外,后果可想而知。一向做事謹慎小心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難道真的只是為了經濟效益而不顧其他?
這是因為多年來,一群“釘子戶”堅守在那里。
成田國際機場的建設計劃始于上世紀6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當時作為國際航線主力的羽田機場已經不堪重負,而當時東京的土地又嚴重短缺。本來計劃在東京灣內填海造機場,但受限于當時的工程技術并不能達到要求,政府只得考慮將新機場建在東京都旁邊的千葉縣。
新機場的預定地點,最初并不是現在的成田機場所在地。當年一位機場建設方案的制訂者回憶說,“其實日本準備在千葉縣境內修建機場。一開始選的是富里市,其實那里的條件比成田還好,但就是因為那里的居民抵抗得更厲害,所以才改為成田的三里塚。日本土地是私有的,國家不能不經允許奪走居民的土地。這是成田斗爭的直接誘因。”
其實,日本政府還有一個算盤,就是那里的主要土地屬于宮內廳下總御料牧場,是國有地,容易解決。在這片區域內的住戶大多數是“二戰”以后來開荒墾殖的農民,生活貧困,動員搬遷容易。并且千葉縣政府支持中央政府的決策。當時的自民黨副總裁川島、首相佐藤榮作曾分別召見千葉縣的縣長友納,友納明確表示支持。而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曾嘗試在富里地區建設機場,但因為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同意,所以當農民的反對運動激化時,地方政府袖手旁觀,最后不得不放棄此案。日本中央政府首先和地方政府溝通,采取一致步調,顯然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訓。
但日本政府忽略了和他們認為容易動員搬遷的三里塚地區農民的協商。當然,這并非無意的疏忽。在佐藤內閣通過成田機場建設案的前一天晚上,運輸省次官(副部長)與農林省次官交換意見,農林次官曾問到是否得到了當地農民的理解,運輸省次官回答說:“修建機場是由上邊來決定的,一般地說,農民服從決定是原則,迄今為止都是采用這種方式,從來沒有發生過問題。”
白骨的怨恨
事實也正如這位運輸省次官所言。1967年6月17日,在千葉縣成田市三里塚、芝山地區修建機場的方案被提了出來,只對當地農民做了一次形式上的說明,7月4日就被佐藤榮作內閣批準,前后不到三個星期。隨后,盡管遭到農民的強烈反對,日本政府也沒有改變強制性地征用土地的決策,而是通過具體負責建設工程的新東京國際機場公團,與部分同意搬遷的農民進行價格交涉,試圖運用經濟手段來解決問題。對于堅決拒絕搬遷的反對聯盟的農民,則不惜動用暴力,強制執行。這是因為,按照日本政府的邏輯,他們已經履行了所有的法律和行政程序,他們的行為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于是,國家的邏輯和農民的道義也就在這里出現了嚴峻的對峙和沖突。生活在三里塚地區的住民,大多數都曾被迫參加過侵略亞洲的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把自己寶貴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日本國家所發動的戰爭。戰后,為了解決糧荒,他們又響應政府的號召來到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開荒,辛勤耕耘,把荒原改造成了沃土。而現在,國家又一次要他們做出“奉獻”,并且是不容分說,只能服從。
這種輕率的做法激起了民眾的極大反感。這不能不讓他們感到,他們的人格尊嚴一再被國家侵犯,生存權利一再被國家隨意剝奪,1971年1月,農民們在紀念已故的機場建設反對派領袖人物小川明治先生時,寫了一封致首相佐藤榮作的信。在這封題為《白骨的怨恨》的信里,不僅表達了農民們在“親手培育的田地被奪取、寧靜的故鄉遭到破壞”時的憤怒,還明確表示,他們抗爭的目的并不在于經濟補償,“如果你能夠讓我信服,如果能讓我感到服氣,就是不要補償,我也會高高興興地把自己的土地財產拱手相讓”。
但日本政府的行為,不僅不能讓農民信服,反倒讓他們感受到戰爭期間濫用國家暴力的行為又在重演。《白骨的怨恨》尖銳指出,日本政府強制性征用農民土地,其實是對民主原則的踐踏,“此后,便是暴力的強權政治:‘你礙事,就請走開!’”
當地居民成立“機場反對同盟”,對政府進行反抗。在當地民眾奮起反抗的同時,各地工農、學生和環保組織也都給予聲援或直接派代表參加。日本左翼的強勢介入,把這場保衛家園的運動政治化,這是當時很多人沒有預料到的,隨后,成田斗爭迅速失控疾走,很快呈現暴力化。
一開始日本政府的粗暴做法激化了矛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是日本左翼運動的高峰,左翼政黨都把這個事情作為反抗政府的一個重要戰場,有些政黨當時還沒有放棄武裝奪權。在這種狀況下,成田斗爭呈現出暴力化的狀態。
從“東峰十字路”到“成田現地”
警察和抗議者的沖突在1971年9月16日達到頂峰。1971年9月16日到20日,日本政府實施第二次征地行動。各地趕來的抗議者超過5000人,千葉縣則出動了5300名警察。雙方沖突造成3名警察死亡,475名抗議者被捕,150多人受傷,這次事件被稱為“東峰十字路事件”。事件發生后,抗議者東三之宮文男以自殺表示抗議。
東峰十字路之戰,算是讓日本政府拿到了第一期的建設土地,但反對者又建起了一座可以妨礙飛行的鐵塔。1977年5月6日,政府強行拆除鐵塔,兩天后抗議者和警察沖突,造成1人死亡,稱“東山事件”。5月9日,反對派進行報復,襲擊附近的派出所,造成一名警官死亡,稱“芝山町長宅前臨時派出所襲擊事件”。
1967年至1978年間,三里塚共爆發過56次沖突,其中4名警察和1名示威者死亡,3100名警察和5000名抗議者受傷,1900人被逮捕。但此時日本正處于一輪輪紅色高潮的影響之下,被左翼運動所籠罩,成田機場反對同盟與前期的反越戰、后期的反對伊拉克戰爭、沖繩民眾反對美軍基地活動互相支持,遙相呼應。日本左翼甚至宣稱“成田機場就是一個美軍軍用機場”,要求斗爭到底。
當時的三里塚儼如戰場一般,可以說是一處“武斗的盛會”。反抗者修建了大量簡易要塞和前線戰壕,還設立非軍事區,還會使用燃燒瓶一類的武器。警察方面每次也是嚴陣以待,大量使用機動隊(類似于防暴警察)清場,雙方攻防拉鋸,這些場景都是今人不可想象的。當地居民甚至組成青年行動隊、少年行動隊、老人行動隊、婦女行動隊等,個個視死如歸。
終于在1978年第一條跑道完工并預計在3月30日正式開放運行之際,成田斗爭再臨高潮,3月26日,以極左派別“第四國際日本支部”為主力的游擊隊攜帶燃燒瓶駕車沖入機場控制塔臺并進行了肆意破壞,砸毀大量設備。導致機場延期到5月20日開放。這還不算完,反對派又繼續進行“百日斗爭”,包括在機場附近升起氣球、燃燒輪胎,以阻止航班飛行。
其實,成田斗爭歷時30多年,非常漫長,最初的目的到后來就變質了。而且不再是追求土地的保有或者要求換一塊地之類,而是變成極左派的年輕人們集結在“成田斗爭”的大旗下,把那里變成一個武斗場,通過這個來追求存在的意義。這種武裝斗爭以及反映出的社會主義思想,并不容易得到日本人的共鳴,其實并不能得到一般日本人的理解。
為了保護半運作中的機場,一萬名以上的防暴警察長期在成田機場戒備,更設置監視塔、探照燈、電圍欄等。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間,日本發生的700多起“游擊事件”中,大約500起都與成田機場問題有關,這些事件造成13人喪生,其中5名是警察。機場開始營運后政府依然高度緊張,機場周圍遍布著金屬柵欄,警察全副武裝地在瞭望塔上巡邏。旅客在進入候機大廳前其行李都要經過嚴格的安全檢查,以防止恐怖活動。
1985年10月20日,約3900名反對者在召開全國集會,警察包圍集會場所引發沖突,惡斗持續兩個小時,59名警察受傷,3臺裝甲車被嚴重毀壞。反對同盟241人被逮捕。這場成田機場啟用以來最大規模的沖突被稱為“成田現地斗爭”事件。
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實際上也借助了這個事情在試圖擴大自己的權力范圍。當時有一個現象,警視廳的長官可以列席閣僚會議。但按照常理,警視廳只是東京警察局,其局長不應該出席類似活動,正是因為當時社會運動非常的激蕩,才有了這個非常態的處理。
對于強烈的反抗,日本政府認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農民反對運動,而是破壞法制、挑戰民主制度,將會對相關行為進行徹底的檢舉和取締。就這樣,反抗也反過來強化了強制措施,日本政府制定了《成田治安限時立法》,在國會通過時僅一人反對(曾任東京都知事的小說家和演員青島幸男)。千葉縣警察還成立了專屬的機動隊“新東京國際空港警備隊”。
同時,由于恐怖活動,日本社會也都對成田斗爭產生了疏離感。據說當時京成鐵路線沿線的居民對反對派都給予白眼。長期暴力斗爭也嚴重影響了附近農村的社會經濟生活,導致了凋敝的狀況。1984年,反對派出現了互相暴力襲擊的事件。同時,極端分子把恐怖活動擴大到個人,他們綁架并毆打了千葉縣土地征收委員會的律師小川彰,由于嚴重的后遺癥,小川彰在2003年自殺,這些導致了極端行為逐步喪失民意基礎。
成立隅谷調查團
同時,雖然在激烈的斗爭中,成田機場還是建成,但是計劃已經數次修改,日本政府也開始妥協。1991年,為解除成田機場問題,成立了隅谷調查團,這是一個日本知識分子團體,由5人組成,包括研究勞動經濟學的日本女子大學校長隅谷三喜男,東京大學名譽校長宇澤弘文,中京大學教授、環境問題專家河宮信郎,記者兼高千穗商科大學教授山本雄二郎以及日本空港協會會長、運輸省航空局局長高橋壽夫。調查團的目標是找出成田機場問題的原因,找到符合社會正義的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各方斡旋下,1995年,日本政府宣布放棄在成田機場動用《土地征用法》,并由首相村山富市代表日本政府向當地居民公開道歉。而機場周邊部分居民覺得已失去了繼續抗爭的根基,開始慢慢搬家。1999年,成田機場第二跑道開始修筑,并趕在2002年日韓世界杯開幕前投入使用。第二跑道落成之時,仍舊有不少“釘子戶”堅守在成田機場,占有共計約4400平方米的土地。其中,有7戶居民還留在機場第二跑道上。
日本社會一向都是分左中右,他們對成田問題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日本社會對于成田當地的老百姓有著充分的同情,不光是社會輿論如此,司法界乃至政府機關也是如此。有一次成田機場方面將當地數百塊土地的業主一起告上法庭,但是千葉縣地方法院只受理了很小一部分。這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司法救濟。
為了避開7個“釘子戶”,第二跑道北移了800米,跑道也不足2500米的計劃長度,只建了2018米長,導致波音747之類的寬體大型客機無法起降。用谷歌衛星地圖查看成田機場,可以發現第二跑道因為有民居和田地,結果只能向北移。較細的那條是滑行道,為了避免“釘子戶”只好修成S形。
本來日本政府希望能讓成田機場成為亞洲代表性的樞紐機場,但由于成田機場只能以一種“非效率”化的狀態運作。這個地位就讓給了韓國的仁川機場。現在如果在成田機場起降的話,雖然不能說危險,但航運控制非常復雜。而對于現在還在機場附近住的居民來說,一方面噪音很讓他們煩惱,也存在一定的危險性。另一方面他們又熱愛那里的土地和歷史,所以我覺得很難用簡單的理由來理解他們長期的斗爭。
經過40余年的對峙,從武力對抗到道歉和談,政府不再敢貿然侵犯私人土地。日本人也轉換了思維,比起曠日持久的從農民那里征地,還不如選擇填海造田。于是,新建的兩座大型國際機場—西部機場與關西機場,都建在了填海新地。
少數人也不該受侵害
2011年9月開始,成田機場與一名“釘子戶”達成和解,2012年8月下旬,該戶居民搬離,小屋被拆除。面對這種主動撤離的罕見做法,機場相關人員稱:“通過對話方式解決用地問題取得了很大進展。”
實際上,成田問題到現在,已經不是政府與民眾的對抗,而是土地所有者要從居住者手上收回土地,這是東京高等法院已經判決的事情。經過這么多年的抗爭,日本社會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也在生變,加上日本社會左翼思潮幾乎退去,抗爭者越來越難以取得社會的支持。日本社會對此事的關心程度也越來越低。
當初在政府支持下,強行收回土地的開發商們因為自己的做法而受到了批評,這個是確實的。做出賠償也是正當的,但另一方面,很多人拿到了一生都用不完的巨額賠償金,還有人依靠這個建起了豪宅。結果左翼的政治運動,導致了很多人由此獲得了很大的個人的利益,所以這也成為批判成田斗爭的一個依據。
但就像“成田機場鄉土和生活守護會”事務局局長巖田公宏所言:“多年抗爭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守護我們的居民,幫他們抵御因機場而來的各種公害。最初只是涉及一個‘公共利益’的問題,因為談得不好,結果突然機場就開建了,國家的這種做法引發了極大的反抗。說到我們是不是有礙公共利益,其實我覺得還不如說是國家和企業的利益。我想說,即使受到侵害的人非常少,但如果國家和企業侵害了他們最低限度生活的權利,就違反日本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