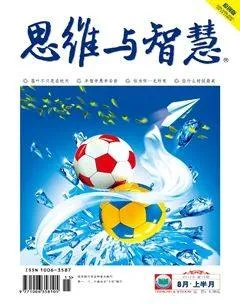書蟲的雅運
2012-12-29 00:00:00程耀愷
思維與智慧·上半月 2012年8期

作為書蟲,我這一生,實實在在的是諸事不順。在人家,常常是大道通天,八面風光,而我,卻是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往迷霧的遠方。直到近年,局面終于稍有轉變,雖然算不上苦盡甘來,然而曾經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夾帶那些揮之不去的煩心事,漸次從我的生活中隱退了。
山光悅鳥性,池月空人心。此處“空人心”,不是心靈被掏空,不是一無所有一片空白,恰是相反,一旦蕩滌了附著在內心深處的癡與妄,心境平和下來,許多美好的東西,醇和的交情,甚至求而難得的運氣,往往不召而自來。
不召自來的包括“雅運”。雅運在收藏家那里,有專門的行話,叫“揀漏”,凡揀一漏,得失之心必以為有吉星高照,自然欣欣然而樂矣。與其不同的是,作為書生,偶得古人遺墨、名家珍玩,便是交了雅運。交雅運,當然也是賞心樂事,只是此樂非彼樂,與揀漏不可同日而語。一個讀書人,書房里即便積書滿架,倘若壁間無字畫,案頭缺文玩,終歸顯得蒼涼顯得暗淡,那是“小姑所居,獨處無郎”的蒼涼與暗淡。
半個世紀之前,雖然家境不振,家族的長輩們,多少還是給我留下幾粒玉屑,不外青銅器、玉佩、線裝古籍、文房用具之屬,如果平安保存至今的話,足以令我的陋室蓬篳生輝。只可惜世事蒼茫難自料,臨到我獨自面對人生,人世間一會兒“寒雨連江夜入吳”,一會兒“風物凄凄宿雨收”,隨著潮起潮落,傳到我手中的家族遺物,曾是寂寞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內中最不堪回首的,是那一方鏤花松鼠葡萄山水舟楫徽硯,石材與手藝,都是上乘,父親至愛,視之為鎮宅之寶,上世紀50年代,為地方權勢者所“借用”,從此,一別音容兩茫茫,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痛。
也許歷史也有所謂的“補償性代謝”吧?飽受失硯之痛的我,到頭來居然是石硯開啟了我的雅運之門:2003年春夏之交,當我結束在大江南北的漂泊生涯,我的行囊里,至少多了一臺端硯和三臺徽硯,它們的來歸,或多或少能撫平內心的隱痛。之后,又在皖南的一處山溝里,巧遇一臺光緒十年的“鐘兔硯”,雕工精細,大不盈掌,既能作擺設,亦可當把玩。去年春,獨游西南,在攀西大峽谷,得羅氏“苴卻硯”兩臺,色彩艷麗,手捫如玉,對我來說,那種感覺,簡直就是一場艷遇。
在鄭州,我擔任過一家房地產公司顧問,那是個閑差。因我對國畫的精粗與真偽,略有心得,老板到文物市場選畫之時,我于一旁咨詢,頗合其心意,待我任職期滿,老板送我一尊雙耳綠釉陶罐,罐高20厘米,罐耳的兩側,有兩對栩栩如生的壁虎,妙的是每一對中,似有雌雄之分,雄者昂首,雌者搖尾,觀者縱然是鐵石心腸,也難免意惹情牽。這尊釉陶壁虎罐,我不曾拿去請專家斷代,因為我知道,專家的眼光與儀器的精微,在一件藝術品的魅力前面,肯定是不得要領的。
秦磚漢瓦早已不再充當建筑材料了,但它卻成了中國文化的一種符號。一直以來,我有一個心愿,但愿有一方寄身于山林海陬的古磚,有一天能自己走進我的陋室,伴我讀書,伴我嘯吟。恰巧有一年到蚌埠,拜會文友,朋友引我等到一IdKh6L7kj5ZRwwNiofokZLeq/1oMmeWqdHBL9QLp7PA=位中學校長的辦公室里品茶,校長室的布置,透露出主人的諸多雅好,大家都挑自己喜歡的東西欣賞品鑒,獨有我留意一塊用玻璃盒保護起來的漢磚。我在不少人家中,見到過這類古塊,因為磚塊的圖案或文字的空靈古雅,成為人們追慕的對象。蚌埠歸來,每到一地,即使荒村野店,我的目光總是在那些被人們棄之不顧的舊磚瓦堆里不停地搜尋。記得在秋浦河的源頭,一個擁有多叢進士墓的李村,我的愿望似乎觸手可及了,遺憾的是,磚上的花紋不堪日曬雨淋,面目早就模糊不清了。盡管空喜歡一場,但我依然堅信,會有夢想成真的那一天。果然,我的一位淮南親戚,也為我上心這事,他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里,光臨寒舍,將半塊漢磚,放到我的書案上。據說原本是整磚,一半破損嚴重,有礙觀瞻,他索性用切割機除卻破損,保留下來的一半,反而愈顯精神。磚的側橫面的圖案,竟然是罕見的人物像。一見那圖像,關漢卿《謝天香》第一折里那句“必定是峨冠博帶一名士大夫”的那句話,就在我的耳邊響起。再看磚面,基本完好的包漿下面,流暢的線條,足以牽愁惹恨。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此生只合為書蟲。眾多頭頂各種光環的精英們,以寶馬香車醇酒美婦為享受對象,書蟲則另有快樂之道:古代的書蟲,得劍如同添健仆,失書每憶似良朋。現代書蟲如我者,書籍之外,再加上硯、罐、磚,已是雅運當頭了,至于古人山水,名賢墨寶,有也罷,無也罷,都可看淡。
(編輯 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