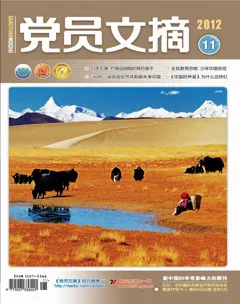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博士大還是縣長大?”七年前,在莫言被授予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時,得知喜訊的父親曾這樣問他。如今,莫言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不知道父親會作何感想。
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講,回顧了自己的創作生涯,那個在高密山頭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長為一個世界知名的作家。今天,回過頭再去聽聽他的自述,你也許會更了解他。作為作家,莫言對文學有著自己的理解和認識。
寫作沖著一天三頓餃子開始
1957年,我家來了個大學生鄰居。他講,當年他在濟南時,認識一個山東省比較“腐敗”的作家,一天三頓都可以吃餃子。我們當時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餃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對文學對當作家的夢想,就是沖著一天三頓都可以吃餃子開始的。
后來,我把村里的書借來看了以后,才真正有了關于文學的概念。在我們村子里,有《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隋唐演義》等幾種古典章回體小說。
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比如幫別人干活,跟別人換東西什么的,把村里的這幾本小說都看完了。當時我以為我已經把天下所有的書都讀完了。
筆名“莫言”
和喜歡講真話有關
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孩子,在我們農村把這種孩子叫做“炮孩子”。后來我寫了小說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個“炮孩子”,其中也有我個人的經歷。也因為我喜歡說話,喜歡說真話,給我們家里帶來了很多麻煩。
所以過了幾十年以后,當我要寫小說準備發表時,使用的筆名叫“莫言”,就是告誡自己要少說話。事實證明,我一句話也沒有少說,而且經常在一些特別莊嚴的場合,說出實話來。
我覺得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講假話,不但對社會無益,也會大大影響其文學作品的品格。因為好的文學作品,肯定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里邊,尤其是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面貌。
我的很多小說一旦發表以后,有些讀者不高興,因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徹底。當然我不會迎合這樣的讀者,而犧牲自己文學創作的原則。在我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后記里,最后一句話就是說“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中國文學如何跟世界對話?
中國文學真正能夠跟世界對話,真正超越了狹隘的階級觀念,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的。這時候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閱讀翻譯過來的西方小說。這大大開闊了這批中國小說家的眼界。
我上世紀80年代的幾個作品帶著很濃重的模仿外國文學的痕跡,譬如《金發嬰兒》和《球狀閃電》。到了《紅高粱》這個階段,我就明確地意識到必須逃離西方文學的影響,一定要寫自己的東西,自己熟悉的東西。
這就需要到民間去尋找,真正豐富的文學資源還是隱藏在民間。當然我說的民間并不僅僅是荒涼的偏僻的農村,城市也是民間。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勞》。
所以包括我個人在內,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實際上是借助了這兩種力量。我們借助了翻譯過來的西方小說,對我們自己的文學觀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后又從民間尋找到豐富的資源,這才有了當今中國小說的現狀。
有的人為了獲獎,將作品特意貼上中國標簽。什么是中國標簽,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記里面說,我想在語言上有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寫給外國翻譯家看。
一個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寫作追求限定在一個什么獎上,也沒聽說哪一個作家為了得什么獎而調整了自己寫作的方向,改變了自己寫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變,變得了嗎?
該怎么寫,還怎么寫;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摘自《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