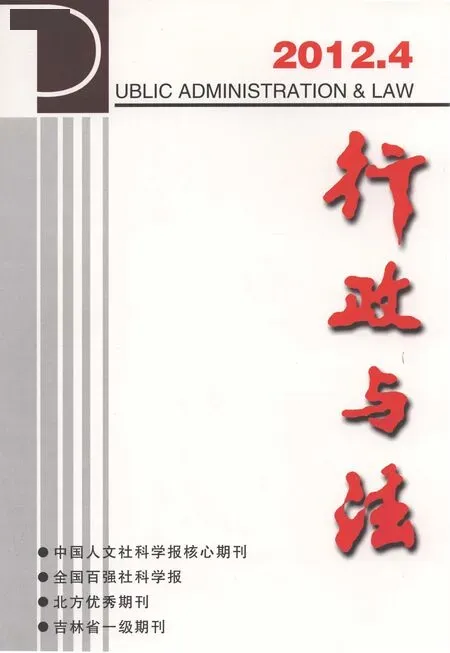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及其現實意義
□ 湯景楨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及其現實意義
□ 湯景楨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3)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深入,對和平與安全的期盼使得國際法治成為國際社會的理想與目標。為了建立以和平為目標的國際法律秩序,凱爾森提出了國際法治理論,即通過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法院和確立個人違反國際法的責任來構建世界和平。本文將以此為基礎,探討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對國際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分析國際刑事法院在實現國際刑事法治化過程中面臨的政治制約因素,以期國際刑事法治和國際法治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國際法治;凱爾森;國際秩序;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刑事法治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漢斯·凱爾森一生著述豐富,在法哲學、憲法學與國際法學等領域都產生了世界范圍內的重要影響,其首倡的“純粹法理論”于西方法律哲學之影響更是勿庸置疑。凱爾森一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飽受戰爭顛沛流離之苦,親眼目睹戰爭對人類文明的破壞。因此,對世界和平尤其渴望的凱爾森于20世紀40年代撰寫了《經由法律而致和平》、《國際關系中的法律與和平》等著作,系統論述了國際法律秩序下的和平思想與國際法治理論。在國內,學者們對凱爾森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純粹法理論、國家與憲法理論、國際法優先說等方面,鮮有視角觸及其國際法治理論。本文將以凱爾森的和平思想與國際法治理論為基礎,以國際刑事秩序為視角,探討國際法治理論在國際刑事秩序法治化的應用上所具有的現實意義,以期進一步推動國際刑事秩序法治化的完善,以及國際法治的發展。
一、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概述
在全球化的時代,在各國已經不可能再孤立發展的背景下,法治的理想也開始超越一個民族國家的界限,走向世界。這就是“國際法治”。[1]
(一)國際法治的內涵
國際法治究竟是什么,迄今為止仍是個見智見仁的問題。有學者將國際法治表述為國際社會接受公正的法律治理的狀態。[2]有學者認為,“國際法治是指作為國際社會基本成員的國家接受國際法約束,并依據國際法處理彼此關系,維持國際秩序,公平解決國際爭端的狀態。[3]也有學者將國際法治的標準歸納為三點:全面預設規則,即在國際社會應當存有預先設定的能夠對社會生活進行廣泛全面調整的確定規則;預設的規則至上,即具有上述特征的規則必須得到服從;獨立的司法機關專司其職,即在出現國際爭端時該機關對司法擁有壟斷權。[4](p196-213)還有學者將國際法治的概念界定為“國際良法”和“全球善治”。[5]而在聯合國的文件中,國際法治也不再是陌生的詞匯。2000年的《聯合國千年宣言》就提到:“我們將不遺余力,促進民主和加強法治,并尊重一切國際公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發展權。”[6]2005年聯合國世界首腦會議達成的共識更是多次提及法治一詞,如“國家和國際的良治和法治,對持續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以及消除貧困與饑餓極為重要。”[7]
無論國際法治的概念如何定義,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察其內涵:第一,國際法治的目標是構建一種國際法律秩序,這種秩序所追求的是和平、安全、人權、可持續發展等人類所共同崇尚的價值和利益;第二,這種國際秩序必須納入法律的軌道,依照法律的規定,按照法律的程序,接受法律的治理;第三,在這種國際法律秩序中出現爭端時,應當有專門的司法機關壟斷解決,從而促進國際正義的實現。
(二)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
在國際關系演變的歷史實踐中,國際秩序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人類之間的戰爭和矛盾沖突不斷發生改變。每次世界大戰之后都會有新舊國際秩序的交替,以實現對國際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1944年,二戰結束前夕,如何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成為當時國際社會迫在眉睫的問題。在這樣的形勢下,親歷殘酷戰爭、渴望永久和平的凱爾森寫下了《經由法律而致和平》一書,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法律制度戰略,以謀求穩定、普遍的國家間和平,體現了其以法治求和平的思想。
凱爾森在該書序言中寫到,“戰爭是大規模的謀殺,是我們文化最大的恥辱,因此保障世界和平是我們首要的政治任務。……只有建立有效防止地球上國家間戰爭的國際組織,才可能有最基本的社會進步。……調整國家關系的秩序之特殊技巧是國際法,凡希望通過現實途徑達到世界和平的人,必須冷靜地把這個問題當作是國際法律秩序緩慢而又穩定的完善過程。”[8]因此,從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出,凱爾森開明宗義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在國際法的框架下通過建立國際組織,構建國際法律秩序,從而實現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和平問題。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凱爾森探討國際法這一特殊技巧如何能保障國家間的和平。他指出,“毫無疑問,實現世界和平最理想的方法是建立一個由所有國家或盡可能多的國家組成的世界聯邦國家。”[9]然而,凱爾森自己也明白,在當時的情況下,實現這個世界聯邦國家的目標存在很多不能逾越的困難,不在政治現實的范圍之內。因此,凱爾森聲明,“一旦戰爭結束,應創設一個維持和平的常設聯盟,這個聯盟的成員首要的是戰勝國,包括蘇聯。”[10]在闡述這個世界國家聯盟的具體設計時,凱爾森認為其成員的政府形式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聯盟要能體現集中性的制裁。[11]
于是,凱爾森進一步設想,“……盡可能多的國家(包括戰勝國和戰敗國)通過訂立國際條約,從而建立一個具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法院。這就意味著,在聯盟里的所有國家必須放棄戰爭和報復作為解決爭端的方法,必須把所有國際爭端毫無例外的提交國際法院解決,并且要真誠善意的履行國際法院的判決。”[12]凱爾森之所以在世界聯盟的計劃中要建立一個具有司法性質和職能的中心機構,是基于對舊國聯模式失敗原因的分析。凱爾森指出,“國聯失敗的原因在于其運行中心不是國際法院而是理事會,也就是一種國際政府。這是一種致命的設計錯誤,因為國際法中最嚴重的缺陷是沒有司法權威。缺少這種更高的權威,每個國家實際上有能力決定誰違反了國際法,并通過戰爭或報復的形式來打擊那些被推測為違反了國際法的國家。”[13]因此,在凱爾森看來,建立具有強制管轄權的法院是國際關系有效改革的第一步也是獨立的一步,這與國際法治的精神完全吻合。
同時,凱爾森還提出了維護國際和平的另一個有效途徑是追究個人違反國際法的責任,不論他是政府成員還是國家的代表,只要違反了戰爭中的國際法就要追究責任。凱爾森指出,法院不僅授權集體制裁來追究個人的“絕對責任”,而且應該對個人進行審判,懲罰親自負責戰爭罪行的個人,國家也有義務向法院移交犯有戰爭罪行的個人。[14]凱爾森此舉意在防止個別極端犯罪分子利用國家責任做幌子逃避制裁,最大限度地實現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保證國際法的權威。
除了在《經由法律而致和平》一書中系統闡述了其和平思想和國際法治理論外,凱爾森在后來的相關國際法論著中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通過國際法確保世界和平的觀點。總之,建立以和平為目標的國際新秩序,并使新的國際秩序在法律技術的操作下有序運轉,實現國際社會的法治化,這是凱爾森所期待的目標和方向。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為二戰后建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新的國際秩序提供了思想基礎。正如有學者指出,“凱爾森的國際法理論對于戰后國際秩序朝著通過國際司法程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向邁進,起著深遠的作用。”[15]
二、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與國際刑事司法的發展
進入20世紀以后,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空前的災難,但也推動了國際刑事司法實踐的巨大發展。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目的就是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構建世界和平,和平目標的實現路徑,主要是通過建立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法院和追究個人的國際刑事責任。而《羅馬規約》的生效、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正是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在國際刑事司法領域的嘗試與驗證。
在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中,建立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性司法機構一直被認為是維護國際和平必不可少的路徑。因此,同樣在以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為目標的國際刑事司法的發展中,建立國際刑事司法機構也成為國際社會努力和奮斗的目標。因為,“一個有固定場所、能夠長期穩定地行使司法權力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既有利于促進國際法治的安定性,也有利于保障國際法治的公正性。”[16]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勝國經多方妥協達成《凡爾賽和約》,曾設想組織特別法庭審判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犯下的發動世界大戰的嚴重國際罪行,但政治上的種種因素最終阻礙了國際刑事審判的進行。雖然對威廉二世的萊比錫刑事審判夭折了,但《凡爾賽和約》清楚地表明了國際社會要懲罰侵略戰爭發起者的決心和意志,更沒有淡化國際社會創建國際刑事審判機構的愿望。二戰后,紐倫堡和遠東審判的實踐可以被看作是依據國際法對戰爭罪行進行懲處的一種可行性嘗試,個人國際刑事責任的規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為創立一個常設法院奠定了基礎。聯合國安理會于1993年建立的前南斯拉夫國際特設法庭、1994年建立的盧旺達國際特設法庭進一步說明,即使在和平時期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二戰后國際社會先后設立的這些特別的、臨時的法庭,在維護國際正義與和平、緩和地區沖突、避免戰爭升級和解決爭端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和有益的探索。然而,由于它們都是臨時的,其司法公正性一直存在爭議。因此,國際社會的法治化發展進程中需要建立一個獨立、常設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在這樣的背景下,1998年7月17日,在羅馬舉行的聯合國外交大會通過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它標志著國際法在人權的保護、國際司法制度的建設、個人的國際刑事責任、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等方面將實現跨世紀的歷史性突破。”[17]2002年7月1日, 在達到規定的法定締約國數目的情況下,《羅馬規約》正式生效,國際刑事法院終于得以成立,這標志著一個嶄新的、常設性的國際司法機構的誕生。當天,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表聲明表示,“羅馬規約的生效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它重申了法治在國際關系中的核心地位,它使世界擁有一種希望——當個別國家不能或不愿追究犯有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者的責任時,國際社會能夠有所作為。它給未來的暴行一種潛在的威懾。”[18]
另一方面,20世紀以來的這些國際刑事審判實踐也不斷地豐富和擴散了個人國際刑事責任的規范。自紐倫堡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以來,關于個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在一系列國際刑法公約中都明確加以規定。《羅馬規約》的生效和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立標志著在追究個人國際犯罪的刑事責任方面有了歷史性的突破,增加了懲治國際犯罪的有效性。《羅馬規約》關于個人刑事責任的一般原則規定,對應負刑事責任的具體情形的列舉,以及 “對不滿18歲的人不具有管轄權”、“官方身份的無關性”、“指揮官和其他上級的責任”、“不適用時效”、“心理要件”、“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等一系列的規定,使得個人被確立為國際刑事責任的主體,改變了長期以來最嚴重的國際犯罪不受或難以受到懲罰的局面,彌補了國際法運行實踐中只能解決國家間的爭端,對實施國際犯罪的個人無法進行有效懲罰的缺陷。而在關于個人的國際刑事責任的實踐方面,皮諾切特案和米洛舍維奇案成為了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總之,《羅馬規約》對戰爭罪和其它有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的個人追究國際刑事責任,體現了凱爾森提出的追究個人國際刑事責任的主張;國際刑事法院的常設性、獨立性和自治性,以及在國際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與其他國際司法機關相比較,其更接近于凱爾森提出的以司法權為中心的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組織的理論預設。因此,以《羅馬規約》為基礎的國際刑事法院背后的價值理念正是國際法治與全球正義,進一步彰顯和保護國際社會所公認的價值標準。
三、國際法治與國際刑事秩序的法治化
在現代國際法的演變和發展中,對國際犯罪進行有效法律控制,維護世界和平是國際刑事秩序所追求的目標,這與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目標完全一致。關于“國際刑事秩序”,有學者是這樣論述的,“國際刑事秩序主要是指已然的國際刑事治理框架與機制,是討論全球刑事法治的國際刑事司法史基礎。……國際上并無統一的憲政秩序,國際刑事秩序本身也混亂無序。……國際刑事秩序無法治,國際法治就不能真正成型。”[19]“國際刑事法治”①關于“國際刑事法治”一詞,由宋健強率先提出并論證,具體可參見其論文.國際刑法哲學:形態、命題與立場[A].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0卷)[C];國際刑事法治:人類和平與正義的真正希望[A].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7卷);國際刑事法院述評——再論國際刑事法治[A].載趙海峰主編.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壇(第1輯);國際刑事法治:和諧世界的底線保障[A].載.和諧社會的刑事法治[C].中國刑法學會2006年年會文集(上卷).是人類和平與正義的真正希望。[20](p378)《羅馬規約》的生效與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讓人們對國際刑事秩序的法治化充滿了期望,期待著國際社會向國際法治的進一步發展。然而,也有學者擔心,“在當代國際政治背景下,《羅馬規約》對國家主權觀念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現有國際政治結構的突破,使它存在著受政治操縱和濫用的現實危險。”[21](p33)因此,當我們為《羅馬規約》的生效和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歡欣鼓舞時,我們不禁需要思考,在《羅馬規約》生效后的近十年來,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是否能真正實現國際刑事秩序的法治化,實現國際刑事秩序所追求的和平目標?
凱爾森的國際法治理論認為,國際新秩序應當通過以司法權為中心的有行動能力的國際組織來實現。正如他所說的,“首先應當開始設立國際法院,只有在法院通過公正的行為獲得政府的普遍信任,才有可能建立一支有效的國際警察部隊。”[22]這為國際刑事新秩序的構建提供了理論支撐。國際刑事法院在建立之初,被引以為豪的特點就是“常設性、穩定性、獨立性、公正性、自治性和有效性等”。然而,受國際刑事法院審理的對象極有可能是國家前內閣領導,故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處于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因此,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性、公正性和有效性似乎面臨著比其他司法機構更為嚴峻的挑戰。國際刑事法院的理想在于國際刑事法治。實現國際刑事法治的目標,意味著政治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干預越少越好,因為政治干預司法和法治的理念背道而馳。因此,筆者認為,如何減少甚至剔除政治因素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影響,這是實現國際刑事秩序法治化的關鍵。而這個問題集中體現在國際刑事法院與聯合國安理會的關系上,正如有學者認為,“國際刑事法院與安理會的距離有多遠,是考察《羅馬規約》國際刑事法治化程度的主要指標。”[23]
在1998年的羅馬外交會議上,國際刑事法院與安理會的關系一直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安理會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對國際和平與安全負主要責任的機構,而國際刑事法院通過對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這四種嚴重犯罪追究刑事責任,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因此,國際刑事法院與安理會有著相同的使命和一致的目標,本質上并不存在沖突。然而,“安理會代表歷史的、大國的、少數人的政治,國際刑事法院代表現實的、中小國家的、多數人的司法,……一個屬于法律秩序,一個屬于政治秩序。”[24]國際刑事法院通過司法手段追求國際正義,而安理會倚重政治手段維護國際和平。為了共同實現國際和平與安全這個目標,安理會的職權與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必然存在重疊,從而引發分權的困惑。關于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與安理會職權關系的激烈爭論,導致《羅馬規約》采取了妥協性的規定。[25]《羅馬規約》序言規定,“……設立一個獨立的常設國際刑事法院,與聯合國系統建立關系,對整個國際社會關注的最嚴重犯罪具有管轄權。”第2條規定,“本法院應當在本規約締約國大會批準后,由院長代表本法院締結的協定與聯合國建立關系”。因此,從《羅馬規約》的最終文本來看,國際刑事法院被定位為以國際條約為基礎的一個獨立的常設的國際刑事組織,并非聯合國體系內的專門司法機構,更不是安理會的附屬機關。由此,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獨立性與合法性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體現了理想主義的價值訴求。但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其字里行間又巧妙地為借力聯合國做了鋪墊,留下了現實主義的烙印。而作為妥協的產物,《羅馬規約》第5條、第13條和第16條還分別規定安理會對侵略罪認定的先決權、情勢提交權、推遲情勢調查和起訴權,賦予安理會參與司法的權力,直接導致了國際刑事法院與安理會發生沖突的可能。下面筆者將對安理會對侵略罪認定的先決權和情勢提交權作進一步分析,從理論和實踐上考察安理會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影響。
根據《羅馬規約》第5條第2款規定,“在依照第121條和第123條制定條款,界定侵略權的定義,及規定本法院對這一犯罪刑事管轄權的條件后,本法院即對侵略罪行使管轄權”,不過,該款最后又規定“這一條款應符合《聯合國憲章》有關規定”,為溝通國際刑事法院與安理會搭起了橋梁。而根據《聯合國憲章》第39條的規定,“安理會應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為之是否存在。”因此,上述規定隱含了安理會對侵略罪認定上的先決權,也即只有安理會認定某一行為構成侵略行為的前提下,國際刑事法院才能行使管轄權。這似乎有將國際刑事法院置于安理會之下的嫌疑,顯然會對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地位造成不良影響。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6月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在坎帕拉通過了《羅馬規約》關于侵略罪的修正案,規定了侵略罪的定義,并在廣受關注的侵略罪認定權問題上賦予安理會首要責任及對侵略罪的部分認定權,即如果安理會在獲得提交案件后的6個月之內未作出裁定,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可在該院預審庭批準后獨自就侵略罪展開調查。修正案賦予了安理會對侵略行為的部分認定權,而非專屬的獨斷權。這種做法雖然遭到了安理會五常的反對,①率團參會的中國外交部條法司副司長關鍵在修正案通過后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修正案未能完全反映《憲章》和《規約》的相關規定和要求。并介紹,安理會五常在侵略罪的認定權問題上立場基本一致,認為安理會應具專屬認定權。資料來源: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通過《羅馬規 約 》 修 正 案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 -06/12/c_12214419_2.htm,2012-02-12.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安理會對于國際刑事法院的影響,這對確保法院的相對獨立性起到了積極的意義。
《羅馬規約》第13條第2款規定 “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章行事,向檢察官提交顯示一項或多項犯罪已經發生的情勢。”對于賦予安理會情勢提交權是否會損害到國際刑事法院獨立性所引起的爭論,遠沒有安理會在實踐操作中對該權力的運作所帶來的反響激烈。我們把目光投向安理會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動用《羅馬規約》賦予其的情勢提交權作出的1593號決議。自從2003年蘇丹國內爆發大規模暴力沖突以來,武裝沖突造成大量人員傷亡,達爾富爾局勢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擔憂。在經過一系列援助、調查、協商、談判等工作后,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并未得到實質性的緩解。2005年3月31日,安理會通過了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交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發生情勢的1593號決議,其后,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于同年6月宣布對達爾富爾地區展開調查。應當說,這個決議開創了安理會行使情勢提交權的先河,反映了國際社會對防止和終止有罪不罰和維護國際法治與和平的決心。然而,該決議給國際刑事法院帶來的消極影響也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議。一方面,這種由安理會提交給檢察官,繼而由國際刑事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做法,使 《羅馬規約》的締約國,特別是非締約國面臨著通過安理會決議的方式不得不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會產生不公平的現象,因為安理會五常可以通過否決權“逃避”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但對于非常任理事國的國家來講,缺乏否決權的“保護”,其國民極有可能必須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26]另一方面,決議第6段“決定:沒有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蘇丹境外派遣國的國民、現任或前任官員或人員因安理會或非洲聯盟在蘇丹建立或授權的行動而產生的或與其相關的所有被控行為或不行為皆應由該派遣國對其實施專屬管轄權,除非該派遣國已明確放棄此種專屬管轄權。”這段規定導致的一個嚴重問題是:豁免“非締約國”的維和人員,追訴非締約國的蘇丹人,但是對蘇丹人犯罪的或者在蘇丹犯罪的其他締約國和非締約國國民(非維和人員)卻不能豁免,形成一種異常混亂的追訴秩序。[27]該段規定中使用“專屬管轄權”的措辭,實質上是在一定情況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進行了限制,影響了《羅馬規約》的效力和完整性。總之,《羅馬規約》第13條賦予安理會情勢提交權,在實際操作中該權力運作卻偏離了方向,損害了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性和司法性。
綜上所述,《羅馬規約》中關于國際刑事法院與安理會關系的妥協性規定是現實的寫照。作為一個新建立的國際司法機構,一系列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實踐經驗不夠豐富,與安理會在國際關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相比,國際刑事法院如需迅速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信任,就需要依賴與安理會的合作。因此,在當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欲使國際刑事法院完全脫離安理會的影響,并不是現實之事。而且,實踐中安理會對相關權力的適用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動造成干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國際刑事法治要求擺脫傳統以政治權威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以此“塑造一種未來的世界秩序,把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寄托在法律基礎上,希望用國際刑事法院代替聯合國安理會的部分職能,謀求建立以人權為基礎的世界秩序”。[28](p18)國際刑事法治是和諧世界的底線保障,[29]國際刑事法院要實現國際刑事秩序法治化理想,就必須徹底擺脫來自安理會的政治壓力和干預。在當今世界格局下,現有的國際政治格局暫時無法打破。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國際刑事法院必須面對安理會與其在國際刑事秩序競爭的問題。目前,我們只能期待在現行框架下對安理會的權力進行制約,最大可能地保證國際刑事法院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以使這個新生的國際司法機構在國際刑事秩序的法治化道路上走得更遠、更穩。
盡管當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法治化氣氛不斷強化,但凱爾森提出的完全司法管轄權的國際社會法治化局面并未實現。因為,對于國際社會來說,在國家利益面前司法有效性的實現仍然存在很多困難。正如在國際刑事司法領域,國際刑事法院代表著一種實現司法獨立和公正的法律理想,而安理會代表了一種現實政治。在國際刑事秩序的法治化過程中,如果安理會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能夠堅持法治原則,維護建立在法治和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秩序,相信國際刑事法治指日可待。在國際法律秩序的發展中,如果世界強國能遵守國際法,改變原有的利益與安全觀念,國際法治必將從藍圖走向現實。
[1]何志鵬.國際法治:良法善治還是強權政治[J].當代法學,2008,22(02):55.
[2]車丕照.國際法治初探[j].清華法治論衡,2000,(01):124.
[3]張勝軍.試論當代國際社會的法治基礎[J].國際論壇,2007,9(02):1.
[4]鄭永流.法治四章[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5]何志鵬.國際法治:一個概念的界定[J].政法論壇,2009,27(04):63-81.
[6]聯合國千年宣言[EB/OL].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7.PDF,2012-02-12.
[7]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EB/OL].http://www.un.org/chinese/ga/60/docs/ares60_1.htm,2012-02-12.
[8]HansKelsen,Peace through Law,Chapel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viii-ix.
[9]HansKelsen,Peace through Law,Chapel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5.
[10]Danilo Zolo,Hans Kelsen:International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1998),p.317.
[11]牟富強,劉強.現代國際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礎——盧梭、康德和凱爾森之和平架構的比較分析[J].社會科學研究,2008,(02):105.
[12]Hans Kelsen,Peace through Law,Chapel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14.
[13]Danilo Zolo,Hans Kelsen:International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1998),p317.
[14]Danilo Zolo,Hans Kelsen:International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1998),p318.
[15]張乃根.論國際法在國際秩序中的作用[J].北方法學,2010,(03):112.
[16]王莉君.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刑事法院與國際法治[j].環球法律評論,2004,冬季號:478-479.
[17]曾令良.國際法發展的歷史性突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述評[J].中國社會科學,1999,(02):150.
[18]http: //www.un.org/News/Press/docs/2002/sgsm8293.doc.htm,2012-02-13.
[19]宋健強.國際刑事法院對全球刑事法治的杰出貢獻[EB/Ol].在2010年 “全球治理與國際法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http://law.hit.edu.cn /article/2010/08-09 /08081042.htm,2012-02-13.
[20]宋健強.國際刑事司法制度通論[M].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
[21]胡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情況介紹[A].高銘暄,趙秉志.當代國際刑法的理論和實踐[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2]Hans Kelsen,Peace through Law,Chapel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19-20.
[23][24][27]宋健強.蘇丹訴案對《羅馬規約》第13跳(b)的整合解釋[J].刑法論叢,2007,(12):528.
[25]劉健.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與聯合國安理會職權關系論——《羅馬規約》的妥協性規定評析[J].現代法學,2007,29(09):137.
[26]王秀梅.從蘇丹情勢分析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補充性原則[J].現代法學,2005,27(06):182.
[28]黃芳.國際犯罪國內立法研究[M].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
[29]宋健強.和諧世界的“國際刑事法治”——對國際刑法的價值思考[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7,(02):115-116.
(責任編輯:張雅光)
Kelse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ang Jingzh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the hop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has mad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be the ideals and aim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In order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for peace,Kelsen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namely,international peace is guarante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urt endowed with compulsory adjudication and the approval of rules establishing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Based on Kelsen'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international rule of criminal law, and analyses political factors faced by ICC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criminal law,trying to furthe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Kelsen;the international order;ICC;international rule of criminal law
D990
A
1007-8207(2012)04-0067-06
2012-03-12
湯景楨 (1977—),女,江蘇宜興人,復旦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刑事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