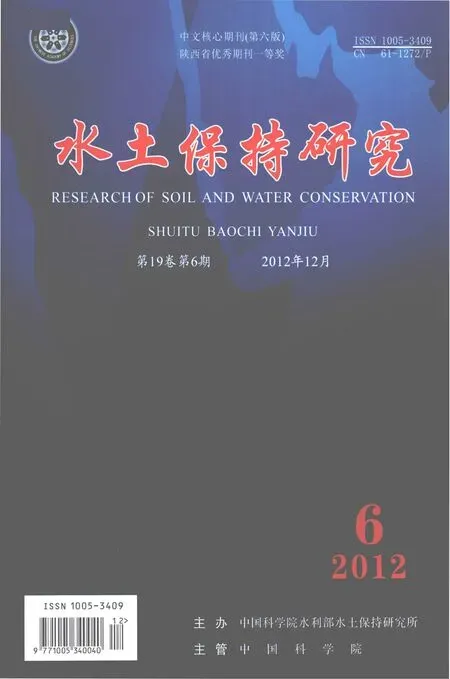基于STIRPAT模型的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社會經濟驅動力分析
郭雅雯,趙敏娟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楊凌712100)
20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口膨脹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人類對包括土地在內的生產資料需求急速增長。按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人類對土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不斷深入,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深入,土地利用變化與土地覆蓋變化愈發活躍[1]。在純粹市場力量的作用下,過多的耕地被轉為經濟收益較高的非農業用地。耕地的過多轉換,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上的壓力,也帶來了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環境問題:土地荒漠化蔓延、酸雨頻繁發生、臭氧層空洞。近年來,全球環境變化研究領域開始重視對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化(LUCC)的研究;其中,在眾多的土地利用類型中,耕地與建設用地的變化是研究熱點之一[2]。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發展中國家,耕地總面積僅占世界耕地面積的7%,但承載的人口卻占世界總人口的22%,人均耕地面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資源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農業技術進步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最主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中,通過運用不同的土地利用描述模型系統地分析耕地利用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并且全面概括分析了影響耕地面積變化的自然、社會、經濟因素。人類活動是影響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驅動力已經得到廣泛認識,但受到認識程度和技術手段的限制,在建立分析模型時難以成功地將社會經濟因子的驅動力貢獻加以定量分析和模擬。因此,加深耕地面積變化機制的研究可以提升對土地覆蓋變化規律的認識。但是,關于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驅動機制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研究區域尺度問題。中國目前土地利用變化研究以大尺度的宏觀研究和小尺度的微觀研究居多,而中等尺度的省域土地利用變化研究較少。二是社會經濟的驅動因子確定依據不足。在確定社會經濟驅動因子時沒有根據研究區域的特點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指標,使得分析結果流于形式,沒有新意。三是土地利用和各社會經濟因子之間以及各個社會經濟因子自身之間存在著各種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乃至相互制約的關系。因此,在定量地分析社會經濟驅動因子對于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時,如果不采取科學嚴謹的計量方法,容易面臨著數據的異方差性和多重共線性問題。
作為西北地區經濟相對較發達的一個省,2010年陜西省全年實現生產總值10 123.48億元,人均生產總值27 133元。這表明陜西省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階段。隨著陜西省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產業結構將進一步優化升級,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之間的矛盾將日益嚴重。陜西省耕地面積由1978年的385.36萬hm2減少到2010年的286.053萬hm2,年均減少3.009萬hm2。基于此,分析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規律,研究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驅動力,對于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實現陜西省區域耕地可持續利用,以及協調好陜西省耕地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運用土地利用變化的描述模型,利用1978—2010年相關耕地資源數據實證分析陜西省耕地現狀,揭示陜西省耕地變化的規律及趨勢,以此作為測算分析陜西省耕地與社會經濟驅動因子之間關系的基礎。然后,分析影響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和各個社會經濟主要影響因素與耕地的因果關系。在對本文研究的主要結論進行解釋和分析的基礎上,針對性提出提高陜西省耕地面積集約節約利用和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政策建議。
1 研究區概況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陜西省地處東經105°29′—115°15′,北緯31°42′—39°35′,屬內陸省份,南北長約1 000km,東西較窄約360km。全省縱跨黃河、長江兩大水系,黃河支流徑河、渭河在此注入黃河,中國鐵路大動脈隴海線橫穿中部,是“新亞歐大陸橋”亞洲段的中心和進入中國大西北的門戶。全省轄11個地級市,3個縣級市,國土總面積20.58萬km2。2010年陜西省耕地面積為286.053萬hm2,總人口38 738 725人,其中農業人口為25 516 043人,占總人口的65.9%。改革開放33a來,陜西省耕地面積總體呈逐步下降趨勢(圖1)。人均耕地面積在2001年之前呈現逐年遞減趨勢,直到2002年以來這一遞減趨勢有所緩解。結合耕地面積年遞減率情況來看,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程度在各個階段有所差異,但總體呈逐漸減少的趨勢(圖2)。

圖1 1978-2010年陜西省耕地、人均耕地面積變化趨勢

圖2 1978-2010年陜西省耕地面積遞減率
1.2 研究方法
基于《陜西六十年》和《陜西省統計年鑒》,以省為統計單位,對陜西省這33a引起耕地面積變化的耕地驅動力進行全面分析。具體方法為:(1)利用陜西省1978—2010年耕地面積統計數據分析其耕地面積變化的特點。(2)利用陜西省1978—2010年眾多社會經濟統計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篩選出影響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社會經濟影響因素。(3)運用逐步回歸法,去除存在多重共線性的社會經濟影響因素。(4)運用STIRPAT模型,分析陜西省耕地面積的變化與這些社會經濟因素的因果關系。
2 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驅動力分析
驅使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因素眾多,但是可以把引起耕地面積變化的影響因素歸結為兩類,即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在自然因素中,耕地面積變化的驅動力主要有氣候、土壤、水文及生態系統結構等;在社會經濟因素中,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主要有:技術進步、城鎮化、人口變化率、社會發展、收入差距、經濟增長、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價值觀念等[3]。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通過線性變換,將原來的多個指標組合成相互獨立的少數幾個能充分反映總體信息的指標,使用提取出的主成分代替原始變量,從而在不丟掉主要信息的前提下避開了變量間的共線性問題,便于進一步分析[4]。基于前人的研究以及陜西省自身經濟發展特點,本文選取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公路里程、社會消費品總額、城鎮人均收入、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市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第一產業職工所占比例、第一產業產值所占比重、第二三產業產值所占比重,這14項指標。將以上14個表征社會經濟對耕地面積變化產生明顯影響的驅動因子視為一個整體,這些因子共同作用,促使了陜西省耕地面積的變化。運用因子分析法,通過這些因子在新組合成的主成分中的荷載,評價其對土地利用變化影響的重要程度。
因子分析結果表明,第一、第二主成分累積貢獻率達到了95.154%,完全可以對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給出充分的解釋(表1)。根據貢獻率可以看出,第一個主成分的貢獻率遠遠大于第二個主成分的貢獻率,因此第一個主成分在本研究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它所含有的因子更能反映問題的實質,也即為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以前二個主成分為基礎,根據各主成分中各驅動因子荷載可分析其在相應主成分中的貢獻率(表2)。主成分載荷是主成分和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從表1可知,第一主成分對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貢獻率高達85.684%,是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影響因子。在第一主成分中,人均財政收入、城市固定資產投資、人均GDP、公路里程、社會消費品總額這5個驅動因子的荷載絕對值均在0.94以上,而這些因子主要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有關。因此,第一主成分可以被認為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發展水平的代表。1978年—2010年,陜西省人均GDP由0.029 1萬元增加到0.506 118萬元(以1978年的價格水平為標準),人均財政收入由0.007 11萬元,增加到0.089 95萬元(以1978年的價格水平為標準)。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由173 684萬元增長到15 234 993萬元(以1978年的價格水平為標準)。表明隨著陜西省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導致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用地需求不斷增加,引起了耕地面積的變化。在第二主成分中,只有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荷載絕對值大于0.8。因此,第二主成分可以概括為城市化水平主成分。1978—2010年,陜西省城鎮人口由454萬人增加到1 707萬人,城鎮化水平由16.3%增長到45.7%,表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鄉基礎設施水平不斷提高,促使陜西省耕地面積發生了變化。從分析結果來看,這些驅動因子都對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是影響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因素。

表1 因子特征值、主成分貢獻率、累積貢獻率

表2 旋轉后的公因子載荷矩陣
3 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STIRPAT模型分析
3.1 STIRPAT模型簡介
STIRPAT模型的前身是IPAT環境壓力等式即:I=PAT,其中I為環境壓力,P為人口數量,A為富裕度,T為技術[5]。此后,IPAT等式在實際應用中得到了不同的重構或擴展。其中Rose和Dietz將IPAT等式表示成隨機形式,即通過人口、富裕度和技術的隨機回歸分析各驅動力對環境壓力的影響,簡稱為STIRPAT模型,其形式通常如下:

式中:a——模型的系數;b,c,d——各驅動力指數;e——誤差。當a=b=c=d=e=1時,STIRPAT模型即為IPAT等式[6]。在實際應用中為測試人文因素對環境I的影響,通常將上式轉化為對數形式:

式中:f,g——方程(1)中a和e的對數。STIRPAT模型由于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對數變換,所以能較好地解決異方差性和多重共線性問題。并且能很好地解決實證分析中如何檢驗各驅動力變化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問題。在本論文中I為耕地面積,P,A,T等自變量為通過主成分分析方法后得出的影響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指標。
3.2 指標的選取
基于以上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驅動力的分析,在第一主成分中選取驅動因子的荷載絕對值均在0.94以上的驅動因子(表2),它們分別是人均財政收入、城市固定資產投資、人均GDP、公路里程和社會消費品總額。在第二主成分中選取驅動因子的荷載絕對值在0.8以上的驅動因子,它是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雖然通過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得出的驅動因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這些驅動因子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存在著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本文通過SPSS軟件,運用逐步回歸法,從這6個因子中篩選出社會消費品總額、市鎮人口占總人口數、公路里程和人均GDP。
3.3 模型結果與分析
3.3.1 模型結果 模型的數據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在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中,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分析一般面臨著數據的異方差性問題。由于采用STIRPAT模型時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對數變換,誤差項反映的是一種相對誤差,而相對誤差往往具有同方差性,因此采用STIRPAT模型本身能較好的解決模型的異方差性[7]。將式(2)利用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各項參數見表3。
從表中可以看出,模型Ⅰ的擬合優度達到了97.9%,且所選的指標系數均在0.05水平顯著不為0,方程擬合效果較好,說明模型Ⅰ能較好地解釋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模型Ⅰ的具體形式為:

式中:Y——耕地面積(103hm2);X1——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X2——人均 GDP(萬元);X3——公路里程(km);X4——社會消費品總額(萬元)。

表3 STIRPAT模型估計結果
3.3.2 模型分析 從模型Ⅰ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城鎮化率每提高1%,將引起耕地面積增長0.060 054%。意味著陜西省城鎮化率對于抑制耕地面積的減少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研究結果與王琳[7]、李春華[8]、王曉軒[9]的研究結果相似。可能的解釋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從而增加了耕地面積。此外,從模型Ⅰ的估計結果還可以看出,公路里程每增加1%,將導致耕地面積增加0.112 851%。這與設想的公路里程的增加將導致耕地面積減少的假設相矛盾。可能的解釋是從單位用地面積形成的路網通行能力看,近年來陜西省隨著公路網等級的不斷提升,結構趨向合理,以相對較少的占地,大幅提升了路網通行能力,促進了公路用地的集約化。此外,陜西地處西部內陸,地形復雜多變,土地利用程度低,農業用地受交通制約性大。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擴大了農產品市場流通范圍,降低了農產品的生產流通成本,使得農業經營主體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從而提高了土地的墾殖率。
人均GDP對于耕地面積的變化影響較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均生產總值每提高1%,耕地面積減少0.112 971%。自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省人均GDP由1978年的291元增加到2010年的5 061元(以1978年的價格水平為標準),增長了17倍。可能的解釋是經濟的增長,促使基礎設施的建設不斷發展和完善,重點建設項目增加,投資增多,工業園區等建設用地的擴展大量侵占了耕地。社會消費品總額每增加1%,會導致耕地面積減少0.096 816%。這一研究結果與李景剛[10]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這說明,自改革開放以來,陜西人民的消費結構不斷發生著變化,人們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更加追求生活質量,從而導致非農用地需求的增加。同時,受比較利益的驅動,農民不斷地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將更多的耕地改造成了經濟效益較高的果園等園地面積,改變了農業用地內部結構,造成了陜西省耕地面積的減少。
4 結論
(1)本文在研究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與各個社會經濟因素的關系時,將用于環境領域研究的STIRPAT模型進一步拓展并運用其中。通過陜西省的實證研究,發現STIRPAT模型能較好地擬合耕地面積與社會經濟指標之間的關系。反映了城鎮化率、人均生產總值,交通,社會消費總額對于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的影響。
(2)根據擬合出的STIRPAT模型以及相關分析,可知陜西省1978—2010年間,人均生產總值和交通對于耕地面積的變化影響較大。其中,人均生產總值的提高,是以犧牲耕地面積為代價的。而公路里程數的不斷增加,致使陜西省農業生產條件進一步完善,間接促進了陜西省農業發展。城市化率的提高對于抑制陜西省耕地面積的減少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導致非農用地需求增長。同時,農業用地內部結構的改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耕地面積的變化。
隨著陜西省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的加快,產業結構將優化升級,土地的稀缺性與經濟發展占用耕地的現象日益嚴重,在這個時期對于陜西省耕地的變化及其社會經濟驅動力分析是深入研究陜西省耕地面積變化規律,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的前提。研究表明,陜西省在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的同時應繼續加強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在不占用耕地的情況下,不斷地完善交通設施及其配套工程,更好地促進陜西省農業發展。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而提高土地集約節約利用程度。
[1] 楊李娜.咸陽市土地利用變化的動態分析及驅動力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09.
[2] 鄭海霞.發達地區建設用地的時空擴展及其驅動力實證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7.
[3] 白利妮.貴州典型喀斯特地區不同尺度土地利用變化的驅動力研究[D].貴陽:貴州師范大學,2004.
[4] 謝菲,舒曉波,廖富強,等.浮梁縣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2):213-217.
[5] Chertow M R.The IPAT equation and its variants:changing views of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0,4(4):13-30.
[6] Rosa E A,York R,Dietz T.Tracking the anthropogenic drivers of ecological impacts[J].AMBIO,2004,33(8):509-512.
[7] 王琳,吳業,楊貴山,等.基于STIRPAT模型的耕地面積變化及其影響因素[J]農業工程學報,2008,24(12):196-199.
[8] 李春華,李寧,石岳.基于STIRPAT模型的長沙市耕地面積變化驅動因素分析[J].農學通報,2010,26(3):258-263.
[9] 王曉軒,夏麗華,鄧珊珊,等.基于STIRPAT模型的廣州市耕地變化社會經濟驅動力分析[J]中國農學通報,2010,26(20):339-343.
[10] 李景剛,何春陽,史培軍,等.近20年中國北方13省的耕地變化與驅動力[J].地理學報,2004,59(2):274-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