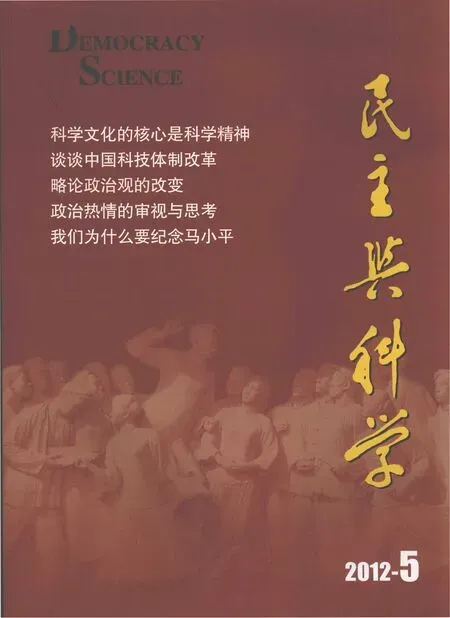建筑大師的悲喜人生
■湯壽根
建筑大師的悲喜人生
■湯壽根
有一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建筑大師梁思成。他曾說過:“建筑是一本石頭的史書,它忠實地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
他懷著對祖國母親深沉的愛,為解讀中華古代建筑藝術的奧秘,曾歷經坎坷而終身不渝;雖身陷罹難但至死無悔,釀成了他可歌可泣的悲喜人生!
梁思成是中國古代建筑歷史與理論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研究出版了我國第一本以現代科學觀點和方法總結中國古代建筑構造做法的讀物《清式營造則例》;他編寫了我國第一本《中國建筑史》;他撰寫了我國第一本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筑史》,使中國建筑在國際上閃耀著燦爛的輝光;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建筑系;他和愛侶林徽因發現并考察了中國現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筑——山西五臺山佛光寺……
喜逢佛光寺
日本人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筑,要觀光唐建木構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梁思成卻始終有一個信念,國內肯定會存在有關的建筑物。《敦煌石窟圖錄》給了他啟示。他發現第61號窟的宋代壁畫“五臺山圖”中繪有大佛光之寺;后來,他在北京清涼山寺找到了有關大佛光寺的記載。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剛從西安返京,立即與同事們結伴奔赴五臺山,探尋大佛光寺。
佛光寺大殿魁偉整飭,從建筑形制特點判斷,超長的屋檐、碩大的斗拱、柱頭的卷剎、門窗的形式處處可以證明是唐代建筑。他倆判斷這座建筑絕不晚于宋代。寬廣的大殿內,在一個大平臺上有一尊高大的菩薩坐像,侍者環立,有如仙林,而平臺左端,卻坐著一位真人大小的便裝女人。在仙人群中,她顯得渺小與猥瑣。和尚們說,這是篡位的武后。為取得確鑿的年代證據,林徽因爬到殿頂探視。藻井內黑暗無光,梁檁上盤踞著千百成群的蝙蝠、木材中聚集著上千成萬只臭蟲,穢氣撲鼻、奇癢難耐。素愛整潔的她,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終于發現在大殿梁下寫有“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字樣。費了三天時間,讀完隱藏在四條梁下的題詞全文;然后和殿外臺階前,經幢石柱上刻文對照,證明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這次考察的結果,與以前發現的最古老木結構建筑比較,還要早一百二十七年。
于是,他們明白了:那位身著便裝、謙恭地坐在平臺一側的女人,并非是和尚們所說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寧公遇本人。寧公遇是古代出資建殿的女施主,林徽因是發現她的現代女建筑家。古今兩位名垂青史的女性相逢于佛光寺,豈非天意!
佛光寺是我國自己發現的第一座唐代建筑。他們察看、照相、測繪,詳盡記錄了整個建筑群。粱思成和林徽因沉浸在狂喜之中。此時此刻,或許是他倆一生中最為歡樂、幸福的時光!
在流亡中成為宗師
苦難的人生啊!為什么歡樂總是那么短暫?正當他們離開五臺山到代縣休整時,從太原帶過來的報紙上赫然在目的是“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點”,戰爭爆發已有一周。七七事變——1937年7月7日,這個刻骨銘心的日子是中國人民的苦難之日、恥辱之日。此后,等待著他倆的日子是:流亡、貧困、疾病……林徽因的肺病一再發作;梁思成的腰背日益佝僂,但他們從未放棄過考察、研究、撰寫。梁思成堅信唐詩中所說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日子即將到來。
梁思成帶著家人取道天津、長沙,于1938年1月抵達昆明。在昆明,他們建立了中國營造學社,并在西南地區對中國古建筑進行調查。他們的研究經費,過去主要依靠外國的基金會贊助。抗戰后資金來源受到很大影響。梁思成夫婦在貧病交迫的困境下堅持工作,并整理、刊出了學術論文。
1940年冬,營造學社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這里的氣候潮濕,冬季陰冷、夏季酷熱;兩間竹篾抹泥為墻的陋室,蛇鼠出沒于頂棚、臭蟲橫行于枕席。不久,林徽因結核病復發,病勢兇險、臥床不起。李莊無任何醫療條件,梁思成只能兼做護士,打針、喂藥。眼見妻子在痛苦中掙扎,他從心底里呼喊著:“神啊!假如你真的存在,請把我的生命給她吧!”只要病情有所好轉,林徽因就硬撐著讀書做筆記,幫助丈夫做撰寫《中國建筑史》的準備工作。她睡的小小行軍帆布床周圍,堆滿了中外書籍。
1944年,《中國古代建筑史》終于誕生了。這部著作總結了中國古代建筑發展的歷史、規律和特點,并與西方建筑比較,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其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梁思成衰老了,林徽因也難以康復了。醫生悄悄告訴他,林徽因將不久于人世。國外的朋友力勸他們接受美國一些大學和博物館的邀請,去美國工作和治病。梁思成復信說:“我的祖國在苦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他倆是用生命的光與熱譜寫了祖國的建筑史!
梁思成曾說:“如果我從李白、杜甫、岳飛、文天祥這些偉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繼承了愛國主義思想,而徽因除此以外,比我更多地從拜倫、盧梭等偉大的詩人、哲學家那里學習了反侵略、反壓迫的精神。她對祖國的愛,是懷著詩人般的浪漫主義色彩的。”
1946年10月,梁思成受邀到耶魯大學講學;其間,又完成《中國雕塑史》的撰寫,把中華文化的瑰寶展示在國際學術界面前。梁思成的調查研究、分析、總結,使過去處于混沌狀態的中國古代建筑,清洗了蒙塵,顯露了它故有的風采。為此,美國東亞問題專家,曾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的費正清,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在我們心目中,他是不怕困難、獻身于事業的崇高典范”,“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做出了寶貴的貢獻”。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他的《中國科技發展史》中,多處引用梁思成的著作。他稱梁思成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的宗師。
梁思成雖然從1930年到1945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建筑史的研究上,但他的視野從沒有局限于古建筑的研究。他始終關注我國新建筑的創作及城市規劃與自然環境關系這一新學科的進展。這是他與我國其他建筑史學家的不同之處。
輝煌與悲壯
1948年,國民黨動員北京的大學教授去臺灣,梁思成堅持留下等待解放。年底,清華園先解放了。梁思成連夜把北京城重要的古建筑標志在地圖上,由中央發給準備攻城的解放軍。后來,傅作義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條件,北京城內的古建筑得以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梁思成的頭上也曾有過不少耀眼的光環……
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前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建筑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和建筑研究所所長。
他與林徽因也曾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過不少卓越的奉獻……
梁思成擔任過中央直屬修建處(建筑工程部前身)顧問;他主持了人民英雄記念碑的設計工作;他與林徽因主持了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他主持設計了在揚州的鑒真和尚紀念堂,這一仿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唐代式樣建筑,獲得全國優秀建筑設計一等獎;他在清華大學創建了建筑系,培養了一大批全國知名的建筑師,他的不少學生主持了全國著名的建筑設計,如1959年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他領導的科學研究集體,因為在“中國古代建筑理論和文物建筑保護”這個領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林徽因在肺部布滿空洞,切除一側腎臟,結核桿菌腎腸轉移的身體狀況下,以驚人的毅力與助手們一起研究設計出適合景泰藍生產工藝的造型、圖案和配色,拯救了瀕于停業的民族工業。當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烏蘭諾娃接過林徽因設計的景泰藍禮品時,高興地說:“這是代表新中國的新禮品,真是美極了!”
林徽因是半臥在床上,伏在一張特制的小桌上,完成這些設計工作的。那時她一天只吃二兩飯、睡眠四五個小時。她是在與生命進行競賽啊!今天,我們仰望著莊嚴的國徽、觀賞著艷麗的景泰藍,人們也許不會想到給她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但是,這位堅強的纖美的女性卻同樣以生命為代價,喚起了炎黃子孫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4月,林徽因告別了塵世,享年51歲。
在新政權下,由于梁思成身上存在的兩個特點,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決定了他將從不斷的磨難中走向劫難……直到生命的盡頭。他和林徽因一樣,沒能等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一、梁思成的專長是建筑藝術,涉及意識形態,在以階級斗爭為綱、高度集權的年代里,缺乏他生存的空間……
二、梁思成是一位剛直不阿的科學家。在他身上體現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知識越多越反動”、“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歲月里,注定了他苦難的人生……
建國伊始,毛澤東主席曾對彭真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梁思成卻上書大聲疾呼,北京城的建筑規模、文化藝術價值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能從消費城市轉化為生產城市。他總結了歐洲城市建設發展的經驗,聯合有關人士向中央多次提出保護老北京,另辟新區建設新北京,作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區域的方案,這樣既能保護古城原貌,又可適應首都的種種需要。他認為保護不是原封不動擱置,而是在不傷原貌的情況下,加以改造。如北京的古城墻可以改造成“10米或更寬的”空間,變為有花圃和園藝的永久性公園;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護城河及兩岸空地可以建成綠色地帶,供人們垂釣、劃船等娛樂。他認為北京的城墻是民族的珍寶、世界的“項鏈”。
但是,這個方案沒有被最高領導賞識,并遭到蘇聯專家的反對。蘇聯專家認為,北京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應當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大城市,建議政府中心設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及東西長安街。為了北京的規劃,梁思成竟然和彭真爭得面紅耳赤。他對彭真說:“在政治上你比我先進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進五十年。”
于是,梁思成的方案被指責為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與毛主席“一邊倒”方針背道而馳。
于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對“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筑思想”的批判運動,開了以運動方式來處理學術問題的先例。
20世紀50年代,北京城在建設發展中把城墻、牌樓、塔樓、碉樓大部分拆除了,護城河消失了。在北海大橋的擴建中,還計劃把團城拆毀。梁思成惱火了,找了周恩來總理,經過總理與梁思成等人的現場勘查,才把團城保留了下來。
事后,梁思成說:“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規劃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據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不幸而言中。不僅如此,正如陳志華在《我國文物建筑和歷史地段保護的先驅》中所言,“個人的記憶是不足道的。但是,民族的記憶不能沒有實在的見證,民族的感情不能沒有實在的依托。這種記憶和感情,同樣牽連著民族的命運。對這種見證和依托的需要,就是文物建筑保護的根據”。
1955年,梁思成多年來不懈地為黨工作和在他看來是同失誤的斗爭把他帶到了衰竭的邊緣。他心力交瘁,住院時發現染上了肺結核。
1964年,世界各國建筑學者會聚意大利威尼斯,研究城市發展與古城保護問題,提出老城與新城不要混在一起,這就是有名的“威尼斯憲章”。這些原則實際上梁思成在30年代就提出來了。有人說梁思成保護古建筑的主張是“向后看”,實際上他是向前看,而且很有預見性。
以后,等待著梁思成的是不斷的苦難……在反右擴大化時,他曾受到沖擊;在經濟困難時期,他也過著艱苦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判、斗爭。但這些磨難并沒有改變他對祖國的忠誠。他一心盼望臺灣回歸祖國大家庭,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臨終的日子里,他曾含淚動情地背誦陸游的詩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966年,暗無天日、顛倒黑白的“十年文革”浩劫開始了。清華園建筑系館門口,貼出了醒目的大字報“揪出黑市委藤上的大黑瓜梁思成!”“梁思成是彭真的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
建筑大師梁思成,佝僂著瘦小、憔悴、病弱的身子,頭上戴著和身體等長的高帽,胸前掛著沉重的“反動學術權威”的大黑牌,目光里透露出強烈的屈辱與羞愧,蹣跚著、蹌踉著,被紅衛兵推來搡去,經歷了無數次殘酷的批斗、游街,無數次的“交待罪行”、“寫檢查”。
在如此慘無人道的折磨中,梁思成卻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我所唯一可奉獻給祖國的只有我的知識,所以我毫無保留地將我的全部知識獻給中國未來的主人——我的學生。沒想到因此我反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罪人。”“如果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斗爭,被‘踏上千萬只腳’,只要因此我們的國家前進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國外去?不!既然祖國都不需要我了,我還有什么生活的愿望?還有什么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愿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去!
讓梁思成最傷心的是,他等待著心愛的學生來和他研究討論,“什么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建筑學’”?然而,沒有一人登門。
當紅衛兵勒令梁思成轉移到系館去隔離審查時,他輕輕地仿佛自言自語地對陪伴他共同經歷劫難歲月的林洙說:“……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林洙強抑著淚水,當著門口虎視眈眈的紅衛兵面前,為了鼓勵他,念了一首毛澤東詩詞:“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在血色迷離的殘陽中,梁思成走向了人生的終點!他是帶著苦惱走的。因為,雖然他懷著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苦苦求索“無產階級建筑學”的答案,但是他至死也沒有明白,這門社會主義革命的技術科學究竟是什么樣的?!他只有無奈地哀嘆:“如果再讓我重頭學一遍建筑,也許還會有這樣的結論。”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