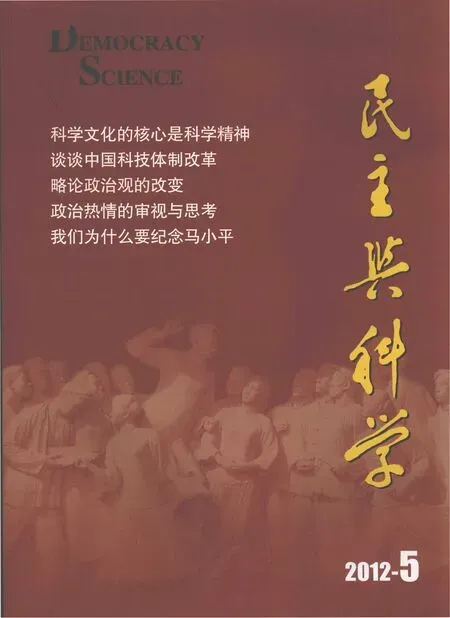生活永遠大于政治
■周國平
生活永遠大于政治
■周國平
前一陣,梁曉聲的電視劇《知青》在網上大招非議,我不看電視,不了解詳情。但我料想,至少有一部分非議是出自把生活縮減為政治的邏輯。我在1997年寫《小說的智慧》一文,內容是讀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的感想,其中第七節《生活永遠大于政治》就是批評這種邏輯的。直到今天,這種邏輯仍甚囂塵上。在許多人看來,毛時代只有政治,沒有生活,因此,當你回憶或描寫那個時代的某一段生活(例如延安時期、“文革”時期、知青生活)時,你只能或者控訴,或者懺悔。倘若你對當時的生活場景和內心體驗有任何正面的敘述,你就是在美化當時的政治,就是站到了人民公敵的立場上。這些人完全無法懂得,生活永遠大于政治,哪怕在專制政治下,生活仍有政治無法取代的內容,哪怕遭到了政治的壓抑或扭曲,青春歲月仍是個人的美好記憶和心靈財富。在我看來,專制政治的最大罪惡是企圖用政治完全取代乃至取消生活,雖然它事實上做不到。就此而言,這些人的思想方式不但是和專制政治一脈相承的,而且竟然要把它貫徹到底,在記憶中也取消生活,只剩下政治。現把《生活永遠大于政治》重刊如下,以期引起思考。
一
對于諸如“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流亡文學”之類的概念,我始終抱懷疑的態度。我不相信可以按照任何政治標準來給文學分類,不管充當標準的是作品產生的政治時期、作者的政治身份還是題材的政治內涵。我甚至懷疑這種按照政治標準歸類的東西是否屬于文學,因為真正的文學必定是藝術,而藝術在本質上是非政治的,是不可能從政治上加以界定的。
作家作為社會的一員,當然可以關心政治,參與政治活動。但是,當他寫作時,他就應當如海明威所說,像吉卜賽人,是一個同任何政治勢力沒有關系的局外人。他誠然也可以描寫政治,但他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上這樣做的。小說不對任何一種政治作政治辯護或政治批判,它的批判永遠是存在性質的。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被昆德拉稱作“一部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因為它把生活縮減為政治,在昆德拉看來,這種縮減本身正是專制精神。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不論站在何種立場上把生活縮減為政治,都會導致取消文學的獨立性,把文學變成政治的工具。
把生活縮減為政治——這是一種極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普遍的程度遠超出人們自己的想象。我們曾經有過“突出政治”的年代,那個年代似乎很遙遠了,但許多人并未真正從那個年代里走出。在這些人的記憶中,那個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運動,剩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蘇聯和東歐解體以后,那里的人們紛紛把在原體制下度過的歲月稱作“失去的四十年”。在我們這里,類似的論調早已不脛而走。一個人倘若自己不對“突出政治”認同,他就一定會發現,在任何政治體制下,生活總有政治無法取代的內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表明,甚至苦役犯也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在受刑。凡是因為一種政治制度而叫喊“失去”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種思考和體驗生活的能力,我們可以斷定,即使政治制度改變,他也不能重獲他注定要失去的生活。我們有權要求一個作家在任何政治環境中始終擁有上述那種看生活的能力,因為這正是他有資格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理由。
二
彼得堡恢復原名時,一個左派女人興高采烈地大叫:“不再有列寧格勒了!”這叫聲傳到了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厭惡。我很能理解這種厭惡之情。我進大學時,正值中蘇論戰,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們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傾聽反修社論,為每一句鏗鏘有力的戰斗言辭鼓掌喝彩。當時我就想,如果中蘇的角色互換,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反教條主義社論,這些人同樣也會鼓掌喝彩。事實上,往往是同樣的人們先則熱烈祝福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繼而又為這個“賣國賊”的橫死大聲歡呼。全盤否定毛澤東的人,多半是當年“誓死捍衛”的斗士。昨天還在鼓吹西化的人,今天已經要用儒學一統天下了。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真正的原因不在受蒙蔽,也不在所謂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而在一種永遠追隨時代精神的激情。昆德拉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其中支配著的是一種“審判的精神”,即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的判決來改變觀點。更深一步說,則在于個人的非個人性,始終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內心生活和存在體悟。
昆德拉對于馬雅可夫斯基毫無好感,指出后者的革命抒情是專制恐怖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當審判的精神在今天全盤抹殺這位革命詩人時,昆德拉卻懷念起馬雅可夫斯基的愛情詩和他的奇特的比喻了。“道路在霧中”——這是昆德拉用來反對審判精神的偉大命題。每個人都在霧中行走,看不清自己將走向何方。在后人看來,前人走過的路似乎是清楚的,其實前人當時也是在霧中行走。“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屬于人的永恒境遇。看不見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霧,就是忘記了什么是人,忘記了我們自己是什么”。在我看來,昆德拉的這個命題是站在存在的立場上分析政治現象的一個典范。然而,審判的精神源遠流長,持續不息。昆德拉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我們世紀最美的花朵——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藝術——先后遭到了三次審判,納粹譴責它是“頹廢藝術”,前蘇聯政權批評它“脫離人民”,凱旋的資本主義又譏它為“革命幻想”。把一個人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縮減為他的政治表現,把被告的生平縮減為犯罪錄,我們對于這種思路也是多么駕輕就熟。我們曾經如此判決了胡適、梁實秋、周作人等人,而現在,由于魯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時代受過的重視,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把他們送上審判革命的被告席。那些沒有文學素養的所謂文學批評家同時也是一些政治上的一孔之見者和偏執狂,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曾經歸附過納粹的人怎么還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而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又如何可以與他所卷入的政治無關并且擁有更長久的生命。甚至列寧也懂得一切偉大作家的創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場的限制,可是這班自命反專制主義的法官又已經在審判列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