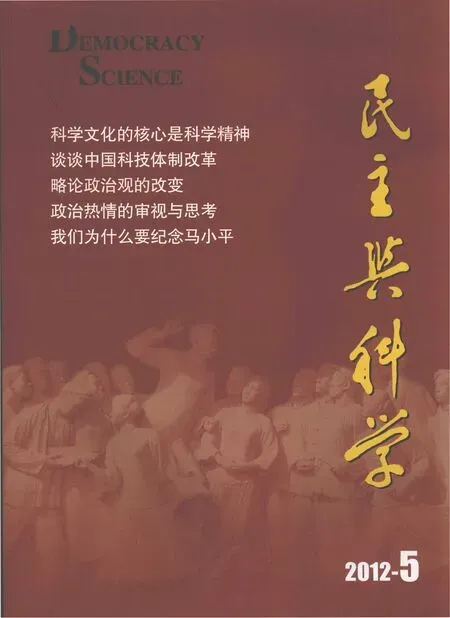警惕沉睡野獸的喚醒者
——現代宗教和神秘主義對科學的批判和否定
■孫紅霞
警惕沉睡野獸的喚醒者
——現代宗教和神秘主義對科學的批判和否定
■孫紅霞
中世紀時期,宗教無情打壓和迫害包括自然哲學在內的異教。伴隨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和發展壯大,這種打壓和迫害也隨之猛烈。19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國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公開攻擊科學理性和建制的“奇跡信仰”,并且廣泛滲透到公眾中。一戰后,被戰爭摧毀了物質和精神家園的人們開始向非理性世界尋求拯救。他們不得不再次面對在100年前曾在歐洲一度風行的反理性主義,以及“揭示宇宙謎團”的非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因此,造成當時占星術等各類超自然信仰肆意流行。除此外,繼承近代神秘主義思想的有神論者開始宣揚宗教和神秘主義拯救的意義,對科學理性、認知模式和方法展開批判和否定。這些來自宗教和神秘主義的激進批判和否定威脅和阻礙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發展。
現代宗教對科學的批判和否定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在一些教堂的圣冥中回蕩著批判和否定科學的微弱余韻。直至1920年代,這些隱蔽多年的余韻開始聚集、膨脹。像荷蘭神學家、宗教學家萊烏曾隱曲地說道,在神秘的入迷狀態下是體驗不到任何可作為客體的東西的,主體與客體融合在一起。天主教哲學家馬里坦直接向科學發動攻勢,他斷言:“科學帶來了‘否定永恒真理和絕對價值’的‘致命的疾病’。”諸如此類的批判和否定層出不窮。其中,以個體形式批判和否定科學的宗教言論對科學本身發展雖然沒有產生根本的破壞作用,但是,卻為敵視和顛覆科學找到了借口。然而,以群體形式批判和否定科學的宗教行為,不僅形成了一定規模和群眾基礎,而且阻礙著科學本身發展的進程,這是需要我們嚴加防范和警惕的。
萊維特與格羅斯告訴我們,恐懼科學、批判和否定科學的直系后裔可以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特別是各種各樣的創世論團體中找到。創世論者主要是以福音派和世紀末分離主義為代表,主張人文、生命和宇宙是超自然作用創造的結果,拒絕任何與其信仰相違背的科學結論。在1922年,美國的反進化論運動提出口號,“把達爾文主義驅逐出學校”。這場運動橫掃了美國各個角落。創世論成為了科學解釋的“標準替代品”,在反進化論者看來,真正的教育是圍繞創世論開展的,不是圍繞進化論而建構的。當年3月,美國田納西州頒布法令,禁止在課堂上講授進化論。標志這場反進化論運動達到頂點的事件是1925年5月5日發生在田納西州的斯科普斯審判(Scopes Trial)。一個名為斯科普斯的高中教師有意違反禁止講授進化論的法律,在課堂上講授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因此遭到政府的傳喚和審判。從科學史角度看,這個事件的作用不遜于1860年發生在牛津的主教威爾伯福斯和赫胥黎之間的辯論,開啟了反進化論運動序幕。反進化論運動的影響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其間,一小撮創世論者還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宗教和科學協會”,其目的是創立一個反對進化論的統一前沿陣線。雖然,1967~1970年,反進化論法在田納西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被廢除,然而,1972年9月對田納西州代頓的一所高校的調查表明:75%的學生相信《創世紀》中的記載,而不相信生物進化論。德克薩斯州教育理事會要求各種講述進化論的教科書要在前言里做一聲明,提醒人們注意進化論只是一種理論,而不是一種事實。《華盛頓星報》的主編在華盛頓特區提出訴訟,要求在生物教科書中寫上圣經中的創世故事。因此,創世論反對科學的言論和主張在教育中的泛濫極大阻礙了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健康發展。
那么,反進化論者怎樣從其所謂的“理論上”批判和否定以進化論為代表的科學呢?在1974年,創世研究會的創始人莫里斯出版了《科學創世論》一書,目的是將“新的生命活力”注入反進化論的創世論運動。他在書中貶低進化論,抬高創世論的地位。他批判進化論僅僅是將多種學科——像物理學和古生物學——的觀察聯系起來的模型。在他看來,“六天創世模型”比進化論模型能夠聯系更多的事實,可以被“實驗驗證”,這個六天創世模型將是可以被信任的。他欺騙人們說,只要信仰它是真的,那么它便是真的。不僅如此,莫里斯還認為人和世界不是進化過程的產物,而是神的特殊創造。他將符合科學的標準和原則直接嫁接到基督教上,并認為基督教是以客觀事實,而不是以主觀壓制為基礎,基督教中的創造、跌落、拯救和復活事實具有有效性,服從于客觀探究的一般標準。他對進化論的極盡歪曲,以及對創世論的極度褒揚誤導了人們對科學的理解,在社會中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宗教創世論對科學批判和否定究其原因為:他們面對科學的迅猛發展,出于自身利益的維護而和科學抗衡。早在詹姆斯·穆爾的題為“新教原教旨主義的神創宇宙”一文中就指出了這個預兆:世紀末的原教旨主義同“占統治地位的進化啟蒙的假設”在一場文化戰爭中將會彼此對抗。但其無力與科學進行角逐,于是將自己粉飾成科學,披上科學的外衣,行惡劣的欺騙行為,這是應該引起我們警惕的。
作為原教旨主義的一個分支——創世論者認為自己的主張和科學的主張一樣具有同等的解釋事實的權威性,甚至給進化論貼上偽科學的標簽。他們從不承認自己反科學,并一再強調他們反對的不是科學,而是沒有被證明的進化論,在他們看來,進化論沒有揭開“進化的實際模型和過程”。創世論對進化論的批判和否定主要集中在生物機體、思想和地質史的進化、太陽系的形成和宇宙的起源問題上。其中嚴格創世論者相信,進化不能夠描述地球上生命的歷史、多樣性和復雜性。例如他們斷言,化石記錄在遠祖和后裔之間缺乏過渡形式。例如放射性同位素衰變率在過去是不同的,如若衰變率比現在快的話,那么就會誤導古代日期的計算。他們認為進化論者只是簡單地主觀接受他們預想的結果,而拋棄其余結果。創世論者拒絕科學家的理論和研究過程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是因為進化論不能符合證據問題。實際上,后來該問題由間斷平衡論所解決。二是因為科學無法解決心靈、情感等問題。在羅特看來,創世論等能夠很輕易地為人類的生死問題提供答案,而科學中那些抽象的理論無法感動凡人的心靈或激發愿望。如果這個原因成立的話,那么,不僅會誤解科學與創世論之間存在的界限,而且勢必抹煞科學在未來發展中對人類心靈世界的關切和介入。然而,人類心靈、情感等問題是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隨著各門科學不斷發展,這個問題必然會在未來得到解決,所以創世論者否定科學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現代神秘主義對科學的批判和否定
從人類誕生開始,神秘主義對科學的前身,即自然知識和自然哲學的批判就出現了。從古代的樸素神秘主義開始,一直影響至今。古代樸素神秘主義懷疑理智的、本體論的思辨,批判面向自然的探索活動。中世紀時期,異端神秘主義教派諾斯替教將古代自然哲學理論綜合到自己的神秘體系中,主張通過體驗對象,并與對象同一的方式獲得真理。從本質上講,這是一種與科學認知模式相對立的神秘主義認知模式。中世紀時期的神秘主義上升為一種非理性主義哲學,主張人們可通過內在的神秘啟示來直接與上帝相通,不需要教會作中介。它鮮明反對人的理性認識和邏輯思維。在近代,神秘主義與浪漫主義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施密特甚至將浪漫主義看作神秘主義的同義詞。自盧梭以來,神秘與浪漫共同表現為一種人的自然天性的內在脈動,這是一種決定著人類行為的普遍因素以及與自我保存的欲望的要素。這些要素促使浪漫主義作家、文學家和詩人倡導“回歸自然”,批判和摒棄科學理性方法。現代神秘主義大部分都產生于1890年代至1970年間。現代神秘主義來源于19世紀的浪漫主義作家、文學家和詩人,并逐漸外溢到19世紀中葉科學家群體內部。當時,古老的巫術復活了,出現了各種催眠術、降神術、通靈術、唯靈論,神秘學也開始復興起來。
從德國到英國,從歐洲到新大陸,在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都在經歷著一場“神秘主義復興”運動。在當時,這一現象被恩格斯捕捉到了,并且反映在他的《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一文中。例如他描寫了華萊士在邁斯麥爾催眠術講演基礎上做催眠術實驗,以及發現了化學元素鉈和輻射計的威廉·克魯克斯先生使用許多物理儀器著迷地研究降神現象。在恩格斯看來,這些現象都是由于錯誤的思維導致的。而這些錯誤的思維一旦貫徹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科學理性道路相反的地方去,即神秘主義。所以,這是輕視辯證法必然導致的后果。
神秘主義思想家的主張與宗教創世論者的主張如出一轍。他們主張確實性的源泉位于內在的經驗、感情和本能中,并武斷地認為最高級的真理是不能被證明的,而只能去感受。他們視信仰、感情和本能是認識較高級的階段。在他們強調,凡是有限理性不能探究的,可以在宗教、審美或道德的感悟中感受或預測到,思辨的理性不能深入到實在的帷幕,而真理由感情、信仰或某種神秘的洞見所產生。這樣的言論有失偏頗,因為即使有限理性不能探究到的,宗教、審美或道德的感悟也不一定能夠探究到。他們批判和否定理性思維和實在,推崇信仰思維和心靈。正如小西奧多·希克、劉易斯·沃思在《新時代的信仰的總結》中刻畫了神秘主義者批判和否定科學的激進主張,即“在我們通常獲取知識的方式之外,還存在其它精神的、神秘的、內在的、更高級的認識事物的方式。如果某種體驗你覺得是真實的,那么它就是真實的。如果一種思想你認為是正確的,那么它就是正確的。我們無法獲得任何關于世界真實本質的認識。科學本身是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它只不過是另一種信仰或信念的體系,或者是一種神話,沒有更多的可證實性”。這種激進主張對科學的批判和否定一方面表現為,將心靈的直覺、感受和體驗捧到天堂,將科學理性、邏輯打入地獄;另一方面表現為,顛倒黑白,模糊科學與神話之間的界域,因而暴露出其對科學本質的歪曲。大浪淘沙,神秘主義的荒唐論調必然被歷史所淘汰。
現代激進宗教和神秘主義不僅是成熟文化的異己力量,而且還是社會動蕩的根源之一。當神秘主義滲透到不同思想領域的時候,它常常表現為與當時的主流文化、制度性宗教和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性質。因此,我們應該深入現代宗教和神秘主義內部考察和發掘其產生和發展的規律和機制,才能有效地遏制它們導致的嚴重危害。另外,面對現代宗教和神秘主義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趨勢和現實,霍耳頓已經嚴正告誡過要警惕這種危險的結合,因為它們將變成“沉睡野獸的喚醒者”。
當前在我國,對內改革步伐矯健,對外開放縱深發展,科學技術飛速前進。然而,此時我們不僅要防范和抵制本土激進宗教和神秘主義對我國民眾思想的侵蝕和破壞,而且還要警惕來自國外極端宗教和神秘主義的消極影響。歷史已經證明,一旦它們與個人、集團利益價值傾向或者意識形態相結合,將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
(作者單位:中國科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