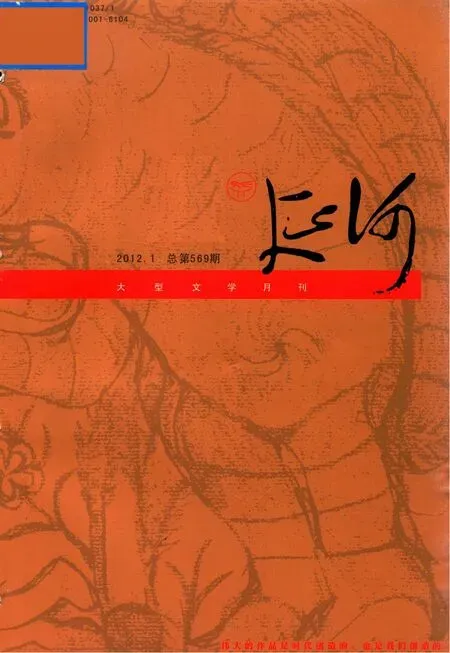首席記者
高永科
一
當了二十年機關報編輯的周成,突然向總編提出他想去記者部當記者而不愿再當編輯的要求。總編摘下架在鼻梁上的簡易花鏡,兩眼直勾勾地把坐在辦公桌對面的周成看了足足有一分鐘。周成被看得有些發毛,就說:“看你這老同學,‘婆娘抓(生)娃暮暮囊囊’的,這滿是皺褶的老臉有啥看頭哩!”
總編“撲哧”一下笑了起來。周成茫然地問:“笑什么笑嘛,就是換個辦公室換個椅子而已,有啥可笑的哩。”
總編邊笑邊說:“我是想起了你那個‘妹浪’來了……哈哈……”
周成不以為然地說:“不就是普通話說得不好么,這有啥可笑的嘛。再者說了,我現在可是小有名氣的老新聞工作者了,普通話不普通話的,不是照樣把工作做得很好嘛,難道不是?”
總編收起了笑容一本正經地說:“也是也是,你老同學是咱報社老人手了,功勞啦苦勞啦都不少,可直到現在還是個中級職稱,應該到第一線走一走,寫出些好稿子獲上幾個新聞獎,盡早把高級職稱解決了,這樣一來工資待遇也就上去了……”
“我就是這個意思嘛。”周成一臉誠懇地說。
“那這樣吧,”總編略微沉思了一下說:“你回去聽信,我和社長說說,很快給你見個話。”
出生于秦西山區農家的周成,二十年前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省立師大中文系。以周成的學習成績原本是要留校教書的,只因他普通話考試屢屢過不了關而罷休。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大都市繁華環境的強力熏陶,竟然一點沒有改變周成的農村生活理念,高等學府四年良好的語言氛圍,亦沒有使周成的普通話水平得到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提高。抑或他壓根就沒打算改變。他有他的說道,那么多的老一代革命家,一輩子都沒有改口音,照樣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一點沒有影響人家世界級偉人的光輝形象。雖然不能與聲名顯赫的政治家相提并論,但世事發展的基本道理似乎是一致的。二十年過去了,周成還清楚地記得那次考試的情景:眾目睽睽之下,老師要他用普通話朗讀一篇散文詩,結果周成一句“啊!拉(那)金誰(色)滴(的)妹(麥)浪,在廣袤無垠滴(的)關針(中)平原上此起彼伏滴(地)翻涌……”直接將監考的幾位老師以及全班同學笑翻,幾個女同學竟笑出了眼淚。周成當時雖然滿臉通紅十分狼狽,但生性固執的他并沒有因此而下不來臺,相反,在走上社會參加工作后,家鄉口音操持得變本加厲且一發而不可收,動輒還輔以農村歇后語來加強他話語的分量。自知不是教書的材料,周成畢業不久就抓住一個招考機關報記者的機會,以遙遙領先的筆試成績和同級同學、現任的總編一起被錄到了現在供職的單位。上班第一天,周成便主動向領導申請做了報紙的文字編輯,這一干就是二十年,他那“妹浪”的段子也傳說了二十年,報社的員工在調侃誰個普通話說得不像樣子時,常常拿周成“啊!拉(那)金誰(色)滴(地)翻涌……”來形容。
二
“換個辦公室換個椅子”,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情,特別在熟識和了解周成的幾位上司眼里,更算不上是什么奢求和非分之想。于是,周成的愿望沒費什么周折就實現了。總編在給周成談話時告訴他,社委會同意了他到記者部工作的申請,還決定讓他擔任首席記者。雖說是資深老同志,而且經見的事情也不少,可突然之間被升了官提了職,對原只打算改換一下工種的周成來說,猶如魚塘里丟進一塊大石頭,猛地一下激起了串串漣漪,叫他頓時感到眼熱、頭暈,有些適應不過來。他略顯羞澀地望著高高胖胖、一臉官相的老同學說:真的假的?我只是想當當記者寫寫好稿獲獲獎,完了把職稱往高里弄弄,別的我可真沒想哦。總編不耐煩地說:你看你,啰嗦不?叫你到記者部干活去呢,又不是叫你去當老爺呢,什么真的假的?明天一早就去記者部報到!
周成在報社干了二十多年,專職當記者卻是頭一回。第二天,周成特意穿了身黑色西服,扎了條深紅色領帶,極其莊重地走進記者部的辦公室。一位正在寫稿的年輕女記者猛抬頭,大吃一驚:“喲呵,周老師今兒這是當了新女婿,還是摸彩票中了獎?打扮得這么酷,是想把大家眩倒還是咋地?我們記者部可沒有‘妹浪’啊,哈哈哈……”
周成寬厚地笑了笑,用他那濃郁的家鄉口音說:“本人今天一不是新女婿,二沒有中彩獎,三也不‘妹浪’,而是到記者部報到干活來了!新媳婦坐月子頭一遭啊,以后還靠各位多多關照哩。”
一位戴眼鏡的女記者表情夸張地說:“哇,您周老師到記者部來那可是F117空降下來了啊,我們巴望都巴望不到呢,咋敢說什么關照哦,是您往后要多多關照我們啊”。
女記者的話如同帶著鞘的刀子,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可周成心里卻跟鏡子一樣明白。此時此刻的他,心情陽光,情緒高漲,不愿掃大家的興,更不愿掃自己的興。他極盡謙虛和憨直地說:“好說,好說。咱們現在是一個飯鍋里攪勺把,一個磨道里推碾子,一個板凳上綁螞蚱……”
正說著,記者部主任推門進來:“呵,老周,周大編輯,歡迎歡迎!”說著跨前一步緊緊握住了周成的手。
周成趕忙說:“不客氣,不客氣,以后還要主任多多關照才是。”
“好說,好說,”記者部主任說:“社領導給我打招呼了,你到咱們記者部來擔任首席記者,分跑社會法制口……”
“就說么,”幾位女記者迫不及待地打斷主任的話,嘰嘰喳喳地調侃說:“周老師今天溫文爾雅酷得不行,人家才是升了官兒呢!看起來今兒中午的飯局有了著落了啊……”
周成說:“沒麻達,沒麻達,不就是請吃個飯么,碎碎個事。是去岐山哨子面館呢還是大香港鮑翅坊?只要大家高興,我把珍藏在書柜里的兩瓶五十年西風也拿出來,咱來個一醉方休,咋個向?”
“好了,好了,吃飯的事往后撂撂,先辦正事。”記者部主任收住眾人的話絮一臉認真狀地說:“老周,你看,咱這都老腿舊胳膊的,官話套話我就不用多說了。現在有一個活兒,你看著全權處理一下吧。”說著遞給周成一封信件。
周成拿著信件在記者部主任給自己指定的辦公桌前坐定,略微收拾整理了一下桌面就打開信件看了起來。信是西京市北林區沙坡村四位村民寫給報社的。信上說,他們四人一周前在村民大會上被選舉為村民代表,可昨天在公布選舉結果時村上領導擅自取消了他們的代表資格,特請求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監督云云。老新聞工作者的直覺使周成立即感到:這是一起踐踏民主、侵犯公民權利的典型事件,很有新聞價值,稿子寫好了沒準能在來年全省好新聞評選中拿個等次獎呢。
說干就干。周成立即帶上一名實習生,照著信件上寫的地址打車趕到了北林區沙坡村。他們首先找到信件反映人對相關事實進行了初步核實。原來,一個禮拜前,這個村的黨支部村委會組織召開了一次村民大會,會上傳達了市、區黨政領導部門的有關文件精神,同時按照上級關于強化農村村務公開的有關要求,在當天大會上公開選舉了村民代表。根據每一千人以下的村十戶一位村民代表的相關規定,共有一百五十多戶的沙坡村,以提名通過的方式選舉產生了十五名村民代表。選舉結果出來之后,主持會議的村領導宣布說,正式代表人選要等村上研究后再予公布。結果,昨天下午張榜公布村民代表名單時,十五名直選代表中有四名榜上無名,而村上領導另行增添了四名未經村民大會選舉的村民作為代表。被取消資格的四位村民代表氣憤地對周成說:我們是被村民大會直接選舉的村民代表,村上領導擅自取消我們代表資格,我們堅決不答應,日死日活也要討個說法!幾位聞訊趕來的群眾也當場證實了這四名代表所陳述的事實。
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周成心里直罵:這些個村干部,狗屁不通瞎胡整,“二十四個狗娃拉車車——亂了繩索”嘛!采訪完畢后,周成看著滿臉無限期待之情的村民解釋說:“各位鄉親,按照新聞工作的程序,我們還得采訪一下村上的領導。如果情況的確屬實,報紙一定會把這件事情登報曝光。但我們只是新聞媒體,只能做輿論監督,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得區上或街道辦來進行。‘一物降一物,喇嘛降怪物’,請大家一定要理解啊。”眾人說:“周記者,俺們都理解,不會暮亂你的。”
周成拿著錄音筆和采訪本趕到了沙坡村村委會。還巧,村支書和村主任都在。周成出示了證件,說明了來意和要了解的問題。村支書和村主任聞言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周成說:“你們不用緊張,我只是核實幾個問題:一、一周前的那天上午村上是否召開了村民大會?二、村民大會上是否選舉了村民代表?三、是否有四個直選代表被村上取消了資格?四、新增添的四名代表是否未通過同等規模的村民大會選舉?”
村主任說:“你說的這四條都是的,但是……”
“‘是’或‘不是’就行了,不要‘但是’”。周成打斷村主任的話說道。
“是……”村主任說。
周成說:“那我就用個不恰當的比喻:二位老兄‘母豬咬狼——膽子太大。’你們這樣做是侵害村民權利,違法著哩……”
村支書打斷周成的話,說:“這四個人在村上表現不好。”
周成問,有沒有違法犯罪?村主任回答說,沒有。周成又問,那是打架斗毆哩還是把誰家媳婦領跑了?村主任說,也沒有。周成哈哈一笑,說,人家既沒有違法犯罪,又沒有胡俅整事,你們憑啥把人家的村民代表資格給取消了?村支書急了:那幾個狗日的不聽村上領導的話……周成無奈地合上采訪本,說,看來你們二位封建官本位思想太重,民主法治意識太差,再談下去我就越位了。情況已經清楚了,我就不多說了。村主任拉住周成的手問,俺村的這事能不能不登報?周成說,這事我說了不算,得看新聞價值高不高,典型意義是大不大,再經我們報社領導審查之后才能決定。
返回報社時周成順路又去了一趟省民政廳,并就沙坡村選舉問題采訪了基政處處長。處長明確表示:群眾大會直接選舉的村民代表,其結果合法有效,如要取消其資格或再行增添人員,必須經過同等規模的村民大會表決通過。沙坡村發生的這件事情在西京市乃至于全省都十分鮮見。處長說,依法推進基層民主建設,是搞好“三農”工作的重要環節,沙坡村的違法事件如能在報紙上刊登一下,其宣傳教育效果肯定是顯而易見的。
有了省上權威部門權威負責人的權威肯定和權威支持,周成感到心里更踏實、更有底了。回到辦公室,周成打開電腦沒費多大功夫就寫出一篇題為《公民權利橫遭侵害(引題)沙坡村四名村民直選代表被擅自取消資格(主題)》的消息稿,第二天就刊登在了《民主法制報》頭版。
當日上午,北林區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在報紙上看到了此篇報道,頓感問題嚴重,立即給兼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區委書記進行了匯報。區委書記戴上眼鏡側著頭把報紙上的報道連看好幾遍,說,沙坡村這是嚴重的胡鬧嘛!說畢,撥開簽字筆的帽子在報紙稿一側批示:“這是一起嚴重踐踏民主、損害公民權利的事件。建議由區委組織部、區民政局和區人大辦抽出工作人員組成專門調查組,對此事件進行認真調查,如情況屬實,堅決予以糾正,并通報全區引以為戒,把正在進行的全面推行村務公開活動扎扎實實地搞好搞出成效。”
北林區委書記批示的事,是總編幾天后從一位在該區任職的老同學那里得知的,而且還了解到,區委調查組下到沙坡村的當天就糾正了該村的錯誤做法,恢復了四位村民代表的代表資格。
媒體的一個輿論監督,竟促進了一方區域的民主法制建設,這無疑是一個良好效果的收獲。在匯報給秘書長、社長并得到充分肯定后,總編高興地在電話里對周成說:老周啊,行啊你,老將出馬,一個頂倆。當首席記者頭一天,就打了一個漂亮仗!可給咱報爭臉了哦。周成樂嗞嗞地回答說:咱就吃這碗飯哩么,拉(那)就和農民務莊稼一樣,做啥就要像啥,像啥就要成啥哩。
三
多年新聞工作的經驗積累和報社領導的熱情鼓勵,使得首席記者周成精神大振,如魚得水,如牛得草,短短幾個月時間,就發表了多篇新聞價值極高的通訊報道,特別是有關輿論監督方面的稿件,在廣大讀者和人大代表中引起了很大反響。
那天臨下班,門房王師傅交給正下樓梯的周成一封信。這是秦北市廟塔煤礦采空區村民聯名寫的情況反映信。信上說:地處秦北市的廟塔精煤公司煤礦采空區發生大面積塌陷,地下水源漏失,嚴重影響了附近三個村群眾的生產生活,幾年來他們向精煤公司反映了無數次,縣人大也曾組織人大代表進行過視察督促,可這家公司自恃央企,財大氣粗,對當地群眾的實際問題漠然置之。無奈之下他們懇請周記者前來作個新聞采訪進行一下媒體曝光,以促其盡快把當地農民的生存危機問題加以解決。情之切切,言之鑿鑿,周成既深受觸動,又感到有些難以承受。他拿著信件趕到總編辦公室,正在關電腦準備下班的總編接過信件粗略看了看說:“既然基層群眾這么信任你,那你就辛苦一趟把這活兒干了。廣大讀者是咱們的衣食父母,對讀者負責,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天職。再者說了,群眾利益無小事,這也是胡總書記的諄諄教導。我報能出一個被讀者如此認可的名記者,是個大好事呢。可你必須記住,咱們只是個新聞媒體,只能做做輿論監督,別的功能咱不具備。一定要把好這個度。”
周成說:“那當然么,這是最基本的常識,難道我當了半輩子接生婆,還能還把娃娃的牛牛當臍帶啥剪了不成?”
總編笑著拍拍周成的肩膀說:“你看你看,又‘妹(麥)浪’了,……”
第二天一早,周成帶了一名實習生搭乘長途大巴車趕往了秦北市,并于當天下午到達廟塔鎮。
黃土高原的寒冷季節比關中平原來得早,雖然時令剛過立冬,可前幾天的一場雨夾雪下過之后,急轉直下的嚴寒氣溫直接把人們的感覺拉到了數九隆冬。周成下了大巴車,瞇眼四望,只見廟塔鎮的塬上、溝渠、坎峁畔盡是積雪,原本被煤塵、枯葉、爛草染得灰黃黑臟的土塬,此刻卻如冰雕玉琢,潔白無瑕。
在長途汽車站附近迎侯周成的當地幾個村干部,及其熱情地開著農用四輪車把周成接到了村委會駐地。一杯熱茶下肚,長途勞頓的疲憊、寒冷頓時減消了不少。周成一邊伸出雙手在火爐上取暖,一邊與村干部們進行著交談。通過座談周成得知:廟塔采空區給當地三個自然村造成的損失,除了十眼水井無水可用,一座水庫完全干枯,三千畝耕地受旱,其中一千五百多畝耕地全部絕收外,還有七個機磚廠因無水而倒閉,一處抽水站因無水而報廢,一百四十多畝果園因無水而枯死等等。
聽說省城的周大記者來了,居住在村委會附近的群眾也都趕到了過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周成提供情況。這是一幫淳樸善良的農民,他們祖祖輩輩繁衍生息在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惹誰,不欺誰,卻被廟塔精煤公司采空區搞得生存都成了問題。事情出現、情況發生之后,當地群眾和地方政府反應十分強烈,但精煤公司卻置若罔聞,只顧抓自己的生產經營,非但沒有對塌陷區進行回填復墾、對群眾進行經濟賠償,甚至不管不問不理茬。
狗日的廟塔精煤公司!現場的村民中有人起了個頭,大家全跟著罵了起來:死皮不要臉!這煤炭資源是國家的,全民的,大家的,不是你家先人給你這一伙鳥人獨傳下的,憑啥你們只顧自己吃飽喝足穿暖,領下的工資獎金往腰里一揣,我們當地農民就該去死?我看你們不是人,完全是驢日下的,豬下哈的!
就像精煤公司的人在現場似的,眾人罵得酣暢,周成聽得痛快。農家后生周成,離開家門二十多年骨子里仍然還是農民。他對聞訊從縣城專程趕來的人大主任說,我日死日活也要幫農民群眾討個說法。
第二天上午,周成趕上班時間到達廟塔精煤公司。聽說省城記者到訪,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全躲了出去。周成攤攤手無可奈何地對接待他的辦公室主任說:“你們公司對當地群眾生存問題和媒體對你們的監督竟然是這樣一個淡漠態度,那我也只好就現面已經采訪了解到的情況在報紙上進行曝光了。”
辦公室主任極其誠懇地拉著周成的手說:“周記者,你甭急,先喝茶,既來之則安之。中午我代表精煤公司給你接風,一會兒咱們在酒桌上詳細進行探討,你看怎樣?”
周成笑著說:“我又不是酒囊飯袋攆到精煤公司來蹭吃喝,我是代表報社前來核實當地群眾反映你們廟塔采空區塌陷給當地群眾造成的損失是否屬實,再想了解一下你們公司在這個問題上有什么具體措施和打算,好給讀者有個交代而已。再者說了,面對采空區那么多受災的鄉親,你們精煤公司的酒飯我也咽不下去消化不了啊。”
辦公室主任說:“周記者言重了。吃頓飯喝點酒是人之常事,也是我們盡的一點地主之誼,不必上升到那么一個高度去看。公司幾個主要領導今天真的都外出不在,而我對情況了解得不是很清楚,的確無法回答什么問題……”
周成打斷辦公室主任的話說:“不是對情況了解得不清楚,也不是回答不了什么問題,你們關鍵是‘大腿上扎刀子——離心太遠’哩!”
辦公室主任難為情地說:“這……我只是個跑腿的……”
周成說:“這樣吧,你們公司領導今天是真不在還是假不在,咱不再探究,以24小時為限,等不到你們的答復我就發稿了。”
在約定的時間里,周成接到了電話。精煤公司辦公室主任斟字酌句地說:公司領導對您的意見非常重視,但表示這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牽涉到很多專業問題,很麻煩,很棘手,一時半會公司恐怕做不了個啥事。周成生氣地連說兩句歇后語:你們這是“夾著嗩吶丟盹哩——把事沒當事”,“驢俅頂門——使勁撐”哩。南方籍的辦公室主任聽不懂周成的話,在電話里使勁喊著:喂——喂——喂,周記者,您說啥?您說啥?周成“啪”一下掛上了電話。周成完全失去了耐心:這些人,‘披著被子上天哩——已經張狂得沒領了。’不給他來點真的他就不知道馬王爺有三只眼,黃鼠狼是麻的。哼!他一邊在心里罵著,一邊打開電腦開始寫稿子。
忽然,手機鈴響了。是省報老孫。老孫是省報政法部主任,周成的老朋友。
“老周,忙什么呢?”老孫問道。
周成說:“我正在趕寫一篇稿子呢。”
“你老兄最近干了個漂亮活兒,人家把錦旗都送到你們報社了,咋就給弟兄們不透透風哦?是怕請客么?”
“不是怕請客,活兒干了就行了,本分事情嘛,搞那么張揚做啥哩。”
“你要再這么低調,弟兄們在你面前可就難活人了哦。”
“別別別,你說這話可是折我的壽哩。我干脆老實交代了吧。事情是這樣的:伊川縣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因與本鄉的人大主席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意見相左,時間長了矛盾便越積越大,于是就假借醉酒砸毀了鄉人大主席辦公室的門窗,還開具介紹信強行把人大主席退回縣上,致使該鄉人大主席不能上班,鄉上人大工作癱瘓了多半年。見縣上幾套班子互踢皮球把問題處理不下,鄉人大主席就把這件事情反映到我們報社,于是社長就責成我前去采訪,然后我就寫了稿發了稿,然后鄉黨委書記就受了黨紀處分,然后鄉人大主席就被接回上班,然后倆人以大局為重握手言了和,然后……然后的事情你已知道了唄。”
“就這么簡單?”
“就這么簡單。不過就是做了五次連續報道吧,要不這事就拿不下來。”
“唉,”老孫嘆了口氣說:“現在這基層的一些行政領導,依法做事的觀念太淡漠,老子天下第一的土皇上封建思想嚴重得很呢。”
周成說:“是啊,要不老百姓咋會那么大的意見啊。哎哎哎,說了半天你是不是找我有啥事啊?”
老孫說:“是啊。有一個活兒想讓您老人家出手呢。”
“不行,不行,”周成說:“我這兩天忙得鬼吹火哩,沒空啊。”
“再忙,還抽不出一天半天時間?你可是省城名記,快槍手利刀子,至于那么緊時嗎?”
“唉……,我這人總是吃心軟的虧。那好吧,你說,啥活兒?”
“電話上不方便說。晚上七點鐘,在老地方——南二環上島咖啡,不見不散。”
晚飯后,周成和老孫如約在上島咖啡見了面。
這是一家環境幽雅,氛圍溫馨的茶社。設在曲徑通幽處的眾多卡座,點綴著光線柔美的精致桌燈,使得剛從寒冷的夜幕中走進來的客人們,立即會感到一種由衷的暖意。被鮮花綠草包圍著的樂池里,一位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姑娘,正在身心盡頃地彈奏著經典名曲《琵琶語》,指尖流淌出的樂句,柔情似水,聲聲入耳,緊叩著人們的心扉。漸漸地,那無數飛瀉的樂符便在姑娘的周圍迭出一個美麗如畫的仙境。
按客人要求,服務生很快就端來一壺熟普洱和兩個茶盅。好友見面,茶,就是美酒,茶,就是情意。一壺熱茶喝下肚,倆人頓覺渾身舒暖,腹肺酣暢,沒有過多的寒暄就直奔了主題。聽完老孫簡單的情況介紹后,周成捏著手中的茶盅皺起了眉頭,說,這件事新聞價值不高沒俅弄頭啊。老孫變戲法似的扔給周成一沓子材料,說,你再看看這些材料,就知道有沒有弄頭。周成把桌燈往近挪了挪,然后鋪開材料詳細翻閱起來。
“啪——”,看完材料周成猛地拍了一把桌子說,狗日的,真夠黑!老孫說,是啊,群眾把這件事反映到黨報、機關報,是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和依賴,咱無權漠視讀者的訴求。周成說,你說得對,咱們當記者的不主持公道不伸張正義,那國家和百姓要咱干俅用哩。老孫說,就是啊。周成放下手中的茶盅說,啥時動身?老孫說,明天一早。周成說,好,就這么定了。
四
初冬季節的黃塬市,百花凋零,枝葉泛黃,一派蕭瑟景象。
黃塬市法院的一樓樓道里,周成和老孫瞅著門牌走進了行政辦公室。一名值班的女警官看完老孫和周成的證件得知他們此行的來意之后,委婉地說:“非常抱歉,我們的主管領導和主審法官都不在。要不你們把電話留下,等著他們回來后給你們去個電話怎么樣?”
如此外交辭令般的逐客話語,周成聽的多見的多了。“禿子頭上長瘡疤——怕人掀帽子呢”!周成不動聲色地說:“也行,可是我倆來了解的這個案子,情況已經非常清楚,有你們的一審判決書為證,我們只是走一下新聞采訪的程序而已。領導在更好,領導不在也行,反正我們把你見了,也就說得過去了,回去該咋發稿就咋發稿唄。那我們走了!”
女警官急了,站起身來說:“哎、哎、哎,先別走,先別走,甭把我扯進去吆,我可負不起責任哦。”
老孫說:“既然你負不起責任,那你看誰能負責任就趕快把誰找來啊!”
女警官皺著眉頭想了一下,說:“那你倆先坐一會,我去去就來。”說著拿著手機走出了辦公室。過了不到一支煙工夫,女警官領著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走了進來,說:“兩位大記者,這位是我們的常務副院長,聽說你們來了,非常重視,趕忙過來見你們……”
話還沒說完,常務副院長已緊緊握住了周成和老孫的手:“歡迎,歡迎!黨的喉舌啊,你們的關注一定會促進我們的公正司法。好,我馬上召集相關人員開個座談會,把相關情況給你們匯報匯報。”
不一會,二樓頂端一間不大的會議室里,黃塬市法院經濟庭的庭長、副庭長、審判員一應人等,全都齊刷刷地坐在了會議桌前。常務副院長將雙方人員進行介紹之后,說:兩位大記者長途跋涉數百公里前來我院指導工作,并就銅陵煤礦與黃塬煤炭公司煤款糾紛一案進行了解,你們經濟庭把這個案件的相關情況匯報一下。
先是主審法官發言。他一開口就是熱烈歡迎兩位大記者前來指導工作,熱烈歡迎兩位大記者給我們提出寶貴意見云云,說著攤開手中厚厚的一疊材料,大一二三,小123,滔滔不絕地匯報了起來。周成越聽越不是滋味,便皺著眉頭打斷主審法官的發言,說:“各位領導,各位法官,請允許我做個小小的說明:第一,我們是報社記者、新聞工作者,不是哪一級領導,不指導什么工作,再說,我們也沒這樣的功能。第二,媒體是做新聞的,只是對群眾反映的一些新聞價值比較高的信息進行采訪核實,不敢說聽什么匯報不匯報,更不必要把事先準備好的材料吧嗒吧嗒念一遍。要不這樣吧,咱復雜問題簡單化,我問你們答,問啥回答啥,能回答清楚的就回答清楚,回答不清楚的能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只要完全真實就行,你們看怎樣?”
“行行行,就按你說的辦,”常務副院長說。
周成跟老孫交換了下眼色,然后翻開手中的采訪本,說:“根據我們目前調查掌握的情況,主要有四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法官:一、黃塬煤炭公司下欠銅陵煤礦貨款180萬,貴院在審理判決時,怎么判給了與貴院勞動服務公司有業務關系的A公司賬上而不是銅陵煤礦的賬上?二、此案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后,依法應重新組成合議庭,貴院為什么在重審時還是原審合議庭,只是換了一個書記員?三、按有關法律規定,案件的審判與執行必須分開進行,可貴院執行此案人員還是合議庭的法官。四、省高級人民法院了解相關情況之后,立即下達了暫停執行的命令,貴院怎么沒有按這一命令辦,而是繼續進行了煤款執行?這四個問題我們不甚明白,請各位庭長、審判長、法官給予回答。”
周成一板一眼的問話,如同一發一發炮彈從天而降,黃塬市法院在場的法官除了常務副院長以外全都傻了眼,甚至有人頭上還冒起了冷汗。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上述四個問題只具備一個就是程序違法,而程序違法就意味著這起案件的判決結果全部無效。
剛才還是輕松、熱烈氣氛,突然之間變得嚴肅、冷森起來,空氣也仿佛凝固了似的,會議室里寂靜得掉下一根針都可以聽見。大家面面相覷,無言以對。不甚了解案情的常務副院長,看著他的部下們尷尬的表情和窘困的樣子,心里已經明白了七八分。作為一位新調來不久又主持全院工作的常務副院長,他實在不愿看到,堂堂的一個市級法院竟然把一個情況明了、過程簡單的案子辦成這個樣子!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在這個案子背后還隱藏著諸多眼下尚不清楚但完全可以肯定是見不得陽光的勾當。可是此時此刻,他不能在這個場合發作,他要顧及部下的面子,而顧及部下的面子就是顧及法院的面子、顧及他自己的面子。于是他在該堅持原則維護法律尊嚴的時候選擇了護犢子、和稀泥。他端起茶杯淺淺地喝了口茶,然后輕輕地放下茶杯,搓了搓手不動聲色地說:“兩位記者朋友,你們問的這四個問題我還是頭一次聽到,容我們下來合計合計,然后再作詳細答復,你們看行不?”
老孫說:“沒問題,你們合計吧,我們等一等。”
常務副院長和部下們全都出去了。半小時后,值班的女警官笑容可掬地走了進來,說:“二位大記者,我們院長已在黃塬市最好的酒店訂了一桌酒飯,中午要隆重宴請兩位遠道而來指導工作的大記者,宴席中間再就案件的有關情況進行匯報。同時,院里還給二位準備了我們當地的一些土特產,請你們賞光品嘗。現在請二位起身,車在樓下等著呢。”
周成不悅地說:“這會兒還不到十點,正是上班時間哩。請你告訴院長,咱就擱會議室里說事,不必進酒店。”
女警官說:“酒店本來就是說事的地方啊。二位大哥,你們來采訪是辦公事嘛,我們招待你們也是辦公事呢……”
正說著,常務副院長走了進來不無寬厚地說:“二位大記者,我剛把情況簡單了解了一下,這個案子比較復雜,一句兩句說不清楚。這樣吧,咱先到酒店,一邊吃飯一邊探討。就算我私人請各位弟兄了,怎么樣?給老兄個面子?”
周成說:“院長老兄,不必客氣,我們就是個普通記者,做個普通的新聞采訪,不是啥大人物,也不是啥大事情,現在能說清了就在這里說清,現在說不清了我們就回去等著你們的電話就行了,吃飯嘛就免了。”
“別介,別介”,常務副院長急忙拉住周成的手說;“人是鐵,飯是鋼,到飯點了不吃飯怎么行啊?”
周成堅決地說:“飯,我們真的不吃。早飯才吃過不久,還沒消化呢。”
“那……”院長一時不知該說啥好。
周成說:“咱們就事說事,不摻雜別的內容。既然貴院不便立即就我所提問題作出答復,那我們就回去等著,等你們給媒體一個正式的確切的答復。”
“那……好吧,”常務副院長無可奈何地說。
老孫不放心地問道:“哎,院長,我們一走你不會把這事扔在一邊不管了吧?”
常務副院長老大哥般地拍著老孫的肩膀,說:“放心吧,大記者,咱們都是公家的人,做的都是公家的事,我們沒有理由不做答復的。再者說了,如果我不做答復,你們按單方面采訪掌握的情況報道出來,那還不把我們法院推到死角了么?”
五
回到省城時,已是半下午。此刻,冬日的殘陽已給古城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涂抹上淡淡的胭紅,縱橫交錯的柏油馬路在凜冽的寒風中顯得格外的冷峻。日月更替,年輪飛轉,城市的輝煌在文明的發展中達到了頂峰,城市的節奏卻讓熟悉的人們日漸陌生。
周成走進辦公室,一眼看見放在自己的案頭的《民主法制報》。這是當天出版的報紙,頭版顯要位置那篇題為《廟塔采空區塌陷給當地農民造成巨大損失(引題)精煤公司置群眾死活于不顧引發民生危機(主題)》的消息稿特別醒目。鄰桌的小楊記者告訴他,中午環資委馬主任給記者部來電話,說常委會分管領導表揚周成這篇稿子寫得很好,要周成繼續追蹤采訪加大對精煤公司輿論監督的力度。還表示,環資委將在近期組織省人大代表赴秦北市進行專題視察調研,全力維護當地群眾切身利益。鑒于精煤公司屬于央企,環資委還打算將此情況報告全國人大相關委員會,請他們配合地方人大依法進行監督,促使精煤公司通過經濟補償、回填塌陷地、修建引水渠、鋪設引水管等措施,妥善解決當地農民群眾的生存生活問題。小楊記者轉達的這番話,如一股暖流傳遍周成的全身。本打算采寫一些有新聞價值的好稿,來年獲上幾個新聞獎的,不料每每還取得一個如此這般的社會效果,周成由衷地感到欣慰、高興,慶幸自己的辛苦沒有白費。
主持召開完報社編委會,總編端著茶杯回到了辦公室。剛打開電腦,桌子上的電話鈴急促地響了起來。總編拿起電話聽筒:“喂,哪位?”
聽筒那邊說:“我是黃塬市法院的副院長。請問您是《民主法制報》總編輯嗎?”
“是啊,有什么事么?”
“是有個事,想跟貴報溝通一下。”
“噢,您說吧。”
“貴報記者周成昨天來我們法院采訪銅陵煤礦與黃塬煤炭公司煤款糾紛一案,您知道嗎?”
“知道。有什么問題么?”
“他們的采訪是在干擾法院辦案呢。”
“周成是我報跑政法口的記者,而且是首席記者,他在全省任何一個政法單位進行新聞采訪,那都是職責范圍內的事情。我不明白,他作個新聞采訪怎么就干擾了你們的辦案呢?”
“記者進行新聞采訪,這是他的職責,沒錯。可是我們的辦案工作都是依法公正進行的,有些案子情況比較復雜,公開報道出去會影響法院的聲譽的。”
“你說的這個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成還沒來得及給我匯報,我也不清楚。可是有一點我不理解:既然你們在依法公正辦案,那咋還害怕新聞記者采訪?”
“看你這話說的,不是我們害怕媒體記者采訪,而是有些案子在審理過程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漏洞,你們曝光以后會使法院工作陷入很被動的境地。咱們都是國家的單位、一家人,不能自己砸自己、自己損自己,應該相互支持、相互包容、一致對外才是啊。”
“我不敢恭維您這話。法院是人民法院,報社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咱們都應該為人民群眾服務對人民群眾負責,怎能把人民群眾當成‘外’來‘對’呢?”
“哎喲,我的大秀才,你是總編我說不過你,咱不爭執了,我請你們辦公廳歐陽主任給你打個招呼行不?他可是我在省委黨校的同班同學了。”
“您請哪個領導出面這是您的權力,我不參與意見。但最好先跟我們記者溝通一下,咱把事情先搞清楚……”
“你們這位周記者,針扎不透,水潑不進,沒辦法溝通啊……”
六
直覺使得總編感到這件事情就是個馬蜂窩,而他的老同學、首席記者周成恰恰就是捅這個馬蜂窩的人。以他的了解,新聞敏感性強、好伸張正義、主持公道的周成,每抓住一條價值很高的新聞線索,他都會高度重視,絕不會半途而廢更不會棄而不做。周成以自己多年的親身經見,深知人民群眾對司法腐敗現象之切齒痛惡,這其實也是媒體特別是法制媒體最為關注的熱點問題。因此,周成所作的新聞采訪常以反腐題材為最多,而黃塬法院這條新聞一旦出現在報紙上,其爆炸力和震撼力無疑一定很強,不但非常吸引讀者的眼球大幅提高報紙的社會關注度,而且在來年好新聞評比中一定會拿到一個很高的獎次。可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如若登了報、曝了光,又將會惹惱黃塬法院且得罪一大圈與該法院關系密切的領導,繼而給報社帶來許多麻煩的。
想到這里,總編突然感到有些心煩、腦脹。他拉開抽屜找了支煙銜在嘴角用打火機點著,不知是根本沒有煙癮還是這支煙在抽屜里擱的時間太久已經變質,只吸了兩三口就被嗆得“吭、吭、吭”干咳不止。他索性掐滅煙頭又泡了杯茶喝了起來。他心里很清楚,如若把這條新聞信息活生生扼死在萌芽之中,不但做采訪的記者不答應、反映情況的群眾不答應,也會使自己的正義良知受到鞭撻,職業操守受到玷污,甚至會使自己懊悔后半輩子。
放下茶杯,總編信步踱到窗前推開了玻璃窗,刺骨的冷風“呼——”地一下吹了進來,他頓時感到腦筋清醒了許多。透過十六層高樓的窗戶放眼望去,大半個古城清晰而生動的盡收眼底,那象征著古老文明的鐘樓、鼓樓和城墻、門樓,似隱似現地躲在洋溢著現代文明氣息的摩天大樓縫隙之間,極其頑強地展現著自己國寶熊貓般的身姿,不遺余力地顯示著自己無與倫比的身價,既滑稽又可愛。樓下的馬路上,潮水般的車流緩慢而堅定地向前涌動著,在展現城市熱鬧繁華的同時,也給南來北往的路人心頭添了層堵。
總編關上窗戶斷然決定:用一個將各個方面都能兼顧上的得力之策,使這條新聞信息有一個比較理想的處理結果。于是,他立即撥通了周成的電話。
聽完周成的匯報,總編很是氣憤:堂堂市級人民法院的法官,肩膀上的那架天平是咋擺正的呢?
周成說:“我想盡快把稿子拉出來發了,促使他們在重審時能夠糾正錯案,從而維護國企職工合法利益和法律的尊嚴。”
總編沉思了一下說:“你對這個案件的采訪,我堅決支持;你對這起案件的看法,我也非常贊同。可是……這是個市級法院,不管怎么說,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國家的司法形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一旦公開在報紙上曝光,其負面作用可能要大于正面作用……”
“狗屁!我才不管呢,”周成打斷總編的話憤憤地說:“這幫鳥法官,啥不法的事他們都敢弄。銅陵煤礦今年效益不好,近千名職工等著這筆血汗錢發工資過冬呢,法院竟然把黃塬煤炭公司下欠銅陵煤礦的貨款劃到他們勞動服務公司的一個關系單位,說是銅陵煤礦欠這家單位十幾萬元的債未還。稍有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便銅陵煤礦欠那個單位十幾萬的債,那也是另案處理的事情,和黃塬煤炭公司欠銅陵煤礦一百八十萬元的貨款屁不相干哩。你說說,這是人民法院干的事情嗎?我就是要給他們曝光,讓人民群眾公開監督。”
總編說:“黃塬法院常務副院長電話稱,咱辦公廳歐陽副主任是他的老同學,他準備給老同學打電話給咱辦招呼……”
周成堅決地說:“你當總編的害怕權勢,害怕官壓,我不怕,你把責任全推到我身上,文責我自負!”
“你看你,都這把年紀了,還這么好激動,”總編有些生氣地說:“我話還沒說完呢,你就哇啦哇啦起來。再者說了,我這總編充其量只是個芝麻官,又沒違法亂紀,又沒違反政策,我怕個俅!我是說任何事情咱都得講個策略,既要把事辦了,還要有效地減少負面效應。”
正說著,辦公桌上的電話又急促地響了起來。總編接了,還是黃塬市法院常務副院長打的。他問總編,你把情況了解了沒?總編說,了解了。常務副院長說,可千萬別給咱登報啊。這兩天我把手頭的緊事一處理就來省城,順便給你們帶些黃塬土特產,到時候請你們和歐陽副主任一起吃個飯。總編說,你放心,我們不公開登報曝光了,至于什么吃飯啦土特產啦就不必了,我們報社有紀律。
周成吃驚地看著總編,咋?不弄了?我忙活了好一陣白玩了?總編說,我答應他們不公開報道但沒有說不登內參嘛。周成說,我還指望這個素材再寫一篇好稿獲獎呢,你給登了內參不就瞎了么?總編說,你不能光盯著你那一畝二分地打小九九,咱要往遠處看辦大事呢。你想想,他們準備請咱領導出面阻止報社公開曝光,可咱領導肯定得掂量掂量不會輕易答應說情。那咱這內參一登,既叫黃塬法院無話可說,也給咱領導解了圍,還把輿論監督的事情從更高的層次上做了一把,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為呢。周成說,到底是總編哩,就是水平高,胡家灣的山神爺——實插兒。
正說著,總編的手機鈴響了:“喂,我是,噢,噢,全國人大《中華環保世紀行》來我省執法檢查,噢,派一得力記者陪同采訪,誰?好,好。”
周成問道:“誰打的電話?”
“社長打的,”總編說:“這樣吧,剛才的電話內容你也聽到了,你就辛苦一趟,代表咱報隨隊采訪。”
“我還出去呀?這幾天我跑了個馬不停蹄,狗吃粽子腰帶都沒顧上解呢。叫別人去吧,我得休息休息哩。”
“環保世紀行活動那可是個重要活動,再說活動后天才開始呢,明天還有一整天的時間,你在家休息一下就好了。誰叫你是‘得力記者’啊。代表報社水平呢,社長說是常委會主管領導點的名,責任重大哦。”總編的口氣不容置疑。
周成說:“那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