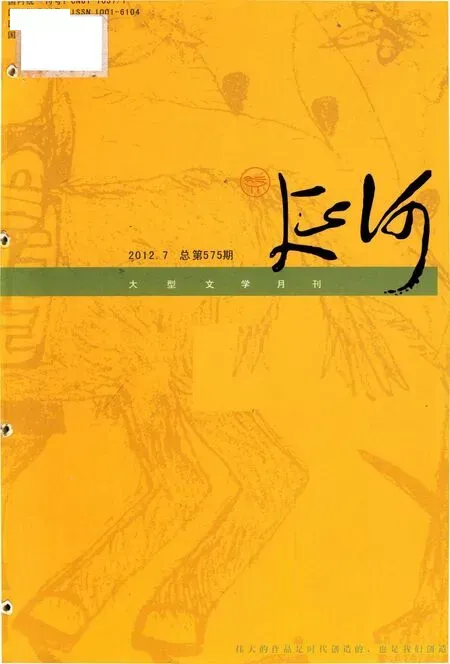托馬斯的詩意
曹文博
在底層抽屜我發現一封26年前收到的信。
一份驚慌中寫成的信,它再次出現仍在喘息。
一所房子有五扇窗戶:日光在其中四扇閃耀,清澈而寧靜。第五扇窗面對黑暗天空、雷電和暴風雨。我站在第五扇窗前。
……
我喜歡閑逛,消失在人群中,一個大寫T在浩瀚的文本中。
——《對一封信的回答》(北島 譯)
話說1927年,有人要提名魯迅獲諾貝爾文學獎,魯迅回復:“諾貝爾賞金,梁啟超不配,我也不配。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就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6日下午1點,瑞典人毫不吝嗇地頒給了自己家門口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似乎正中魯迅的預言。當瑞典學院終身秘書彼得?恩隆德念到“Through his condensed translucent images he gives us fresh access to reality.(他以凝煉、簡潔的形象,以全新視角帶我們接觸現實)”時,他卻像準備好了驚訝:正歇著,在聽音樂,“感覺非常好”。
小島上的藍房子
海子說“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特朗斯特羅默小島上的藍房子每年都要油漆,以抵御嚴酷的冬天,他說“那房子像一張兒童畫。他所代表的稚氣長大,因為某人——過早地——放棄了做孩子的使命。開門,進來!天花板不安,墻內平靜。床上掛著有17張帆艦船的畫,鍍金框子容不下嘶嘶作響的浪頭和風。”我曾想買一本海子全集,猶豫了老半天,問一位老師“他的詩會不會和他的人生境遇一樣憂郁”,老師說海子的詩很溫暖,很陽光。我承認,老師是對的。
每一個詩人都是精靈,在自己的世界里追尋著生命的極限。房子是是詩意的鐐銬,特朗斯特羅默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老式排房是一個“開放與關閉的空間”,詩人就活動在醒與夢之間,在夢的邊緣。藍房子包裹著的生活,是晴天可以捕捉昆蟲做標本,雨天可以穿著高腰雨鞋去采毒蘑菇,一會兒是意識漂流,一會兒是左手彈奏的鋼琴協奏曲。他也出去活動,回到藍房子他將自然、人文、工業、靈魂編制在一個坐標體系里,他的思想如倒影一般在凝固在那里,一動不動。不!是在飛。
他的藍房子有五扇窗戶:日光在其中四扇閃耀,清澈而寧靜。第五扇窗面對黑暗天空、雷電和暴風雨。他站在第五扇窗前。
那個冷峻的中風老頭
特朗斯特羅默是個心理學家,更準確地說是犯罪心理學家,他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按常理,這是一個足以扭曲價值觀的陰暗。但是,別忘了,魔鬼天生離詩人很近,他用詩歌救贖靈魂。
1990年12月開始,他用橫格本,左手,涂鴉式的字體寫字,像海嘯過后,滿本子碎片與枝枝丫丫。詩人中風了,不會說話,右半身癱瘓。幸好,他的妻子是個護士,保姆兼專業翻譯。身體的疾病禁錮不住那顆稀疏花白的大腦,思想如俳句般溢出,冷峻節制、修辭嚴謹,不含雜質,散發著鈍鋼般的力量,一如往常。“黑暗怎樣焊住靈魂的銀河”、“空中充滿犄角和蹄子”、 “落日像狐貍潛入這個國度/轉瞬間點燃青草”、“去往樹線以上的遠方”,你再聽,“橋:一只飛越死亡的巨大鐵鳥”,令人不寒而栗!寫出這些時他才十八歲,不是時間的磨礪而是直接登峰造極,中風后也同樣平衡住了自己的身體,有了六年后《悲傷的康杜拉》。二百多首詩,算不上高產的作家,但每一首都近乎完美。難怪瑞典人家喻戶曉地偏愛這個冷峻的老頭,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不顧點人情面子都不行。
你說,詩是什么?
我不是詩人,首先申明。但是,我要讀懂字句中的情感。詩是形式感漸進的音樂,詩是一幅展開想象的寫意畫,真實的世界消失后,情感并不是瞬間坍塌。一個詩句片段可以延伸上千年,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淚下。是的,詩是不是理性的分析,就像我們都認為詩人是瘋子一樣。他把認識的世界變成幻想,詩句證明自己還活著。某種意義上說,詩延續的是一種神秘和未知,一代一代的詩人在努力登高望遠,不僅是為了獲得廣闊的視野,也為反觀內心超越塵世。
詩人,你在干什么?像句子一樣,正瘋狂地吞噬某個安靜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