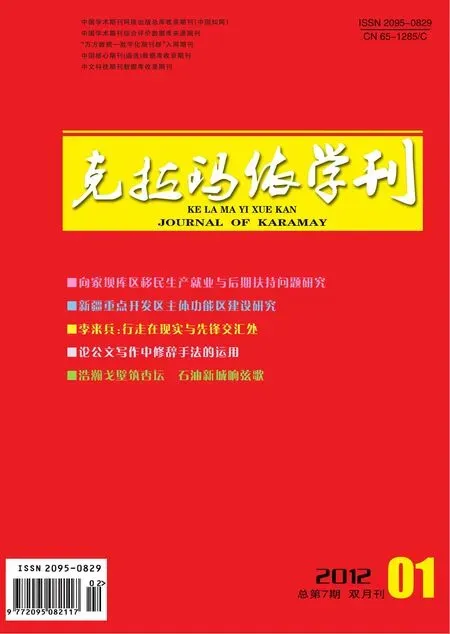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概念改變的跨語言影響研究
張連強
(青島恒星學院 國際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及雙語心理表征研究等的深入和發展,語言研究漸由“形式研究法”(the formal approach)轉向“概念研究法”(the conceptual approach)。語音、詞匯、句法等是語言的表層結構,而概念屬于語言深層結構。許多研究者認為外在的語言行為差異與內在的心理概念過程差異有關。不同語言在表達同一經驗時之所以存在差異,是因為不同語言選擇了不同的概念來進行概念化活動所造成的,由此可見概念在語言學習及運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對概念的研究不僅是認知語言學所關注的,同時也是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認知心理學及心理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研究的重點。
二、語言、概念與概念的改變
關于概念,不同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不同的定義。根據通常的觀點,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屬性(固有屬性或本質屬性)的思維形態。概念是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由符號組成,并以概念或范疇為基礎獲得形式和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語言的形式結構不是自主的,而是普遍的概念化組織、范疇化原則、加工機制以及經驗和環境影響的反映。概念的屬性包括定義屬性(或本質屬性)和可變屬性(或非本質屬性),前者是決定該對象之所以成為該對象并區別于其他對象的屬性,后者是對該對象不具有決定意義的屬性。
關于概念的分類,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及研究目的給出了不同的分類。Gagne把概念分為具體概念和定義概念兩種。具體概念是指那些能夠直接指出來、觀察到的概念,如書本、課桌、樹木等等。定義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直接觀察到,只能根據定義來學習的,如素質、感情、質量等等[1]。Klausmeier認為概念是一種心理表征,包含著某個人對某個或某類事物的結構信息,這種信息使這個或這類事物與其他事物不同并相關。據此,他將概念依據表征形式分為六類:名詞的、動詞的、形容詞的、副詞的、連詞的和介詞的[2]。
語言與概念密切相關。Kesckes指出“除了思維和行動之外,交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概念系統的。所以,語言是探究概念系統的重要證據來源”[3]。Danesi利用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具體剖析了概念與語言,特別是詞匯之間的關系。他提出了概念網絡,并指出概念網絡分成三類:外延網絡(denotative network)、內涵網絡 (connotative network)和隱喻網絡(metaphoric network),這三個網絡共同組成了大腦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structure)[4]。外延性網絡由詞的最基本的、最具體的意義構成,它使得人們能夠以特定的方式談論或思考具體的事物。內涵網絡由詞的一般的、抽象的意義構成。它能使得人們通過推理將具體的意義抽象化,擴大意義應用的范圍。隱喻網絡將抽象的概念和具體的概念聯系起來。由此,抽象概念被理解為帶有具體概念的某些特征,可見詞義之間建立聯系、形成網絡的機制并不是語言形式本身,而是由外延意義、內涵意義和比喻意義通過復雜的路線交織在一起的概念框架的架構過程。
人們已經意識到語言的差異并非表層形式的差異,其實質是概念性的差異。譬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通常具有“純潔”和“清白”的內涵,而在中國文化中白色代表“憂傷”和“死亡”;狗在中國文化中帶有否定的含義,如“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勢”、“狗腿子”等。而在西方狗被看做人們的好朋友,與狗相關的文化也是褒義的,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個幸運兒);Every dog has his day.(是人皆有出頭日);Love me,love my dog.(愛屋及烏)等。由概念缺失而導致詞項缺失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例如,英語中人們非常熟悉的cricket,在俄語和德語中卻沒有對等詞,因為這個概念在俄國人和德國人的概念結構中是不存在的。許多概念反映了一種文化、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所特有的現象。不同語種者思維的差別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概念系統的差別。正如蔣楠指出“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絕大多數思維活動賴以進行的基本單位是存在于我們頭腦中的概念”[5]。所有人都會經歷概念的發展和改變這一過程,這一過程也是教育和生活的軌跡。然而,第二語言的社會化,給了我們一個能夠讓我們看到因為頻繁使用其他語言而引起的需要發展建立一套概念表征的機會。新建立的概念系統會與已經儲存在個體記憶中的概念系統產生共存、競爭、甚至有時取代的關系。概念改變涉及以下一種或多種過程:a)內化,指內化與第一語言(L1)的概念不同的第二語言(L2)的概念;b)重構,指新的元素融入已經存在的概念系統中;c)趨同,指創造與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概念相區別的獨立的概念系統;d)轉移,在某個范疇內,從基于第一語言的概念類型轉換為基于L2的概念類型;e)磨蝕,指之前學習的概念的磨蝕,經常伴隨著新的概念取代之前的概念。這些過程構成一個邏輯的連續體(continuum)。
三、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概念改變的過程
(一)新概念的內化
接觸一種新語言和文化也是接觸一種新的范疇化方式,同時內化那些在L1中未編碼的新概念。語言學家在研究雙語移民時已注意到第一語言移民者在討論新習得的概念時往往訴諸于借詞、借譯以及語碼轉換,這些策略的功能是填補詞匯差異。
Pavlenko研究了“空間”(space)中 privacy和 personal space概念的內化情況。對于privacy和personal space,英語中有詞匯準確表達兩者概念,但俄語中卻沒有[6]。Pavlenko的研究顯示,英語與俄語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同樣的”空間概念[7]。Pavlenko的實驗是讓受試者回憶一個短片,這個短片描述了在公共場所一個陌生的男子與一位婦女坐得太近這一情景。數位英語單語者用對privacy和personal space的“一種侵犯”的措詞描述這種情況,而俄語單語者卻沒有一個人以這種措詞描述[8]。這種結果暗示了privacy和personal space的概念的存在或缺失能夠引導不同語言的說話者以不同的方式區分空間概念(space concept)。然后研究者將這個短片展示給在美國的過了青春期之后學習英語并把英語當做第二語言使用的俄語者。這些受試中的一些人對短片的描述與美國英語單語者相似,在他們的英語描述中借助于privacy和personal space的概念。在用俄語進行的描述中,受試者由于訴諸于一種新的理解方式而導致猶豫、停頓和借譯,例如on vtorgaetsia vee odinochestvo(=he is invading her solitude)(這里privacy被它半對等的翻譯solitude代替)。這個研究顯示了新概念的內化使得以使用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俄語者以一種新的方式區分空間,例如通過借詞翻譯。因此,內化的證據,即向已有的概念庫系統中添加新的概念,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產出中都能發現。
L2使用者內化以第二語言概念的例子很多,但還有兩個理論上的問題。第一個是新內化的概念和同一范疇內其他概念之間的關系。未來需要實證性的研究去檢驗新概念的介入能否導致某個特定范疇內全部結構發生伴隨性的變化,第二個問題是內化過程所需要的時間。Jiang認為L2學習者理解新概念都需要花一段時間,更不用說使用了,例如privacy[9]。相反,Kecskes等認為新的第二語言概念十分容易理解,因為在已存儲的概念體系中沒有跟他們競爭的對象,因此其結果是顯著的[10]。概念習得過程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其中最容易被習得的是更為具體的概念,例如taunhauzy(=town houses)和actas(=result sheets)這種能夠很容易感知的概念。
(二)概念的重構
重構是對已經存在的以某種語言為媒介的概念類型的部分或全部的修正。概念重構在第二語言概念系統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概念的重組涉及到概念的內部結構以及原型、范疇成員、腳本方面的變化。Danesi提出的概念流利學習理論認為概念重組一般有三種:(1)同形概念重組(isomorphic),即目的語詞語與母語詞語概念完全重疊,如:“red”與“紅色”;(2)部分重疊概念重組 (overlapping),這時外語學習者就必須內化有別于本民族的概念結構,如donkey在英語中除指“驢”外還可指“an obstinate person”或“a stupid person”;(3)迥異概念重組,如 a white night(失眠的夜晚),a white elephant(沉重的負擔)等[11]。外語學習初期經歷的同形概念重組在中高級階段逐漸讓位于后兩種類型的概念重組。
概念的重組涉及到概念的內部結構以及原型、范疇成員、腳本方面的變化。Otheguy和Garcia在研究紐約市說西班牙語移民的言語時發現,他們言語中西班牙語詞edificio(=building)快速失掉了原來的概念內涵,被借來的詞bildin替換[12]。乍一看,這種現象可能會顯得比較奇怪,因為在西班牙語和英語中都區分小的住所(例如casa[=house])和大的住所(例如edificio[=building])。然而對受試者的采訪發現了一個新到達紐約者經歷的認知上的變化。新到紐約的南美西班牙語者意識到在美國兩層或三層的建筑仍然能夠稱作“house”(而在拉丁美洲,它們更常被看作edificios而非casas)。然而,當受試者到達紐約后,映入眼簾的雄偉壯麗的高樓大廈與他們在家鄉遇到的任何edificio都不一樣,結果在他們的言語中比那稍小一些的結構就變為了casas。這種變化顯示了在以第二語言為媒介的有關屋子概念的影響下,casas的概念范疇擴大,并且edificio這個詞被換指兩三層的結構的概念后遷移到他們的第一語言概念中。
根據概念遷移研究的相關成果,概念重組的最終結果是形成復合式心理表征,即兩種語言的概念系統經過重組后是存儲在同一個知識庫里的,它包含了基于母語的概念、基于目標語的概念和共享的概念。成功的重組產生新的第二語言概念以及建立起與對應第二語言形式的聯系,從而形成新的概念圖示和內化知識。重組失敗是指沒有建立起新的符合第二語言概念的概念聯結。學習者在使用目的語時,實際上仍然是用目的語詞語表達母語概念,如:
How can we control our time?(manage)
We should cultivate our time concept.(time consciousness)
根據認知語言學研究成果,概念重組的結果是形成雙語思維中的協作概念。Kecskes提出的協作概念假說(hypothesis of synergic concepts),認為協作概念是概念整合的結果[13]。操雙語者通過兩種語言獲取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但由于第二語言學習者大腦中已有的多形式心理表征的存儲器,即“共有潛在概念基礎”(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簡稱CUCB)的存在,被整合的信息只能介于母語概念與目的語概念之間形成協作概念。協作概念并不是知識或信息的簡單相加,而是基于兩種語言詞匯表征的,被打上了每種語言各自社會文化烙印的不同概念組合。例如,對于cowboy一詞的協作概念將會是融合美國西部往往帶有傳奇與浪漫色彩的牛仔文化與中國傳統的牧童概念的組合。
(三)概念的趨同
語言趨同(convergence)一般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或語言變體相互之間變得越來越相似的過程。概念的趨同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概念重構,介于第一語言概念系統和第二語言概念系統之間,并且兼具二者概念類型的特點。事實上,更準確地說來,這個過程應該叫做分離(divergence),因為經趨同后形成的新概念系統既不完全類似于以第一語言為媒介的概念系統,同樣也不與以第二語言為媒介的概念系統完全類似,而是更接近于這兩者的一種混合。
迄今,能夠提供概念趨同證據的研究較少。詞匯概念趨同的典型證據來自于詞匯聯想實驗。例如,Yoshida通過詞匯聯想實驗比較了日語和英語單語者以及35位曾在美國居住一段時間或在美國讀過書的日本大學生詞匯概念趨同的情況[14]。實驗挑選了四類詞進行測試:自然(nature)(e.g.haru=[spring])、日常生活(daily life)(e.g.sensei[=teacher])、社會或思想(society and ideas)(e.g.seifu[=government])以及文化(culture)(e.g.shougatsu[=New Year's Day])。受試者被要求在日語刺激下輸出日語,在英語刺激下輸出英語。在四類測試詞中的一些項,雙語者的大部分反應與英語單語者一致,而在另外一些項,特別測試是文化類時,雙語者的反應跟日語單語者以及英語單語者都不完全相同。這種表現反映了雙語者獨特的概念趨同軌跡。他們中的一些試圖去兼顧兩種文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與單語者具有不同的詞匯概念聯想。關于概念趨同,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自于Ameel及其同事在容器(container)領域的發現[15]。研究者使用Malt和Sloman(cups and dishes)研究中使用的相似的概念指稱[16]。參加測試的是法語單語者和荷蘭語單語者以及法語-荷蘭語雙語者。他們被要求說出物體的名字并且判斷它們的相似性。對單語者反映的分析顯示,盡管法語、荷蘭語兩種語言在命名模式上有一些相似性,但它們還是在許多方面具有不同。例如荷蘭語的bus(=can)在法語中沒有一個對等的概念。荷蘭語者言語中bus的概念可涵蓋法語中的六種概念項,如bouteille(=bottle)和flacon(=small bottle)。荷蘭語中25種可以用fles(=bottle)統稱的物體,在法語中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類別:bouteille(=bottle)和flacon(=small bottle)。
(四)概念的轉移
相互競爭中的概念表征之間的交互作用也會導致概念從L1概念到L2-(L3-,etc.)概念的轉移(shift)。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情況發生在移民者或者長時間在目標語語言社區居住的人身上。到目前為止,概念轉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顏色(color)、情感(emotion)和日常生活(daily life)領域。
在顏色領域的研究方面,Andrew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他研究了具有一個基本詞匯blue的英語與具有兩個基本詞sinii(=dark blue)和goluboi(=light blue)的俄語的區別[17]。他發現俄語單語者和在美國的成年俄國移民能夠區分這兩種blue。相反,未成年的俄國移民在使用這兩個詞時概念有顯著的重合,與英語單語者對blue一詞的概念感知相似。
Pavlenko的研究提供了情感領域概念轉移的證據[18]。情感通常用形容詞以及假分詞來表達(e.g.She is upset.),而在俄語中,像 angry,happy,upset以及concerned這些情感狀態往往通過不及物動詞來表達 (e.g.ona rasstroilas'=she upset[herself]),強調情感體驗的過程性方面。在用英語表達情感時,俄英雙語者對動詞的使用比英語單語者形容詞和假分詞的使用更為頻繁,更為強調情感體驗的過程性方面。
Von Stutterheim使用敘述電影的方法證明了概念轉移的發生[19]。母語為德語的人在描述電影中的事件時,著重強調事件的終點,而母語為英語的人則不會如此。例如,母語為英語的人會說:
Two nuns are walking down a road.(兩個修女正在小路上散步。)
而母語為德語的人則會說:
Zwei Nonnen laufen auf einem Feldweg Richtung eines Hauses.(兩個修女沿著一條小路走向一座房子——其中房子是整個事件的終點。)
英語的框架模式是可遷移的。母語為英語的德語學習者使用德語對事件進行描述時會說:
Zwei Nonnen laufen auf der Strasse lang.(兩個修女沿著街道走。)
其中并沒有提到事件的終點,即“一座房子”。根據Von Stutterheim的解釋,這種框架結構的不同與英語語法中進行體的重要性密切相關,相反,在德語語法中,進行時的作用并不明顯。這種類型學上的差異也反映出了語言使用者認知上的不同,英語中進行體的顯著性促使語言使用者從分析的角度看待事情,而德語則要求語言使用者從整體上對事件進行描述。
(五)概念的磨蝕
在不同語言交互作用下,相互競爭中的概念表征變化涉及的另一過程就是概念磨蝕。目前對于語言磨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語音、詞匯、句法等層次,而對概念磨蝕的研究鮮有涉及。隨著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及第二語言習得等研究的深入,對非病理性特別是詞匯概念損失的研究將會提供更多概念磨蝕的證據(如不恰當的貼標、語碼轉換、借詞、語義轉換、框架遷移、詞匯概念范圍縮小等)。
Pavlenko研究了情感領域可能的概念磨蝕[20]。她調查了動詞perezhivat'(=to experience things keenly,to worry;literally:to suffer things through)的使用。在俄語單語者和英語-俄語雙語者的敘述中,她發現單語者頻繁地喚醒這個概念,雙語者的敘述中雖然這個概念被同樣的視覺刺激引出,但是僅出現一次并且是順便提及。在頻率上的這種下降表明在L2社會化過程中,新的情感概念的內化可能導致不再適應已構建起來的新的概念網絡的舊有概念部分的磨蝕。Ben-Rafael報告了相似的發現,在她的研究中,受訪的在以色列的法國移民的情感詞匯只展現了法語情感詞匯的一部分,如triste(=sad),heuteux(=happy)以及 content(=glad,content)[21]。毫無疑問,這些法語-希伯來語雙語者仍然理解其他的法語情感詞,但是他們不再能夠準確地使用它們,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概念的磨蝕。
四、總結及啟示
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涉及概念的內化、重構、趨同、轉移和磨蝕等多個過程,但它們并非呈歷時性發生,而是呈邏輯性發生。這對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概念改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其理論意義在于概念改變的研究結果能夠驗證或補充語言相對論。語言相對論認為一個人所講的某種語言會影響他的思維方式,語言是思維的一部分,而思維又可稱之為“語言思維”或“概念思維”。對于概念改變的研究可以在從認知的角度驗證語言相對論的假設,并補充完善這一理論。關于概念改變研究的實踐意義在于幫助第二語言學習者深入了解在第二語言學習中概念系統變化的過程,以便促使學習者采取措施或方式促進某些概念改變的發生,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
目前,關于跨語言影響的本質和特點仍存在廣泛的分歧和爭議,比如第一語言在何時、何地、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第二語言的理解和運用以及第二語言學習又是怎樣反作用于第一語言,對于這些問題研究者們仍未達成共識。在概念層面上,目前所進行的研究只提供了一些概念改變的間接證據,將來的研究需要提供直接的證據。同時,在影響概念改變的因素方面,需要進一步研究影響概念改變的各種因素及各種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及相互作用。
[1]Gagné R.M.What should a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professional know&do?[J].Performance&Instruction,1985(7):6-7.
[2]Klausmeier H.J.Concept learning and concept teaching[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1992(27)267-286.
[3]Kecskes,I.Conceptual fluency and the use of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 in L2[J].Links&Letters,2000(1):141-161.
[4]Danesi,M.Sem iotics in Language Education[M].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0:39-119.
[5]蔣 楠.外語概念的形成和外語思維[J].現代外語,2004(04):378-386.
[6][18]Pavlenko,A.Emotions and the body in Russian and English[J].Pragmatics and Cognition,2002a(10):201-236.
[7][20]Pavlenko,A.Eyewitness memory in late bilinguals:Evidence for discursive relativity[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03a(7):257-281.
[8]Pavlenko,A."I feel clumsy Speaking Russian":L2 influence on L1in narratives of Russian L2 users of English[A].In V.Cook(Ed.),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M].Clevedon,UK:Multilingual Matters,2003b:32-61.
[9]Jiang,N.Lexical repres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J].Applied Linguistics,2000(21):47-77.
[10]Kecskes,I.&Papp,T.Foreign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M].Mahwah,NJ:Erlbaum,2000.
[11]Danesi,M.Learning and teaching language:The role of conceptual fluen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5(1):3-20.
[12]Otheguy,R.&Garcia,O.Diffusion of lexical innovations in the Spanish of Cuban Americans[A].In J.Ornstein-Galicia,G.Green,&D.Bixler-Marquez(Eds.)Research issues and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nish:Latin American and Southwestern Varieties[M].Pan American University at Brownsville,1988:203-242.
[13]Kecskes,I.Conceptual fluency and the use of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 in L2[J].Links&Letters,2000(1):141-161.
[14]Yoshida,K.?Konowing vs.Behving vs.Feeling:Studies on Japanese bilinguals[A].In L.A.Arena(Ed.),Language proficiency:Defining,teaching and testing[M].New York:plenum,1990:19-40.
[15]Ameel,E.,Storms,G.,Malt,B.&Sloman,S.How bilinguals solve the naming problem[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2005(52):309-329.
[16]Malt,B.&Sloman,S.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object naming by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J].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2003(29):20-42.
[17]Andrews,D.The Russian color categories siniji and goluboj: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the standard and emigre languages[J].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1994(2):9-28.
[19]Von Stutterheim,C.Linguistics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The case of very advanced learners[J].EUROSLA Yearbook,2003(03):183-206.
[21]Ben-Rafael,M.Language contact and attrition:The spoken French of Israeli Francophones[A].In M.Schm id,B.K?pke,M.Keijzer,&L.Weilemar(Eds.),First language attri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ethodological issues[M].Amsterdam:Benjamins,2004:16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