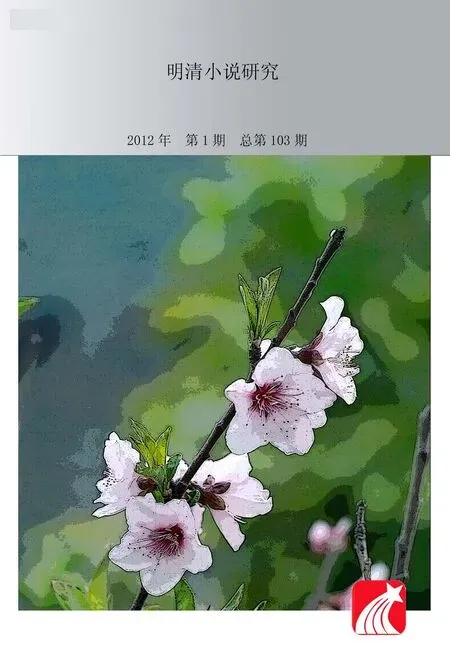從幽明婚戀題材看《聊齋志異》之后文言小說的走向
· ·
幽明婚戀題材是文言小說的傳統題材,大抵分人鬼邂逅結緣、復生離魂結合、夫妻陰陽隔世、神鬼強娶民女等類型。自魏晉至清,隨著文言小說的發展,它本身也形成了清晰可循的演變軌跡。魏晉時的幽明婚戀小說,雖簡樸滯澀而不失幽怨風情;至唐時始肆意言情述異,語帶春風;宋元時雖數量壯觀、種類齊全卻質量日下,泯然書肆間;明代作品悲風淋漓,文采有所回歸;清初的《聊齋志異》猶如平地起波瀾,帶動幽明婚戀題材進入了徹底式微前最后的創作高潮。
蒲松齡對這一傳統題材進行了酣暢淋漓的發揮,在其中寄寓了對美好愛情的追求,抒發了蕭騷文人對艷遇的暢想,并借鬼寫人、以幻喻世,在人鬼共處中展現世情百態。蒲松齡筆下的幽明婚戀,既沒有魏晉時的陰慘之感,也沒有唐時的風月流氣,更區別于宋明的拘謹平淡,而是充滿理想化的色彩。他借傳統的鬼神思維模式為外殼,結撰出了詭譎奇麗的鬼怪世界,但這個世界的精神內質卻是個人化的,對現實人生的關懷、對普遍自我的表現成為他的創作主旨。
《聊齋志異》的巨大成功,帶動了一股創作神鬼精怪小說的風氣。自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本刊行后,近兩百年間陸續有三十幾部《聊齋》仿作面世,和邦額《夜譚隨錄》、沈起鳳《諧鐸》、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王韜《淞隱漫錄》等是其中比較優秀的作品。其中小說多說鬼說狐、侈陳怪異,文筆曲折、才情橫溢。與此同時,在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帶動下,出現了一批抗衡“聊齋體”的筆記小說,如袁枚《子不語》、樂鈞《耳食錄》、俞樾《右臺仙館筆記》等。可以說,在《聊齋志異》之后,文言小說的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分流,大抵是才士之文與學者之文的分歧,一者重才情,一者重學問;一者情節杳渺,盡其曲折之能事,一者諷世勸世,現身說法語重心長;一者偏重個人感情抒發,一者更多普遍社會關懷。這種分流一直持續到清末,成為《聊齋志異》之后文言小說發展最重要的特點之一。而除了總體風格的分流之外,我們從幽明婚戀題材的演變中,也可把握到《聊齋志異》之后文言小說更具體的走向。
一、故事類型的簡單重復
在《聊齋》仿作及《閱微》等筆記小說中,大多數幽明婚戀小說比較陳舊。它們或循著之前的套路,甚至對《聊齋》等優秀作品原樣搬用;或回歸到六朝筆記式的粗陳簡陋,筆墨既無可觀,勸懲亦顯陳腐。
此期人鬼邂逅成婚故事大都難脫窠臼,但有些模仿作品情節婉轉,文辭婉艷,亦有可觀。《諧鐸·鬼婿》、《螢窗異草·祝天翁》、《螢窗異草·梁少梅》、《益智錄·瑞雪》、《埋憂集·趙孫詒》、《淞隱漫錄·馮佩伯》、《里乘·王素芳》、《子不語·贈紙灰》、《斛剩·筠湄幽婚》、《右臺仙館筆記·海鹽吳鴻吉》等,皆是凡男與女鬼的婚戀故事。復生離魂故事,包括人鬼婚戀中以復活、投胎、離魂、借軀為成就婚姻方式的故事,亦包括夫妻情人的兩世情緣。《夜譚隨錄·倩兒》、《耳食錄·夕芳》、《小豆棚·黃玉山》、《螢窗異草·溫玉》、《淞隱漫錄·窅娘再世》等是其中寫得較為動人者,情節概是女子復生嫁與男子,或輾轉幾世終成夫妻,略無新意。有意思的是,清人竟然總結出了鬼魂投胎復生的法門:“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①亦有一番趣味。
夫妻陰陽相隔后重逢,這類故事也較為常見。有亡人不舍家事者:《閱微草堂筆記·癡鬼戀妻》、《子不語·癡鬼戀妻》、《子不語·鬼買兒》、《耳食錄·文壽》、《淞隱漫錄·李韻蘭》、《淞濱瑣話·鬼戀婦》、《北東園筆記·鬼訛詐》等。故事多寫亡人“結戀之極,精靈不散”,紛紛還家了事,或一慰相思。另有夫妻反目成仇類:《閱微草堂筆記·亡夫捉奸新寡之妻》、《子不語·負妻之報》、《耳食錄·大赤蛇》、《女聊齋·陸氏女》、《北東園筆記·鬼妻索命》等。故事多寫亡人痛恨生人再醮或再娶因而殘忍報復。兩類故事均無甚構思,不過宣揚夫妻乃天定,雖死不忍相忘,雖死不應背棄等,是中國古代傳統婚姻意識的另類體現。
廟靈神像與生人婚配,是幽明婚戀中頗有民俗色彩的一個小類,如《子不語·鄱陽小神》中金某死為鄱陽小神,其婦盛裝打扮,言其夫索同往,遂卒。《子不語·紫姑神》述尤琛過紫姑神廟,對廟塑愛憐題詩,是夜,神女叩門自薦,后神女投胎與尤琛成婚。《螢窗異草·瀟湘公主》中邵生娶衡山大帝之女瀟湘公主,后以事下獄而死,成為鬼仙。再有《夜雨秋燈錄·假無通神》、《子不語·陳姓婦啖石子》、《小豆棚·小青》、《淞濱瑣話·鄒生》等。故事多是男性神鬼主動外出找人間女子,除卻《小豆棚·幽宮詩》等個別篇目外,極少出現女子入廟為廟神所睹而被錄的情形。這一方面投射出清代社會的淫風亂俗,一方面也真實反映出了清代女性活動的特點。清朝統治者出于肅清南方邪教,對女性入廟游寺嚴令禁止。如順治年間規定婦女不許私入寺廟燒香,違者治以奸罪。到雍正時江南浙江等省又令禁止婦女游山入寺。《幽宮詩》中末尾亦有:“婦女入廟燒香者,笞四十。”②可見小說創作的思路雖源自前人,作者并無脫離當下的社會實際。
除了以上幾大類,亦有兩鬼之間的婚娶故事。如《子不語·鬼借官銜嫁女》、《子不語·洗紫河車》、《淞濱瑣話·田荔裳》等等。此外,為人與鬼、鬼與鬼保媒作伐的“鬼媒人”也數有蹤影,如《子不語·何翁傾家》、《子不語·替鬼做媒》、《耳食錄·跨衛者》、《醉茶志怪·鬼結婚》、《北東園筆記·與鬼說情》等,尤其是《子不語·替鬼做媒》一文,將鬼文化與冥婚民俗巧妙結合,見出當時社會風氣。
由于有《聊齋志異》等大量文言小說在前,故多有重復創作、難以突圍,表現在對各類題材的蜂擁創作,對各種情節模式的一再摹寫,對《聊齋》中人鬼久處寫法的廣泛套用等等。如《子不語·蔣金娥》酷似《河間男女》,《瑩窗異草·溫玉》乃翻版《聊齋志異·蓮香》,《淞隱漫錄·鵑紅女史》模仿《剪燈新話·翠翠傳》,《淞隱漫錄·窅娘再世》的開頭部分幾乎照搬了《聊齋志異·章阿端》。一些作者甚至以模仿《聊齋》相似而自得,如王韜言:“使蒲君留仙見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過我矣!《聊齋》之后,有替人哉!’雖然,余之筆墨,何足及留仙萬一,即作病余呻吟之語,將死游戲之言觀可也。”③但是,這并非《聊齋志異》以后幽明婚戀題材發展的全貌。
二、情節模式的靈巧變通
前代人對幽明婚戀題材類型開掘殆盡,《聊齋志異》在幽明婚戀寫法及內涵上造詣空前,這種狀況為后人的創作帶來了不小的困惑。他們一方面癡迷模仿,一方面也試圖另辟蹊徑。盡管整體的突破并不大,但有些作品還是不乏亮點:
1.大膽的人物設置
以往的幽明婚戀故事主角,不外乎人與鬼、鬼與鬼。《聊齋志異》以后,出現了許多新的搭配方式,令人眼花繚亂。
有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名人,如《瑩窗異草·夏姬》述屈原與夏姬“幽冥相聚,幾兩千年”④。夏姬是荒淫之尤,屈原乃忠君之魂,兩者竟千載相伴、三生結緣,這種寫法實在有惡搞之嫌。亦有人與神物的同穴之義,如《螢窗異草·玉鏡夫人》。玉鏡夫人本為玉鏡所化,機緣巧合為王友直所得,從此朝夕相伴。后王遂卒于越溪左側,與玉鏡、玉鉤合葬。還有人與狐鬼、鬼與狐的情緣。在《小豆棚·李嶧南》中,狐女月潤之兄娶已亡常氏女風娟,三載而亡。這段情節雖是作為故事背景而設,卻與該文的主題很貼合。小說本為刺淫,故讓惑人之鬼、狐自相克制,以收警世之效。《螢窗異草·綠綺》中李生之父生前與一狐女燈窗共話、兩情眷眷,狐女因李父有家室而離去。后李父死,狐女來相迎。李生后在陰間看到其父納狐女為妾。
新元素的引進亦可歸入此類,如對蠱毒的涉及。《小豆棚·金蠶蠱》中畢路娶蠱戶之女蓮珠,后被其家人害死,復生后娶其姐妹三人。文中對蠱毒的介紹對中原人來說非常神秘。再有《螢窗異草·昔昔、措措》中昔昔、措措均是中惡蠱而死,復生后為蠶神侍女,后雙雙嫁給湖南鄒生。蠱是一種古老的南方巫術,是用殘忍手段配制培養出的巫化毒物。早在干寶《搜神記》中就有對犬蠱、水蠱等的介紹,但進入冥婚題材,似乎僅此二篇。
除了蠱女外,再有《續子不語·僵尸據賊》中生人娶僵尸為婦,《螢窗異草·徐小三》中人與半人半鬼聯姻,《淞隱漫錄·田荔裳》中男子與花妖結兩世奇緣等等。這形形色色的搭配,相當新穎。
2.渾然的情節移植
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是小說家們常用的手段。雖有投機取巧之嫌,卻得以重現許多經典情節。且好的作品往往能在取舍揚棄間把握分寸,將他人作品中情節與自我創作的靈感很好地糅合到一起,讓作品獲得不同與純粹模仿作品的新價值,讓讀者在似曾相識中倍感親切與新奇。
《小豆棚·胡曼》述麥秀中斷腸草之毒,死后與黎氏女之魂私奔。數年后兩人生子返家,黎氏魂與身合。兩人除盡毒草,造福地方。這則故事開頭“是《聊齋·水莽草》一段情景脫化出來”⑤,之后情節又與《離魂記》相仿。故事中鬼與魂私奔生子、不異常人,比人與鬼私奔在想象上又要前進一步。《螢窗異草·挑繡》述鄒大任寓居山寺讀書,經眾鬼撮合,與女鬼挑繡成婚。兩人先是不解床笫之事,后鄒生經友人用孔孟之道啟發,遂成。而鄒生到處炫耀,口無遮攔,挑繡又貪玩愛耍,不解閨禮婦道,讓生之兄嫂擔憂不已。小說對兩人不解風情的描寫類似《嬰寧》,但彼文中王子安是個社會性角色,本文中兩人主人公都是不懂世情:一個似懵懂頑童,不知溫柔鄉為何物;一個是癡傻嬰孩,純潔個性出自天然。這種設置有對嬰寧純真人性的追慕意味,同時,兩人皆癡卻造成了一些戲劇性的相處場面,如友人以圣人之道啟發鄒生、鄒生與挑繡著衣而寢等,都為文章帶來了喜劇效果。
一夫二妻、雙美兼收,是明清之際才子佳人小說中盛行的結局樣式。如《玉嬌梨》、《平山冷燕》、《定情人》、《金云翹》等,其中男子均會得到兩位人品才貌不分軒輊的女子。在《聊齋志異》中,這種“雙女”情節就已經較引人注意,顯示出不同語體作品對時代風尚的同樣捕捉。在《聊齋》以后,作家對“雙女”結構的運用更加普遍,且每每有所創意。如《小豆棚·娟娟》講述女鬼娟娟與張如瞻有約,后附其妹好好之身,姐妹同嫁張生。再有《益智錄·梅仙》中女鬼劉氏助湯武得梅仙為妻,梅仙離去前又幫湯武娶得萬若蘭,劉氏可隨時據其體。正可謂“一佳人而有二魂,妻之如對二艷妻”⑥。之前的借體或是借新死人之軀體即借尸還魂,或暫時借用活人之身即鬼上身,前一種有借無還,后一種時間短暫。像《娟娟》、《梅仙》中所寫長期一身兩魂而相安無事的構想前所未有,但用古人的形神觀念似乎也能說通。然而,作者顯然不是對鬼魂有興趣,奇思妙想之下不過是男性對佳人雙收而家宅安寧的憧憬罷了。
借鑒與套用往往尺度很難把握。在洶涌的創作浪潮中,作家為了趕上潮流,很容易將創作變成重復勞動,尤其是在情節結構相對簡單的短篇小說中。所以從情節來看,后《聊齋》時代中優秀的模仿作品非常少見,大多淪為上一小節所介紹的重寫類作品。
3.充分的人性熔鑄
從魏晉時的可懼鬼物,到唐時的參差可喜,再到《聊齋》中的美麗鬼仙,古人對鬼的看法由排斥漸漸趨向認同。也許在蒲松齡時代時,現實生活中人們還是談鬼色變,但在小說家的筆下,鬼已經是一個可以隨意加工的文學對象了。這種轉變非常重要,它讓作家的創作心態掙脫了敬畏懼怕的陰影,轉而將更多的人性、娛樂性灌注到筆下的鬼身上。
鬼雖來去自由,男女嫁娶也隨便不得。《子不語·吳生手軟》中有女鬼百計與吳生作“歡喜冤家”⑦,吳生終不愿,女鬼只能離去。《瑩窗異草·鬼書生》中,鬼書生與一少艾先后葬于一地。二鬼互慕風雅兼同病相憐,“兩美既合,兼之同穴,但乏斧柯,抱愧鶉鵲”⑧。遂求路人二將其控碟焚于城隍司并啟冢同葬,可見鬼在一起亦要名分。夫妻關系乃人倫之始,鬼亦看重之。《閱微草堂筆記·鬼訟》中載一佃戶見“二鬼冢上格斗,一女鬼癡立于旁”⑩。原來女鬼乃妓女出身,在冥途依然送舊迎新,“凡多錢者皆密定相嫁娶”,故引來爭斗。一旦名份確定,鬼夫妻之間還會相互庇佑護短。如《子不語·城隍殺鬼不許為聻》中,轎夫馬大死后騷擾民婦朱始女,受城隍枷責。其妻乃恨,附朱女之身掐其眼。家人又訴諸城隍。城隍怒,將二鬼嚴懲。
鬼的情感紛擾不異于人。之前冥婚題材中誘人之鬼多是少女,此期有家室之女鬼亦開始紅杏出墻。《閱微草堂筆記·鬼爭婦》中附見聞一則,云:“有合窆與妻墓者,啟壙,則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雙魂,作何相見。”真乃咄咄怪事。此故事尚是筆記雜錄性質,若以小說筆法為之即是陰間的婚戀紛爭。如《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四》中記一學子偶結識一美婦,兩相燕好,婦臨別贈以二釧。日后再至,其夫忽現,手批其頰,并時時詬厲。原來夫妻皆鬼,學子后竟以不起。又如《鏡花水月·張鬼耳》中一女鬼與老嫗論及閨中不如人意事,欲尋求婚外戀情。
人世有買賣妻子之惡俗,冥間亦有之。《子不語·死夫賣活妻》所述故事如其名。李福乃陶家已故仆人,在陰間將在世的妻子陳氏賣與老主人為妾。陳氏遂中風發狂,不治而死。為互相方便還會交換妻子。換妻其實是買妻賣妻的變相。如《閱微草堂筆記·鬼爭婦》中載有人遷其婦柩,誤取別家婦柩,而“婦故有夫,葬亦相近,謂婦為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抵”。婦不從,故鬼斗洶洶,不知結果如何。還有鬼同活人換妻之創聞。《閱微草堂筆記·甲乙夫婦》中甲乙相交甚契,后乙卒,甲婦亦卒。甲遂娶乙婦,而甲婦與乙亦于地下相得甚歡。
另有《諧鐸·香粉地獄》中提及鬼開妓院、《埋憂集·陳三姑娘》中鬼神欲娶民女被丑容驚走等等。這類故事一般見于筆記小說,篇幅短小,品味低下。然而世俗生活場景的融入,卻讓小說在幾百字之內收到了人情鬼意莫辨的效果。它們代表了作家在幽明婚戀題材高潮后尋覓突破的新思路。
三、對題材本身的反思批評
《聊齋志異》之后的一大批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作家對幽明婚戀本身的反觀思索。隨著社會上一些思想家對與幽明婚戀有血緣關系的冥婚習俗進行總結質疑,在小說領域內也掀起了對人鬼結合的普遍討論。這些討論主要涉及人鬼幽婚的存在性、合理性等,亦有少量涉及對亡魂冥婚的一些意見。
多數作品力爭人鬼幽婚存在且合理。《耳食錄·葆翠》中葆翠以幽鬼之身嫁給某生,兩人白頭到老。文中以“情”解釋人鬼冥婚:“若情之所結,自有而無,亦自無而有,由生而滅,亦由滅而生,山川不能間,死生不能隔,而天帝神明不能禁也。”情能跨越生死,故人鬼婚戀完全有可能。《小豆棚·鬼妻》更是以齊生死、等人鬼的觀念為冥婚辯護:“夫鬼,人為之也。人能為鬼,鬼即可以為人。使人即與人合,而以鬼道處其人,則人亦與鬼近矣。茍人而與鬼合,而以人道交其鬼,則鬼特為人用,即人也,何鬼之有?”至于鬼妻促生人壽命這一顧慮,《夜雨秋燈錄·東鄰墓》中女鬼認為:“靜好相依,鬼偶何礙?淫欲過度,人妻亦亡。”《螢窗異草·裊煙》有類似表述。原本古人認為“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故人鬼交接對人不利。而鬼神觀發展到此時,人鬼關系雖仍是陰陽對立,卻已經有明顯的陌路共存意識。紀昀即曰:“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人出以晝,鬼出以夜,是即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即異路焉耳。故天地間無處無人,亦無處無鬼,但不相干,即不妨并育。”但鬼不再是幽邪之物、中者即亡,而是與人死生相隔的另一個世界中的“人”。他們或有形無質,或形質兼有,除了體冷、不飲食盥濯外,基本與人無異,亦可與人共處。如“人未離形之鬼,鬼已離形之人耳”、“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已死之人也”等說法每每見于此期小說,見出時人對人、鬼關系的新理解。
亦有作品對人鬼婚配頗有微詞。《夜譚隨錄·邵廷銓》述邵廷銓與女鬼秋霞交往,后被其友察覺。邵父乃焚秋霞之尸身,以免邵廷銓死為鬼婿。邵知曉后也心有懼意。篇末作者感言曰:
擁骷髏而為佳麗,世間寧少此人哉?但只覺其美而不知其惡耳。嗟乎!蛾眉皓齒,轉盼成空;斷隴荒郊,凝思莫釋。天壤間癡情人能自解哉?一夕歡娛,釀成粉骨碎身之禍,此女亦不智矣!
對邵生來說,他人鬼不分,以骷髏為紅粉,險些淪入鬼道;對秋霞而言,她貪圖歡娛,不解人鬼分殊,將自己身家斷送。文章借佛家之紅粉骷髏寓意說明人鬼之交不可久,可見作者對幽婚之抗拒。對存有“人貴鬼賤”心理的人來說,做“鬼婿”或說娶“鬼妻”確是不智之舉,做“狐婿”則要勝之。正如紀昀所說:“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
對鬼索人偶之荒唐,《耳食錄·婉姑》中總結得比較詳細。文中認為幽婚者概有三種情況:“同牢合巹,共枕連衾”之賢伉儷。一朝離別,中道解攜,故意絕新歡,愿圖合冢,是曰“伉儷情深,溫柔鄉何難一死”;“已偕風卜,末駕魚軒”之準夫妻。泉下凄涼,蒲柳無依,故返求故偶,重牽斷魂。是曰“誓堅皦日,室雖異而穴必同”;“曾謀數面,久許同心”之有情人。未卜他生,倏成隔世,故決意輕生,魂隨千古。是曰“心托清塵,形已銷而誠不泯”。除卻這幾種情況,未曾謀面之人與鬼成婚實在荒謬,一來沒有感情基礎,二來“貞魂稍蕩于地下,則穢史遂流于人間”,影響不好。所以人鬼幽婚不足取:“崔羅什事本無稽,杜麗娘尤安可效?”篇中女鬼最終放棄了主動相求的輕薄男子。《小豆棚·馬二娘》中馬氏亦曰:“游魂所變,半涉荒幻。即令復起,無能益我。適足禍人,不屑為也。”言罷煙然。
有些作品則否認幽婚存在。如《淞濱瑣話·李延庚》中,李明知女為鬼,卻沉迷其美色而浮想聯翩,下跪求婚。面對如此癡情男兒,女鬼的反應令人始料未及:
女益笑不可仰,手拍闌干曰:“請起而言,勿惡作劇。此君自向床頭人演習長技,施之于儂,殊覺英雄氣短矣!世間所傳幽歡冥會之事,盡出文人妝點,悉屬寓言,君乃信以為真哉?即如儂之形質,可聚可散。徒以精靈未泯,故尚游戲人間。然不過宜于冷靜幽獨之境耳,其時則月白風清,其地則深山昧谷,寂寞無人,自行其適。安能再履塵土,在熱鬧場中作生活哉?君休矣。勿生此妄想。”
鬼魂自言“世所傳幽歡冥會之事”皆出于“文人妝點”,事實上并不存在。此論一語道破幽明婚戀故事的實質,直可為自魏晉《紫玉》故事以來的所有幽明婚戀情節畫心。然本文雖言陰陽相隔,人鬼通婚乃滑天下之大稽,但仍不否定鬼之存在。其實,清代小說家對幽婚的討論從未超出鬼神論的范圍,但其中仍有分別。
一類是紀昀這樣本身就有鬼神論思想的。他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中鬼神故事占了大部分,且每每寫得活靈活現。他在《閱微草堂筆記·有講學者論無鬼》中舉數例力辯鬼之存在,并借朱子之氣論反駁朱子:
朱子大者,謂人秉天地之氣生,死則散還于天地……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為一,于事理毋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于何起?當必有心,心地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且未聚以前,此億萬微塵,億萬縷縷,塵塵縷縷,各有所知,則不止一鬼矣。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紀翁誠高明!他不僅雄辯滔滔,還多次援引自身及親友經歷證明鬼之存在。如他提到曾見到死去的婢女文鸞,他的三女兒能自料死期等等,紀昀鬼神信仰之堅定可見一斑。然紀昀雖則堅定,卻亦有不解之處。他曾云云:“鬼則人之余氣,其靈不過如人耳。人不能化無為有,化小為大,化丑為妍。而諸書載遇鬼者,其棺化為宮室,可延人入;其墓化為庭院,可留人居。其兇終之鬼,備諸惡狀者,可化為美麗。豈一為鬼而即能歟?抑有教之者歟?”顯示出了對長期民間觀念、鬼怪小說中積淀下來的鬼之屬性的懷疑。這種懷疑一旦過了界限,就會走向對鬼神怪異的否定。
一類是對鬼神存在有所保留的,寫幽明婚戀僅是有意的文學虛構。俞樾在《右臺仙館筆記》卷二中感慨:“鬼神之事,真有不可知者……鬼果安在乎?延陵季子則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鬼不過人之余氣。人之生也,非舟不能行水,非車不能行陸,乃其余氣為鬼,遂能無所不之。’是鬼轉勝于人矣!”連鬼到底是居室廟還是居墟墓都搞不清楚,生死人鬼之事“孔子亦有所不知”,小說家憑空捏造鬼之種種超能力豈不荒謬?然他對幽明婚戀題材小說的創作卻是不遺余力,《右臺仙館筆記》中相關作品共有31則。俞樾本人對冥婚事跡也有關注,如他的《茶香室叢鈔》中記載過“迎矛娘”之俗,《耳郵》中亦有冥婚習俗記載。這種留意與他的幽明婚戀題材小說創作之間可能有內在聯系,但他對現實民俗和小說虛構仍然有明晰的區分。《瑩窗異草》作者長白浩歌子則專賦《鶯鶯灰》一文,將文人對美麗女鬼的想象徹底推翻。長白浩歌子認為:“人必因疾而后歿,歿之時必羸尫無甚可觀,乃傳記多艷稱之,似乎非物之理矣。”就是玉環、飛燕這樣的傾城美色,一旦死亡,也只會消融于塵土。哪復見美麗容顏?何可與才子冥會?這樣的論調相當有唯物色彩了,而他作為鬼神論的反對者,卻寫出了《溫玉》、《祝天翁》、《梁少梅》、《裊煙》等情節曲折動人的幽明婚戀故事,可見此時作家對敘述者與作者本人的區別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
清代作家對幽明婚戀的討論是小說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產物,是小說批評意識作用的結果。它與清代乾嘉漢學的考證風氣密切相關,亦為我們研究時人鬼神觀念提供了重要材料。整個清代的文學走向,都是崇雅馴而鄙放誕。對于幽明婚戀題材來說,它本以奇思妙想取勝,卻被斥責為詼奇詭譎之詞、艷麗淫邪之說,甚至作家自己也嘲笑幽婚故事的不合理。這種氛圍顯然是不適合題材成長的,雖然受《聊齋志異》影響,一直有創作,然而在作家來說,始終難以真正突破對虛構的心理障礙,只能流于對前人的模仿,或者做一些邊邊角角的小修改。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幽明婚戀題材的反思,與其說是《聊齋志異》之后文言小說發展的新現象,不如說是幽明婚戀題材也是文言短篇小說必然衰落的征兆。
綜上所述,幽明婚戀題材在《聊齋志異》之后,或是簡單重復,或是變通移植情節,或是反思調侃,進入了創作生命力的盲區。對一種文學題材來說,創作不是要去質疑它的現實可能性,而是要運用題材來展現社會生活、寄寓人性思考,尤其是對小說這樣的虛構文學,追究題材的合理性、科學性就更是無稽之談。幽明婚戀這樣綿延數千年的傳統題材,它的發展演變,記錄了同期文學的美學風貌,滲透了當時的文化歷史。而它在《聊齋志異》之后的走向,它想象力的匱乏與道學化的傾向,也見證了中國古代文學走到了收束階段時普遍的反思與收斂。
注:
⑥[清]解鑒《益智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版,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