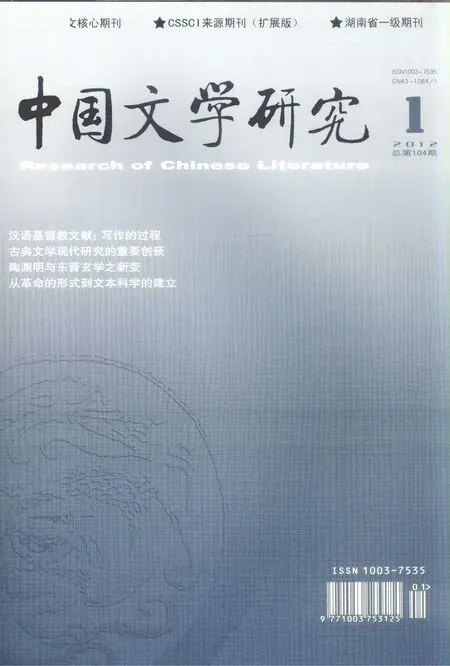從《新中國未來記》來看梁啟超對政治小說的選擇與接受
曹亞明
(韓山師范學院 中文系 廣東 潮州 521041)
在晚清西學東漸的進程中,梁啟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迅速快捷的日文學習方法——和文漢讀法來譯介西學,同樣也是受到實用理性與啟蒙目的的功利驅使,明治日本興起的政治小說浪潮引發了其濃厚的興趣,無意之中顯露了他思想中強烈的政治訴求和新民構想,那就是期望借助西方政治小說的文本形式以實現啟蒙民眾的目的,最終實現“新民”、“新國”的理想圖景。所謂“政治小說”,按梁啟超的界定,主要是“專欲發表區區政見”而作。由此可見,他對政治小說的選擇最為明顯地體現了其政治化的接受視角,而這一選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晚清及五四時期的文學譯介和創作傾向。
一、梁啟超對政治小說的提倡與譯介
早在1898年秋,剛剛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就注意到政治小說對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巨大影響,從域外文學中選擇政治小說作為突破口,借此提出改良小說目標,并在《清議報》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大力鼓吹政治小說,期望借西方政治小說形式實現自己啟蒙民眾的目的,倡導中國的“小說界革命”。
“政治小說”多通過對話、演說、辯論的方式來直抒己見,常與本國政治相結合,雖然缺乏文學性,但的確能起到開啟民智、改良社會的作用。“政治小說”雖然在日本紅極一時,但是最早還是源自英國。19世紀后半期,“政治小說”由日人丹羽純一郎引入日本,使得這一概念在日本獲得了新的生命。明治時期日本所翻譯出版的西方政治小說,有725部之多,到1887至1888這兩年間進入全盛時期。政治小說除了直接展現作者的政治構想外,還有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不管在英國,還是日本,或是中國,其作者都是聲名顯赫的政府官員或社會名流。英國著名政治小說作家迪斯累理(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和布韋爾-李頓(Bulwer-Lytton,1803-1873)的近20部政治小說被陸續譯成日文,成為日本維新第二個十年翻譯文學勃興時期最走紅的作品,而迪斯累理曾兩度出任過英國首相,李頓則曾任英國國會議員;日本的政治小說家也有著濃厚的政治背景,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日本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的作者柴四郎(1852-1922),便是大阪《每日新聞》第一任社長;而在戊戌時代便聲名鵲起,流亡日本時被稱之為“輿論界之驕子”,回國后更是在政治活動中不停奔波的梁啟超,則是中國第一位翻譯政治小說的帶頭人。因此,無論是從創作主體的身份背景和政治訴求,還是從其實用理性的創作目標來看,都注定了政治小說文學性的缺失,也注定了梁啟超在文學成就上的失意。
然而,政治小說的引入和興盛雖然背離了文學的正途,但是卻反映了時代的需求和民族的選擇,歷史則總是以某種偶然和巧合來體現這一選擇的必然性。19世紀70年代,丹羽純一郎在返回日本的輪船上,讀到了英國作家李頓的政治加愛情小說,便如獲至寶,回國后便很快將其譯成日文,就這樣在日本掀起了一場翻譯和創作政治小說的時代風潮。而時光流轉20年后的19世紀末年,歷史又一次把機遇和選擇放到了一條由中國開往日本的海輪上,正是在這艘船上,梁啟超第一次開始閱讀日本政治小說——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據《任公先生大事記》記載:“戊戌八月,先生脫險日本,在彼國軍艦中,一身以外無文物,艦長以《佳人之奇遇》一書俾先生遣悶。先生隨閱隨譯,其后登諸《清議報》,翻譯之始,即在艦中也。”〔1〕(P158)而由于該書是運用漢文直譯體寫成,非常適合當時不通日文的梁啟超閱讀。可見,和文漢讀法這一學習方法的特點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梁啟超的文學選擇。
與丹羽純一郎一樣,身為政治流亡者的梁啟超受到了強烈的思想震撼,他驚喜地發現了政治小說所蘊藏著的政治理想和啟蒙民眾的巨大作用,上岸后便一邊學習日文,一邊運用他的“和文漢讀法”開始翻譯這部小說。為了刊登這部小說,還特地在《清議報》上開辟了“政治小說”欄目,在《清議報全編》卷首的《本編之十大特色》中大力渲染政治小說之特色:“本編附有政治小說兩大部,以稗官之體,寫愛國之思。二書皆為日本文界中獨步之作,吾中國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讀,不忍釋手,而希賢愛國之念自油然而生。〔2〕”自《清議報》創刊始,梁啟超便將《佳人奇遇》的譯文連載于此報,為了配合政治小說的宣傳,還在《清議報》第一冊上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
《譯印政治小說序》是第一篇闡明翻譯“政治小說”重要性的理論文章,也是我國翻譯文學史上的綱領性文獻。梁啟超不僅著重強調翻譯文學作品的重要意義,還在此文中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說”的概念,表現出期望借西方政治小說形式以實現啟蒙民眾目的的愿望。該文開篇第一句便說:“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首次明確界定了政治小說的概念和來源,并闡明了翻譯政治小說的重要意義。梁啟超認為,翻譯外國的政治小說將會起到啟發民智,發揚愛國精神的社會效果。“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3〕(P34)”文中對著者的政治思想以及其所吐露政治思想的目的和產生的效果,一一進行了闡述,并高度評價政治小說對改造國民、改造社會的巨大作用。通過這樣的論述,從理論上論證了“政治小說”的合法性,并把“政治小說”作為一種新的文類引入到中國來。在梁啟超的帶動下,譯介西學的注意力也逐漸從自然科學類著作轉向文學類著作的翻譯,而譯介“政治小說”之風則尤為引人注目,包括《埃及近世史》、《經國美談》、《政海波瀾》、《波蘭憲政史》在內的許多政治小說陸續被翻譯過來。
《佳人奇遇》是《清議報》連載的第一篇政治小說,接著還連載了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這兩篇小說在當時的中國都轟動一時。最打動梁啟超心弦的,并不是政治小說的藝術技巧,而是寄寓其中的政治理想與愛國熱忱。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中,就可以看出其政治化的接受視角:“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美人芳草,別有會心;鐵血舌壇,幾多健者。一讀擊節,每移我情;千金國門,誰無同好?”〔3〕(P55)《佳人奇遇》這部小說通過作者和其他人的對話,表達了作者的政治見解。寫的是作者遍游歐美時,與西班牙頓卡爾洛斯黨員幽蘭、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斗士紅蓮的邂逅,通過對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愛情的描寫,廣泛地描繪了從北美獨立戰爭、法軍入侵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反抗、朝鮮東學黨起義直至甲午戰爭一百多年來中外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歷史畫卷,生動地展現了大國欺壓弱國,以及弱小民族忍受欺侮、慘遭涂炭的悲哀境況,表達了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和獨立的愿望。在這部小說還沒有完全出齊以前,日本就有人批評這部小說是論文式的,而不是小說,不過這一主題正符合了梁啟超當時啟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對于中國的民眾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這便是梁啟超翻譯這篇小說的主要原因,小說的情節簡單,結構松散,其語言有完全漢文化傾向。除了貫串其中的政治意圖外,也許這正是梁啟超選擇《佳人奇遇》作為翻譯對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其漢文化的語言尤其適合運用“和文漢讀法”。
其后,梁啟超又在《清議報》上刊載了留日學生周宏業翻譯的《經國美談》。《經國美談》是日本作家矢野文雄的作品,和英國的李頓、日本的柴四郎一樣,矢野文雄也是一位著名政治家,曾擔任過駐華公使。該小說內容主要寫齊武名士威波能、巴比陀、瑪留等人的經歷,他們歷盡磨難,推翻專制統治,確立民主政治,并在盟邦雅典的支持下打敗了斯巴達,最終爭霸全希臘。小說運用了歷史演義的模式,全文情節曲折多變,人物描寫類型化、理想化,表現了作者爭取自由和獨立的政治思想。而這一歷史演義式的敘事模式顯然啟發了梁啟超對《新中國未來記》的構想。
《佳人奇遇》和《經國美談》都是日本政治小說的代表作,而梁啟超也正是選擇這兩本書作為譯介政治小說潮流之開端,他對這兩篇小說評價很高。在《飲冰室自由書》一文中,他指出,在日本政治小說中,“浸潤于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便是《經國美談》、《佳人奇遇》二書。這兩部小說都是配合當時日本維新運動寫的,帶有鮮明的政治意圖和理想色彩。而且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其主人公的身份都非常相似,都是因在國內從事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流亡異國的政治家,敘述了他們在國外歷經艱難,終于返歸故土的故事,而這一敘事框架與荷馬史詩的《奧德賽》尤為相似,另一方面也讓亡命日本的梁啟超感同身受,自然讀來十分親切,更迎合了這位政治家急切的啟蒙心態。在梁啟超的帶動下,許多政治小說被翻譯過來。據不完全統計,自1898年始,陸續被翻譯過來的主要作品有:《佳人奇遇》、《埃及近世史》、《累卵東洋》、《日本維新女兒奇遇記》、《經國美淡》、《極樂世界》、《未來戰國志》、《政海波瀾》、《游子風云錄》、《雪中梅》、《花間鶯》、《啞旅行》、《千年后之世界》、《新舞臺》、《旅順雙杰傳》、《波蘭憲政史》等。
相對來說,梁啟超等人對于西方政治小說的譯介并不多,反而是對一衣帶水的日本作家創作的政治小說情有獨鐘。西方政治小說的影響多數是通過日本作家的接受和傳播轉道而來,從而對我國近代小說的創作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的創作
2010年,在上海世博會舉行之前,東方出版中心重新整理出版了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和陸士諤的《新中國》,并將三部小說合成一部《世博夢幻三部曲》。通過對中國與世博會歷史的考證,人們驚奇地發現:梁啟超、吳趼人、陸士諤三位文化名人在一百年前創作的小說中,竟不約而同地預言上海將舉辦世博會。《世博夢幻三部曲》由王蒙撰寫總序言,黃霖教授校注并撰寫導讀,有了知名作家、學者的推崇,加上百年世博夢的奇跡般巧合,還有幾代人關于國家富強的共同理想,激發了人們對于過去這些逐漸被冷落,積滿歷史風塵的近代小說的關注,也重新炒熱了梁啟超的這部斷編之作——《新中國未來記》,為這部未能完成的政治狂想曲找到了新的市場契機。
1902年11月(光緒二十八年十月),梁啟超在新創刊于日本橫濱的《新小說》雜志上,開始發表他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新中國未來記》不僅是中國的第一部標明為“政治小說”的小說,也是梁啟超一生中創作的惟一一部小說。這部作品醞釀的時間頗長,但是由于梁啟超政務繁忙,且興味太多,最終僅成五回,而且由于第五回未署名,連作者到底是不是梁啟超本人都還存在爭議。在這部政治小說中,我們看到了當年的梁啟超對于新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與豪情,用他一貫激情豪邁的筆在小說中構想了百年后在中國舉辦世博會的情形。《新中國未來記》開文“話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歷二千零六十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孔子降生是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此后的二千五百一十三年應該是1962年,而不是梁啟超所寫的2062年。話說1962年的正月初一,中國維新成功五十周年大慶典,諸友邦均遣使前來慶賀,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會議新成。小說隨即鋪陳上海世博會的設想:“恰好遇著我國舉行祝典,諸友邦皆特派兵艦來慶賀,英國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國大統領及夫人,菲律賓大統領及夫人,匈加利大統領及夫人,皆親臨致祝。其余列強,皆有頭等欽差代一國表賀意,都齊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熱鬧。那時我國民決議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這博覽會卻不同尋常,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時開聯合大會(是謂大同)。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4〕
在1902年《新小說》第一號“論說”欄中,梁啟超筆挾雷霆萬鈞之勢,以充滿激情、富有感染力的語句高舉“小說界革命”的大旗,借此提出改良小說目標,從域外文學中選擇政治小說作為突破口,并創作了寄寓其政治理想的《新中國未來記》,這部政治小說,是我國的第一部政治小說,也是中國近代采用倒敘法較早的一部小說。但是,陳平原先生也很直率地指出,梁啟超“缺乏創作小說的天分和才華”〔5〕(P21)。確實,如果從藝術技巧上來講,《新中國未來記》確實不算成功之作。從行文中很明顯地顯示出日本政治小說的影響痕跡,而倒裝敘事的技巧又顯然受了美國烏托邦小說《百年一覺》和日本政治小說《雪中梅》的影響。梁啟超借小說預言六十年后(1962年)之中國繁榮富強,以倒敘方式,敘自1902年以來六十年間中國歷史的發展,旨在“發表政見,商榷國計”。整部小說借仿照日本政治小說的演說調,讓孔老先生在博覽會上開設《中國近六十年史》講座,敷演清末時期愛國志士黃克強等人的救國行跡。孔覺民是全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大博士,也是孔子的旁支裔孫子,就這樣梁啟超借上海世博會搭建了小說倒敘的平臺。通過世博會在上海的舉辦,頓使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起勢不凡,借助虛擬性的敘事,直接陳述了有關上海世博會的創意設想,同時分明烘托出梁氏的世博強國夢。通過黃克強和李去病的44次舌戰,我們可以感受到梁啟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間的徘徊和迷茫,也可以窺見其思想的矛盾和變化。黃克強代表立憲派的觀點,擁護君主立憲,李去病代表革命派的觀點,擁護共和政體。其中黃克強的觀點基本上就代表了梁啟超本人當時的政治態度和觀點。《新中國未來記》是梁啟超受西方政治小說影響而寫下的一部標本式的“新小說”,其政治化的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晚清及五四時期的文學譯介和創作傾向。
1905年,在梁啟超的啟發下,吳趼人在《新石頭記》第40回中也寫到了萬國博覽會和萬國和平會。這部小說以賈寶玉再度入世為敘事線索,巡覽近代中國,尋求救亡圖存的良方。此外,受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影響的,陸士諤在《新中國》中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以夢為載體暢想立憲40年后的新中國的美好景象,并在第三回“創雨街路政改良,筑炮臺國防嚴重”提出將在上海浦東舉辦萬國博覽會。通過陸云翔與友琴女士之口對上海進行了細致的描述,二人乘坐地鐵出車站后看到跨過黃浦江的大鐵橋后展開了一段議論。最讓人們興奮的是,陸士謙的文中所述博覽會竟然也是在2010年召開,他還精確預言地點就是上海浦東,跨江大橋橫跨浦江兩岸,黃浦江底也鋪設了過江隧道,電車可以快捷地直行浦東,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切都成為了現實。我們在驚嘆之余,不能不佩服作家們那超凡的預見力!相對于吳研人和陸士謙兩位小說家而言,梁啟超顯然更加重視小說中寄托的政治理想。這部作品作為“新小說”的標本式的作品,是梁啟超受西方和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小說啟悟而寫下的一部政治預言小說,也是梁啟超所發動的“小說界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可以說,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是有關上海世博會的最早的民族想象,同時也承載著中華民族復興的想象,并由此開啟了憲政派烏托邦小說的序列。
三、以“稗官之體”寫政界大勢與愛國之思
為了發表《新中國未來記》這部小說,梁啟超還專門創辦了《新小說》雜志。隨后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申明《新小說》宗旨是:“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傷德育者在所必擯”。〔6〕這既是他創辦《新小說》雜志的目的,也是“小說界革命”的宗旨。中國的政治小說除了《新中國未來記》,僅有《黃繡球》、《猛回頭》、《獅子吼》等寥寥幾部,而且很多為未完之作,藝術上也很不成熟。選擇翻譯和創作承載著政治使命但藝術水準不高的政治小說,這并非梁啟超缺乏藝術鑒賞力,作為學識淵博的學者,他不可能視當時日本和西方的一流作品而不見,也不可能看不到政治小說自身的弱點。其重要原因在于,伴隨著梁啟超強烈求知欲的,是同樣強烈的現實感,他所考察的主要不是某一學理的真偽高低,而是其中對中國現實的作用大小與正負。正是由于政治小說的特點與開啟民智、改良社會的目的暗合,梁啟超才選擇了最能傳達政治思想、最易為國人接受的“政治小說”來實現他“覺世”的政治主張。真正令他感興趣的,并不是政治小說的藝術技巧,而是作者的政治寄托。他對小說尤其是政治小說的推崇,顯然是以之為政治斗爭的手段,這種強烈的功利性使其理論與創作潛伏著危機。
而實際上,政治小說在19世紀西方文壇上并未形成主流,也沒有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即使在日本,政治小說的興起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那就是明治時期,由于自由民權運動的實際需要,才掀起了翻譯和創作政治小說的社會高潮。但是,日本文學在借助政治運動把小說地位提高之后,就與政治分道揚鑣,走上了一條超越政治又緊貼人情世態的所謂“純文學”道路。至20世紀初,政治小說在日本已如昨日黃花,代之而起的是以二葉亭四迷、坪內逍遙為代表的寫實主義文學和以森鷗外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可以說,日本在成功吸收外來文學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文學體系。而令人感到遺憾的卻是,梁啟超從啟迪民智和改良社會的政治需要出發,一味強調政治小說的社會功用價值,而極大地忽略西方與日本現代小說的藝術審美特性,究其根源,是其思想意識仍無法擺脫“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文化觀念。王國維就曾批評說,梁啟超將學問為手段而非目的的做法不足以仿效;而梁本人也坦言承認對他來說文學就是手段而非目的,“新民”才是他理想中的終極思想追求。
然而,梁啟超強調小說的教化作用,將小說當作“改良群治”的工具利器,從長遠意義來看,非但不能抬高小說的社會地位,反而使其淪為了現實政治的機械附庸,最終使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陷入舉步維艱的尷尬境地,只能在啟蒙與救亡的夾縫中艱難前行。川端康成在評論日本明治文學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總認為,明治以后,隨著國家的開化和勃興,雖然出現了一些大文學家,但許多人在西洋文學的學習和移植上花費了青春和力量,為啟蒙事業消耗了半生,而在以東方和日本為基礎、進行自我創造方面,卻未達到成熟的境地。他們是時代的犧牲者。”〔7〕同樣,這一現象在近代中國也普遍存在,正是因為對啟蒙的執著,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一批知識分子也成為了時代的犧牲品。無論是“和文漢讀法”的譯介方法和對日本政治小說的文本選擇,還是其“急于用世”的啟蒙心態,都決定了梁啟超在西學東漸浪潮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過渡時代中的“失意之英雄”。
“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無志。”〔8〕(P100)從《志未酬》一詩中,我們能感受到梁啟超壯志未酬的失意,但是這首詩也依然洋溢著昂揚的斗志和積極進取精神。在經歷了晚清至五四西學東漸的急遽沖擊后,傳統文化的陰影依然籠罩著近代思想文化先驅對異域文化的選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西文化觀決定了晚清對西學的接受是有所選擇和有所偏向的,梁啟超對西學的接受便是典型的“中國式接受”,他在政治化的選擇視角和愛國主義的燭照之下選擇了政治小說這一文體形式,他所譯介的政治小說顯然也經歷了幾重文化的皴染和語言的串味,作為他創作的唯一一部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也具有極為獨特的文化史意義。《新中國未來記》是梁啟超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的政治宣言,融匯了政治家們民族富強的熱切渴望和“中國往何處去”的理性思索。今天距梁啟超寫作此書時,已經一百余年,而孔老先生那場演講,也已經“過去”近五十年了。“回憶未來”的敘述模式和“國富民強”的家國之夢在這樣一個語境下絕不僅僅是一個有趣的思想游戲,還是一份沉痛的民族省思。
〔1〕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梁啟超.本編之十大特色.清議報全編〔N〕.日本橫濱:新民社,1903.
〔3〕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4〕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N〕.新小說(1)1902(11).
〔5〕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6〕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N〕.新民叢報(14),1902.
〔7〕〔日〕川端康成.美的存在與發現〔J〕.日本文學,1985(2).
〔8〕鄭振鐸.梁任公先生.追憶梁啟超〔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