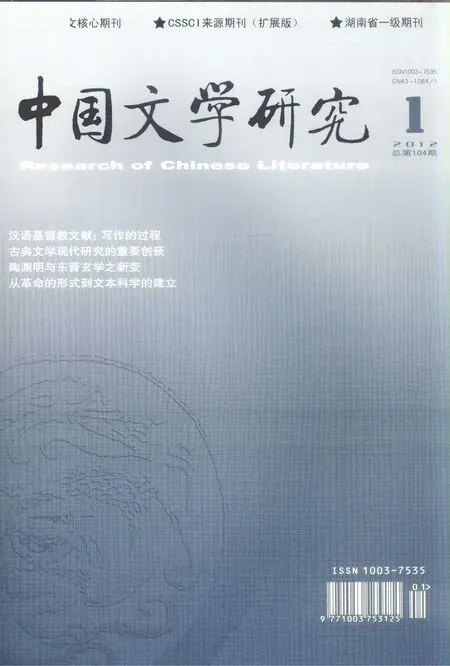古典文學現代研究的重要創獲:任訪秋先生文學史遺著二種校讀記
解志熙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北京 100084)
近兩年,我陸續校錄、整理了先師任訪秋先生的三部文學史遺著《中國小品文發展史》、《中國文學史講義》和《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它們撰寫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而在任先生生前都沒有機會出版,留下的是部分石印講義和更多的手稿,至今已約七十年了。
任訪秋先生1929年夏從河南一師畢業后,隨即考入北平師范大學國文系,1933年畢業后即赴洛陽師范任教,開始文學史的撰著;1935年秋又入北京大學研究院做研究生,師從周作人、胡適之,專攻晚明文學,1936年夏以《袁中郎研究》的論文通過答辯后,重返洛陽師范任教;1940年轉任河南大學講席,自1946年秋隨河南大學遷居開封,從此直到終老,一直生活工作在河南大學和開封。在那時的河南,能夠真正預流新思潮、新學術而全力開展中國古典文學的現代研究者,幾乎只有任先生一人。這一時期,任先生發表了數十篇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其中部分結集為《中國文學史散論》,師友社1948年印行),廣泛涉及從先秦到明清的中國古典文學;但現在看來,真正能夠代表他這一時期學術水平的集成性成果,還是上述三部文學史著作,它們都是任先生的用心之作,其中《中國小品文發展史》撰寫于1936—1937年間,《中國文學史講義》撰寫于1934—1938年間,而《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則撰寫于1943—1948年間。可惜,由于戰亂的時世,無法安心治學,所以這三部書稿都未能完成全稿、及時問世。雖然如此,這三部未完成的文學史論著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現代學術史意義:它們不僅代表了任先生當年最好的學術水平,而且就當時國內學界文學史研究的整體水準而言,也允稱有大見識之佳作。至其局限與問題,也與新文化思潮和現代學術之新的傲慢與偏頗之通病相關。《中國小品文發展史》是中國學術上的第一部小品文史,其校訂稿已連載于《漢語言文學研究》2011年第2、第3期,并附發了我的校訂札記,對其成就與問題,略有評騭。此處就其余二書的創獲與問題,談談自己的若干感想,以就正于學界友朋。
一、新的洞見與新的偏見:關于《中國文學史講義》
與作為專題史的《中國小品文發展史》不同,《中國文學史講義》是一部文學通史,其學術規模無疑更為宏大、學術難度也更為艱巨、因而所耗心力也更為繁劇,而任先生的學術立意也更為高遠。那時,任先生剛從新文化和新學術的中心北京歸來,可謂風華正茂而且訓練有素、學有所成,所以在該書第一章“緒論”中,他總結了截止1934年現代學術界在中國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既有成果之得失,除了肯定“專體的研究頗有幾部杰出的,如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魯迅的《小說史略》、劉毓盤的《詞史》,陸侃如、馮沅君所合著的《詩史》,都是精心結撰”之作外,對斷代史與通史的既有成果則少所許可,尤其致憾于通史之作,以為“就近年來所出版的中國文學通史來看,幾乎連一部令人滿意的作品都沒有”。有鑒于此,任先生提出了自己關于通史的研究旨趣,特別強調的乃是科學的方法、歷史的解釋和客觀的態度,可謂理據充分、持之有故,顯示出躍躍欲試的學術豪氣和超邁前人的學術抱負。
果然,這部文學史講義出手不凡,充滿了迄今仍然值得珍視的歷史洞見和文學卓識。
舉其犖犖大者,比如第二編講述“周至秦的文學”,乃斷制為“周民族的文學”、“楚民族的文學”、“秦民族的文學”三章,即以周、楚、秦三民族的興衰更替為線索來敘述周秦文學之演變,最終結之以南北文學的由分到合與秦的統一,誠可謂綱舉目張而條理井然。按,任先生所說的周民族、楚民族、秦民族,乃是后來漢民族的三個先導族群,仿照當時“方國”的說法,稱之為“方族”或許更為適當些。而迄今為止的文學史論著講到這個中國文學的奠基期,都是先《詩經》后《楚辭》,從西周到東周而至秦,……縷縷鋪敘,視野不免局促,而從未見有如此綜觀時空、概括為三大民族文學者,而任先生的這種概括,也顯然更符合中國上古的社會史與文學史之實際,所以給人實事求是而又舉重若輕之感。再如第四編講述唐詩,任先生力破初、盛、中、晚分期的瑣碎與矛盾,而力推胡適之以安史之亂為界區分為前后期之說,于是乃以李、杜作為前后期的樞要詩人,縱論唐詩前后期之變遷大勢,同樣給人綱舉目張、井然有序、品評得當之感,確非大手筆莫辦,顯示出深造自得者的自信和從容。
任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的大見識,特別表現于一些專章的“余論”一節。這些專章已經比較詳細地敘述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歷程,但作者顯然意猶未盡,還有一些綜觀前后時代的重要文學史識需要集中表達,于是乃于章末特設“余論”一節,所論往往是承前啟后的文學史演進之大勢和文學流變之關鍵,所以特別地精警透辟而啟人思索。例如在敘述了兩漢文學的發展之后,任先生寫了這樣一節“余論”,縱論兩漢文學之史的意義及其后續演變云——
我們現在試統觀兩漢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除了那些汪洋浩瀚的賦,為本期特有的產品外,其余如詩歌、散文,似乎都可以說是魏晉六朝文學的一個序幕。樂府本身固有它不朽的價值,但要專就這一點來說,不僅量的方面不能成為大觀,即在質的方面,也不能令我們十分的滿意,因為有些地方表現的粗疏與幼稚,是不能諱言的事實。所以站在文學史的觀點上來看,與其說樂府的價值在于它本身的優美,無寧說它的價值在于它能孕育出新興的五言體。所以在魏晉能產生出像子建、嗣宗、淵明、康樂諸偉大的五言詩的作家,你不能說這不是多少受樂府之賜。說到散文,漢代的大致可分為三派:一是承先秦的余波的,二是開古文一派的先河的,三是開駢文一派的先河的。其間尤以后者的演進的痕跡為最明顯,從西漢的董仲舒起,似乎已開了一個小小的源頭,后來漸漸的擴大起來,竟成了滔滔汩汩之勢,大有不達于海而不終止的樣子。從仲舒到伯喈,這種劇烈的變化,使你不能不驚,但由伯喈而到齊梁時期的庾子山同徐孝穆,似乎又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把兩漢魏晉南北朝,在文學史上分為一個段落,在此段落中又分為四個小的段落:兩漢為第一期,一切都是做了個開端。魏晉為第二期,不管詩歌同散文,都如日到中天,臻于極盛的境地。南北朝為第三期,漸漸的傾向于形式的雕琢,內容漸趨于貧窳,已大有江河日下的趨勢了。隋為第四期,終于南北統一,因為與異民族的文化的交融,于是文學就不得不舍舊而謀新,走到一個新的時代去!
而在講述了魏晉文學之后,任先生又有這樣一段“余論”——
在這個段落中文學上的成績,已遠非兩漢所能比。先就詩歌來說,從三世紀初到五世紀初,僅僅不過二百年左右,產生了三個偉大的詩人——曹植、阮籍與陶潛。尤其是陶潛,在中國詩歌史上除了屈原同杜甫,可以說沒有再能比得上他的了。魏晉本是五言詩的黃金時代,而陶潛的作品,更是使五言的進展達到了最高峰。唐代五言詩的作者輩出,有誰能來超過他?所謂王、孟、儲、韋要算是最擅長五言的作家了,但還不能望他的項背,其余的,更不必說了。賦的方面雖說大變漢人之舊,但要站在文學立場上看,無寧說比漢人還要高出一籌。散文方面比諸兩漢似乎有點遜色,過去一向人都是這樣說。的確!從這一期中,那還能找出司馬遷那樣縱橫不可一世的大家呢?不要說史遷了,即如班固之淵雅典麗,也很難覓得匹敵。至于嵇康的清竣,淵明的閑適,在質的方面何嘗不好,但這不過是一池一沼之秀美,比著那汪洋浩瀚、風起云詭的江海大觀已差得多了。又何況那才既拙而學復儉的文士們,來裝點詞采,以自炫耀,不更將為班、馬所笑嗎?不過,魏晉確是中國文學復興的時代,因為思想的解放,政治的紊亂,士大夫階級的苦悶,都足以促進文學的發展。所以這一期,在總成績上之超過兩漢,自是無足怪的。
同樣精辟的,還有在講述了南北朝文學之后的那一節縱論南北文學特點及其由分趨合大勢的“余論”,……諸如此類的“余論”,多從文學史的上下文著眼,扼要總結一時代文學的文學史意義,真正是要言不繁、語語中的,顯示出任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發展大勢和關鍵環節,委實是爛熟于心,所以發為議論,才能獨出心裁、深切著明、得其體要,而這些文學史洞見,不僅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史論著中穎然秀出,即使在今天那些寫得越來越繁重的文學史著作中也甚為罕見,所以至今讀來仍然讓人深深感佩其以少總多、啟人神智的力度與美感。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史著中,任先生的這部文學史講稿還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點。
其一是特別注意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文學問題。本來,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文學思潮常常與學術思潮相交融、共消長,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而任先生在河南一師的老師嵇文甫先生乃是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專家,而任先生在北大研究院的導師之一胡適之先生,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國思想史權威,受這兩位老師的深刻影響,任先生治中國文學史,也便特別注意從學術思想的角度看文學問題了(這事實上成了任先生一生治文學史的突出特點)。比如論到賈誼的文章風格——語言夸張、常帶感情而析理明晰,從而肯認他確“是一位頗有政治眼光的文學家”,更進而考究賈誼文章特點之源,則以為“這些特點,我們要追溯它們的淵源,第一是受著縱橫家的影響;第二是受著《楚辭》的影響;第三是受著法家的影響。本來賈生的思想,就不主一家,儒法雜糅,而又羼以縱橫,且富于詩人的氣質,受屈原的熏陶也很深,所以他的作品就形成這樣一種特殊的風格。”這不能不說是發人之所未發、道人之所未道的創見。再如討論到中國歌詠自然的一派詩歌之起源時,便推原到道佛思想的影響及詩人信守之真偽,從而做出了相當深入愜當的區分與評騭——
詠歌自然的詩歌,與道佛的思想實在有著極密切的關系。中國的詩歌在魏晉以前,還沒有產生出有意識來歌詠自然的篇什。到了魏晉以后,因為社會環境的惡劣,與道佛思想的勃興,于是士大夫為的要“茍全性命于亂世”,就產生出陶淵明與謝靈運兩位偉大的詩人。不過陶的修養較深,人格亦高,所以他的作品極其樸質而自然。至于謝呢?雖然也一樣的來描寫自然,但因過于求工,結果反不免于做作。自此之后,在中國詩史中無形就樹下歌詠自然的派。在這派中又可分為田園和山林兩種。前者是詠歌田家的生活,所謂自然也不過是作者描繪生活時的背景而已。后者是歌詠個人隱居的生活,但常常有專一刻畫自然的篇什。本來中國的文人自來就有入世與出世的兩派。入世的自然是處處關心國計民生啦,至于出世的大半都是以道佛思想為主,以守命安命自足,而鄙棄世人之汲汲皇皇為利祿而奔馳。不過出世也有真假之分。真的一派,他們的確是看穿了人生,而自己甘心長為農夫以歿世,他們的胸懷是沖淡的,他們的生活是悠閑的,所以他們的作品才是真正自然的。陶淵明的詩就是這一派。至于所謂假的,大都是熱衷于名利,但是宦途坎坷,于是故而隱居,以自鳴高。他們并不是真個愛好自然,又不是實在忘情利祿,所以他們的作品常常是“心纏機務,而虛言人外”,實在是不自然的。謝靈運就屬于此派。
如此將思想、世情與詩歌綜合聯系進行分析,得出的判斷自然就明敏而中肯了。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特點,即是努力運用辯證的思想方法來看待文學的流變及其與社會的關系。任先生的這種思想方法之萌芽,當然與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嵇文甫之最初的啟發有關,而在三十年代又深受“最懂得辯證法”的魯迅之沾溉(三十年代的任先生即被文壇視為“擁魯派”)和蓬勃開展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之影響。于是任先生在撰寫這部文學史講稿的過程中,便自覺地運用辯證的觀點來觀察文學史的問題,力求在廣泛復雜的關聯中深入發掘文學與社會之矛盾運動的辯證關系,從而發為深切透辟之論。比如,論到東晉文學趣味的流變與其時社會現實之隔閡的奇特關系,任先生便辯證地分析道——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衰微時期。胡人對漢民族的凌逼同壓榨,對中原文化之踐踏與掃蕩,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社會是那樣的混亂,人民終天在黑漆漆的地獄中過日子,按平常的情理來說,在文學上自然應該產生出比杜甫的《北征》同《奉先詠懷》一類的詩歌還要沉痛的作品才是。事實上大謬不然,這類作品很難從當時作家的集子中找到。反之,倒產生了些虛無縹緲的游仙詩,同恬淡閑適的田園詩。這種原因,一則由于時代的不安,一些文人不得不遁逃到另外的一個世界中來,暫且隱身;再一方面,則由于老莊方士思想的熾盛。本來老莊同依附于老莊的方士,從魏晉以來就漸漸的在思想界抬起了頭,正始文人幾無不受他們的影響。到了西晉的初年,似乎因為政治上的統一,文學大有走向唯美化的趨勢,但不久大亂一起,社會震動,一般詩人的作品,就又渲染上了游仙與遁世的色調。不過,文學之唯美化的趨勢并未中止。與所謂閑適詩人陶淵明并世的謝靈運,雖然在詠歌自然這一面,不無受老莊思想的熏染,但在技巧上則純粹是從太康文學一脈相傳下來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東晉的文學乃正始同太康兩種極不相同的文學的源流之并時再現。
那時的任先生還是一個不過三十歲的青年學者,卻能如此辯證地看待時代與文學的復雜關系進而準確考鏡文學變遷之源流脈絡,實在不能不讓人佩服。
以上所說,多是關于一些文學史大問題的大判斷,至于具體到一些文學作家和作品,任先生此著也頗多發明。雖然這部文學史講義篇幅不大,文字比較簡明,但對于一些名家名作則不惜重點突出,敘述品評頗為詳贍而且富于學術個性。比如講到陳思王曹植,任先生就有相當細致的分析,而結尾更回顧學術史,提出了對子建詩學淵源與影響問題的個人觀點——
過去論子建詩者,鐘嶸說他“出于國風”,以后都無異辭。這話固然不錯,但我覺得這還有點偏不概全之病。實際《楚辭》、樂府給子建作品的影響也極大。即如《妾薄命》之與《九歌》、《招魂》,《美女篇》之與《陌上桑》,很明顯的有著源流的關系。子建的思想是儒家的,很有用世之志,但沒機會來使他表現,故抑郁而不得志,所以他的作品上承屈原而下開工部。又因他生長在富厚的境地中,所以風格高華,無絲毫寒儉之色。鐘嶸說“陳思之于文章也,譬鱗羽之有龍鳳,女工之有黼黻。”的確是一點也不錯。
這無疑比傳統觀點更接近曹植的實際。再如張籍之被視為韓派詩人,是歷來相傳的定論,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雖然指出白居易“認張籍為同志”,〔1〕(P382)但還是受限于張籍與韓愈的交情,而沒有把他直接列為白派詩人,其他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史論著,也都在韓派詩人的范圍里來論張籍。可是,任先生卻獨排眾議,斷然將張籍置于白派詩人之列——
文昌是韓愈的好友,一向都把他列進韓愈派詩人中。不過就他的作風說,與其把他放進韓派,無寧把他放進白派更為合適些。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是“詩歌合為事而作”,他平生推評的并世作者除元微之之外,就要數到文昌了。
檢點同時論者,也只有錢鍾書先生同持是論——《談藝錄》論張文昌詩,以為“其多與元白此喁彼于,蓋雖出韓之門墻,實近白之壇坫。”〔2〕(P110)按,錢先生的《談藝錄》寫于四十年代上海淪陷期間,而任先生的觀點則在三十年代末的石印講義里就提出了,可謂慧眼所見略同。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作為一個受過新文學、新思潮洗禮的現代文學史家,任先生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家作品的看法,顯然多了一層世界文學的視野或者說比較文學的眼光,因之綜合觀照、得會其通,一些向來聚訟紛紜的問題,到他那里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如對于陶淵明的《閑情賦》和《桃花源記》的批評,就是典型的例子。關于前者,任先生給予了非常同情體貼的現代闡釋——
為蕭統所譏為“白璧微瑕”的《閑情》一賦,在現在我們看來,倒是很有趣的一篇文章,寫一位害著單相思的男子,因為實際不能與所愛的女子接近,所以就幻想著只要能使自己變為她的日常所用的衣物,得與她常常接近就好了,可是又怕這些衣物過時了,會為她所拋棄,……因為“考所愿而必違,徒契闊以苦心”,于是就想到郊外去散步,也許偶然之間,可以碰到她。但終于是白走了一趟,這時天也黑了,外邊只刮著冷冷的風。于是又盼望著就寢,在夢中或可同她相逢,可是偏偏就“惘惘不寐,眾念徘徊”,害起失眠癥來。不得已,又起來走到門外,望著天邊的行云,想托它把自己的一片相思之情帶給她,可是行云呢,竟無語而逝。這番深情終究無由申訴,末了只有任它去了。周作人先生在他的《苦竹雜記·文章的放蕩》中曾論過梁簡文帝的“文章且須放蕩”的話,中引英國靄理思“文學是情緒的操練”一語,來說明簡文帝的話是對的。從這看來,則淵明雖有《閑情》之作,當也無傷于他為一位隱逸的高士也。
關于后者,任先生則接過梁任公的觀點而進一步發揮道——
《桃花源記》是寫他自己理想的鄉土,梁任公稱它為“唐以前的第一篇小說”。為了這篇東西,后來引起了許多無謂的揣測:唐人像王維(《桃源行》)、韓愈(《桃源圖》)、劉夢得(《桃源行》、《游桃源一百韻》)都認為淵明所寫的乃是仙境;到了宋代的王荊公(《桃源行》)、蘇東坡(《和桃花源詩》)都否認唐人之說,這自然是比較唐人要高明一點,不過他們仍不免拘泥于一方,認為桃源也許是實有其地;直至任公才算一語道破了淵明寫這篇東西的真意。本來文學有寫實、有理想,淵明生逢亂世,退隱田園,所有的詩篇都是他自己的生活的寫照,從他的詩中,看不到亂離的描寫,不過時或有一二憤慨之語罷了,但你能說他對于時代不關心嗎?不過他不愿從正面來表現,他寫出自己的理想鄉,正是要借此來反映他所處的是一個亂離的社會。后人不明白這一點,來任意的推測,結果淵明的真意,竟被他們所曲解了。
顯然,正是這種有別于舊派學者的世界文學視野和比較文學的眼光,才使任先生能夠快刀斬亂麻,徹底廓清歷來舊說之迷誤,而直探淵明為文苦心于一千五百年之后。而特別難得的是,任先生在比較品評中西文學時,并不止于類比,也很注意區分其間的差異。比如在評價白派詩人時,任先生使用了“寫實”這個西洋文學的名詞,但又慎重地區分了元白的寫實與西方近代的寫實之差別——
近代的寫實主義,大抵是專來表現社會的黑暗,而不隨便發議論,也可說是專寫病案,而不開藥方。只不過提出問題,讓讀者去評判,去解決罷了。可是樂天同微之就不然了,他們是要來諷喻,同西漢的經生們拿三百篇當諫書的意味頗有點相同。他們不采取正顏厲色的方式,而拿詩歌來從容諷諫,所以不但要指出病狀,而且還要列出醫治的方劑,希望當道能夠隨時采納。這種差異的產生,我覺得還是政治背景不同的緣故。近代的寫實主義,乃是產生在民主政治之下,自然是以博得大眾的注意為目的,而九世紀的寫實主義,是產生在專制的政治之下,所以不能不偏重在天子這方面。元白的新樂府中,之所以不免常常要羼進大量的說理成分,的確也是無足怪的。
如此見同而知異,較諸當時和后來學術界簡單照搬西方文學概念術語來論中國文學的做法,就慎重而且明達得多了。
從總體上看,這部文學史講義講述先秦到唐詩的部分,寫得比較從容詳贍、深入淺出、新見迭出,而宋元明部分則顯得比較簡略而乏深入獨到之論。考其原因,一則當然與抗戰戰局的轉變有關。先秦到唐詩部分,寫于戰前和抗戰之初,那時作者生活比較安定、研究條件也比較好,所以得以從容地考究與寫作;而1938年之后戰局轉急,不斷顛沛在亂離途中的作者,自然沒有條件和心情仔細續寫了,而不得不草草結束,以至清代文學沒有來得及續寫。二則恐怕與作者的學術準備有關。應該說,三十年代的任先生對先秦至唐代的文學已有獨立的研究,學術準備比較充分,而對宋元明清文學,除了關于晚明詩文尤其是小品文有比較充分的研究基礎外,對其余詞、曲、小說都還缺乏獨到的研究(四五十年代之交,任先生的學術興趣,才轉向宋元明清的俗文學以及近現代文學),所以這部早年的文學史講義論詞、曲、小說的部分,多依據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比如講詞,就多依據王國維和胡適之二家之論(任先生1934年在北平即撰有《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一文,同時又看到胡適的《宋詞人朱敦儒小傳》一文)而加以折中綜合,于是將兩宋詞人簡單區分為溫婉派、豪放派和清淡派三支,所謂清淡派其實只有朱敦儒一人支撐,卻于一代大詞人李清照未置一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缺憾。其實李清照與朱敦儒都是由北到南的詞人,如果說南宋詞壇真有所謂清淡一派,《樵歌》的作者朱敦儒何以當之?一代才女李易安或許更適合為其開山人物吧。
當然,關于宋代以前的文學,這部文學史講義也有措置未安之處。比如,講唐代文學而只限于唐詩,對韓柳主導的唐代古文運動,則棄置不論,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失。而造成這個缺失的原因,倒未必是任先生對古文缺乏研究,而是他的文學觀念存在著新的傲慢與偏見。從這部文學史講稿里可以看出,三十年代后期的任先生雖然已經認識到“中唐實是文學上的革新時代,韓、柳是努力于散文的革新,而元、白則是努力于詩歌的革新”,但實際上他推尊的乃是元、白,而對韓愈的人、文、詩則頗為不屑,所以有這樣的譏議——
退之最初本是極倔強的人,但遭了這次打擊后,銳氣頓消,馬上可變了那副剛直的面孔,反來阿諛乞憐了。當他到了潮陽之后,給憲宗上表,先說那里地方的惡劣,他年已衰邁,受不了那種折磨;次說他“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假若天子不憐恤他沒有人肯替他講話;接著說他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但好學問文章,將來那種歌功頌德的文章,自己敢說勝任而無愧;末了又說了一大堆諂諛的話,勸憲宗把自己的功業應定之于樂章,告之于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俾可垂之萬世而不朽。表上遂改授袁州刺史。
…………(中略)
不過我總覺得退之的詩缺乏樸質與自然,所以令人感不到親切的意味。他學工部的奇險,結果流而為虛矯,學太白的豪放,結果流而為粗獷。至于李、杜兩人的長處,所謂空靈飄逸與懇摯質實,則彼實槩乎其未之聞。至退之的作品,為什么竟走上這樣一條路?我認為還不外他的思想與修養的關系。我們試讀他的散文《原道》,就可以看出他是以道統自任的一個人,而他的朋友張籍也曾勸過他來擔負道統(《新唐書·一七六·張籍傳》)。因此他就不能不故意的裝腔作勢,擺出規矩尊嚴的樣子來。加以他又是不能忘情名利的熱衷者,他勸他的兒子要努力讀書,因為惟有讀書,才能夠富貴利達。……(中略)這種純以利祿來誘導子弟,就可以曉得退之這個人的修養是如何了。像他這樣不真率的人,怎能寫出真率的詩呢。
其實呢,所謂封建時代的士大夫,當遭貶左遷而不得不上書“謝恩”之際,對皇帝說一點軟話,乃是官場的常理常例,又何嫌于退之?何況退之“認錯”的官話套話,也未必就沒有皮里陽秋的意味在,豈能按字面意思句句當真?至于韓愈做詩希望兒子讀書上進以期將來“比肩于朝儒”(《示兒》),亦是那個時代的人之常情,他能夠那樣坦白地寫出來,而不故作淡然蕭散之態,正見出其為人做詩的坦直真率、表里如一,又何損于他的思想與人格?
推原任先生之所以對韓愈有此譏議,以至對整個唐代古文運動都棄置不道,其實還是緣于他仍受限于新文化、新文學和新學術觀念之影響。從這些“新”的立場上看,“文以載道”的古文,由于其所載之道,既不合近代“人的文學”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正確性,也不符合“純文學”的藝術正確性和純粹性,自然難免遭否定之災,而韓愈則因為是這個道統和文統之開山,也就首當其沖,成了最遭批判的古典作家了。批判最激烈也最持久的,就是任先生的導師周作人。按,自三十年代以來,為了抬高所謂獨抒性靈的“言志”小品,周作人極力非難“載道”的古文之首領韓愈,寫了不少聲討文章,簡直視韓愈為不可饒恕的假道學、戕害文學的罪魁禍首。①而說來有趣的是,周作人之狠批韓愈,不僅遵循著“載道”有害“作文”的新理念,而且沿襲了宋代一些理學家頗嫌韓愈為道不純、作文害道、人品文品皆有缺的舊說法,卻不解韓愈之“不純”、“有缺”,正是他與故作正經的偽道學之不同處、正足見其為人為文之可愛也。然而,乃師周作人對韓愈和古文的批判,實在相當深刻地感染了任先生。由于截止1938年周作人尚未公開附逆,所以任先生這部文學史講義的先秦至唐代部分,仍然頗多援引周作人的觀點,而任先生對韓愈和古文的看法,顯然與周作人如出一轍。這種出自新文化、新文學理論邏輯的批判,當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可也確實帶著新的傲慢與偏見,而不免苛求和曲解了古人。究其實,韓愈乃是針對中唐以來藩鎮割據、佛老糜費、民不聊生、國將不國的現實,而思有以矯之,于是才重倡古典人文主義思想和古典藝文的傳統,豈可以其“文以載道”之不合于現代文學的理念和理想,就不加分析地予以拒斥?并且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說,在古代文論中,分體言之,則“詩以言志”、“文以載道”,合而觀之,則同一人既可寫“言志”之詩也可做“載道”之文,并不覺得有什么矛盾,今人又何須從狹隘的純文學觀出發去特意褒“言志”而刻意貶“載道”?〔3〕更何況,從中外幾千年的文學史來看,文學又何嘗能純和可純到僅只是為文而文地獨抒性靈趣味——從某種意義上說,“不純”的生活感想和深摯的道德感懷乃是文學創作的初衷,唯此才能使文學言之有物、充盈堅實,然則,有感而發、有所持守的“文以載道”,即使不合于今,又何足為古文的千古不赦之罪?
由此看來,新文化、新文學和新學術的觀念,在使任先生獲得超乎往常的視野和卓識的同時,確也不免使他有所遮蔽和偏見。因此如何克服新的遮蔽和偏見,從而對中國文學史做出更富歷史同情的批評和更合歷史實際的分析,對年輕的任先生來說尚須時日以深長思之。
二、辯證之卓識與自我之糾正: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
令人欣喜的是,到了四十年代的中后期,經過持續不斷的戰火洗禮和深思熟慮的學術思索,人到中年的任先生在學術上顯然地趨于成熟,所以才能于繼續發揮新見卓識之外,自覺地克服年輕時的遮蔽與偏見,特別體貼把握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現象和問題的復雜性,從而做出更為辯證中肯的分析。這在他此一時期的學術論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里多所表現。
如所周知,在關于中國文學的現代研究里,中國文學批評史是成績最為顯著的一個部門。自1927年陳鐘凡先生出版了比較簡略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后,到任先生完成他的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論著的中冊之第二分冊的1948年初,在這短短二十年間,先后出版有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1934年出版,下冊1947年出版)、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年出版先秦至六朝部分,1943年至1945年又出版了增訂的《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和《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方孝岳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年出版)和朱東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年出版)。郭、羅二著都是考鏡源流、詳述歷程的宏篇巨制,允稱扛鼎之作;方、朱兩書,則以批評家為主,評騭短長,誠所謂片言居要,頗有精審之論。然則,在這種情況下,任先生撰寫這部篇幅不大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又所為何來、特點何在?一則當然是為了教學之需。按,任先生1943年在河南大學開“中國文學批評”課程,此時除了朱東潤先生的著作尚未出版外,其他郭、羅、方三人戰前出版的著作,任先生應該都是看過的(書稿中明確提及的是郭著)。就教學而言,郭、羅的著作均詳贍繁富而都不免博而寡要,未必適合教學之用;而方著篇幅簡短、時見精義,卻不免過于具體以至零亂而缺乏史的概括勾勒,其實也不大適合教學之需。這應該就是任先生撰寫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的直接動機。不過,這并不是任先生撰寫此書的唯一動機。事實上,任先生自二十年代末走上學術之路以來,即對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問題頗感興趣,三十年代更有獨立的思考,部分成果已寫入《中國文學史講義》,此后也一直持續鉆研、思考轉深,比如在1940年隨河南大學遷徙于嵩縣灘頭之際,任先生即撰寫了《<文賦>疏證》的專著(現存手稿)……而隨著研究和思考的深入,他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問題,顯然有了不同于時賢的獨到看法,乃謀著述以自表見,這應該說是他撰寫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論著的另一個重要動機。
誠如舒蕪先生晚年評論他的父親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時所說,“文學批評是為文學本身服務的,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也應該為文學史的研究服務,這一點可惜并不是文學批評史家們經常記住的。”〔4〕舒蕪先生并將此概括為“文學與批評一貫的原則。”這是不錯的。但當舒蕪先生由此進而發揮說:“其實,根據‘文學與批評一貫’的原則,也只有對一國文學本身是內行,然后對這一國的文學批評,方能是內行。”〔5〕這話若在近代以前說出,自然無可疑議,但若就五四以后而論,則縱使相當內行于一國文學,也未必就是能夠明了一國文學之究竟的充要條件了。在一個新的世界化了的時代,正如西諺所云:“只知其一者,是為不知”。當然,對方孝岳先生這類新舊過渡時代的學者,是應該諒解而無須苛求的。任先生比方孝岳年紀略小,但他自童蒙及少年時代,受的仍然是傳統教育,卻又不必受科舉應試之限,所以對古典詩書之熟習,并不讓與傳統士子,甚至眼界更為開闊些,而稍長入新式師范、大學、研究院,更系統接受新文化、新文學的教育和現代學術以及傳統治學方法的訓練,成為既有舊學根底又有現代眼界的新一代文學史研究者。其“現代眼界”表現之一,就是具有比較開闊的“世界文學”視野,尤其是比較了解西方文學和文學觀念,故此當他們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時,就不僅“對一國文學本身是內行”,而且還有一種來自世界文學的比較會通以至跨學科的眼光,因而也就能夠“對一國文學本身”之變遷大勢“識其大體,明其究竟”了。此所以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雖然比較簡要,卻絕不簡單,而獨具手眼和創見。在開宗明義的第一章,任先生就參考西方的文學批評概念,提出了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兩條方法論。第一就是應該從“文學批評與文學演變之關系”著眼,他以為——
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就關系上說,是互為影響互為因果的。蓋批評之產生,最初由于對流行作品之分析與歸納,其結果批評之傾向常與一時作品之風尚相應合,故文學批評之轉變,恒隨文學之趨向為轉移。……至批評、創作中間相互影響之樞紐,又常在于后者。大抵文學本身,最初自有其演進之趨勢,在此趨勢未達至頂點之時,有一二學者出,窺出此種之趨勢,因設為理論以推波助瀾,助長其發展,加速其演進,于是風氣以成。迨風氣既成,而此趨勢轉眼即達于最后之境地,于是追風趨時者紛紛而出,因之流弊亦隨之而生。當此時期,又有一二明哲之士睹此趨向已無由再行發展,如循此而不變,只有江河日下,愈趨卑陋,于是遂倡為新的理論,而大聲疾呼以矯之。于是所謂文學上之革命運動以興。及此種運動成功之后,創作又走入新的方向,過一時期,又有流弊,于是再有人以另一種理論出而矯之。如是循環往復,遂形成所謂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
這不正是舒蕪先生所謂“文學與批評一貫的原則”之更為辯證的說法么?當然,此前的文學批評史研究者,事實上也不可能脫離文學的實際來研究文學批評史,但發為自覺而且辯證的方法論之思考者,乃是任先生,而“文學與批評一貫”之典型表現,就是籠罩一時以至數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那正是任先生文學批評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同時,任先生又提出研究文學批評史的第二個方法論,即必須注意“文學批評與學術思想演變之關系”,他以為——
文學批評之產生,最初往往附麗于哲學思想,即由某種哲學觀以觀察文學,而得到某種之見解。即以吾國先秦而論,儒家思想為積極的入世主義,故其文學觀即為實用主義的。道家為消極的遁世主義,故其文學觀即為自然主義的。稍后則文學批評之風氣又常隨哲學思潮以為轉移。即如在兩漢為儒家一尊時代,因之當時之文學批評,鮮能逃出實用主義軌范范圍之外者。魏晉南北朝為老莊及佛學盛行時代,于是兩漢時代文學批評之風為之一變,自然主義與唯美主義遂代之而興。此后而隋唐,而元明,文學批評幾無不與學術思想互為消息,故吾等研究中國文學批評之演變,應把握其所以演變之樞紐。此樞紐為何?一曰文學本身之趨向,二曰時代思潮之演變。明乎此,則中國文學批評之演變,及其所以演變之故,可以知其大略矣。
自然,以往和并時的文學批評史研究者,事實上也不可能不注意文學批評與學術思想的關系,但發為自覺而且辯證的方法論者,仍是任先生,他對此持守而不怠,成為其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此外,任先生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以至整個中國文學史,還有一個沒有說出的方法論,那就是來自外國文學修養的比較觀照之手眼。應該說,正是以上三條方法論的結合,使得任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雖不能與時賢的著述在詳博具體上爭勝,卻顯著地具有了迥異于時賢的特點和優勢。
那特點和優點之一,就是對“中國文學批評之演變,及其所以演變之故”,能夠“識其大體,明其究竟”。而要做到這一點,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即如郭紹虞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里,也試圖扼要概括,將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分為三期:一、文學觀念演進期(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二、文學觀念復古期(隋、唐、宋)。三、文學批評之完成期(元、明、清)。正如任先生所批評的那樣,“顧此等分法,余覺其甚為籠統,未能顯示其錯綜之變化。故本書不從其說。”而任先生則以上述三種方法論作為觀察的角度,而綜觀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于是乃能“識其大體,明其究竟”,以為自先秦至清末的中國文學批評,就其演變之大勢而論,可概括為三大思潮交替錯綜發展的六個時期。那三大思潮就是實用主義、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六個時期則為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其中尤以對先秦至唐宋時期的文學批評史源流演變之大勢的論析,最為得其體要而且圓通得當。如第二章概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之演變大勢,首先指出先秦哲人各自發揮其思想,而以儒、道、墨最為著名,后來“墨家思想中道夭殂,惟儒道二家源遠而流長,而其影響亦至巨,整個之中國文學批評,其思想基礎幾無不源于此二家。”而“儒家重實用,道家重自然”,既是中國哲學也是中國文學上之實用主義和自然主義思潮的源頭。接著縱論兩漢至唐宋的文學批評史,乃將文學與世變、文學與學術、創作與批評融為一體,發為考鏡源流、洞察錯綜之卓見——
漢初當大亂之后,學術思想悉承先秦余波,此時文學,楚辭之風最盛。循此以進,則頗有漸趨于唯美主義之勢。無如自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府遂以通經為仕進之階梯。以后經學漸盛,而一般經學家之文學觀,悉以儒家為準,故彼等之見,無非實用主義者。漸漬漸久,此等觀念影響于整個社會,以揚子云之辭賦家,最后亦薄文辭,而目之為雕蟲篆刻。以王仲任思想之反時流,而其文學觀亦仍不脫實用主義之窠臼。楊、王二子尚且如此,則其余可以知矣。東漢末年,君昏臣嫚,政府橫征暴斂,人民不堪其苦,因而爆發黃巾起義,接著又發生董卓之亂。迨董卓既平,遂分而為三國。西晉統一僅短短數十年間,天下又分崩離析。此時期可謂中國政治最不上軌道之時期。因大亂之故,于是名、法、老、莊及西方之釋,遂乘機而起,儒家思想已失其統治之效力。此時反映于文學批評者,為自然主義與唯美主義之代實用主義而興起。所謂自然主義,乃系受老莊思想影響之作家,彼等以自我表現為目的,無視格律,而更不含絲毫實用之觀念,此派可以叔夜、嗣宗、淵明等為代表。唯美主義派乃系沿南方文學發展之趨向而產生者。此派之見解實肇端于相如與子云,至曹丕《論文》出,遂大張旗鼓,以后陸機繼之而加以發揚,至沈約、劉勰出,而此派之理論遂臻于完成。當唯美派全盛之時,一時希聲附和者遍天下,因之流弊叢生,于是久已潛伏之自然主義派、實用主義派遂起而矯之。由此發展,遂釀成唐代之復古運動焉。
隋代為時甚暫,一切均為唐開其端。唐初文學批評,其趨向有二:在詩歌上,有自然主義派之反齊梁,陳子昂、李白可為此派之代表;另外則有實用主義派之沿齊梁,杜甫可為此派之代表。在散文方面,仍為實用主義之反齊梁,獨孤及、蕭穎士等可為此派之代表。至唐之中葉,韓、柳、元、白出,不論彼等在詩歌上見解有何不同,但其為實用主義則一致。韓、柳從散文方面倡復古之運動,而元、白則從詩歌方面向復古發展。總之,彼等均為儒家思想之信徒,其反對六朝之無所為而為之文學觀,實毫無二致也。
唐末五代唯美派之伏流又起,至北宋之初歐陽修出,又從事于二次之復古運動。但實用主義派為實用計,故主于文質并重,雖注意內容,但并不輕忽形式。試觀韓愈雖反齊梁,但推尊揚、馬,可以知矣。但當北宋中葉,一般道學家出,彼等因受道家自然主義之影響,故輕視文采,但又受孔、孟實用主義之影響,故特別尚用,因此遂以古文家之重文為足以害道。至南宋朱子出,始矯周、程諸子之偏,而中國傳統之文學觀,遂于焉以成。
如此將實用主義、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三大文學思潮在一千八百多年間的源流變遷及其錯綜調和之大勢,解說得一清二楚、各得其所,卻只用了寥寥千余字,真是言簡意賅、筆力千鈞!比較而言,此前或同時的文學批評史著作,在詳博或精細上皆有足多者,但像任先生這樣洞察關鍵、提綱挈領的大手筆和大見識,則似乎不多見。
顯然,實用主義、自然主義和唯美主義這樣的概念術語都來自西方,甚至是跨學科的概念,因此把它們移用來概括中國文學批評思潮,就必須注意它們的適用范圍而不得不有所訂正。對此,任先生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實用主義這個概念,現在往往被籠統地當作功利主義的同義語,概指一切有倫理道德、社會政治追求的文學取向,所以從古代儒家、法家的文學主張以至現代的革命文學主張,都被稱作實用主義的或功利主義的。但任先生卻對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做了分疏,以為“實用主義派為實用計,故主于文質并重,雖注意內容,但并不輕忽形式”,而僅以功利主義指稱墨家、法家的文學主張,對于唐宋以來的實用主義文學主張也給予了具體的分析——“竊以實用主義派自唐以后分為兩支:退之、永叔等以實用為主,而實竊取唯美派之長;而理學家則比較接近自然主義,及走于極端,則內容上為實用主義的,而在形式上則為自然主義的。”這就中肯得當多了。至于用“自然主義”來概稱中國文學主潮之一,任先生是經過一番慎重仔細的考究的。事實上,任先生起先使用的概念乃是“浪漫主義”,但后來幾經考慮,覺得還是用“自然主義”這個概念更為恰當貼切些,所以遂把“浪漫主義”改換為“自然主義”,現存手稿上還有個別涂改未盡之處。在中國,自然主義的文學思潮當然導源于老莊,而到魏晉時期乃臻于極盛,在任先生看來,中國的自然主義文學思潮實近似于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它們往往能在文壇守舊沉悶之際,以回歸自然、自由表現相號召,發揮出顯著的解放作用。即如——
從嗣宗到淵明這一派自然主義的作家,有些地方很有點近于歐洲十八世紀的浪漫派,其返回自然,一也。主于自由表現,二也。輕視社會之規范,三也。對舊時代之思想,是革命的態度,四也。將個人之見解寄托于理想的故事之中以表現之,五也。(如淵明的《桃花源記》)所不同者,僅浪漫派主于表現奔放的熱情,而此派則否耳。(按,歐洲之浪漫主義為老莊思想與希臘思想混合而成,而中國則純為老莊的,故重收斂而不重發揚。晚明文人稍有不同,即因受王學影響所以重發揚而不主收斂,故晚明文學為浪漫主義的。)所以至此派對后世之影響,以其在內容上重視自我的表現,在形式上主于信腕直寄,不擬古,不模古,無視一切的格律,故寫出之作品,其風格之高者,則清新活潑,一片化機;即其次者,亦如天馬行空,不受羈勒。故在中國文學上,凡當文壇風氣流于拘泥迂腐、陳陳相因之際,往往宗法此派者一出,即頓改舊觀,而視聽為之一新焉。
這是非常明澈精辟之論。顯然,任先生是在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啟發下,才在中國發現了近似的文學思潮的,但在一番比較考究之下,他最終還是放棄了西方的浪漫主義概念而決定啟用中國固有的“自然”論,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在他看來,如其中國本土的概念已足以為一種主導性的中國文學觀念、文學思潮命名,那就盡量不用異域的概念。這是一種更為成熟的學術態度和風度。應該說,“自然主義”確是一個更明快也更符合中國文學實際因而更具有本土特色的概括,所以毫無疑問,用它來為中國的一種主導性的文學觀念以至于文學主潮命名,乃是任先生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大發明和貢獻——由于他的這一原創性的概括,中國文學批評史以至中國文學史的上許多頗為糾纏的問題,都可渙然冰釋了。
而尤為難得的是,任先生并不以三大思潮的概述為滿足,更進而著力揭示這三大思潮在中國文學史上如何“錯綜之變化”的復雜情況,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入地辯證分析中國文學史復雜實際的卓見。比如,關于隋唐時代的“文學復古”,似乎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而一般學者向來都認為,支撐這一時期文學復古的思想觀念就是儒家的實用主義。但任先生卻指出,在隋唐之際針對唯美主義而進行文學復古運動的,其實有自然主義和實用主義兩種思潮。稍后,在唐代真正完成了文學復古運動之大業的,乃是杜甫和韓愈等,而杜、韓之關懷世道與治道,似乎顯然地宗奉著儒家的實用主義了。然而,任先生卻從唐代文學與此前南北朝文學(“北朝文學重實用,偏于所謂實用主義;南方文學重華美,偏于所謂唯美主義”)的關系著眼,指出以杜甫、韓愈為代表的成功而且成熟了的文學復古論者,乃是經過了唯美主義的洗禮,所以其文學觀實際上是實用主義與唯美主義的一種錯綜之綜合和辯證之揚棄——
就在文學批評上,實用主義派也又重新抬起了頭。初則,由北朝的幾個文人發端,到了唐代,繼起者引端賡緒,于是就造成了震撼一代、影響百世的復古運動。不過,我們要以為唐代的實用主義派與六朝以前的實用主義派,在創作的見解和態度上完全相同,那就錯了。因為這是經過一個唯美主義全盛階段以后的實用主義。雖然在口號上他們是反對唯美主義的,而實際是經過了一番揚棄的過程的。他們遺其皮毛而襲其精神,所以才造成了韓、柳二人在散文上偉大的建樹。至于詩歌,工部的作品同見解,更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在鎔鑄南北文學之長,而奠定了他的詩圣的地位。明乎此,才能了解由隋到元這一段的文學同文學批評。
這實在是辯證分析、切中肯綮的洞見與卓識,為此前和迄今的許多研究者所隱約有感卻未能闡明者。而任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見識,則無疑是得益于他的辯證的思想方法。前面說過,自三十年代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以來,任先生就嘗試著運用其歷史觀,尤其是辯證法,來觀察和分析中國文學史上的復雜問題。到了四十年代,任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尤為服膺而心儀,運用起來也更為得當和得體。這在那時研治古代文學的學者中,是很少見的。當然,任先生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他著意領會的乃是其辯證地觀察復雜問題的思想方法。正因為如此,他這一時期的文史學研究,才特別注意文學史的“錯綜之變化”和“揚棄的過程”,故而頗多發覆燭隱的精彩之論,至今讀來仍然給人深刻的啟發。
任先生對一些大問題如三大文學思潮千百年來的“錯綜之變化”的辯證分析,其精彩已如上述;至其對一些重要的作家和批評家的文學觀念發展變化之“揚棄的過程”的辯證剖析,也同樣的精深透辟,這個則可以他對韓愈文學觀念及文學趣味的辨析為例證——前邊已說過三十年代的任先生對韓愈之新的傲慢與偏見,現在不妨看看四十年代的任先生對韓愈的看法有何改變,也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
此時的任先生當然仍舊認為韓愈是個文學上的實用主義者,但已不再簡單地因為韓愈的“文以載道”和反對佛老而否定其文及人了,倒是熱情地贊譽韓愈“在散文上偉大的建樹”等等,而尤為精彩的是他對韓愈文學思想及文學趣味之復雜性的辯證分析——
一般的說來,退之是宗信儒家思想的,那么他的文學主張自然不成問題的是屬于純粹實用主義啦。其實不盡然。反之,他倒是受唯美派的影響甚深。這話說來似乎頗為費解,因為他不是主張復古,主張反唯美主義嗎?可是我們只要把他的論文的話仔細加以分析,就可以曉得這里面有它們的矛盾的統一在。
首先退之對于文章的技巧是最重視的。你說他遵道,無寧說他是重文。……(中略)至他自己,也確切在寫文上下過極深的功夫。……(中略)他這種對文章慘淡經營的態度,不是同唯美主義派完全相同嗎?他對文章要“終其身而已矣”的精神,不很有點近于曹丕把文章視為“不朽之盛事”的見解嗎?他所說的“唯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不是與陸士衡所說的“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的主張完全吻合嗎?所不同者,不過是唯美派主張自由抒寫,而他主張明道;唯美派在形式上趨于排偶,而他則主張散體就是了。
其次,還有一點是他折中于唯美與實用兩派的鐵證。他原是提倡復古,而反對當時駢儷之作的。……(中略)他雖是如此,但同李華、獨孤及、梁肅、柳冕等則不同。李等不滿意于六朝浮靡之作,同時等而上之,連屈原、宋玉、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也都在攻擊之列,說他們“不近風雅”(李華),說他們“華而無根”(梁肅),說他們“亡于比興”(柳冕)。可是退之則不然,他雖提倡復古,但他并沒有明昭大號的反對六朝的文章,甚至對屈、宋、揚、馬之徒,推挹備至。
他在《進學解》中說:“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又道:“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答劉正夫書》)前邊一句是自述其在作文上所得力的古人的著作,后邊一句說他在漢代文人中所最佩服的幾位作者。所以退之的文章不只是法六經、史遷,而且是學屈、宋、揚、馬。
他的文章體制,雖是以北方的散體為主,但他受南方辭賦的影響也非常的深。所以他對于唯美派的作品,可以說是能夠襲其精而遺其粗。從劉彥和、顏之推兩人所主張的實用與唯美兩派調和折衷的理論,所謂“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顏氏家訓·文章篇》)的理想,到退之的文章,可以說完全實現了,也無怪后世推他為文章的山斗,而東坡譽之謂“文起八代之衰”了。這種地方非從理論上來探討,是不會洞徹的了解的。
應該說,像韓愈這樣的文學大家,大家都是比較熟悉和關注的,而韓愈的人、文、思想之特點也都堪稱鮮明,惟其如此,人們也就往往只根據那鮮明而不免單純的印象而論韓愈,卻常常忽視了掩映其后的復雜性,此所以任先生要說“這種地方非從理論上來探討,是不會洞徹的了解的。”而任先生此處所謂“理論”,除了一般的文學理論而外,其實還特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思維方法——沒有這個思想方法,任先生是不可能做出韓愈的文學觀念乃是“矛盾的統一”的判斷的。竊以為,任先生這樣辯證中肯、深入貼切的評論韓愈,乃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述要》一書的最見精彩之處,而他能如此發為實事求是、體貼入微之論,顯然包含著對自己先前簡單化的偏見和遮蔽的自我糾正,同時也可能暗含著任先生身處萬方多難、民族危亡的抗戰時代,對民族文化傳統和先賢道德情懷之感同身受的親切體認吧。
至于此書比較明顯的弱點,或者乃在用“唯美主義”來標示中國文學的一種主潮了。誠然,從漢代司馬相如、枚乘、揚雄等等“極麗靡”的辭賦,到魏晉六朝的所謂“文之自覺”及聲律論和宮體詩的發達,再到晚唐的溫、李和兩宋的婉約艷冶且重聲律之美的詩詞,還有宋初的所謂西昆體詩文,……中國文學史上確實有這么一股文學思潮在激蕩起伏,它們與西方唯美主義文學也確有相似之處,但究其實畢竟不同科;至于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更與唯美主義表里不同,很難說是“唯美主義的復古運動”了。當然,任先生當年使用這個概念,恐怕也是不得已——他顯然有所發現而又苦于無以名之,于是才起用了唯美主義的概念,并且加以限定,用來指稱中國文學史上比較崇尚和追求文學的藝術形式之美的一派,但畢竟有些牽強,不如“自然主義”那樣切合中國文學的實際而且富于中國文論的特色了。
在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中,像任先生這樣的得與失都是應有和必有的事,而其成功的經驗和失誤的教訓,則值得后繼者深長思索和總結。毫無疑義,中國古典文學的現代研究,已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斤斤計較于“一國文學本身”之中,而必須參照外國文學,才能洞達其變遷大勢和是非曲折。當然,以外例中而恰如其分的情況并不多,此所以任先生既經使用了“浪漫主義”的概念,幾經考慮又決然放棄,還是換用了更合中國文學實際也更具中國特色的“自然主義”概念;而“自然”的觀念雖然在古代中國向稱發達,但起用它來標識中國文學以至中國思想的一股主潮,在任先生來說也并非手到擒來的那么容易,而顯然受了西方浪漫主義觀念的啟發。在這過程中,綜合觀照而又折中損益,乃是必然的工作和必須的工夫。循著任先生的這個成功的先例,所謂中國的唯美主義文學,似乎也可從中國文論中生發出比較貼切的概念來概括,比如,“麗靡主義”或許就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概念——古人早就有“辭人之賦麗以淫”、“極麗靡之辭”、“詩賦欲麗”、“詩緣情而綺靡”以至“詞為艷科”等等說法可為張本,而由“麗”及“靡”,也恰如其分地顯示了“麗靡主義”文學思潮之由合理必臻于極端的特性。自然,這只是我的一點粗淺的感想,遺憾的是再也不能向訪秋師當面討教了。
2011年8月25日至9月21日謹撰于清華園之聊寄堂
〔注釋〕
①周作人最早提到韓愈,是1921年1月1日發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號上的《〈舊約〉與戀愛詩》一文,不過順口提及,發表于1924年5月14日《晨報副鐫》的《“大人之危害”及其他》一文,仍然比較諒解地說:“當時韓文公揮大筆,作《原道》,諫佛骨,其為國為民之心固可欽佩,但在今日看來不過是感情用事的鬧了一陣,實際于國民生活思想上沒有什么好處。”此后幾年便很少說到韓愈。可是進入1930年代以來,周作人在大力提倡獨抒性靈的晚明小品的同時,明顯加多了而且加重了對韓愈與古文的撻伐,如《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年)、《談韓退之與桐城派》(1935年)、《關于家訓》(1936年)、《宋人的文章思想》(1936年)、《談方姚文》(1936年)、《〈瓜豆記〉題記》(1936年)、《讀書隨筆》(1936年)、《談孟子的罵人》(1937年),……至1939年所寫《國文談》一文,還借錢玄同之口大罵韓愈與古文,此后亦持續批判,直至八十多歲,還寫了《反對韓文公》一文,可謂始終而不懈。
〔1〕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M〕.新月書店,1929.
〔2〕參閱錢鍾書.談藝錄〔M〕.開明書店,1948.
〔3〕參閱中書君(錢鍾書).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J〕.新月,1932,4(4).
〔4〕〔5〕舒蕪.重印緣起〔A〕.中國文學批評〔M〕.三聯書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