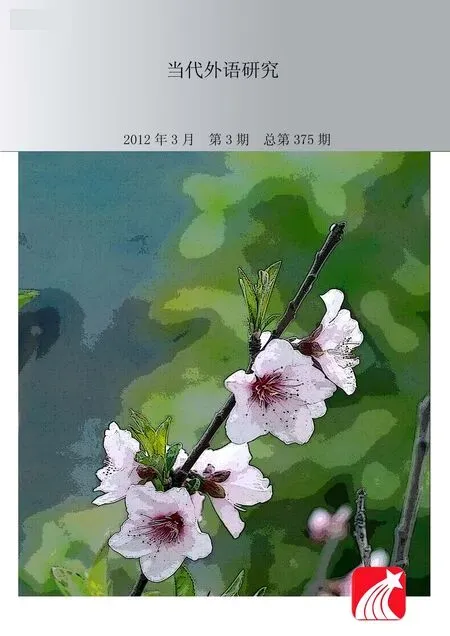Translationese及相關概念探析
柴秀娟
(聊城大學,聊城,252059)
2. 國外“Translationese”與相關概念
2.1 Translationese,Third Language與Interlanguage
根據《牛津英語大詞典(簡編本)》(Stevenson 2002:329,858),Translationese一詞產生于1930~1969年之間,由translation加上后綴-ese構成,用來指翻譯(尤其是質量差的譯文)不符合譯入語語言習慣的語體特點。后綴加強了這個詞在一般使用中常見的貶低意味,用法類似于journalese和officialese。具體說來,該詞包括兩個層次的意義:(1)內涵意義——翻譯語言特征;(2)評價意義——質量差的譯文。這種詞典釋義符合國內外多數研究者對Translationese的理解。如Nida和Taber(1969:210)認為它指“一種非自然的譯入語言形式,違反了正規的語法和語義結構型式”。Newmark(1988:285)認為它指的是“沒有引起恰當理解的直譯”,又稱作translatorese。Gellertam(1986:88)將它形象地比作一套源語留在譯入語上的“指紋”。Baker(1993:249)則認為Translationese是“一種異常的語言特征分布狀況”。
上述定義與《Routledge翻譯研究指南》(Munday 2009:236)和《翻譯學詞典》(Shuttleworth & Cowie 1997:187-8)的解釋一致,指譯文中不恰當的語言表達,與Third Language——失去統一風格的譯文拼湊式語言(Duff 1981:10)——涵義相同。因為外語能力發展的階段性和不完善性,應用語言學領域的Interlanguage也會在譯文語篇中留下Translationese的語言特征(Toury 1979:224)。簡言之,上述三個概念都是對語言表達的負面評價。但Third Language側重于從語言學的角度描寫翻譯語言在詞匯、結構、意義和修辭手段上造成理解困難的不合適的表達方式(Duff 1981)。Interlanguage則側重于從應用語言學的角度描述外語能力不完善的狀態,這種狀態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能力。Translationese側重于從翻譯評價的角度描述譯文讀者對譯文語篇語言的直覺印象。
2.2 Translationese與Translation Universals,Third Code
Puurtinen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描述翻譯研究從“完美”譯本追求到“現實”譯本的回歸,從語言、文學、觀念形態等方面承認了譯文在譯入語文化中的應有價值。近年來,對譯本語言的基本態度也從負面評價轉向中立的研究,Translationese一詞的用法在實踐研究中也已轉向“中性意義”,用來指“翻譯特有的語言”(Puurtinen 2003:391)。Baroni和Bernardini(2006)以及Tirkkonen-Condit(2002)也有相同的用法,其論文標題中使用的Translationese的具體研究內容都指向Translation Universals——“譯文語篇中出現的典型語言特征”(Baker 1993:243),即與目標原創語言不同的、翻譯語篇語言上表現出的規律性特征。
對于Baker來說,Translationese與Translation Universals不同,前者所指的語言特征異常,出自缺乏翻譯實踐經驗或目標語語言能力的譯者之手,往往是受到源語語言系統或結構的干擾所致。至于語言特征的異常程度的一些文字細節,Baker并沒有論及。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特征則是對翻譯作為一種不同語言間中介交際行為的本質反映,不受具體語言對和具體翻譯內容等因素的控制和影響,是對翻譯過程譯者認知活動規律的概括,沒有評價傾向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具有三種最常見的語言特征:明確化(Explicitation)、簡略化(Simplification)及規范化(Normalization)。
Schmied和Sch?ffler(1996)以及Balaskó(2008)認為,大多數研究者對于Translationese的界定止于簡單寬泛的描述,缺乏細致的分類。他們都認為Translation Universals是Translationese的一種。另一種則是由于受語言系統差異和翻譯規范影響而產生的分布、頻率或型態上的綜合語言特征(如圖1所示)。Balaskó(2008:61)進一步指出,Translationese類似于Third Code,是一種特殊代碼,顯性地或隱性地存在于語言的各個結構層次,可以用于區分翻譯語篇和原創語篇。

圖1 Translationese=Third Code的范圍
Third Code最早由Frawley(1984:168)提出。他認為,翻譯過程所產生的譯文語篇就是具有獨特語言特征的“第三代碼”——“同時考慮母體代碼和目標代碼時產生的次代碼,是對母體代碼和目標代碼的雙邊順應”。根據《翻譯學詞典》(1997:172),Third Code可以用Translation Universals下的語言表達實例來說明,但在偏離目標語規范表達的方式上更加隱蔽和難以察覺。
由此可見,如果排除負面評價,Translationese的意義內涵與Translation Universals和Third Code相當,都是指偏離目標語慣用表達的特有語言形式特征。但是,它們在立論角度、研究目的和概括性程度上不同。擺脫了負面評價色彩的Translationese也擺脫了翻譯評價的角度,通常是利用語言的個案分析,從文體研究的角度,重新審視各種翻譯語言存在的表征和功能。Third Code從符號學的理論高度強調賦予翻譯語言及其構筑的語篇世界一個本體研究的關鍵位置,理論價值高于實踐價值。而Translation Universals作為近二十年翻譯研究的熱點論題,從翻譯過程的認知本體研究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普遍性規律假設,抽象程度高,解釋力較強。
3. 國內對應的漢譯概念
3.1 翻譯體、翻譯腔、翻譯癥
國內翻譯研究界在引進Translationese概念之后,不同的研究者和翻譯研究詞典就根據各自對Translationese的理解和感受,選用不同的漢語譯名。常見的有三種——“翻譯體”、“翻譯腔”和“翻譯癥”(楊普習等2009:53),其中流傳最為廣泛的譯名為“翻譯腔”。這可以通過如下數據證實:通過關鍵詞Translationese檢索1999~2010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得到論文31篇,其中14篇相應的中文譯名為“翻譯腔”,10篇為“翻譯癥”,6篇為“翻譯體”,剩下的1篇則未譯,保留英文原稱。“翻譯癥”譯名比起“翻譯腔”,更加強了Translationese的“惡”性——“文筆拙劣……甚至不知所云”(方夢之2004:26)。Translationese的名聲之壞,令其為中國翻譯研究界主流所詬病,通常用來描述某種由于明顯依賴源語的語言特色而形成的目標語用法,代表著一種因不符合譯語表達習慣而有失自然、不夠流暢的譯文風格(楊普習等2009:53)。
另外,不少研究者雖然采用了相對中性的譯名“翻譯體”,但實際用法還是取其貶義。譬如,劉宓慶(1999:245)指出:“翻譯體帶有貶義。貶義中的翻譯體是機械主義翻譯觀和方法論的產物。這種所謂翻譯體的顯著特點是不顧雙語的差異,將翻譯看作語言表層的機械對應式轉換。他根據目標語規范、語境、文化形態、民族心理、接受者心理、社會功能和效果各個因素,闡釋了“翻譯體”在語言選擇、修辭手法設計、文化及風格等方面的具體表現。對于劉宓慶來說(1998),站在文體學和翻譯研究角度,真正的“翻譯體”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翻譯色彩”濃重與否的問題。顯然,這僅僅是從接受美學角度來看的語體特征的評價問題,不同的接受者對于同一譯語表述的感覺和印象可能會迥然而異。
另外,程熙旭(2006:105)將“翻譯體”重新定義為“在某一時期內翻譯中產生的不自然的語言形式,這種形式帶有源語言的特點,違反了目標語的習慣表達”。這一定義指明了“翻譯體”的歷史性,一個時代的翻譯體可能變成下一個時代目標語的規范表達。譬如,五四時期被認為歐化漢語的連接詞“與其……不如”業已成為規范的現代漢語。另外,為了消除“直譯等同于翻譯體”的誤解,程熙旭特別指出直譯只是一種翻譯策略,不一定能導致翻譯體。更多情況下,是沒有任何翻譯策略的“硬譯”和“死譯”導致了翻譯體的產生。
3.2 翻譯體、翻譯語體與翻譯共性
Translationese譯為“翻譯體”,對于另外一些研究者(胡衛平、李可夫2009)來說帶有積極的創新價值,這種用法主要出現在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研究中,強調異質因素給目標語語言帶來的新鮮感和異國情調(Reynolds 2003)。更有甚者,有些人還刻意模仿Translationese的語言特征,冒充譯文發表或出版,如多年前人民網批露的《執行力》一書。這種偽譯(pseudo-translation)現象,一方面反映了強勢文化的市場效應,另一方面作為翻譯表象下的創作,客觀上承認了翻譯語言特征作為一種語言變體的獨立存在,即翻譯語體(胡顯耀2010:451)。
對于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理論研究,國內學者(李德超2006)在成功引介外來成果的同時,作了理論上的剖析和反思。吳昂、黃立波(2006)充分回顧了翻譯共性研究的歷程(前語料庫時期和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時期),總結了目前對翻譯共性研究的質疑,指出以Mona Baker為代表的翻譯共性研究在研究對象的界定和方法論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他們認為翻譯共性的研究不應局限于翻譯過程本身,還應從具體語言對、翻譯方向、譯者因素、文體類型等多個視角進行。黃立波、王克非(2006:40)回顧了翻譯普遍性特征的具體內涵和存在問題,強調了翻譯普遍性研究的三個層次:描寫、歸納和解釋,目前的研究僅僅達到了第二層面。總之,這些學者研究翻譯共性的綜合性和批判性視角,構想未來研究的方向,但對于上述概念的實質內容和相互關系,尤其是Translationese、“翻譯語體”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之間的關系,缺乏足夠清晰的闡釋。
4. Translationese相關理論研究評價
4.1 概念的界定問題和混用現象
綜上所述,在對Translationese進行界定時,貶義、中性和褒義的色彩浸染其中,用來下定義的形容詞(artificial,unusual,unnatural等)只是主觀印象式的描述,直接造成對“翻譯語言特征”主觀印象式的感性研究分析。這個問題一方面是由Translationese的本質屬性——“語體特征”在接受程度上的漸變區域——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則受到翻譯目的、體裁以及翻譯研究的目的和內容的影響。在描述翻譯學的研究范式下,翻譯語體特征無所謂好壞,關鍵在于能夠確定譯文語篇的文體特征,反映譯者語言選擇的語境因素,以及預測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情況。在翻譯批評和譯文鑒賞的研究領域,評價意義就是翻譯語體特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據目標語讀者可接受程度和理解的效果,來確定個別例子Translationese程度的大小,評估譯文整體Translationese數量的多寡。在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研究中,翻譯語體特征同樣具有評價意義,需要聯系語言、文學、文化和歷史等因素,綜合評估Translationese的美學價值。
Translationese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在文獻出現的頻率遠遠高于其他的概念,所以在這里重點討論一下這兩個概念的混用和關系錯位問題。兩者混用的主要原因在于:(1)Translationese研究的內容涵蓋了一部分體現Translation Universals具體語言表達形式的實例。(2)前一表達比經濟,一個詞相對于一個詞組要簡潔得多。(3)翻譯研究者之間相互影響,形成了所在學術界的內部術語的特定用法;或者概念已經存在,但相對合適的術語暫時缺位。(4)Translationese在主流的翻譯研究中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和分析,Baker和Saldanha(2009)編寫的《Routledge翻譯百科全書》沒有專門解釋Translationese,僅出現兩次,都是與負面信息關聯:它是直接對源文的模仿,出自缺少翻譯能力的譯者之手。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翻譯研究中的Translationese部分內涵已經被Translation Universals替代。
關于關系錯位問題,這里主要指Schmied和Schaffer(1996)以及Balaskó(2008)把Translation Universals歸為Translationese范疇之下的觀點。前者指向翻譯過程的普遍性規律;而后者則指向翻譯語言的形式特征。前者為認知規律,抽象程度高;后者為具體語言表達特征,抽象程度低于前者。本質不同,包含關系無從談起。這種關系錯位的問題是由于當前翻譯研究中Translation Universals概念不成熟造成的,概念內涵中同時內嵌認知和語體維度,卻在維度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譬如,“明確化”作為翻譯共性之一,既可以指翻譯理解、表達認知過程的明確化,也可以指明確化的語言形式特征。
這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需要深入對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相關研究,需要“從人類認知心理學、社會學和文化的角度對各類翻譯普遍性做出更高層次的解釋”(黃立波2006:40);另一方面,需要“翻譯共性”和“翻譯語言特征”的中間范疇。“翻譯語體”可擔此重任,因為該概念主要用于對各類翻譯語言現象從語言內部及跨語言的角度進行歸納。從翻譯實踐上看,“翻譯語體”類似于英語中的Patterns of translationese或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聯通了外部歸納式解釋的具體翻譯事實描寫。但鑒于Translationese內涵的歷史復雜性,建議英語譯名為Translational Variation,才能更好地體現出“翻譯語體”作為一種社會語言變體,是出現在一種翻譯的語境之中。
4.2 成因研究薄弱
對于Translationese的成因問題,Nida和Teaber(1969:210)認為這是由“過分追求形式對等的努力”造成的;Newmark(1988:285)認為通常起因于“目標語非譯者慣用語言情況下產生的語言干擾,或者機械照搬詞典釋義”;Balaskó(2008:61)則認為它是“翻譯的特定環境中,翻譯過程中源語與目標語抗衡的結果”。Schmied和Sch?ffler(1996:48)則指出Translationese可以歸因于兩種不同的認知過程——“a)轉換,即源語影響目標語;b)回避或過度發揮的翻譯策略”。
由上可知,Translationese的成因研究大多嵌入在對概念界定的闡釋之中,很少有單獨的、系統全面的專門論證。從上述簡單的成因說明中,可以初步歸納出形成Translationese的四個要素:譯者、源語、翻譯過程、翻譯策略及方法,其中譯者最為關鍵,因為譯者的主體性,決定了在翻譯過程中的各種選擇:選擇什么源語進行轉換?選擇如何進行翻譯?選擇翻譯語境中的什么作為遵循的原則?另外,譯者對翻譯理論及語言對比知識的儲備,也會影響到譯文的語言特征。因此,Translationese成因研究屬于綜合性研究,需要對語言學、認知心理學、文體學等多門學科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深入的研究。
4.3 方法論問題
對翻譯語言特征本體研究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對于Translationese的研究,則更是由來已久。傳統的Translationese研究方法包括針對譯者譯作的個案分析或對比分析,還有針對語言個別項目的實例論證。這些質性的研究方法,如果沒有嚴格的研究對象的確定,很容易流于個人主觀印象,重復性研究多,不同研究之間互相借鑒性不強,不利于整體研究的發展;另外,由于闡釋分析的拓展性,研究內容的容量不大,對于長篇幅的體裁,很難做到全面系統的研究。
根據目前相關的實證研究(如Laviosa 1998;Kenny 2001;Puurtinen 2003;Olohan 2004;Balaskó 2008),Translation Universals研究主要是基于語料庫進行定量的翻譯普遍規律分析,利用客觀的語言表達形式的頻率、分布等特征來驗證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假設,從而形成了語料庫翻譯學的專門研究領域。不可否認,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實踐為“翻譯語體”特征的描述和歸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技術手段,近年來大量基于語料庫的翻譯共性研究推動了整體翻譯研究的發展。然而,Bernardini和Zanettin(2004)認為基于語料庫的翻譯普遍性研究存在兩方面問題:對普遍性概念的界定和所采用的方法論。界定問題(詳細論證,請參考4.1小節)的關鍵是把握Translationese、Translational Variation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相對理論位置。方法論問題則需要更具體的研究模式作為支撐,這也是確保語料庫翻譯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基本前提。
5. 結語:翻譯語言特征研究的研究框架
綜上所述,Translationese、Translational Variation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都涉及了翻譯語言特征的研究,而翻譯語篇中的語言選擇是譯者思維活動的結果,體現了譯者的思維風格——Mind style,即“個體的心智自我在語言表達上的獨特呈現”(Fowler 1977:103)。因此,我們基于Boase-Beier(2006)翻譯研究的認知文體學途徑,以“思維風格”為核心概念,提出翻譯語言特征的認知文體研究框架(見圖2)。這只是一種全景式的綜合研究設想,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這個框架能更加清晰地展示上述三個概念的理論層面和相互的關系。簡言之,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研究發生在解釋層面,解釋了譯者同時作為讀者和寫作者的認知過程的共性,這種共性通過譯者的“思維風格”體現在對語類、翻譯語體和風格分析中。Translational Variation的研究發生在歸納層面,歸納翻譯語體特征要依據語類的社會文化基礎和讀者接受效果的調查研究。Translationese的研究發生在描述層面,描述翻譯語言表達偏離目標語慣用表達的細節,需要聯系接受的語境進行分析。

圖2 翻譯語言特征的認知文體研究框架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 In Baker, M., G. Francis & E. Tongnini-Bonelli (eds.).TextandTechonology:InHonourofJohnSinclair[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33-50.
Baker, M. & G. Saldanha (eds.). 2009.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2rd edn.) [Z]. London: Routledge.
Balaskó, M. 2008. What does the Figure show? Patterns of translationese in a Hungarian comparable corpus [J].Trans-kom(1): 58 -73.
Baroni, M. & S. Bernardini. 2006.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ese: Machine-lear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text [J].LiteraryandLinguisticComputing21(3): 259-74.
Bernardini, S. & F. Zanettin. 2004. When is a universal not a universal? Some limits of current corpus-based methodologi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 [A]. In Mauranen, A. & P. Kujam?ki (eds.).TranslationUniversals-DoTheyExis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oase-Beier, J. 2006.StylisticApproachestoTranslation[M]. Manchester: St. Jerome.
Duff, A. 1981.TheThirdLanguage:RecurrentProblemsofTranslationintoEnglish[M]. Oxford: Pergamon.
Frawley, W. 1984.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A]. In Frawley, W. (ed.).Translation:Literary,LinguisticandPhilosophicalPerspectives[C].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59-75.
Gellerstam, M. 1986. Translationese in Swedish novel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A]. In Wollin, L. & H. Landquist (eds.).TranslationStudiesinScandinavia[C]. Lund: Gleerup. 88-95.
Kenny, D. 2001.LexisandCreativityinTranslation:ACorpus-basedStudy[M]. Manchester: St Jerome.
Laviosa, S. 1998. The English comparable corpus: A resource and a methodology [A]. In Bowker, L., M. Cronin, D. Kenny & J. Pearson (eds.).UnityinDiversity?CurrentTrendsinTranslationStudies[C]. Manchester: St Jerome. 101-12.
Munday, J. 2009.TheRoutledgeCompaniontoTranslationStudies[Z]. London: Routledge.
Newmark, P. 1988.ATextbookofTranslation[M]. New York & London: Prentice Hall.
Nida, E. A. & C. R. Taber. 1969.TheTheoryandPracticeof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Olohan, M. 2004.IntroducingCorporainTranslation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Puurtinen, T. 2003. Genre-specific 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ed and non-translated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J].LiteraryandLinguisticComputing18(4): 389-406.
Schmied, J & H. Sch?ffler. 1996. Approaching translationese through parallel corpora and translation corpora [A].InSynchronicCorpusLinguistics:PapersfromtheSixteen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nglishLanguageResearchonComputerizedCorpora(ICAME 16) [C]. Amsterdam -Atlanta: Rodopi. 41-56.
Shuttleworth, M. & M. Cowie. 1997.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Z]. Manchester: St. Jerome.
Stevenson, A. 2002.ShorterOxfordEnglishDictionary[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rkkonen-Condit, S. 2002. Translationese: A myth or an empirical fact? A study into the linguistic identifiability of translated language [J].Target(14): 207-20.
Toury, G. 1979. Interlanguag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translation [J].Meta24: 223-31.
Venuti, L. 1995.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M]. London: Routledge.
程熙旭.2006.翻譯體與直譯[J].語文學刊(高教外文版)(6):103-7.
方夢之.2004.譯學詞典[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胡衛平、季可夫.2009.翻譯乃翻“異”——論異質因素的重構[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1):36-40.
胡顯耀.2010.基于語料庫的漢語翻譯語體特征多維分析[J].外語教學與研究(6):451-58.
黃立波、王克非.2006.翻譯普遍性研究反思[J].中國翻譯(5):36-40.
李德超.2006.《翻譯普遍規律是否存在?》評介[J].外語教學與研究(3):237-39.
劉宓慶.1998.文體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劉宓慶.1999.當代翻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吳昂、黃立波.2006.關于翻譯共性的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5):296-302.
楊普習、劉典忠、周小巖.2009.Translationese:翻譯體?翻譯癥?翻譯腔?[J].中國科技術語(3):52-54.
附:
從師感言
光陰荏苒,自2002年師從于胡老師,已不覺十年時光逝去。歲月的砂輪磨鈍了記憶,十年間發生的許多事情都淡忘了,但有些事情卻愈發地清晰,如顆顆流光溢彩的珍珠,照耀著我的未來,豐富著我的人生,溫暖著我的心靈。
初識胡老師,我還只是聊城師范學院大三的學生,捧著《語言學教程》崇拜著老師的印刷體名字;如今,我依舊在故地,拿著老師親筆簽名的《高級語言學教程》,傳遞著包含老師心血的思想火花。閑暇時候,摩挲著一本本“秀娟留存 胡壯麟”的簽名作品,回想著胡老師每當有作品問世必送諸位弟子每人一本的傳統,體會著老師用心的意味深長。
在北京師范大學讀博士期間,我常常有機會去老師家里拜訪,對師母準備的酸奶水果至今仍記憶猶新。與老師談學習,談生活,老師智慧和慈祥的目光、幽默的言語、樸素平和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斷感受到老師的生活智慧和人格魅力。
胡老師為弟子們安排不定期聚餐,大家都很喜歡。因為師母的點餐技術一流,總能達成健康與味覺的完美結合;每次聚餐時談論的真實版趣聞軼事,簡直就是文學小說。老師和師母之間相濡以沫的感情,實為模范婚姻中的典范。我慢慢體會到,胡老師身教重于言教的風格已經化于生活的每個細節,處處皆學問,處處都是對人生的指導。
胡老師洞察一切的敏銳力,幫助我發現成長路上的絆腳石:我不善交流,他時時鼓勵和督促我;老師樂于助人,古道熱腸,幫助我化解求學期間在經濟上的困難和窘境;老師以不失赤子之心的大家風范與弟子同樂,善于捕捉生活的情趣。
胡老師對每位弟子的掛念體現在每一封發給弟子們的電郵中,表露于每一次學術會議短暫的重逢時刻。作為在北京以外工作的弟子之一,我體會尤其深刻。博士畢業后離開北京,雖然距離胡老師遠了,但老師的鼓勵和教導,時時回響在我的耳邊,鞭策著我勇敢前行。
謝謝胡老師和師母!值此慶生專刊出版在即,虔誠地祝福胡老師和師母:康樂,如意!

柴秀娟與恩師胡壯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