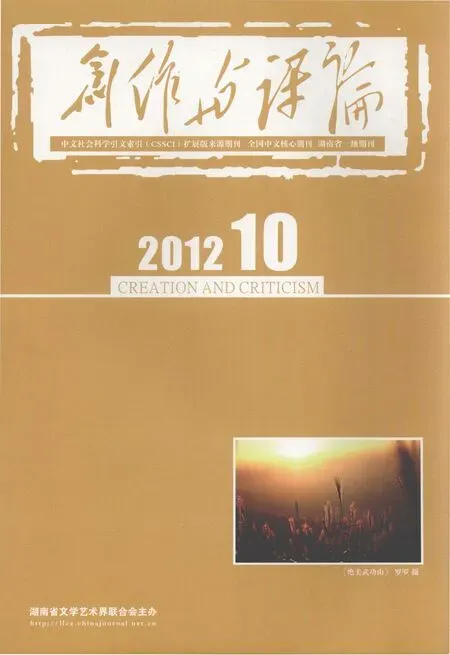顏家龍書(shū)法藝術(shù)初探
■ 蘇美華
一、銅琶鐵板——雄強(qiáng)是顏家龍書(shū)法的脊梁
欣賞顏家龍先生的書(shū)法,有如錢塘觀潮,泰山觀日,你會(huì)受到一種強(qiáng)烈的震撼。細(xì)品他的作品,又如讀太白的詩(shī)東坡的詞,激起你深深的共鳴——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氣勢(shì),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fēng)流人物的豪邁,使你的心潮也隨之澎湃,你無(wú)法抗拒那強(qiáng)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
而認(rèn)識(shí)顏家龍書(shū)法的雄強(qiáng),須作一番認(rèn)真的審視與思辨。他的作品并沒(méi)有故作驚人之態(tài),沒(méi)有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形式,追求所謂新意,沒(méi)有亂頭粗服招搖過(guò)市賺取廉價(jià)的回頭,沒(méi)有劍拔弩張不可一世的浮躁與霸氣。先生的書(shū)法以其獨(dú)特的面目吸引人,雄強(qiáng)的氣勢(shì)鼓舞人,深遠(yuǎn)的意蘊(yùn)征服人。無(wú)疑,豪雄是先生書(shū)法的主旋律,是先生書(shū)法最為顯著的風(fēng)格精神。其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
1.雷霆萬(wàn)鈞的氣勢(shì)
“飛砂走石天風(fēng),崩云激電雷聲,駿馬長(zhǎng)車戰(zhàn)鼓”,我曾在一首詞里這樣描繪先生的書(shū)法意象。觀其作品,無(wú)論尺寸大小,無(wú)論字?jǐn)?shù)多少,一掛上墻壁,一進(jìn)入展廳,就能馬上攫住你的目光。或動(dòng)或靜,或疏或密,無(wú)不重勢(shì)。有的飛動(dòng)如千軍萬(wàn)馬,有的空闊如大漠孤煙,胸羅萬(wàn)象而又高屋建瓴,審時(shí)度勢(shì)而毫無(wú)驕橫之氣。先生作書(shū),條幅多為行草,如一彪輕騎縱橫決蕩。扇面既有唐楷之莊嚴(yán),又有魏碑之峭勁。其行書(shū)楹聯(lián)更具特色,豪邁而不失沉著,頓挫中別有精神。
2.痛快淋漓的揮運(yùn)
米芾論書(shū)最主張沉著痛快,并視之為書(shū)法之最高境界,這是極有見(jiàn)地的。只求沉著或只求痛快,都較容易辦到,兩者兼得則實(shí)難。而顏先生率情恣意,心手雙暢。觀其揮毫作書(shū),簡(jiǎn)直是一種藝術(shù)的享受。仔細(xì)分析先生的運(yùn)筆,主要具有以下三個(gè)特征。第一、節(jié)奏強(qiáng)烈。先生執(zhí)筆特高,肘腕高懸,五指齊抓筆端,運(yùn)動(dòng)范圍大,濡墨揮毫,或正或側(cè),騰挪跌宕,縱斂疾徐,提按頓挫,得心應(yīng)手。其變化神本無(wú)端,如舞蹈家跳舞,如公孫大娘舞劍,而極富節(jié)奏美和韻律美。第二、筆力千鈞。先生運(yùn)筆,最擅鋪毫。使轉(zhuǎn)騰挪,皆能萬(wàn)毫齊力,入木三分。其大字對(duì)聯(lián),筆力蒼雄,筋豐而骨勁,其行草書(shū)作,筆鋒老辣,如萬(wàn)歲之枯藤。懸于國(guó)內(nèi)外名勝的楹聯(lián)尤其令人贊賞。先生之書(shū)不僅點(diǎn)畫(huà)豐盈骨力洞達(dá),就連牽絲映帶也是真力充實(shí)。既主強(qiáng)勁,又深內(nèi)蘊(yùn),剛?cè)嵯酀?jì),韻趣天成。第三、生澀蒼辣。“翰不虛動(dòng),下必有由”,顏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翰墨浸染,自然老到。那種潦潦草草、拖泥帶水、線路不明或故作驚人之態(tài)實(shí)則無(wú)筆無(wú)墨、無(wú)骨無(wú)筋的線條,在先生的作品中無(wú)法找到。但先生決不滿足,他始終重視筆墨的錘煉。為了使自己的書(shū)法以嶄新的面貌出現(xiàn),先生總是自覺(jué)地面對(duì)并解決熟與生、雅與俗的矛盾。為求熟后之生并達(dá)到大雅的境界,他刻意研究了張瑞圖、傅山等書(shū)家的各自特色而加以借鑒,并有意用左手揮毫,尋求一種獨(dú)到的生辣,經(jīng)過(guò)多年的探索與鍛造,終臻爐火純青之境。
3.宏闊深遠(yuǎn)的意境
顏先生的書(shū)法并不是完全沒(méi)有小橋流水式的作品,恰恰相反,他有的小楷作品散淡而秀美,別有一種風(fēng)情。但就其整體風(fēng)格而言,其作品氣象雄偉、意境宏闊。我曾見(jiàn)先生書(shū)寫(xiě)毛澤東《沁園春·長(zhǎng)沙》一詞,八尺橫幅,寫(xiě)來(lái)筆勢(shì)連貫,虛實(shí)相生,有如洞庭波涌,煙霞變幻。至于縱式長(zhǎng)幅,更是汪洋恣肆,渾然天成。先生的少字書(shū)法,在用筆、結(jié)字及章法上都具獨(dú)特個(gè)性,強(qiáng)化其疏密、虛實(shí)的對(duì)比,從而使作品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沖擊力,使每一幅作品都有詩(shī)的意境,畫(huà)的韻趣。
方孝孺在論李杜之詩(shī)時(shí)說(shuō)道:“瀟湘洞庭不能喻其廣,龍門劍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tài),千軍萬(wàn)馬不足喻其氣。”在此,借這幾句話來(lái)評(píng)論顏先生的書(shū)法,也應(yīng)該是比較妥貼的。
二、法古求變——?jiǎng)?chuàng)新是顏家龍書(shū)法的精髓
書(shū)法的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是一對(duì)難以處理難以解決的矛盾。古往今來(lái),不少學(xué)者陷入其中,不能自省,不能自悟,不能自拔。有的偏重傳統(tǒng),專在前人的故紙堆里翻尋,臨習(xí)幾十年,終是人家面目,落得一介書(shū)奴,實(shí)在遺憾,這種情況,在古人為多。而有的不重傳統(tǒng),或反對(duì)傳統(tǒng),空談創(chuàng)新,夢(mèng)想一夜之間成為書(shū)壇領(lǐng)袖,引導(dǎo)潮流,結(jié)果雖有自家面目卻俗不可耐,也很可悲。
顏家龍先生站在歷史的高度,審時(shí)度勢(shì),認(rèn)真分析書(shū)法現(xiàn)象,不斷觀照歷史,不斷審視自身。他經(jīng)常教導(dǎo)青年,要有創(chuàng)新意識(shí),但要靠傳統(tǒng)功夫的深厚積累。顏先生書(shū)法的風(fēng)格也正是在不斷學(xué)習(xí)、不斷汲取、不斷肯定與否定中逐漸顯露出來(lái)的,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那么,就讓我們一起看看顏先生的書(shū)學(xué)之路吧。
顏先生幼承庭訓(xùn),蒙童時(shí)即迷上了書(shū)畫(huà)。其叔祖父顏昌峣先生是清末民初湖湘頗有影響的學(xué)問(wèn)家、書(shū)法家,曾任毛澤東的歷史教員。他的字雄強(qiáng)勁拔,為書(shū)法界所推崇。顏家龍心摩手追,臨池特勤。后叔祖父因戰(zhàn)亂返回鄉(xiāng)里,有更多的機(jī)會(huì)親聆教誨,故其進(jìn)步神速。十三歲便為叔祖父代寫(xiě)一般應(yīng)酬對(duì)聯(lián)而在鄉(xiāng)間小有名氣。
在中學(xué)和大學(xué)求學(xué)期間,得到周達(dá)、潘天壽、諸樂(lè)三等先生的指導(dǎo)。三十歲前,除篆書(shū)外,其他諸體均有所涉獵,但主攻楷書(shū)、行書(shū),而于李北海《麓山寺碑》用功最勤。在此期間,先生多用意于筆畫(huà)之法度,骨力之健勁和結(jié)字之端穩(wěn)。
這個(gè)階段可謂顏書(shū)的植根立骨階段。
之后,顏先生對(duì)漢隸和北魏碑狠下了一番功夫。期間,他臨習(xí)了《史晨碑》、《乙瑛碑》、《爨寶子》、《張猛龍》、《張黑女》等一批碑版。漢碑的厚實(shí)與博大,魏碑的凝重與雄強(qiáng),對(duì)顏先生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yuǎn)的影響。先生臨池學(xué)書(shū),常是日以繼夜,寒暑不輟。而先生尤重思索,每每對(duì)一種碑帖先做初步的研究,然后落筆臨摹,以求心中有數(shù)。通過(guò)臨摹實(shí)踐,再悉心揣摩,常有所得,從而提高自己的認(rèn)識(shí)能力和理論水平。反過(guò)來(lái)又用理論指導(dǎo)自己的實(shí)踐。幾經(jīng)反復(fù),先生對(duì)原碑的造型特征和精神風(fēng)貌有了精深的研究。既能找到各個(gè)碑帖的藝術(shù)特征,又能融會(huì)貫通,變?yōu)榧河小Ec此同時(shí),還廣泛地臨摹二王一路行書(shū),對(duì)王羲之、王獻(xiàn)之、蘇軾、黃庭堅(jiān)、董其昌、趙孟頫等做了較深入的分析。這二十年中,學(xué)習(xí)碑帖最多,以漢魏碑強(qiáng)其骨格,以二王行書(shū)增其靈氣。
這是顏書(shū)的廣納博取階段。
五十歲以后,先生便集中精力研究王羲之、黃山谷、米芾、王鐸等名家的行草書(shū),仔細(xì)探究其氣韻的構(gòu)成。同時(shí),將自己的主攻目標(biāo)定為行草。
為了達(dá)到這一既定目標(biāo),這二十多年里,對(duì)行草書(shū)苦心經(jīng)營(yíng)。一是對(duì)古代行草大家廣泛涉獵,務(wù)使自己的行草合乎法度。二是汲取左筆書(shū)法的不同韻致,使得其書(shū)法更具拙味而更加險(xiǎn)絕,兩相交替,因而更富神采。三是在執(zhí)筆方面,改為五指聚于筆梢,腕肘高懸,關(guān)照整體,筆勢(shì)開(kāi)張。四是加強(qiáng)書(shū)法理論修養(yǎng),大凡能借到能購(gòu)到的古人的論書(shū)著作,總要羅列案前,細(xì)加分辨,偶有所得,或加記錄,或吟誦成詩(shī)聯(lián)。
經(jīng)過(guò)二十多年的努力,先生的行草書(shū)已風(fēng)格特出:亦行亦草,氣勢(shì)開(kāi)張,結(jié)字險(xiǎn)峻,骨力洞達(dá),用筆簡(jiǎn)練而氣韻生動(dòng)。
這便是顏書(shū)的張揚(yáng)風(fēng)格階段。
在這一階段,顏家龍先生特別從書(shū)法美學(xué)的角度進(jìn)行了針對(duì)性的研究與探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的作品,橫看成嶺側(cè)成峰,富有典型的意象美。高度精練的藝術(shù)語(yǔ)言,作品風(fēng)格的程式美,使其作品登上了書(shū)法抽象美的高峰。而最能體現(xiàn)他風(fēng)格的,是其作品所特具的能與人交流、動(dòng)人心魄的表情美:一是淋漓酣暢的痛快,他飽蘸豪情,盡情宣泄,筆勢(shì)翻卷,橫掃千軍。二是凝重沉著的莊嚴(yán),榜書(shū)大字,行楷對(duì)聯(lián),筆力雄厚,墨氣氤氳,有如廟堂之尊,凜然不可侵犯。人們習(xí)慣用最簡(jiǎn)練的字概括書(shū)法用筆特征,有人寫(xiě)字,有人畫(huà)字,有人描字,也有人刷字。顏家龍先生則不同,有人認(rèn)為他是刮字,取其筆筆周到,萬(wàn)毫齊力,而更準(zhǔn)確更有趣的應(yīng)是鑄字,這是不斷熔煉的結(jié)果,它有分量,有氣勢(shì),有溫度,有立體感。三是悠然自得的恬適。其扇面小品表情儒雅,不激不厲,凸顯出一種修煉后的中和美。
由此綜觀顏先生六十年來(lái)的書(shū)法歷程,可以看出先生沿著一條自我設(shè)計(jì)自我完美的道路向前闖進(jìn),這條路越來(lái)越清晰,越來(lái)越寬廣。我們可以看到先生的每一個(gè)腳印都是踏踏實(shí)實(shí)的,又都是有著自我開(kāi)拓精神的。先生法古而決不泥古,創(chuàng)新而守法度。可以說(shuō),法古是顏先生書(shū)法立根的基礎(chǔ),創(chuàng)新是顏先生書(shū)法的精髓。沒(méi)有創(chuàng)新,就沒(méi)有先生的自家風(fēng)格,就經(jīng)不起歷史的推敲與淘洗。
三、功在書(shū)外——博藝是顏家龍書(shū)法的血脈
無(wú)脊梁無(wú)以挺立,無(wú)氣血無(wú)以滋養(yǎng)。顏家龍書(shū)法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矚目的成就,是與其博藝分不開(kāi)的。
顏先生自幼聰穎好學(xué),又得塾師、長(zhǎng)者鞭策獎(jiǎng)掖,熟讀《三字經(jīng)》、《幼學(xué)瓊林》、《千家詩(shī)》、《詩(shī)經(jīng)》、《楚辭》等,打下了良好的古詩(shī)文基礎(chǔ),后又從師友吟詩(shī)屬對(duì),言志抒情,偶得佳句,便筆墨記之,自樂(lè)其樂(lè)。近二十年來(lái),先生在書(shū)畫(huà)之余,大量精力投入古詩(shī)文研究,境界日漸高遠(yuǎn)。“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顏老的詩(shī)文也是愈老愈見(jiàn)功力,愈老愈見(jiàn)思想。故近年來(lái),不少人向先生問(wèn)序求聯(lián)。自臺(tái)灣返湘的黎民敏先生國(guó)學(xué)根底深厚,書(shū)法也流譽(yù)臺(tái)灣,得知顏先生兼擅詩(shī)文,先親自拜訪,再互贈(zèng)翰墨,1992年出書(shū)法集,囑先生作序,有相見(jiàn)恨晚之慨。1998年黎先生再次問(wèn)序,足見(jiàn)顏先生國(guó)學(xué)之精深。
我們還是再看看顏先生的詩(shī)聯(lián)吧:
枝葉婆娑嶺上松,
峰巒列列插蒼穹。
云濤如海蕩胸過(guò),
萬(wàn)壑千崖出沒(méi)中。
——《黃山即景》
好一棵嶺上松,插于峰巒之巔,仰接蒼穹,俯瞰云海。這是歷經(jīng)風(fēng)霜雨雪而傲然挺立的蒼松,不禁使人聯(lián)想起“無(wú)限風(fēng)光在險(xiǎn)峰”的佳句。
對(duì)峙幽崖如壁立,
一泓碧水漫平流。
漁舟幾點(diǎn)風(fēng)波里,
鷗鷺不驚任自由。
——《湄江紀(jì)游》
在這里,清幽的景致,閑散的鷗鷺,多么自然,多么淳樸!寫(xiě)景抒情,豪華落盡,頗有王摩詰、孟東野遺風(fēng)。
麓山云涌千重翠,
湘水波浮萬(wàn)里銀。
——題岳麓山東大門
看綠水長(zhǎng)流,一派豪情朝大海;
數(shù)丹楓不盡,三秋艷色醉游人。
——題長(zhǎng)沙南郊公園數(shù)閣
如果說(shuō),前一副還偏重寫(xiě)實(shí)的話,那么后一副對(duì)聯(lián)不僅對(duì)仗工整,而且氣勢(shì)磅礴,境界高遠(yuǎn),情景交融。
最妙的自然是題桃花源的一副對(duì)聯(lián),先生不從山水美景落筆,而是別出心裁另辟蹊徑,不落窠臼,令人拍案,叫人回味:
世上覓桃源,都是奇文惹出;
人間有仙境,全憑雙手創(chuàng)來(lái)。
而顏先生有的聯(lián)富有哲理,是人格精神的寫(xiě)照。他曾撰自勉聯(lián):
厚德于人煙消云散,
微恩及已刻骨銘心。
寫(xiě)到這里,我想,作為一個(gè)書(shū)法家,一個(gè)畫(huà)家,一個(gè)藝術(shù)教育家,先生之為藝,先生之為人,又怎能不叫人也刻骨銘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