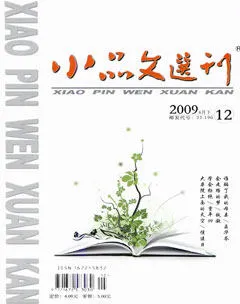母親的針線笸籮
房玉清
夜里做夢,見母親膝前放著一個針線笸籮,她一邊納鞋底,一邊絮絮叨叨地囑咐我好好讀書。這是童年常見的情景,可我從夢中醒來后,百感交集,再也不能入睡。我想到那個針線笸籮陪伴了母親一生,里邊實際上裝滿了她的辛勞、慈愛和對我的期望,實在是件珍貴的紀念品。不知在故鄉還能不能找到這種老物件?要是把這個老物件陳列在民俗博物館里,是一種很好的弘揚慈孝文化的展品。
舊時,慈溪三北姑娘出嫁,嫁妝中一般有一個上了紅漆的小筐,幫很淺,是用藤條或竹篾編成的,用來放針線,所以叫針線笸籮。其實里邊不但放針和線,還放剪刀、小鉗子、頂針等工具。婦女生了孩子以后,都是自己為孩子縫衣裳、做鞋,很少去買現成的衣裳和鞋。
我小時父親患重病,完全靠母親撫養。母親生了四個兒子,大兒子比我大九歲,抗日戰爭時隨姨父逃難到內地(龍泉),一直不在她身邊。母親身邊留下三個年齡差不多的小男孩:一個是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另兩個是一對雙胞胎,就是淘氣的我和弟弟;母親要在戰亂中養育這三個小男孩實在不容易。在我的記憶里,她除了干別的事,坐下來就手不離針線笸籮。
母親的針線笸籮也是我小時候喜歡倒騰的“工具箱”,里邊的鉗子呀,剪刀呀,針呀,線呀,尺呀什么的,對我都很有用。我常常從笸籮里拿一枚針做釣魚用的釣鉤:先把針在煤油燈的火焰上燒紅,然后用鉗子把針彎成釣鉤。母親洗被子時,把縫被子的線拆下來繞在線板上,我把這些線連接起來,變成了放風箏的長線。那時,釣魚和放風箏是我的兩大樂趣。
我印象最深的是母親把針線笸籮放在膝蓋上納鞋底。做布鞋先要按孩子腳底大小,做一個鞋墊一樣的東西,把碎布一層一層疊起來,疊成“千層底”,再用一塊白布把碎布蓋住,縫上幾針。然后納鞋底,用頂針把一根帶線的、很粗的針頂過鞋底,再用小鉗子把針和線從鞋底拉過去,輕輕拉緊,才算納完一針。納一只鞋底,一般要整整齊齊地納上數百針,非常辛苦。至于做鞋幫更費事:她要用漿糊把從舊衣服上拆下來的碎布一層一層粘起來,貼在木板上晾干,做成“布箔”;然后再按孩子腳的大小剪成鞋幫,縫上好看的鞋面,在邊緣緄上邊;如果做棉鞋,還要加棉花縫制。把鞋幫縫到鞋底上,是一種技術活,要用木楦頭做模型一針一針地縫,叫“绱鞋”,只有手巧的婦女才干得了。母親一年到頭為一家人的生存操心,一有空,就為三個孩子做布鞋、打毛衣和干其他許多家務,現在想起來實在使我感動。
可是,我小時候常為布鞋的事感到煩惱:南方多雨,上學、放學時突然下起雨來,我沒有膠鞋,要么穿著布鞋在雨水里走,要么脫了布鞋赤腳走。我想到母親做布鞋不易,總是赤腳走的;不過,天氣暖和還湊合,到了冬天,赤著腳在雨水里走,既冷,又感到寒磣,我多么希望有一雙膠鞋啊!但是,對母親來說,三個孩子都買一雙膠鞋,實在是不小的開支,何況孩子的腳都差不多大,長得快,要每年給三個孩子買一雙新膠鞋,這只有有錢的人家才辦得到。那時正打仗,物資極其匱乏,橡膠是戰爭物資,買一雙膠鞋很貴。至于塑料鞋,是戰后才發展起來的。
我家沒有錢,孩子的布鞋全靠母親自己做。我上中學時也穿母親做的布鞋。那時,滸山還沒有中學,要到余姚縣立中學寄宿,為了省錢,母親讓三個孩子走路去余姚上學。每學期,我們爬過白霧嶺,走過王家畈,去一趟余姚,來回要走將近一百里路。走路費鞋,母親雖然省了路費,但她自己不知要在針線笸籮旁付出多少辛勞!我讀中學時,老師說我的嗓門兒好,叫我參加合唱隊。合唱隊經常有活動,有時要參加演出或比賽。有一次,去演出時下大雨,我沒有膠鞋,想不去參加。可是合唱隊里缺男高音,非要我去不行。我從來不借同學的膠鞋,唯有這一次,不好意思地向一位同學借了膠鞋,這件事至今我還感激他。
母親自己沒有上過學,但她千方百計要讓孩子上學。為了讓三個孩子都上中學,她開始變賣家產。每年開學前,她想盡一切辦法為我們籌劃學費,常常愁得睡不著覺。在我讀初二時,她不惜一切,連她結婚時用過的寧波床也賣掉了,這使我終生難忘。我希望自己快快長大,能夠自食其力。我們兄弟三個,在貧困中讀了不少進步的文學作品,對革命很向往,希望有機會參加革命。1949年年底,寧波軍分區青年干部學校在余姚招生,我和雙胞胎弟弟一起去報考,竟然錄取了,那時還只有15歲。不久,我哥哥也考上了華東軍政大學,三兄弟都參了軍,成了革命軍人。母親雖然覺得當兵太危險,但在我們的勸說下,還是無奈地同意了。那時部隊只發單衣和棉衣,不發夾衣,在冬天有點冷;母親知道后,把我們小時穿過的舊毛衣拆成線,把多種顏色的毛線湊起來,居然織成三件毛衣寄給參軍的兒子。1952年,哥哥和我先后奉命赴朝鮮作戰。最初我們瞞著她,后來從朝鮮寫信給她,她知道后非常擔心,據說每天一早都要聽小山墩廣播站廣播有關抗美援朝的消息,每天為我們祈福。在朝鮮的冰天雪地里,我穿著母親織的毛衣,心里感到無比溫暖。我常常輕聲唱:“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那時,我感到母親給了我力量。盡管她有舊思想的限制,然而她的愛是偉大的。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們三兄弟已經到了古稀之年,退休后生活相當富裕。遺憾的是,母親去世太早。她是1963年去世的,那時我國還處在困難時期,物質條件和醫療條件都較差。三個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她晚年很寂寞;當時生活還很艱苦,沒能過上好日子。我特別感到內疚的是,那時給她寄的錢很少;因為離家很遠,很少回家看看。由于當時我的工資很低,來回的路費相當于一個月工資,所以回一趟家很不容易。1962年我弟弟患重病,我借了路費從北京趕到福建前線去看他,接著又順路到滸山看母親,她也正有病。沒想到,第二年母親病危,她去世時我沒能回家最后看她一眼。我覺得對不起她,終生感到內疚。
懷念母親時,我常常想到她納鞋底的情景,很想撫摸撫摸她膝前的針線笸籮。我總覺得它是慈孝文化的見證,雖然已經被歲月磨損,然而永遠裝著母親的辛勞、慈愛和對孩子的期望,它是母愛的象征。孟郊的《游子吟》出自肺腑地歌頌這種母愛:“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他把母愛比喻為春天溫暖的陽光,把游子的心比喻為小草的嫩芽;沒有“春暉”的普照,“寸草”就不能成長;然而區區“寸草”之“心”,怎能報答博大而溫暖的“春暉”?到了老年,背誦兒時學過的這首唐詩時,禁不住要流下淚來。我突然想到,還能不能找到母親用過的針線笸籮,也許撫摸撫摸這個老物件,能表示我對母親的親近和感恩,能減輕一點我的內疚。
選自《慈溪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