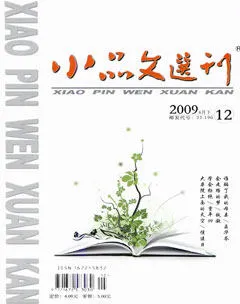窗外有藍天
劉 墉
“老婆畢竟不是血親,她今天跟你鬧翻了,明天就可能成為別人的老婆。”有個朋友冷不防地對我說,“還是孩子好,你再罵他,他跟你再不高興,還是你的孩子,還姓你的姓,叫你取的名字。”
“你為什么會想到這些?”我問,“你跟老婆又吵架了嗎?”
“是啊!上禮拜有一天,我上班之前跟她吵架,回家發(fā)現(xiàn)沒帶鑰匙,按鈴,她居然不給我開門。幸虧兒子在家,硬不管他媽攔阻,跑出來給我開了門。”嘆口氣,“妙不妙?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會忘記帶鑰匙,每次出門之前一定檢查,帶了,有安全感了,才敢出門。”
一個十一歲的中國男孩,因為鋼琴才藝驚人,拿到紐約茱麗葉音樂學院的獎學金,由媽媽帶著來美國深造。
沒想到,才來不久,他的爸爸就因車禍死了。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他媽媽不得不出去找工作。
“那孩子真奇怪,一天不知道要打多少次電話到辦公室找他媽媽,隔一下就來個電話,問他媽媽在不在。”有一天,他媽媽的雇主對我說。
“這是可以同情的。”我說,“因為他突然就沒了爹,他沒有完全感,惟恐媽媽一下子也沒了。”
一個家在臺灣,卻總在祖國大陸經(jīng)商的朋友,對我說的故事就更感人了——
“每次我離開家,八歲的女兒都哭著喊著不讓我走。”那朋友說,“我實在受不了那種心痛,也忍不得看她哭,有一次就瞞著她,趁她上學的時候離開家,沒想到麻煩大了。”
“什么麻煩?”
“從那以后,每次我回臺灣,孩子上學之前都要不斷問:‘爸爸今天會不會去祖國大陸?每次她出門,都回頭再回頭,眼睛里全是恐懼,好像我一下子就會不見似的。”
看非洲獵豹的動物影片,獵豹媽媽生了四個小寶寶。但是爸爸早失蹤了,媽媽要獵食,不得不常常離開洞穴。
就見那四只小獵豹相互依偎著,一動也不敢動,仿佛冬眠一般。影片的旁白說,小動物都是這樣,當媽媽不在的時候,它們?nèi)狈Π踩校伦约旱臒崃烤S持不到媽媽回來,所以只好盡量減少消耗。也因此,媽媽不常在旁邊的幼獸,總生長得比較慢。
可不是嗎?據(jù)說早產(chǎn)嬰兒在保溫箱里,除了喂奶,還要專人每天戴著手套撫摸,才長得好、長得快。
撫摸,使他們有安全感。
我也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因為十三歲那年,一場大火,不過半個小時,就燒光了我的家。
我的錦旗獎狀沒了,我最愛的圖畫書沒了,父親留下的古董字畫沒了,我寵愛的波斯貓也被燒死了。
從那以后,雖然從臺北搬到紐約,又搬到長島,但是每次離開家,都有幾分忐忑;每次回家,看到家門,都有一種“真好!家還在!”的歡欣。
我的母親也一樣,記得孫子才四歲的時候,我們一家去廬山旅行,她晚上居然在旅館做噩夢,夢見孫子掉下了懸崖,于是第二天堅持不去看瀑布。
“大概倒霉日子過多了,現(xiàn)在日子雖好了,心里卻不踏實,還不敢相信好日子真能維持多久。”老母后來對我說,“苦命啊!連有福氣,都怕消受不起。”
讀哲學大師羅素的女兒凱瑟琳寫的回憶錄。
羅素四十歲時有一天,坐在椅子上看書,看一半,把書放下來,站起身,走出門,騎上腳踏車離開家。
從此,羅素就再也沒回過那個家門,他跟結(jié)婚十七年的愛莉絲就這樣分開了。
書上說后來羅素又交了個親密的女朋友,每次羅素看書看一半,站起身,那女朋友都會緊張地問:“你要到哪里去?”
她一直對羅素沒有安全感。
遭遇“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人的生活整個改變了。
也許應該說,生活沒改變多少,改變的是心情,最起碼在紐約可以見到這種心情。
那心情是無形的,深深藏在人們的心底。以前在曼哈頓的街頭,見到的總是無憂無慮的紐約客。但是現(xiàn)在不同了,表面看,他們依然坐在路邊喝咖啡,躺在公園日光浴,但是稍微一些震動,即使是車子爆胎或緊急煞車,都可能引起驚悸的目光。
人們可能不說,但是在許多人的心底,都猜,會不會人群里正有炸彈客?會不會地下鐵就將冒出沙林毒氣?會不會天上飛過的那架飛機,正要撞向自己的家。
安逸的美國人,失去了過去擁有的安全感。
只是想想,這世界上何曾有過沒恐懼的日子?病痛是恐懼,戰(zhàn)爭是恐懼,父母可能遽逝是恐懼,房子可能失火是恐懼,太太可能不開門是恐懼,連幸福多了些,都惟恐失去。
只要我們不能預知明天,不能預知下一刻,就可能恐懼。誰知道下一秒鐘會不會發(fā)生八級地震,震碎一切。
于是知道:只有把握現(xiàn)在,看得到、摸得著的最安心。只有把握自己,小心開車,小心過馬路,小心保養(yǎng)身體,小心做個好人,有一天發(fā)生了不幸,才能沒有悔恨、沒有虧欠。
幸福總在當下——
窗外有藍天,多美的日子!窗外有陰天,多美的日子!窗外有雨天,多美的日子!
能看到家、看到孩子、看到妻子、看到親人、看到朋友,那是多美的日子!
選自《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