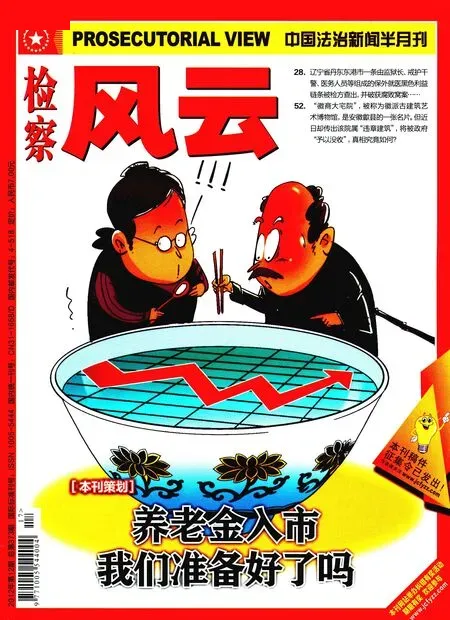姚洋:“中國奇跡”的動力來自體制創新
客座總編輯
本期欄目主持人:靳偉華 jinweihua1014@sohu.com
姚洋:“中國奇跡”的動力來自體制創新
客座總編輯
本期欄目主持人:靳偉華 jinweihua1014@sohu.com

本期客座總編輯: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 一位宏觀經濟、制度創新領域的引航者,一位秉持平等自由和社會公正的經濟學家,一位直言不諱自己為“中左”政治傾向的經濟學者……近日,姚洋對從“泛利性政府”過渡到“中性政府”的相關言論,引發了社會各界的不少爭議。那么,姚洋究竟怎樣解釋“中性政府”的概念?他又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改革奇跡的?
檢察風云:您怎樣評價中國經濟改革30年來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
與蘇聯、東歐國家實行的“振蕩療法”不同的是,中國的體制轉型變革幾乎都是“自下而上”的,先在少數地方試行,成功之后,在全國推廣。
如果說有不足,我覺得應該分階段來看。這30年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頭十年是理論準備期,1980年代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1990年代是改革期,重要的改革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進入第三個十年的時候,政府又開始回過頭來把社保重新撿起來,開始注重一些民生問題。而當我們進入下一個十年的時候,我們要做什么?我覺得要做的就是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要更多地關注民生。如果到2022年,政府能基本退出經濟領域,集中力量搞民生,那中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基本上就有希望了。
檢察風云:近來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那么,中國目前究竟存不存在這種危險,未來中國式的解決方法是什么?
姚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000美元時,因快速發展過程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導致經濟回落或停滯。
我認為,中國還沒有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收入分配不均確實是潛在威脅。導致“陷阱”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技術進步跟不上。在這方面,“十二五”規劃出臺以來,我國政府對技術進步的投入很大。預計到“十二五”期末,研發投入將占GDP的2%以上。所以技術這方面我們肯定不會落入陷阱。但是收入分配卻越來越不平均,這一點可能會成為“陷阱”的潛在威脅。
檢察風云:在《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一書中您提到,中國奇跡的關鍵原因是中國有一個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在什么條件下實現的?
姚洋:所謂中性政府,就是不代表任何社會集團的利益,也不被任何社會集團所挾持的政府。所謂中性,指的是相對于社會集團之間利益爭奪的中性,即政府不在社會集團利益爭斗中采納任何立場,不傾向于任何一方。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相對于整個社會持中性的態度,相反,政府可以有強烈的利益訴求,而且,也不排除政府對社會集團采取歧視性的政策。
我是相對于發展中國家這種狀態提出的“中性政府”概念。之所以認為中國奇跡的關鍵是中國有一個中性政府,是因為中國已經通過革命建立了相對比較平等的社會。
主動收集線索。在傳統的12309舉報電話受理群眾舉報公益損害的同時,全面推廣建成“公益眼”“隨手拍”等移動實時在線舉報平臺,便于公眾積極參與。建立公益損害巡查制度,聘請專業人士以及污染區群眾等擔任公益損害觀察員,發揮網格員的作用,拓寬線索發現路徑。加快公益訴訟線索平臺建設,為線索的綜合分析研判夯實基礎。加強與監察委的協作配合,建立線索雙向移送機制,發揮各自優勢,形成維護公益的合力。
但中性政府是政府相對于社會集團之間的爭斗而言的,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但由于這種利益不受社會集團左右,所以經常和全社會的利益掛鉤,產生一致性,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發展。
從中國經濟改革走過的30年歷程里,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是一個中性政府。一方面,改革是國家放權于民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精英的革命;另一方面,改革也沒有遷就部分民眾的利益,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主要以國家長遠經濟發展為導向。回顧中國政府在過去30年所采納的經濟政策,可以發現,就短期而言,它們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總是偏向某些群體。但是,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采取這些看似歧視性的政策,是因為它并不特別地照顧任何群體的利益,這樣才可能放開手腳采取有偏的經濟政策。
任何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利益集團,如果這些利益集團比較平均,那么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比較容易成為一個中性政府。其實不光是中國,在韓國、日本、新加坡,這些東亞經濟體的社會結構其實基本上都比較平均,沒有某個強勢的主導階級足以主導這個國家的命運,這就容易形成一個中性政府。
檢察風云:“結構失衡”是近來經濟學界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對此您怎么看?
姚洋:進入21世紀之后,傳統的改革議程基本完成,如價格改革、企業改革和對外開放等,中國經濟增長趨于常規化。如同其他東亞經濟體一樣,中國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外延擴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口的增長。但是這種外延增長積累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以及巨額經常項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這些問題的產生和中國的人口結構及城鄉關系有關,但是體制的弊端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對其起到了放大作用。
首先,結構失衡和中國國情有關。我國當前國情有兩大最顯著特點:一是處于人口紅利最高峰時期,二是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衡量人口紅利的最重要指標是勞動人口(16~65歲人口)和被撫養人口(低于16歲和65歲以上人口)之間的比例,我國的這一指標是2.5:1,即2.5個勞動人口只負擔一個被撫養人口,是世界上最低的。同時,盡管農村人口大量轉移到城市,但我國仍有4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而農業產出只占GDP的11%,這意味著中國尚未脫離剩余勞動力的階段。
其次,結構失衡還有體制原因。雖然我國已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但一些要素價格仍被政府控制,或受政府干預。政府干預市場價格本身沒有問題,但如果政府的定價嚴重偏離要素的稀缺程度,就會出現大問題。
再次,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比較落后,且結構不合理。我國金融市場以銀行為主導,而銀行業的集中度非常高,主要被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四大銀行控制。在四大行之外,商業銀行數量有限,全國只有300余家。缺少小銀行,是除利率管制之外造成中小企業貸款難的重要原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參與以及公共財政的缺失。20世紀后20年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縮小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然而,過去幾年中,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大有回潮之勢。大量經濟刺激投資由政府完成,這樣就帶來很多問題:一是擠出民間投資;二是增加了壞賬風險。
檢察風云:該從哪些方面重啟改革歷程呢?
姚洋:結構調整需要體制改革,結構失衡是重啟改革議程的契機,給我們指明了改革方向。
第一,政府要逐步退出經濟領域——不僅僅包括競爭性領域,而且包括非競爭性領域,一句話,就是要實現經濟的“去國家化”。當前我國政府深入參與的經濟活動,多數可以由民間完成。杭州灣大橋和北京地鐵四號線的成功表明,民間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是完全可行的,關鍵是成本和收益安排要適當。
第二,要建立真正的公共財政,強化政府的公共性質。當前,預算公開正在全國展開,但這遠遠不夠,因為目前公開的預算還是粗線條的,即使民眾知道了預算內容,也沒有對預算的修改和決策權,而有決策權的人大代表又沒有充分的時間和專業知識對詳細預算發表意見。
第三,改革金融體系,向國內民間資本開放金融市場,鼓勵地方性中小銀行的發展,積極探索地方性資本市場的可行性。為了防止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發生關聯交易的潛在風險,要采取限制民間資本設立的銀行接受儲蓄。這個方案中的銀行實際上是借貸公司,沒有信貸擴張功能。
第四,積極推進要素價格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這兩項改革已經啟動,但速度和深度還不夠。要素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改革,牽動老百姓的生活,因此要特別小心。談到要素改革,就繞不開人民幣匯率,匯率的實質是調節出口品和進口品以及不可貿易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本幣低估相當于提高出口品的價格,降低進口品和不可貿易品的價格。2009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加快城鎮化步伐,解決進城農民的戶籍問題”,這是一個極有遠見的政策,如果得到實施,不僅將結束長達半個世紀的城鄉隔離,而且將加快我國的結構調整步伐。
特約采訪:史亞娟
編輯:靳偉華 jinweihua10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