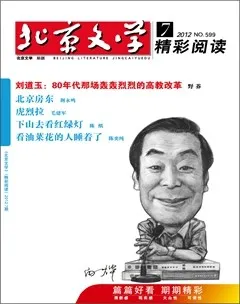北京房東

方悅是富人,在北京西南郊有別墅,某日她終于捉到丈夫的奸,離了婚,嫁到日本,最后又回到了中國(guó)。她的人生經(jīng)歷告訴她,“男人可以愛(ài)著一個(gè)人而去和別人睡覺(jué),但女人不行。當(dāng)她想用同樣的方式去報(bào)復(fù)對(duì)方的時(shí)候,她的愛(ài)情就已經(jīng)不存在了。”她的人生經(jīng)歷還告訴她:有的人有房子沒(méi)家,有的人有家沒(méi)房子。讀者諸君你認(rèn)為是這樣嗎?
1
我的第二任房東是個(gè)酒膩?zhàn)印K蟹介L(zhǎng)貴,40多歲,體格健壯,喉音很重,說(shuō)話有一種嗡嗡的回音。我總是想,這樣寬洪的嗓子比較適合于唱美聲,而他卻偏偏選擇了喝酒——四兩的啤酒杯,一揚(yáng)脖便干了個(gè)精光,好像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喉嚨而是直接倒進(jìn)了肚里。那天晚上他來(lái)取房租,在我的餐館里,我們先是滋潤(rùn)了四個(gè)“小二”,接著又灌了八瓶啤酒,他才梗著脖子,像是抑制不住,又像是很費(fèi)勁地打了幾個(gè)響亮的啤酒嗝說(shuō),“兄弟……呃……差不多了,今兒就這么著吧……”
送走了方長(zhǎng)貴,我和妻子趕緊往家走。一路上頭重腳輕,走進(jìn)胡同拐角的時(shí)候還差點(diǎn)沒(méi)撞到墻,被妻子一把拉住了胳膊。她嗔怪地說(shuō),“你就是逞能,最后那兩瓶啤酒就不應(yīng)該喝!”“你別說(shuō)酒的事啦行不行?”她一提到酒,我的胃里就有點(diǎn)條件反射往上涌。她挎著我的胳膊,絆絆拉拉往家走。好不容易撐到家,那種天旋地轉(zhuǎn)、翻江倒海的勁兒就上來(lái)了,結(jié)果差點(diǎn)沒(méi)把腸子吐出來(lái)。一通折騰之后,才酣然入睡,死了一般。
第二天,我妻子什么時(shí)候起的床,什么時(shí)候去的餐館,我一概不知。在一種朦朧的狀態(tài)中,我聽(tīng)見(jiàn)似乎有人闖進(jìn)屋里,又跑了出去,再返回來(lái),同時(shí)像是喊了句什么……我毛毛愣愣睜開(kāi)眼睛,在一種“不知今宵酒醒何處”的失憶狀態(tài)中,只見(jiàn)地上夢(mèng)幻般地站著一個(gè)陌生的女人,正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我。
我疑惑地看著她,“你是誰(shuí)?”
“這正是我要問(wèn)你的!”
女人的聲音很大,甚至很憤怒。此時(shí)我已經(jīng)徹底清醒過(guò)來(lái),這不是在夢(mèng)里,是真事兒!
是真事兒,反倒讓我更加糊涂了。我不知道這個(gè)女人是誰(shuí),也不知道她是怎么進(jìn)到屋來(lái)的……我已經(jīng)來(lái)不及吃驚,只想把事情立刻搞個(gè)明白。
我問(wèn)她有什么事。
“事兒大啦!是誰(shuí)讓你住到這里的?”
我剛想說(shuō)方長(zhǎng)貴,馬上又改口說(shuō),“我表哥……”
“你表哥是誰(shuí)?”
我說(shuō),“方長(zhǎng)貴。”
“……什么?方長(zhǎng)貴是你表哥?”
我說(shuō),“是。”
她“嘿”了一聲,不無(wú)譏諷盯著我,“這么說(shuō),我還是你表妹呢?”
一句話,又讓我墜到了云里霧里。我怔怔地趴在床上,一時(shí)間不知道該說(shuō)什么。這時(shí)候?qū)Ψ浇嚯x的形象越發(fā)清晰,她三十五六歲,一頭深棕色的秀發(fā)散亂地披在肩上,風(fēng)姿綽約,長(zhǎng)得漂亮!同時(shí)我聞到了一種高級(jí)化妝品的幽香。這就越發(fā)加重了我的窘迫與難堪。更重要的是,趴在被窩里跟一個(gè)陌生人對(duì)話不得勁兒,方式不對(duì)。我建議她能不能回避一下,讓我先起床,再說(shuō)話。對(duì)方也好像意識(shí)到了這一點(diǎn),很配合,或者說(shuō)很給我面子,她立刻轉(zhuǎn)身出門(mén),退到院子里。
我穿好衣服,首先把屋里的窗子和門(mén)全部打開(kāi)。我知道,被一個(gè)酒鬼睡了一夜的屋子,空氣中肯定有一種不太好的味道,同時(shí)也有點(diǎn)打開(kāi)天窗說(shuō)亮話的意思——對(duì)方畢竟是女人,而且是個(gè)不明來(lái)歷的陌生女人。
之后,我把女人叫進(jìn)屋里,開(kāi)始我們的第二輪對(duì)話。毫無(wú)疑問(wèn),穿上衣服說(shuō)話我就仗義多了。事實(shí)上,為了急于了解事情真相,在這個(gè)突如其來(lái)的漂亮女人面前,我已經(jīng)忘了拘謹(jǐn)和自卑。
我問(wèn)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經(jīng)說(shuō)開(kāi),事情還真有點(diǎn)復(fù)雜。原來(lái),我們租的這間房子的主人不是方長(zhǎng)貴,而是眼前這個(gè)女人,她叫方悅。方悅是方長(zhǎng)貴的妹妹。方長(zhǎng)貴往外租房子這件事,方悅?cè)徊恢8鶕?jù)她的說(shuō)法,她是想在雨季之前看看這房子有沒(méi)有漏雨的地方,需要不需要維修一下,“哪想到,一進(jìn)來(lái),發(fā)現(xiàn)屋里竟睡著個(gè)大活人,差點(diǎn)沒(méi)嚇?biāo)溃 ?/p>
“這么說(shuō),我是被你哥給騙了唄?”我不解地看著她。
“你交了錢(qián),也住了房子,他騙你什么了?他騙的是我!”
“既然是你的房子,你哥他怎么有鑰匙?”
她說(shuō)是她給他的。但馬上又說(shuō)成是“他肯定自己配的”!
聽(tīng)她這么一說(shuō),讓我馬上想起一件事來(lái)。剛住進(jìn)這間房子的時(shí)候,我妻子就有些擔(dān)心,她說(shuō)這房子也不知道多少人住過(guò)了,最好換一把新鎖,安全。我看了看,門(mén)是鋁合金的,鎖是那種里外能開(kāi)的長(zhǎng)把鎖,裝得嚴(yán)絲合縫,就像是門(mén)上長(zhǎng)出來(lái)似的。我研究了半天,又估計(jì)了一下自己的能力,覺(jué)得對(duì)付這件事肯定有相當(dāng)大的難度……就沒(méi)換。現(xiàn)在我終于意識(shí)到,如果當(dāng)初換了門(mén)鎖,就不會(huì)被一個(gè)漂亮的女人堵在了被窩里。太難堪了。
接著,那個(gè)叫方悅的女人便一項(xiàng)一項(xiàng)地問(wèn)我,啥時(shí)候租的房子,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的……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又突然想起似的問(wèn)我,那“表哥”又是怎么回事兒。
說(shuō)起來(lái)這都是方長(zhǎng)貴的主意。我們租房子那天,他告訴我,院里有兩個(gè)鄰居,老是愛(ài)管閑事兒,“您住進(jìn)去之后,就說(shuō)我們是親戚。”
方長(zhǎng)貴的意思我明白。當(dāng)時(shí)有關(guān)部門(mén)在房屋出租方面管得很?chē)?yán),無(wú)論單位還是個(gè)人,出租房屋必須向幾個(gè)部門(mén)申報(bào),先辦手續(xù)。不但麻煩,還得納稅。一般情況下,房主都是和出租人私下簽訂協(xié)議,前提是,租房的人必須遵紀(jì)守法,可靠,同時(shí)還不能讓鄰居們有什么說(shuō)道,所謂民不舉官不究吧。
我說(shuō),“行,啥親戚呢?”
方長(zhǎng)貴想了想,“您比我小吧?”
我說(shuō),“我四十。”
他說(shuō),“您瞧,小兩歲呢……就說(shuō)是我表弟吧。”
我說(shuō),“行。”
不過(guò),這個(gè)稱(chēng)呼我一次都沒(méi)用上過(guò)。搬進(jìn)這間房子之后,我們和院里的鄰居都處得不錯(cuò),彼此雖沒(méi)什么實(shí)質(zhì)性的交往,見(jiàn)了面都挺客氣,啥事兒沒(méi)有,我再對(duì)院子里的人去撒謊,說(shuō)我是方長(zhǎng)貴的表弟,有這個(gè)必要嗎?
我簡(jiǎn)單講了事情的經(jīng)過(guò)。方悅無(wú)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他可真有一套,我算是服了他了!”
至此,我已經(jīng)覺(jué)察到方長(zhǎng)貴和方悅在房子的問(wèn)題上肯定有什么說(shuō)道。但無(wú)論如何,那是他們兄妹之間的事,我不管,也管不著。我只關(guān)心這房子我還能不能住下去。而且我已拿定主意,并相信我有足夠的理由來(lái)維護(hù)我的權(quán)益。
我找出了和方長(zhǎng)貴簽訂的租房協(xié)議。
方悅看了幾眼,默然無(wú)語(yǔ)。她突然掏出手機(jī),飛快地按出了一串號(hào)碼。看樣子,她是想立刻和方長(zhǎng)貴討個(gè)究竟。但是呼叫音一直響著,卻沒(méi)人接聽(tīng)。方悅生氣地按掉手機(jī)。她告訴我,可以暫時(shí)保留我的居住權(quán),事情究竟咋辦,她要先問(wèn)問(wèn)方長(zhǎng)貴,然后再說(shuō)。
2
我們是半年前搬到這間房子里來(lái)的。在此之前,我和妻子一直住在我們餐館附近的另一條胡同里。那也是個(gè)大雜院,我們租的那間房子很簡(jiǎn)陋,而且是個(gè)倒座子房,光線很暗,即使白天也得用電燈照明。但就是這么一間房子,我們一住就是兩年。作為外地人,我們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臨時(shí)的,不安定的,我們只是從一種相對(duì)的角度,希望生活能夠安定一點(diǎn),不愿意折騰。無(wú)奈的是,有一天,房東來(lái)告訴我們,說(shuō)那條胡同要拆遷,讓我們有個(gè)準(zhǔn)備,最好提前找房。當(dāng)時(shí)有兩個(gè)居委會(huì)老太太常到我們餐館來(lái)發(fā)鼠藥,檢查婚育證,或者組織集體殺蟑螂什么的,跟我妻子混得很熟。聽(tīng)說(shuō)我們想在餐館附近租一間住房,便熱心地表示替我們?nèi)ゴ蚵?tīng)打聽(tīng)。結(jié)果沒(méi)過(guò)兩天,就打聽(tīng)到在我們餐館前邊的一條胡同里有一家的房子空著,并從院里的鄰居那里抄來(lái)了房主的電話號(hào)碼。
房主就是方長(zhǎng)貴。
我第一次給他打電話,就覺(jué)得這是個(gè)既認(rèn)真而又啰嗦的人。我問(wèn)他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他先說(shuō)沒(méi)有,接著又問(wèn)我聽(tīng)誰(shuí)說(shuō)他有房子要出租。我告訴他是居委會(huì)的兩個(gè)老太太。他警覺(jué)地說(shuō),“居委會(huì)的?那院里也沒(méi)有什么居委會(huì)的老太太呀。”
我想跟他解釋一下,又覺(jué)得解釋起來(lái)很麻煩,也沒(méi)必要,便直奔主題地說(shuō),“方師傅,咱長(zhǎng)話短說(shuō),我只想是問(wèn)一下,你的房子出租還是不出租?”他說(shuō),“不租了。”
我心想,不租我還跟你磨嘰個(gè)啥?我叭地放了電話。剛轉(zhuǎn)過(guò)身去,電話響了。我以為是訂盒飯的呢,卻還是那個(gè)渾厚的京腔兒。
“丫怎么斷線了呢……您貴姓?”
我告訴他。
他問(wèn),“北京的‘京’?”
我說(shuō),“不是,是荊州的‘荊’。”
他說(shuō),“明白了,劉備大意失荊州啊……這姓兒好!”
接著,他又問(wèn)我是哪里人,多大年齡,做什么工作的,租房子是一個(gè)人住還是夫妻兩個(gè)人住等等,問(wèn)得比人口普查還詳細(xì)!但我還是不厭其煩地作了回答。從對(duì)方不斷插話的口氣上,我聽(tīng)出他對(duì)我的“自然情況”還是比較滿(mǎn)意的。他告訴我,他再考慮一下,然后給我個(gè)信兒。
等了兩天,一直沒(méi)信兒。我妻子有些著急,她說(shuō),“出租個(gè)破房子都這么磨嘰,好像往外嫁女似的……你再打個(gè)電話問(wèn)問(wèn),他不租拉倒,總不能在他這一棵樹(shù)上吊死!”我打了好幾個(gè)電話,家里一直沒(méi)人接聽(tīng)。到了中午,才終于打通了。這次對(duì)方倒是挺痛快,不再問(wèn)這問(wèn)那了,他讓我定個(gè)時(shí)間地點(diǎn),見(jiàn)了面再說(shuō)。
下午,方長(zhǎng)貴準(zhǔn)時(shí)來(lái)到我們餐館。
小平頭,大個(gè)子,身材魁梧,長(zhǎng)得隨便,甚至有點(diǎn)粗糙。不過(guò),倒是蠻和善的一個(gè)人,至少要比在電話里給我的感覺(jué)好得多。我們聊了一會(huì)兒家常,他又考察了一下我們的基本情況,才切入正題。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那間房子原來(lái)出租過(guò)幾次,都鬧得挺不愉快,本來(lái)不想出租了,麻煩!但看我們是踏踏實(shí)實(shí)做生意的人,還成,靠譜兒,他可以把房子租給我們。問(wèn)到租金,他說(shuō),“這個(gè)不忙,先看了房子再說(shuō)。”
房子還行。比我們?cè)瓉?lái)住的那間要大一點(diǎn),有十五六平米的樣子。關(guān)鍵是房正,朝陽(yáng),窗子也大,一進(jìn)屋便給人一種陽(yáng)光明媚的感覺(jué),和以前租的那間房作對(duì)比,我和妻子一眼就看中了。一問(wèn)租金,對(duì)方開(kāi)出的條件是每月600元,兩個(gè)月一付。我和妻子交換了一下意見(jiàn),覺(jué)得還可以,沒(méi)超出事先的預(yù)測(cè),也就沒(méi)還價(jià)。回到餐館,我按照上次的租房合同,扒了一份協(xié)議,用復(fù)寫(xiě)紙謄好。雙方簽了字。我又預(yù)付了兩個(gè)月的房租。方長(zhǎng)貴點(diǎn)了點(diǎn)頭說(shuō),“沒(méi)錯(cuò),成,這就齊活了!”
我告訴廚師做幾個(gè)菜。既然成了房東與房客的關(guān)系,總得喝點(diǎn)酒,聊聊天,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兒。第一次喝酒,我就看出方長(zhǎng)貴是個(gè)喜歡喝酒的人,人往桌前一坐,便滿(mǎn)臉快活。他原先在一個(gè)高低壓開(kāi)關(guān)廠工作,前幾年廠子破產(chǎn)時(shí)買(mǎi)斷了工齡,現(xiàn)在是賦閑在家。平時(shí)養(yǎng)養(yǎng)鴿子,釣釣魚(yú),也是閑不著。有時(shí)候,還和一些鴿友參加一些賽鴿活動(dòng)。他說(shuō),“對(duì)啦,去年夏天我還去過(guò)你們赤峰。”
我問(wèn)他感覺(jué)怎么樣。
“一個(gè)干凈的城市,挺涼快!草原上的達(dá)理湖也好,沒(méi)污染,我們?cè)谀抢锍赃^(guò)一次魚(yú)宴,嘿,那叫一個(gè)鮮!”
酒席間,方長(zhǎng)貴不斷地夸獎(jiǎng)我餐館的菜做得棒,好吃。作為一種回報(bào),他給我講了許多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道理,說(shuō)既然到北京來(lái)發(fā)展,就得多吃苦,踏踏實(shí)實(shí)地奮斗,往好了整,往大了干。他還試圖引用拿破侖那句名言,但沒(méi)有成功。最后說(shuō)成了“不想當(dāng)大老板的人,做小生意也絕對(duì)是馬馬虎虎,不靈!”
接著,他還舉了個(gè)例子。說(shuō)幾年前他住的那條胡同來(lái)了一對(duì)溫州夫妻,本來(lái)是拿著5000塊錢(qián)想到北京來(lái)做生意的,可在火車(chē)上被人割了包,分文沒(méi)剩。到了北京沒(méi)地方落腳,就在他們那條胡同的一個(gè)墻角住了好幾天。后來(lái)兩口子給一家商店打工,賣(mài)皮鞋。方長(zhǎng)貴停了停,說(shuō),“現(xiàn)在怎么著?人家是自己開(kāi)鞋店,哪是小啊,兩層樓!”說(shuō)到這里,他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看著我,似乎是想檢驗(yàn)一下這個(gè)例子在我的臉上有沒(méi)有產(chǎn)生一種“震驚”的效果。
我只好用“震驚”的表情看他,“是嗎?”
坦率地說(shuō),即使我對(duì)他的話題興趣不大,也必須保持一種“興味盎然”的樣子,至少也是對(duì)這位老兄苦口婆心的一種尊重。只有他的話題告一段落的時(shí)候,我才趕緊端起酒杯說(shuō),“方大哥,咱們?cè)僬豢冢俊?/p>
“什么叫整一口呀,干了它!”
說(shuō)完,半兩酒,一飲而盡。
當(dāng)時(shí),一瓶二鍋頭已經(jīng)下去了,方長(zhǎng)貴還依然沉浸在一種酒猶未盡、興猶未盡、言猶未盡的狀態(tài)之中……說(shuō)實(shí)話,我真是有點(diǎn)陪不起了。但陪不起我也得陪著——畢竟,我是餐館的主人,他是我的房東,我總不能說(shuō)“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別喝啦,我餐館的伙計(jì)們?cè)撔菹⒘恕薄3醮我?jiàn)面,有這么說(shuō)話的嗎?
我妻子看出我有些支撐不住的樣子,她幾次湊過(guò)來(lái),給方長(zhǎng)貴敬上一杯酒,并就此搭訕幾句,問(wèn)他住在什么地方,回家坐幾路車(chē),末班車(chē)是幾點(diǎn)……言外之意我都聽(tīng)出來(lái)了,而方長(zhǎng)貴卻渾然不覺(jué),他說(shuō),“愛(ài)他媽幾點(diǎn)幾點(diǎn),我不坐丫的啦,我打車(chē)回去!”結(jié)果,一直熬到夜里12點(diǎn),方長(zhǎng)貴終于覺(jué)得“差不多了”,他看著我說(shuō),“兄弟,時(shí)候不早了,今兒就這么著吧。”
謝天謝地。送走了方長(zhǎng)貴,我長(zhǎng)長(zhǎng)地松了口氣。我妻子則嘮嘮叨叨地說(shuō),“酒膩?zhàn)樱∧氵€叫他有時(shí)間就過(guò)來(lái)喝點(diǎn)呢,煩死……”話未說(shuō)完,她突然盯著窗子一怔,說(shuō),“可毀了,他怎么又回來(lái)啦?”
我回頭一看,方長(zhǎng)貴果然搖搖晃晃地走進(jìn)了餐館。我趕緊迎過(guò)去,問(wèn)他是不是忘掉了什么東西。方長(zhǎng)貴呵呵一笑,嗔怪地說(shuō),“我忘了,您怎么也不跟我要哇!”他舉起手來(lái)——這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他的手指上捏著一把光禿禿的鑰匙。
3
方悅是怎么問(wèn)的方長(zhǎng)貴,方長(zhǎng)貴又是怎么說(shuō)的,我就不知道了。兩天后,方悅來(lái)到我們餐館。人還是那么漂亮,但說(shuō)話的語(yǔ)氣和態(tài)度卻像是變了一個(gè)人似的,非常客氣,甚至給人一種愛(ài)說(shuō)愛(ài)笑的感覺(jué)。我覺(jué)得北京的女性就是這樣,她們開(kāi)朗、大氣、熱情、周到,同時(shí)源于一種天生般的優(yōu)越感,又處處充滿(mǎn)了自信。方悅看了看我們的餐館,又聊了幾句家常,她告訴我們說(shuō),她問(wèn)了方長(zhǎng)貴,也問(wèn)了院里的鄰居,都說(shuō)我們兩口子人不錯(cuò),不惹事兒,這房子我們可以接著住下去。
我和妻子交換了一下眼神,都暗暗松了一口氣。事先我和妻子已經(jīng)探討過(guò),假如方悅執(zhí)意要收回她的房子,我們當(dāng)然會(huì)據(jù)理力爭(zhēng),只是糾纏起來(lái),即使她退還我們兩個(gè)月的房租,或者勉強(qiáng)允許我們?cè)僮∩蟽蓚€(gè)月,再收回,其結(jié)果還是一個(gè)樣,無(wú)非是我們?cè)僬曳孔樱侔峒摇傊莻€(gè)麻煩。現(xiàn)在,既然我們所擔(dān)心的事情并沒(méi)有發(fā)生,我和妻子的心情便可想而知。
中午,我們留方悅吃飯。方悅挺爽快,沒(méi)有推辭。當(dāng)我妻子問(wèn)她喜歡吃點(diǎn)什么的時(shí)候,她還主動(dòng)接過(guò)菜譜,親自點(diǎn)了一道小炒牛蛙。從經(jīng)驗(yàn)上說(shuō),大多數(shù)北京人都吃不了辣的,方悅是個(gè)例外,“我還就喜歡這個(gè)麻辣,越辣越想吃!”說(shuō)到北京的傳統(tǒng)菜和那些有名的傳統(tǒng)小吃,她反倒沒(méi)什么興趣,像炒肝啦,鹵煮啦,麻豆腐啦,感覺(jué)都一般。“哎,對(duì)了,你們喝過(guò)老北京豆汁兒?jiǎn)幔俊蔽液推拮佣颊f(shuō)沒(méi)有喝過(guò)。她說(shuō),“有時(shí)間你們?nèi)ズ纫淮卧囋嚕隙ê炔涣耍裁赐嬉鈨海娌幻靼自趺磿?huì)有人喜歡那么一種說(shuō)不來(lái)的怪味兒!”
上菜了,我問(wèn)她喝什么酒,啤的,還是白的?
“無(wú)所謂,什么都成。”
據(jù)方悅自己說(shuō),她喝酒的潛能是被一個(gè)東北人給“開(kāi)發(fā)”出來(lái)的。她老公是一家外企的部門(mén)經(jīng)理,平時(shí)應(yīng)酬多,偶爾也拉上她去湊個(gè)熱鬧。在一次酒桌上,她老公被一個(gè)東北人灌得一個(gè)勁拱手作揖,對(duì)方還是不依不饒,被逼無(wú)奈之下,只好由她替喝。她本以為一杯就醉,沒(méi)想到喝了一杯沒(méi)事兒,再喝一杯還沒(méi)事兒,那就喝吧!結(jié)果碰了十多杯,眼瞅著那個(gè)東北人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她愣是啥事兒沒(méi)有……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還有這么點(diǎn)長(zhǎng)處。“可能是遺傳,”方悅說(shuō),“我爸在世的時(shí)候就能喝,我哥也能喝……”
我妻子一聽(tīng)就笑了,她說(shuō),“方大哥可不是一般的能喝。”
方悅說(shuō),“哎,對(duì)了,他是不是總到你們餐館來(lái)蹭酒啊?”
我說(shuō),“沒(méi)有沒(méi)有。”
的確是沒(méi)有。方長(zhǎng)貴的家在前門(mén),離我的餐館很近,但他沒(méi)像我告訴他那樣“沒(méi)事就過(guò)來(lái)坐一坐”,只是到了我該預(yù)付房租的頭一天,他才會(huì)準(zhǔn)時(shí)打來(lái)一個(gè)電話,問(wèn)我忙不忙,餐館的生意怎么樣,卻閉口不提房租的事。這時(shí)候我就會(huì)主動(dòng)告訴他,我該交房租了,問(wèn)他有沒(méi)時(shí)間過(guò)來(lái)。方長(zhǎng)貴還挺吃驚,說(shuō),“是嗎?您瞧,我都忘了這碼事兒了……這時(shí)間可真他媽快!怎么著?那我明晚兒過(guò)去,您方便嗎?”我說(shuō),“方便。”他說(shuō),“得嘞!那明兒晚見(jiàn)。”多含蓄啊。
我說(shuō),“方大哥挺好的。”
“那是你不了解他。”方悅笑了一下,“當(dāng)然了,我哥人倒是不壞,有時(shí)候我還覺(jué)得他怪可憐的。他沒(méi)工作,兒子上大學(xué),只靠老婆一個(gè)人上班。家里窮不說(shuō),一個(gè)大男人,整天被老婆管著,一點(diǎn)地位沒(méi)有。話說(shuō)回來(lái),經(jīng)濟(jì)上不行,哪來(lái)的地位呀,是不是?說(shuō)實(shí)在的,頭兩年我真是沒(méi)少幫他,你倒是長(zhǎng)個(gè)心眼呀,哎,他不!我給他錢(qián),不管多少,他都會(huì)像表功一樣,全都交給了老婆。可反過(guò)來(lái)呢?他想買(mǎi)一盒三塊錢(qián)的煙,我嫂子都不給他錢(qián)……”
不知為什么,我妻子對(duì)于這樣的家長(zhǎng)里短最感興趣了,特別是聽(tīng)到哪家女人刁蠻呀、男人受氣之類(lèi)的話題她就興奮。她說(shuō),“是嗎?我看方大哥挺拿得起放得下的,不像是受老婆管束的人呀?”
方悅說(shuō),“這事也不能全怪我嫂子,關(guān)鍵是他不爭(zhēng)氣,沒(méi)追求,整天游游逛逛,啥也不干,手里一分錢(qián)沒(méi)有,還養(yǎng)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鴿子。”
說(shuō)到鴿子,我想起來(lái)了,記得有一次來(lái)取房租,他是和一個(gè)像瘦猴似的男人一起來(lái)的,介紹說(shuō)他們是“鴿友”。酒席間,兩個(gè)人一直聊著鴿子的話題,什么“李鳥(niǎo)”啊,“常州花”啊,“飛輪兒”啊……聊得津津有味,眉飛色舞。
我說(shuō),“養(yǎng)養(yǎng)鴿子,這不挺熱愛(ài)生活的嗎?”
方悅說(shuō),“不僅養(yǎng)鴿子,他還養(yǎng)女人呢。”
方悅一語(yǔ)驚人。然后,她又像失言似的轉(zhuǎn)換語(yǔ)氣,“不過(guò),也不能說(shuō)‘養(yǎng)’,說(shuō)‘養(yǎng)’就高抬他了,他沒(méi)錢(qián)拿什么‘養(yǎng)’?說(shuō)白了,就是找了個(gè)傍家兒,在一起瞎‘作’。”
方悅毫不避諱地抖摟她哥哥的隱私,讓我感到驚訝。同時(shí)又讓我有一種她沒(méi)把我們當(dāng)“外人兒”的感動(dòng)。
我妻子就不同了,聽(tīng)說(shuō)方長(zhǎng)貴找了個(gè)女人,表情立刻變了。她說(shuō),“是嗎?真是看不出來(lái),方大哥這么做可不對(duì)啦!”
方悅說(shuō),“我哥是不對(duì),我嫂子也有毛病,長(zhǎng)得一點(diǎn)不好看,還啥啥都說(shuō)了算……說(shuō)實(shí)話,我要是個(gè)男人,也會(huì)反感的。”
我樂(lè)了。
接著,就說(shuō)到了房子的事。據(jù)方悅講,她爺爺是個(gè)商人,死的時(shí)候留下了八處房產(chǎn),到了“文革”的時(shí)候只剩下了兩處,其余的全都被政府代管了。父母過(guò)世后,剩下的兩處房子她和方長(zhǎng)貴每人一處。她結(jié)婚后住進(jìn)了樓房,這間平房先后有四五個(gè)熟人和同事住過(guò),都是借住。直到兩年前才騰出來(lái)。當(dāng)時(shí)正好趕上她哥哥方長(zhǎng)貴下崗,為了幫他,她就把房子的鑰匙給了方長(zhǎng)貴,讓他把房子租出去,租金歸他。這本來(lái)是個(gè)好事兒,沒(méi)想到這房子卻被方長(zhǎng)貴租得三起三落,磨磨嘰嘰。
“說(shuō)起來(lái),也怪那些租房子的人不爭(zhēng)氣。”方悅說(shuō)。
頭一次是一對(duì)夫妻,30多歲,也是生意人,在東華門(mén)小吃街上賣(mài)酸辣粉。也不知道為啥,兩口子凈打架,沒(méi)日沒(méi)夜地打,還是女的打男的。女人竟追到院子里,拎小雞似的把男子摔到地上,騎著揍,有時(shí)候竟把那個(gè)男人打得號(hào)啕大哭……
方悅笑了,“你們說(shuō),這叫什么事兒呀!”
第二次,是個(gè)開(kāi)發(fā)廊的女子。單身一個(gè),倒是不吵架了。可沒(méi)過(guò)多久,便開(kāi)始往家里帶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白天就在屋子里鬼混。院里住的都是上了年紀(jì)的老人,哪瞧得慣這樣的人!因此,像頭次一樣,房子租出去沒(méi)多久,鄰居們又打電話,告訴她那租房子的人怎么怎么不像話,“大白天的就在屋子里折騰,什么玩意兒呀!”她只好告訴方長(zhǎng)貴,趕緊攆人。
第二個(gè)住戶(hù)被清出去之后,過(guò)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沒(méi)動(dòng)靜。她給方長(zhǎng)貴打過(guò)幾個(gè)電話,問(wèn)他房子租出去沒(méi)有,每一次問(wèn)他,方長(zhǎng)貴都說(shuō)沒(méi)碰到合適的主呢。那就碰吧,找吧。可是有一天她又接到了鄰居的電話,告訴她,說(shuō)方長(zhǎng)貴自己搬到那房子去住了。她聽(tīng)出鄰居的話里有話,到了那兒一看,這才發(fā)現(xiàn)了方長(zhǎng)貴的出軌行為。有一次她還碰巧見(jiàn)到了那個(gè)女的。“又老又丑,看上去比方長(zhǎng)貴還大呢。”講到這里,方悅有點(diǎn)激動(dòng)了,“當(dāng)時(shí)我那個(gè)氣呀!我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唉,就說(shuō)圖個(gè)樂(lè)吧,你倒是找個(gè)差不多的呀?還趕不上我嫂子好看呢!”
我妻子說(shuō),“打個(gè)比方,那就是王八瞅綠豆——對(duì)上眼珠兒啦!”
方悅說(shuō),“大姐比喻得太對(duì)了,當(dāng)時(shí)我都想罵他一頓。”
我妻子鄙夷地說(shuō),“要真是那號(hào)人,罵也沒(méi)用,管不住。”
“沒(méi)用也得管啊,”方悅說(shuō),“你們不知道,我哥身體不行,看著他五大三粗的,一身毛病!高血壓,糖尿病……最關(guān)鍵的是他腎還不好,這么鬧下去,不純屬作死么!一氣之下,我干脆把鑰匙要了回來(lái),不讓他租了。沒(méi)想到,他竟偷著配了一把,趁我出國(guó)的時(shí)候,又偷著把房子租給你們了。”
原來(lái)有這么多的前因后果,難怪我租房子的時(shí)候方長(zhǎng)貴那么猶豫不決。
我問(wèn)方悅,“我們住進(jìn)來(lái)之后,鄰居沒(méi)給你打過(guò)電話?”
她說(shuō),“沒(méi)有,我在韓國(guó)呆了半年,剛回來(lái)。”
我問(wèn)她去韓國(guó)是工作還是學(xué)習(xí)。
方悅解釋說(shuō),她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主要是去進(jìn)修一下韓語(yǔ),充充電。
我突然想到了一樁正事,問(wèn)她以后我的房租交給誰(shuí)。
方悅說(shuō),“交給我。”
我說(shuō),“要不要給方大哥打個(gè)電話,說(shuō)一聲?”
方悅說(shuō),“甭打,你打電話,說(shuō)不定他會(huì)不好意思的。我跟他說(shuō)好了,沒(méi)零花錢(qián)我給他,但在房子這件事上,我不叫他瞎摻和了。”
我說(shuō),“那好吧。”
打那之后,我再?zèng)]見(jiàn)過(guò)方長(zhǎng)貴。但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我會(huì)在某一個(gè)瞬間想起他。比如,天空中突然掠過(guò)一陣?guó)澤冢揖蜁?huì)抬起頭來(lái)想:這許不是方長(zhǎng)貴的鴿子啊?
4
此后方悅便成了我們餐館里的常客。她的家住在安定門(mén),距離王府井不是很遠(yuǎn)。據(jù)說(shuō)她的單位很輕松,老公常出差,又沒(méi)孩子,周末了,閑得沒(méi)事,即使去逛百貨大樓,也會(huì)順便到我們餐館坐一坐。有時(shí)候,我正悶在家里寫(xiě)我的小說(shuō)呢,我妻子會(huì)突然打回電話說(shuō),“你過(guò)來(lái)吧,方悅來(lái)了。”
自從見(jiàn)面之后,我妻子對(duì)方悅的印象一直很好,她說(shuō)別看人家是城里人,長(zhǎng)得又漂亮,一點(diǎn)沒(méi)有瞧不起人的架勢(shì),有啥說(shuō)啥,實(shí)實(shí)在在,比他哥可強(qiáng)多了。方悅喜歡吃我餐館里做的小炒牛蛙兒,每次來(lái),我妻子都會(huì)讓她吃上一份,再帶走一份。而方悅也有方悅的回報(bào),有時(shí)候是一條漂亮的絲巾,還有一次是一套很高級(jí)的進(jìn)口化妝品……如此一來(lái),女人之間的那種感覺(jué)就出來(lái)了。隔一段時(shí)間不見(jiàn),我妻子還會(huì)念念叨叨,她說(shuō),“方悅最近怎么沒(méi)動(dòng)靜了呢?”
至于我,對(duì)方悅的印象當(dāng)然也不錯(cuò)。坦率地說(shuō),她的漂亮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她性格挺開(kāi)朗。雖說(shuō)是從老北京胡同里長(zhǎng)大的,但她的“京味”不是很濃,沒(méi)有那種過(guò)多的客套,不虛張聲勢(shì),不一見(jiàn)面就喊“哎喲喂”,也基本上不使用“我他媽如何如何”那種讓人反感的句式……不僅如此,她還把我們的餐館稱(chēng)為“咱家的餐館”,把我們住的房子說(shuō)成“咱家的房子”,雖說(shuō)一字之別,卻給人一種親情似的溫暖。總之,我喜歡和方悅聊天。她的直言快語(yǔ),讓我從中獲得了許多愉悅。而方悅到了餐館,如果我不在,她也總是要問(wèn)上我妻子一句,“大哥不在啊?”
方悅對(duì)我的稱(chēng)呼不是很固定,有時(shí)候是“老板”,有時(shí)候是“大哥”,后來(lái)聽(tīng)說(shuō)我發(fā)表過(guò)幾篇小說(shuō),她又管我叫“作家”。有一回,她還突然想起似的盯著我說(shuō),“哎,我哥不是讓你叫他表哥么?那我也得叫你表哥啊。”
我趕緊說(shuō),“那可不敢當(dāng)。”
方悅笑著說(shuō),“嗨,什么敢不敢的,這年頭瞎叫唄。”
方悅的性格大大咧咧,對(duì)什么事都看得很開(kāi),甚至是一種沒(méi)心沒(méi)肺般的不在乎。說(shuō)到她為什么沒(méi)孩子時(shí),她毫不避諱地告訴我們說(shuō)不行,懷上過(guò)三次都流了,愣是坐不住。我妻子很同情,也很惆悵,“那是咋回事兒呢,沒(méi)想想辦法啊?”方悅說(shuō),“啥法都使了,沒(méi)用。一來(lái)氣,我還不要了呢!真是的,現(xiàn)在的年輕人都‘丁克’了,我還為生不出個(gè)孩子犯愁,讓作家說(shuō)說(shuō),我不犯傻了嗎?”
我妻子沉吟著說(shuō),“事倒是這么回事,可你老公愿意嗎?”
方悅笑著說(shuō),“他不愿意有個(gè)屁用。我跟他說(shuō)了,想要孩子,你想找誰(shuí)生找誰(shuí)生去!我是不受那個(gè)罪了。”說(shuō)到這里,她像突然想起來(lái)似的說(shuō),“對(duì)了,有時(shí)間我把我老公帶過(guò)來(lái),讓你們認(rèn)識(shí)一下,他挺好的。”
方悅的老公叫張弈勝,大個(gè)子,小平頭,一表人才。實(shí)話實(shí)說(shuō),頭次見(jiàn)面,他給我的印象不是很好。我覺(jué)得這個(gè)外企公司的銷(xiāo)售部經(jīng)理有點(diǎn)端架子,無(wú)論你說(shuō)啥,他都是淡淡一笑,或微微點(diǎn)頭,給人的感覺(jué)不僅是城里人,是外企的小頭目,套用一位作家說(shuō)過(guò)的話,好像他褲襠里的家伙都是玉的。直到方悅夸了半天我和妻子為人如何如何,又告訴他我還是個(gè)“作家”之后,他又故意矜持了一段時(shí)間,然后才把那副假模假式的墨鏡摘下來(lái)。漸漸聊開(kāi)——特別是幾杯酒下肚之后,居然特別能侃!而且還不愧是個(gè)外企人,一張口都是一些國(guó)際性的話題。他說(shuō)世界上最漂亮的不是男人,不是女人,是泰國(guó)的人妖;皮膚最細(xì)嫩的不是白種人,不是黃種人,是黑人;俄羅斯人愛(ài)喝北京二鍋頭;荷蘭人最開(kāi)放,男人出差,女人幫助收拾行李的時(shí)候,總忘不了在丈夫的行李包里塞上一盒安全套……他還說(shuō),在日本,不管在超市,還是在餐館,只要你認(rèn)準(zhǔn)了,確定他是個(gè)日本人,啥也別說(shuō),上前“啪啪”抽丫兩個(gè)嘴巴,轉(zhuǎn)身走你的,啥事兒沒(méi)有。
當(dāng)時(shí)方悅都怔了,她審視著張弈勝說(shuō),“快得了吧,那還不得人腦打出狗腦子來(lái)呀?”
張弈勝說(shuō),“你這就外行了吧?我跟你說(shuō),丫站在那里,一動(dòng)都不動(dòng)。”
我就,“那是咋回事兒,打愣了?”
張弈勝怔怔地看著我說(shuō),“什么叫打愣了呀,日本人善于反思,你打了他耳光,人家不會(huì)像中國(guó)人那樣立刻還手,而是得先想明白了:這人是誰(shuí)?他為什么要打我?我在什么地方得罪過(guò)這個(gè)人嗎?趁丫在那兒反思,你早就撒丫子沒(méi)影了,知道嗎?”
我哈哈大笑。
張弈勝到我餐館來(lái)過(guò)幾次,我記不清了。從后來(lái)的接觸上看,我覺(jué)得這個(gè)人也不錯(cuò)。盡管能侃,沒(méi)邊沒(méi)沿,云山霧罩,但為人卻很仗義,很哥們兒。后來(lái)每次到餐館來(lái),他幾乎都帶一瓶酒,有一次還扔給我一條煙,而他自己卻不會(huì)吸。還有一次,他曾指著鼻子告訴我:“沒(méi)錢(qián)你說(shuō)話!”讓我挺感動(dòng)的。
最讓人感動(dòng)的還是方悅。
有一天下午,她打來(lái)電話,說(shuō)她家里換下一張雙人床,問(wèn)我要不要,要的話,就到她家里取;不要,她就賣(mài)給收破爛的了。
說(shuō)起來(lái),這簡(jiǎn)直是雪中送炭。我們住進(jìn)那間房子之后,睡的還是原來(lái)的一張雙人床,鐵的,不知被多少人用過(guò)了,很破了,我用鐵絲綁過(guò)好幾次,還是不行。睡在上面,只要你一動(dòng),它就會(huì)“咯吱”一聲……尤其是在夜深人靜的時(shí)候,特別煩人。依照我早就想換了它了,我妻子不同意。她說(shuō),“住在別人的房子里,你買(mǎi)什么床!不住的時(shí)候你還想搬著走呀?快將就著用得啦。”因此聽(tīng)方悅那么一說(shuō),我叫上兩個(gè)伙計(jì),蹬上三輪車(chē)就去了。
方悅家住在十層樓。撤換下來(lái)的床放在門(mén)外的走廊里。我看了看,是那種組裝式的,床頭,床屜,包括厚厚的席夢(mèng)絲床墊,幾乎還是新的。我問(wèn)方悅這么好的床怎么不要了。她告訴我,床是不錯(cuò),就是窄了點(diǎn),一米八,這次換了個(gè)兩米二的。直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當(dāng)時(shí)的所思所想:只有特別熱愛(ài)生活、講究生活質(zhì)量的人,才會(huì)如此把床當(dāng)成一回事吧?
那天張弈勝?zèng)]在家。就在兩個(gè)伙計(jì)往樓下運(yùn)床的時(shí)候,方悅還邀請(qǐng)我到他們家里看了看。那是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裝修不錯(cuò),歐式風(fēng)格,本色的實(shí)木地板,面包似的沙發(fā),厚厚的純毛提花地毯,鑲著金色相框的小油畫(huà)……一切都給人一種高貴、豪華之感。臥室里,是那張剛剛安好的全包式大床,柔軟,霸氣。床頭上方掛著主人的結(jié)婚照,男人神態(tài)瀟灑,女人嫵媚可愛(ài)。此外,房間里擺放有序的各種小物件,新奇,古怪,讓人聯(lián)想到主人生活情趣上的優(yōu)雅與精致。
方悅陪著我在房間里走了一個(gè)來(lái)回。
“還行吧?”
“啥叫還行呀,用你們北京話說(shuō),太棒啦!”
方悅對(duì)我的評(píng)價(jià)很高興,她說(shuō)有時(shí)間再帶我去他們別墅看看。
5
方悅家的別墅很遠(yuǎn),在北京西南郊。那時(shí)候的郊區(qū),對(duì)一些城里人來(lái)說(shuō)已經(jīng)很有吸引力了。在餐館,我就常聽(tīng)一些人談?wù)撝p休日要去哪哪郊區(qū),那種興沖沖的勁頭,好像是工作了一周,就為了周末能到郊區(qū)去。是啊,郊區(qū)有山,有水,有野花野草,有城市里呼吸不到的新鮮空氣,到那里去爬爬山,釣釣魚(yú),搞搞野餐什么的,的確別有一番情趣。不過(guò),那時(shí)候有這種情趣的大都是一些優(yōu)雅的窮人,而奔著自家別墅去的人還不是很多。
方悅和張弈勝算一個(gè)。他們是富人。
那年中秋節(jié),我們就是在方悅家的別墅度過(guò)的。當(dāng)時(shí),我和妻子不想去,一是對(duì)餐館放心不下,二是覺(jué)得去別人家過(guò)節(jié)不合適,太麻煩。方悅卻好說(shuō)歹說(shuō),非要拉上我們?nèi)ネ嫱妫潘煞潘伞Kf(shuō),“整天泡在餐館里多膩呀,還是作家呢,不體驗(yàn)生活,整天閉門(mén)造車(chē)哪成啊!”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只好去了。
那天是方悅親自駕車(chē),車(chē)上只坐著我和妻子兩個(gè)人。她老公則開(kāi)著單位的車(chē)去接別的朋友。方悅的車(chē)技不錯(cuò),兩只手很隨意地扶著方向盤(pán),白玉似的手腕上吊著金色的飾鏈。出城之后,她打開(kāi)了車(chē)內(nèi)的音響,是卡朋特的《昨日重現(xiàn)》,那是我第一次聽(tīng)到這首歌,盡管是英文,我聽(tīng)不懂歌詞,但是好聽(tīng)。直到現(xiàn)在,每當(dāng)聽(tīng)到這首歌曲,我就會(huì)油然想起我們坐著方悅的車(chē)去她家別墅的情景,那是相當(dāng)愉快。40多公里的路程,感覺(jué)很快就到了。
那片別墅區(qū)叫“楓林小寨”,環(huán)境優(yōu)美,非常漂亮。車(chē)駛進(jìn)大門(mén)之后,只要見(jiàn)到的保安,就會(huì)“啪”地一個(gè)立正,同時(shí)行一個(gè)正規(guī)的軍禮,不知道的,還以為車(chē)?yán)镒氖鞘组L(zhǎng)呢。方悅把車(chē)開(kāi)到一座兩層小樓近處,停下。她先是帶著我們?cè)谛^(qū)里轉(zhuǎn)了轉(zhuǎn)。真的不錯(cuò)。一座座獨(dú)立的兩層小樓,風(fēng)格別致地散落在樹(shù)叢中、草地上,像一片微型的小教堂。小區(qū)里有湖,湖中有曲橋,有涼亭,有成群結(jié)隊(duì)的紅色小魚(yú)……湖邊的假山啦,瀑布啦,都做得逼真。正是金秋時(shí)節(jié),天氣好得無(wú)可指責(zé),和人的心情一樣清朗、歡暢。我們?cè)谛^(qū)里轉(zhuǎn)了一圈兒,又回到了方悅的兩層小樓,上上下下地參觀。格局不錯(cuò),大約有200多平米,裝修得沒(méi)有市內(nèi)的家豪華,用方悅的話說(shuō),他們只是偶爾來(lái)住一下,換個(gè)心情,就沒(méi)怎么弄它。
緊接著,有五輛轎車(chē)相繼到達(dá)。20多個(gè)男女,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單挑兒。方悅告訴我們,都是她老公的朋友和同事。一到別墅,所有人的眼神兒都活躍起來(lái),相互握手,寒暄,嘰嘰嘎嘎地說(shuō)笑。我和妻子都不認(rèn)識(shí),只好垂手站在一邊。方悅在人群里走來(lái)走去,快樂(lè)地和每個(gè)人打著招呼,并不時(shí)拉過(guò)一個(gè)來(lái)給我和妻子介紹。只是忙了一周遭,幾乎和所有人握了手,到最后我連一個(gè)人的名字都沒(méi)記住。接下來(lái),活動(dòng)照常進(jìn)行。我妻子和一個(gè)胖女人協(xié)助方悅準(zhǔn)備晚上的酒菜,其他人各取所樂(lè)。有搓麻將的,有打牌的,有吵吵嚷嚷著要去泡溫泉的……張弈勝則興致勃勃地慫恿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隨便‘作’!”
一直“作”到夕陽(yáng)西下,又開(kāi)始喝酒。喝酒的場(chǎng)面就不用細(xì)說(shuō)了。男女聚會(huì)的場(chǎng)面大體相當(dāng)。無(wú)非是招招呼呼地喝酒,扭扭捏捏地唱歌,侃大山,吹牛皮,一個(gè)葷段子講出來(lái),便會(huì)引出一陣哄堂大笑……都這樣。值得說(shuō)明的是,在這幫城里人面前,盡管我和妻子的身份有點(diǎn)特殊,但酒桌上卻沒(méi)感覺(jué)到有什么讓人不舒服的地方。相反,他們的一句問(wèn)話、一杯敬酒,甚至一個(gè)溫暖的眼神兒都讓我們?yōu)橹袆?dòng)。后來(lái),在方悅的慫恿下,我還大起膽子朗誦了蘇軾的一首詞《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shí)有)》,并博得了滿(mǎn)堂喝彩。事后我和妻子回憶,都覺(jué)得那個(gè)中秋節(jié)過(guò)得有意思,很難忘。
后來(lái)我知道,方悅一生的痛苦就是從那一天開(kāi)始的。
6
中秋節(jié)之后不久,方悅來(lái)取房租。那天我妻子去了木樨園小商品批發(fā)市場(chǎng)。我留方悅吃飯,她說(shuō)忙著,不吃飯。
“抽你支煙吧。”
我狐疑地看著她,“你啥時(shí)候?qū)W會(huì)抽煙了?”
她笑了笑,“無(wú)聊,抽著玩唄。”
我按著打火機(jī),給她點(diǎn)上。
她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吐出煙霧。
“我問(wèn)作家個(gè)問(wèn)題。”
我笑了,“什么作家不作家的,你說(shuō)。”
她看著我,“你們男人是不是都好色?”
坦率地說(shuō),平時(shí)我和方悅說(shuō)話是比較注意分寸的,只有我妻子不在場(chǎng)的情況下才偶爾開(kāi)個(gè)玩笑。記得有一回說(shuō)起我們頭次見(jiàn)面時(shí)的情景,方悅說(shuō)當(dāng)時(shí)她恨不得把我從被窩里拖出來(lái)。我說(shuō),“那可慘啦。”她看著我,“為什么呀?”我說(shuō),“那天我連褲頭都沒(méi)穿……”方悅聽(tīng)了咯咯直笑,“什么人這是!”
現(xiàn)在,我沒(méi)想到方悅會(huì)提出這樣的問(wèn)題。這可是個(gè)拷問(wèn)靈魂的問(wèn)題。而方悅的神態(tài)分明是認(rèn)真的,她用期待的目光看著我,這就讓我更加不好意思了。
我躲開(kāi)方悅的眼睛,笑著說(shuō),“這事讓我咋說(shuō)呢……”
“直說(shuō)。”
我沉吟了一下,嘿嘿兒地樂(lè)了。
至此才意識(shí)到,有時(shí)候直言不諱還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方悅放下目光,泄氣般地一笑,沒(méi)再追問(wèn)。
時(shí)間很快到了年底。我給方悅打電話,讓她來(lái)取房租。她回答說(shuō)忙,“過(guò)段時(shí)間再說(shuō)吧,我都不急你急啥?”以往方悅說(shuō)完這話的時(shí)候,肯定會(huì)托出一串銀鈴般的笑聲,但這次沒(méi)有,說(shuō)完她就掛了電話。
我跟妻子說(shuō),“方悅好像有什么事。”
我妻子不以為然,她說(shuō),“整天像裝在蜜罐子里似的,她有啥事?”
半個(gè)月之后,方悅來(lái)到了我們餐館。一見(jiàn)面,我和妻子都禁不住大吃一驚。過(guò)去的方悅總是那么整齊、干凈、光彩照人,而眼前的方悅卻憔悴得像個(gè)女巫。
我妻子問(wèn)她咋這么瘦,是不是生病了?
方悅說(shuō),“沒(méi)有呀,怎么了?我這不挺好嗎?”
我妻子說(shuō),“……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沒(méi)過(guò)來(lái),你忙啥呢?”
方悅說(shuō),“忙著離婚唄。”
一句話,讓我和妻子全都怔住了。
按說(shuō),在當(dāng)時(shí),這樣的話題已經(jīng)很平常了。如果說(shuō)誰(shuí)誰(shuí)離了婚,無(wú)異于聽(tīng)說(shuō)誰(shuí)誰(shuí)丟了輛自行車(chē)一樣,沒(méi)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了。相反,倒是那些沒(méi)離婚的人,往往成了人們打趣的對(duì)象,“還咬著牙堅(jiān)持吶?差不多就行啦,離吧!”
但方悅的話我還是不信。在我眼里,她和張弈勝的感情非常好,每次來(lái)我們餐館都是挽著胳膊來(lái),挽著胳膊走。即使張弈勝?zèng)]邊沒(méi)沿兒地吹牛皮,方悅都是用很溫柔的表情瞧著他;而張弈勝對(duì)方悅也是彬彬有禮,有一回還親自挾起一塊小炒牛蛙送進(jìn)方悅的嘴里……這樣的夫妻怎么能說(shuō)離就離了呢?
我妻子盯著方悅,“你別瞎說(shuō)了。”
方悅點(diǎn)上一支煙,吸著,“真的,前幾天辦的手續(xù),利索了。”方悅的聲音平靜、倦怠,近乎于冷漠。
我妻子問(wèn)她怎么回事。
方悅吸了一口煙,又把煙灰往煙缸里彈了彈,說(shuō),“小三兒插足。”
我妻子說(shuō),“是嗎?那女的是干啥的?”
方悅說(shuō),“你們見(jiàn)過(guò),就是上次在別墅唱英文歌兒的那個(gè)。”
我的記憶里立刻浮現(xiàn)出一個(gè)漂亮的女孩。高鼻梁,大眼睛,上身穿一件白色寬松T恤衫,下身一條深藍(lán)色牛仔褲繃在腿上,優(yōu)雅、筆直。吃飯時(shí)她就坐在張弈勝旁邊,不說(shuō)話,一雙大眼睛看來(lái)看去,閃爍出一種浪漫主義的幻想……記得那天她唱的英語(yǔ)歌就是方悅在車(chē)上播放的《昨日重現(xiàn)》,嗓音渾厚,好聽(tīng),特別是那句“沙啦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悅告訴我們,她就是那次在別墅看出“事兒”來(lái)的。在酒桌上,她就發(fā)現(xiàn)兩個(gè)人的眼神都不對(duì)勁兒,后來(lái)我朗誦“但愿人長(zhǎng)久”的時(shí)候,別人都鼓掌,只有張弈勝坐在那里,光喊“好”,不鼓掌。她側(cè)眼往桌下一看,才發(fā)現(xiàn)他一只手在撫摸那個(gè)女孩的大腿……當(dāng)時(shí)她假裝沒(méi)看見(jiàn)。但這事她可記下了。回家后,她像平時(shí)一樣,該怎么著還怎么著,只在心里觀察張弈勝的一舉一動(dòng)。有段時(shí)間,她發(fā)現(xiàn)張弈勝回家后無(wú)精打采,兩眼無(wú)神,但襯衣卻一天一換,她覺(jué)得他肯定有事兒。果然,在后來(lái)三個(gè)多月的時(shí)間里,她就親自抓住過(guò)他們兩次!
“頭一次,我說(shuō)我?guī)F(tuán)去韓國(guó),其實(shí)我哪兒也沒(méi)去。第二天晚上我是十點(diǎn)鐘回的家,嘿,兩個(gè)人已經(jīng)睡上了。說(shuō)起來(lái)像做夢(mèng)一樣,但事情確實(shí)發(fā)生了。當(dāng)時(shí)我沒(méi)有大喊大叫,沒(méi)像電視劇里似的去揪打那個(gè)女孩……我蒙了。就那么站在臥室門(mén)口,看著他們把衣服穿好。然后我只說(shuō)了一句話,問(wèn)他,是讓我走還是讓那個(gè)女孩走?結(jié)果當(dāng)然是那個(gè)女孩滾蛋了。她走到門(mén)口的時(shí)候,我才覺(jué)得我有話要跟她說(shuō),我說(shuō)‘你丫給我站住!’那女孩嚇了一哆嗦,但挺聽(tīng)話,她回過(guò)來(lái)看著我,臉都白了。我告訴她,‘如果你再讓我在這個(gè)屋子里見(jiàn)到你,我就讓你在這個(gè)世界上消失!’話一出口,我才意識(shí)到我他媽挺傻的,這不等于告訴人家事情就這么過(guò)去了嗎?
“其實(shí)沒(méi)過(guò)去。女孩走后,我開(kāi)始‘作’他,摔手表,砸茶幾,電視機(jī)也被我踢了一腳,沒(méi)踢壞,那玩意兒還真他媽結(jié)實(shí)。張弈勝?lài)槈牧耍ё∥遥蛔屛覄?dòng),一個(gè)勁兒地說(shuō)他錯(cuò)了,給我下跪,媽都叫了,哭得還真像個(gè)孩子……他一直給我解釋?zhuān)豢赡芨莻€(gè)女孩有什么結(jié)果,就是玩玩。其實(shí)他甭解釋我也知道,一個(gè)外地的丫頭片子,工作都是臨時(shí)的,他不可能娶她。但即使這樣,我還是‘作’他,飯也不做,兩個(gè)多月一次都沒(méi)讓他碰我。”
方悅又摸起一支煙,點(diǎn)上。
“兩個(gè)多月之后我們才和好。感覺(jué)比原來(lái)還好。去年年底,他說(shuō)要去河北出個(gè)短差,兩天就回來(lái)。我說(shuō)你去吧。第二天,我在單位老是心神不定,腦子里突然一閃,他是不是在騙我呀?哎,我跟你們說(shuō),我的第六感覺(jué)特準(zhǔn)!當(dāng)時(shí)我想都沒(méi)想,開(kāi)上單位的車(chē)就奔著別墅去了。說(shuō)實(shí)話,第一次抓他們,我是特別想成功。這次在路上我卻突然害怕了,如果這次我再成功,就等于我徹底失敗了。
“到了別墅,我連車(chē)都沒(méi)下,就坐在車(chē)?yán)铮粗ㄏ騽e墅的竹林小道,我拿不定主意過(guò)去還是不過(guò)去……就在這時(shí),我聽(tīng)到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咔咔咔,緊接著兩個(gè)人就挎著胳膊出來(lái)了。他們同時(shí)也發(fā)現(xiàn)了我。我啥也沒(méi)說(shuō),開(kāi)車(chē)就走。
“我到家的時(shí)候,他已經(jīng)坐在沙發(fā)上等我了。這一次,他不但沒(méi)跟我道歉,沒(méi)有一個(gè)像樣的解釋?zhuān)炊鴨?wèn)我為啥要跟蹤他。我們吵了起來(lái)。他嚷得比我還兇,說(shuō)‘這都什么年代了,我不就是玩玩嗎,而且還是免費(fèi)的,怎么啦?’我說(shuō),‘得!我不管你免費(fèi)不免費(fèi),你不說(shuō)就是玩玩嗎?我還想玩呢!咱們自個(gè)兒玩自個(gè)兒的,你說(shuō)怎么著吧?’你們猜,他是怎么說(shuō)的?他想都沒(méi)想地說(shuō),‘那肯定不行!’我說(shuō),‘那好,咱他媽誰(shuí)也甭廢話了,離!’”
我插話說(shuō),“這說(shuō)明他對(duì)你是有感情的。”
方悅把煙頭戳進(jìn)煙灰缸里,慢慢捻滅。
她說(shuō),“也許吧,男人可以愛(ài)著一個(gè)人而去和別人睡覺(jué),但女人不行。當(dāng)她想用同樣的方式去報(bào)復(fù)對(duì)方的時(shí)候,她的愛(ài)情就已經(jīng)不存在了。”
7
離婚后,方悅開(kāi)始拼命工作。用她自己的話說(shuō),這么多年,她一直過(guò)著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生活,沒(méi)理想,甚至沒(méi)有幻想,只把張弈勝當(dāng)成她的全部生活,當(dāng)成她的整個(gè)世界。工作上馬馬虎虎,無(wú)論是同事還是鄰居,甚至連個(gè)知心的朋友都沒(méi)有。離婚后,她只好用工作的方式擦亮心情,為自己療傷。她開(kāi)始帶團(tuán)出國(guó),經(jīng)常在東南亞一帶轉(zhuǎn)來(lái)轉(zhuǎn)去,少則一周,多則十幾天。
夏天,她去新馬泰之前到我們餐館來(lái)過(guò)一次。看上去,她顯得比原來(lái)還整齊,漂亮,皮膚黑了點(diǎn),精神不錯(cuò)。那次她取走了我們兩個(gè)月的房租,給我留下了一把她家的鑰匙,她說(shuō)她養(yǎng)了兩盆花,麻煩我隔幾天去替她澆一次水。能為方悅做點(diǎn)什么,讓我感到高興。我只是告訴她,必須把家里錢(qián)和存折藏起來(lái)。方悅咯咯直笑,她嗔怪地說(shuō),“什么人這是!”
方悅還是住在安定門(mén)外的那套房子里。據(jù)方悅說(shuō),那原本是張弈勝婚前買(mǎi)的房子,但郊外那座別墅卻屬于他們婚后的共同財(cái)產(chǎn)。離婚時(shí),當(dāng)她提出要這座房子的時(shí)候,張弈勝因?yàn)樾奶摾硖潱阆裱a(bǔ)償自己過(guò)失似的,表示無(wú)論方悅提出什么樣的要求,他都會(huì)無(wú)條件地接受。
第一次給方悅澆花,是我和妻子一塊兒去的。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凈,一切都像原來(lái)那么柔軟、高貴。只是床頭上方的結(jié)婚照不見(jiàn)了,取而代之的是安格爾的那幅著名的油畫(huà)《泉》。我靜靜地望著那幅畫(huà),不知道方悅想以此寓意什么。
我妻子小心翼翼地把客廳和臥室看了一遍,并為此產(chǎn)生了一種深刻的惆悵,她感慨地說(shuō),“有房子的沒(méi)家,有家的沒(méi)房子……這個(gè)世界到哪兒說(shuō)理去啊。”
方悅養(yǎng)的是兩盆蘭花,不知什么品種,一黃一紫,都開(kāi)得好看。后來(lái)她告訴我,那叫“胡姬花”,是從新加坡帶回的。我想,難怪她如此精心。
后來(lái),我又去給方悅澆過(guò)幾次花,記不清了。她每次從國(guó)外回來(lái),我都會(huì)向她交一次鑰匙,而她卻總是說(shuō),“過(guò)幾天還得走,就放你那兒吧。”
我說(shuō),“你什么時(shí)候走再給我。”
她說(shuō),“你這人怎么這么麻煩呀?這事兒我就賴(lài)上你啦,怎么著吧!”
我不可能怎么著。恰恰相反,能把一個(gè)女人家的鑰匙掛在自己的腰帶上——無(wú)論從哪個(gè)角度說(shuō),這種感覺(jué)都挺好的。
直到現(xiàn)在,我仍然認(rèn)為方悅是我們?cè)诒本┳钚刨?lài)我們的房東,也是我們最好的房東。遺憾的是,好景不長(zhǎng)。那年秋天,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像上次一樣,我們所住的那條胡同也要拆遷了。而且說(shuō)拆就拆,一時(shí)間鬧得整條胡同雞飛狗跳。作為一戶(hù)臨時(shí)的房客,我們不得不去尋找新的住處。只是想到我們和房主的關(guān)系處得不錯(cuò),離開(kāi)那間房子的時(shí)候,我和妻子都多少有一點(diǎn)留戀和傷感。
終止了房東與房客的關(guān)系之后,我們和方悅的交往差不多持續(xù)了一年。這期間,她偶爾會(huì)到我的餐館吃一次小炒牛蛙;在她帶團(tuán)出國(guó)的時(shí)候,我還像原來(lái)一樣,去給她的兩盆胡姬花澆一次水。
有天傍晚,方悅打來(lái)電話,想請(qǐng)我和妻子吃飯。
其實(shí),這之前她已經(jīng)請(qǐng)過(guò)我們兩次了。一次是她家附近新開(kāi)張了一家餐館,她說(shuō)有幾道菜做得非常棒,讓我們?nèi)テ穱L品嘗,借鑒一下。還有一次是她親自做了幾個(gè)菜,讓我們?nèi)プ8K?8歲生日。這一次則她“特想找人喝點(diǎn)酒”,又不愿意動(dòng)彈,便邀請(qǐng)我們到她家附近的餐館去換換口味兒。
我知道,方悅是個(gè)喜歡熱鬧的人,離異后一直過(guò)著孤單、寂寞的生活,她請(qǐng)我們吃飯,無(wú)非是想請(qǐng)我們?nèi)フf(shuō)說(shuō)話,聊聊天。不巧的是,我妻子兩天前回了老家,我便實(shí)話實(shí)說(shuō),告訴方悅以后再說(shuō)吧。
方悅卻非常執(zhí)拗,她說(shuō),“什么叫以后再說(shuō)呀,有一個(gè)算一個(gè),你自己過(guò)來(lái)還怕我吃了你?”
我答應(yīng)了她。我想,如果我堅(jiān)持不去,一來(lái)讓方悅失望,二來(lái)也有點(diǎn)不識(shí)抬舉了。與此同時(shí),和一位漂亮的女人單獨(dú)對(duì)飲,可能也是一種不錯(cuò)的體驗(yàn)。
在地壇西門(mén)的一家餐館里,我和方悅面對(duì)面地坐下。熟悉的場(chǎng)面,不一樣的感覺(jué)。我說(shuō)過(guò),我對(duì)方悅的印象絕對(duì)不壞。柔和的燈光下,她顯得比平時(shí)還漂亮,看著她認(rèn)認(rèn)真真點(diǎn)菜的樣子,一時(shí)間,眼前的一切恍若夢(mèng)境,讓人立刻泛起一種繾綣的心緒和一種類(lèi)似于懷舊般的溫馨。我暗暗調(diào)整情緒,努力尋找平時(shí)和方悅吃飯時(shí)的狀態(tài)。
我平靜地看著她,問(wèn)她為什么今天“特想喝點(diǎn)酒”。
方悅遲疑了一下,“說(shuō)出來(lái)你肯定會(huì)笑。”
我說(shuō),“說(shuō)說(shuō)看。”
她說(shuō),“今天是我捉奸一周年的日子……”
我的確想笑,但我沒(méi)笑。我不知道方悅為什么會(huì)把這樣一個(gè)日子記得這么清楚。后來(lái),我曾特意“百度”過(guò)“捉奸”這兩個(gè)字,網(wǎng)上是這么說(shuō)的:
捉奸基本上算是一件損人不利己的事,它等于是主動(dòng)把對(duì)方造成的傷害和侮辱最大程度地固定在自己的臉面和心靈上,也等于是把自己和配偶的尊嚴(yán)同時(shí)折殺殆盡,并把彼此推到了無(wú)可挽回的絕境上。
對(duì)于這件事,我不知道方悅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對(duì)自己的行為是不是產(chǎn)生過(guò)后悔。我單是知道,離婚后方悅一直不忌諱關(guān)于前夫的話題。有一次,說(shuō)到張弈勝如何干凈,又如何會(huì)做菜的時(shí)候,她的眼睛還能發(fā)亮。事后我和妻子推斷,兩個(gè)人復(fù)婚的可能性非常大。為此,我妻子還勸過(guò)方悅,“事兒都過(guò)去了,抻上一段時(shí)間,讓他知道知道鍋是鐵打的,就行了,該復(fù)婚就復(fù)婚吧。”對(duì)此,方悅的態(tài)度似乎不是很積極,她笑了笑,含糊其辭地說(shuō),“聽(tīng)天由命吧。”
我們沉默了半天。然后,我問(wèn)她和張弈勝還有沒(méi)有聯(lián)系。
方悅搖頭,“他結(jié)婚之后就沒(méi)聯(lián)系了。”
我詫異地說(shuō),“他結(jié)婚啦?”
方悅用一只手指撥弄著桌上的打火機(jī),平靜地說(shuō),“有幾個(gè)月了。”
“是和那個(gè)外地女孩嗎?”
“不是。北京的,也是個(gè)20幾歲的女孩。我真是納悶了,現(xiàn)在的女孩咋這么犯賤……”
“我還以為你們能復(fù)婚呢,”我不無(wú)遺憾地說(shuō)。“既然這樣,那你……也該早作打算才是。”
“這不是早打算就能解決了的事兒。”方悅說(shuō)。這時(shí)候,我意外地發(fā)現(xiàn)方悅的眼窩濕了。沉默了一會(huì)兒,她突然無(wú)奈地一笑,“人這玩意兒真是不可思議。”
我不知道她要表達(dá)什么,附和著說(shuō),“是啊,高級(jí)動(dòng)物嘛。”
“你還記得我哥吧?”
“你說(shuō)方大哥呀?我當(dāng)然記得。”
方悅說(shuō),“知道嗎?當(dāng)我知道他找了個(gè)傍家兒的時(shí)候,我只擔(dān)心他把自己的身體作壞了,別的,我還真沒(méi)有多想。比方說(shuō),如果因?yàn)檫@事兒我嫂子和他糾纏起來(lái),我肯定會(huì)替我哥說(shuō)話,去開(kāi)導(dǎo)我嫂子。可是,事情突然落到我自己頭上的時(shí)候,我咋就接受不了呢?”
我想了想說(shuō),“人都是這樣。”
方悅依然困惑著表情,“說(shuō)實(shí)話,張弈勝對(duì)我一直不錯(cuò),平時(shí)我要什么他給什么,即使我要個(gè)星星,他也會(huì)有辦法不讓我失望。我就是不明白,他這么寵著我,為啥還會(huì)去跟別的女孩睡覺(jué)。”
我記得好像是哪個(gè)作家說(shuō)過(guò),性是一種充滿(mǎn)了無(wú)理性的東西。我想了想說(shuō),“也許是一時(shí)沖動(dòng),也許是為了尋找刺激,有時(shí)候還是一種湊巧而來(lái)的機(jī)會(huì)吧。”
“和愛(ài)情沒(méi)有關(guān)系?”
“有時(shí)候有,有時(shí)候沒(méi)有。”
“比如。”
“比如……說(shuō)得具體點(diǎn)吧,張弈勝和那個(gè)女孩他們不是沒(méi)結(jié)婚嗎?”
方悅說(shuō),“他可是想結(jié),是人家那個(gè)女孩不干!”
我沉吟著說(shuō),“這樣啊……在小說(shuō)里,一般都是城里的男人玩夠了鄉(xiāng)下的女孩,然后再把她們甩掉。”
她看著我,“生活比你們作家編的故事更復(fù)雜吧?”
我說(shuō),“那肯定是。”
她突然想起似的,“哎,對(duì)了,你可別把我的事兒寫(xiě)到小說(shuō)里去啊……”
我笑著說(shuō),“不會(huì)的,至少現(xiàn)在我還沒(méi)想過(guò)。”
“算了,寫(xiě)就寫(xiě)吧,我都這樣了還怕啥呀?我啥都不怕了!來(lái),喝酒!”
那天我們喝的是方悅帶的一瓶洋酒,什么酒我忘了,只記得是一種大肚子酒瓶,700毫升。方悅在我們的杯子里分別加了冰塊,入口的感覺(jué)有點(diǎn)苦。
我們邊喝邊聊。說(shuō)新加坡的夜間野生動(dòng)物園,說(shuō)日本的人體盛宴,說(shuō)美國(guó)大片,說(shuō)伊朗的《小鞋子》。有一陣,不知怎么的,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原點(diǎn),竟討論了半天世界上有沒(méi)有真正的愛(ài)情。其實(shí)這是一個(gè)既簡(jiǎn)單而又復(fù)雜的問(wèn)題。也只有那些純情的少女和在婚姻上失敗的女人才會(huì)提出這樣的問(wèn)題吧。這一次我倒是來(lái)了直言不諱,反正不涉及自己的靈魂,瞎說(shuō)唄。所謂有沒(méi)有真正的愛(ài)情,十有八九的人,肯定都會(huì)說(shuō)有,泛泛而談,還可以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但在我看來(lái),那畢竟都是別人的事——用別人的事例來(lái)說(shuō)明有沒(méi)有真正的愛(ài)情,就像討論這個(gè)世界有沒(méi)有鬼一樣,與自己沒(méi)有太大的關(guān)系。說(shuō)到底,愛(ài)情不過(guò)是一種完全自我的感覺(jué)而已。記得當(dāng)時(shí)我是這么說(shuō)的:“你認(rèn)為有,那肯定是有;你認(rèn)為沒(méi)有,即使真有,對(duì)你又有什么用?”
方悅瞇著眼睛,出神地想了一會(huì)兒我的話,然后,她隔著桌子把胳膊伸過(guò)來(lái),神經(jīng)質(zhì)似的和我握了握手,半天才松開(kāi)。
我們又繼續(xù)喝酒。
開(kāi)始,我感覺(jué)那瓶洋酒沒(méi)什么勁兒,當(dāng)我們把那瓶酒差不多要喝完的時(shí)候,才覺(jué)得這酒后勁挺大,有點(diǎn)上頭。看方悅的眼神兒發(fā)飄,有些神思恍惚(以前我從沒(méi)見(jiàn)她喝到這樣),我建議不要再喝了。方悅不肯,非要把瓶里的酒喝完。結(jié)果我們又喝了一小杯,她便捂著嘴,搖搖晃晃地去了洗手間。我趕緊跟過(guò)去,卻無(wú)奈被一個(gè)“女”字的標(biāo)志擋在了門(mén)外。我愛(ài)莫能助地站在那里,聽(tīng)見(jiàn)她在里邊不停地嘔起來(lái),好像吐得搜腸刮肚……我暗想,吐吧,再吐一次,吐出來(lái)就好了。
可是沒(méi)好。回到座位上,方悅用雙手撐著額頭,長(zhǎng)時(shí)間一動(dòng)不動(dòng)。過(guò)了一會(huì)兒,我問(wèn)她能不能走。她話都軟了,“哥啊,不行,我頭暈,你先走吧,我得呆一會(huì)兒……”
我能先走嗎?又坐了一會(huì)兒,我問(wèn)她怎么樣,要不要我送她回家。她搖了搖頭,說(shuō)著“不好意思”,卻軟綿無(wú)力地站起來(lái),同時(shí)把一只手遞給了我。
8
時(shí)值秋末,天上竟然落著零星的雨點(diǎn),稀疏的雨絲在路燈下閃閃發(fā)光。此時(shí)晚高峰早已經(jīng)過(guò)去了,但路上的車(chē)流卻仍然很大,流速也快,紅黃兩色的車(chē)燈如同兩條交錯(cuò)而過(guò)的河流,發(fā)出潮水般嗚嗚的響聲。
方悅的家距離餐館很近,過(guò)了馬路天橋,走進(jìn)一條小街,不到200米就是她居住的小區(qū)。方悅走得綿軟無(wú)力,我攙著她的胳膊,和她并肩而行,我能夠隱隱約約地嗅到她頭發(fā)上洗發(fā)香波的味道。一路上,我們誰(shuí)也沒(méi)有說(shuō)話。在進(jìn)入電梯的一剎那,方悅無(wú)力地向后一靠,我右臂本能地一攬,我的手碰到了她的乳房。也許是因?yàn)榫凭淖饔茫彝蝗蛔隽艘患屛易约憾几械襟@詫的事,竟在那高聳柔軟的部位上輕輕地捏了一下,一種血流加快的感覺(jué)立刻涌遍全身。與此同時(shí),方悅低下頭,一把抓住我的手……但她并沒(méi)有把我的手立刻掄開(kāi),而是死死按住我的手背,令我的手一動(dòng)不動(dòng)。
電梯準(zhǔn)確地停在了十層。
進(jìn)家后,我把方悅扶到沙發(fā)上。而我卻突然有一種想去衛(wèi)生間的欲望……
這是一個(gè)獨(dú)身女人的衛(wèi)生間。透明的玻璃淋浴房,零零碎碎的各種化妝品。黑乳罩,小小的紅色三角褲,高筒襪子……女人全部隱私用品差不多都陳列在這里。我的目光在每件物品上停留了5秒鐘……
回到客廳時(shí),我看見(jiàn)方悅在沙發(fā)上換了個(gè)姿勢(shì),她苦笑一下,“今天出丑了。”我說(shuō),“這算啥呀,很正常。”此后我們誰(shuí)也不說(shuō)話。方悅疲憊地閉著眼睛,那神態(tài)就像坐在候車(chē)室里無(wú)奈地等待一列晚點(diǎn)的火車(chē)。
過(guò)了一會(huì)兒,我問(wèn)她要不要喝水。
“不喝,你喝就自己倒吧。”
“我也不喝。”
更深的沉默籠罩了房間。我們誰(shuí)也不說(shuō)話,似乎在傾聽(tīng)自己心律的跳動(dòng)。我擔(dān)心這么坐下去她可能會(huì)睡著,便試探著說(shuō),“看你挺難受的,要不到床上去休息吧。”方悅猶豫了一下,又點(diǎn)了點(diǎn)頭,卻沒(méi)有行動(dòng)的意思。我只好走過(guò)去,攙起她一直送到臥室,方悅?cè)彳浿眢w一連說(shuō)了好幾句“不好意思”,剛挨到床邊便斜著身體躺了下去。我站在地上,正不知道該怎么安排自己,就在這時(shí),我的手機(jī)令人詛咒地響了起來(lái)。
我來(lái)到客廳,在沙發(fā)上的外衣口袋里找出手機(jī)。是我妻子打來(lái)的,她問(wèn)我怎么沒(méi)在餐館。我撒謊說(shuō),我正在去餐館的路上。話一出口,我就懊悔得想給自己一個(gè)耳光。她說(shuō),“行了,一會(huì)兒我往餐館里打吧。”還沒(méi)等我說(shuō)啥,她就把電話掛了。
我一下子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這就是撒謊的代價(jià)——你說(shuō)了一句謊言,就必須得再用十句謊言去掩蓋它……總之,就是這么一個(gè)電話,把我當(dāng)時(shí)的情緒一下子搞得面目全非。
我回到臥室的時(shí)候,方悅微笑地看著我。
“大姐在查你的崗。”
“不是……你感覺(jué)好點(diǎn)了嗎?”
方悅點(diǎn)點(diǎn)頭,含意不明地笑了笑。
我說(shuō),“……那你休息吧。”
說(shuō)完,為了有一個(gè)體貼性的過(guò)渡,我還像個(gè)紳士似的,主動(dòng)去給她拉上窗簾,又去客廳倒了一杯水,放在方悅旁邊的床頭柜上(事后,每當(dāng)想起這事兒的時(shí)候,我覺(jué)得我特猥瑣,特像個(gè)小丑)。然后,我又關(guān)切地問(wèn)了一句,“沒(méi)事吧?”
方悅側(cè)臥在床上,輕輕地?fù)u搖頭,一聲不響地看著我。
這時(shí)候,我又聽(tīng)見(jiàn)自己在說(shuō),“那……你休息吧,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出來(lái)的時(shí)候,我還用我的那把鑰匙,給方悅鎖上了門(mén)。我知道這種門(mén)鎖的屬性,明天早晨,方悅會(huì)在里邊用她的鑰匙把門(mén)打開(kāi)。
回來(lái)的路上,我一直想著應(yīng)該編織什么理由進(jìn)行自救。可是回到餐館,我問(wèn)了一下伙計(jì),奇怪的是,我妻子并沒(méi)有把電話打到餐館。我禁不住自嘲地想,無(wú)需自救了,妻子已經(jīng)救了我。
那天晚上,我很久都睡不著覺(jué)。
躺在床上,回憶著整個(gè)晚上我和方悅獨(dú)處時(shí)的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有一會(huì)兒,我還是抑制不住地想給方悅打個(gè)電話,看她是不是醒酒了。拿起手機(jī),我發(fā)現(xiàn)上面有方悅發(fā)來(lái)的短信,打開(kāi)一看:
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種男人,一種是好色的,一種是非常好色的。現(xiàn)在我才發(fā)現(xiàn)還有另外一種男人……
我體味良久。明知道我自己就是謎底,但還是給方悅回了一條短信:
愿聞其詳。
方悅沒(méi)有回復(fù)。
9
此后我就再?zèng)]見(jiàn)過(guò)方悅。北京很大,主要是各自都活得很忙。應(yīng)該說(shuō),在每個(gè)人的交際圈子里,一年、兩年不見(jiàn)面、不通話的朋友多的是,很正常。更主要的是,那天喝酒的事兒我一直記著,我擔(dān)心見(jiàn)了面,被方悅直接捅出來(lái),或者一不小心說(shuō)漏了嘴,讓我妻子知道我曾單獨(dú)把方悅送回過(guò)她的家里,事情就復(fù)雜了。因此,有好幾次我妻子念叨起方悅的時(shí)候,我都沒(méi)怎么打攏。
大約幾個(gè)月之后,我妻子突然告訴我說(shuō),她夢(mèng)見(jiàn)方悅到我們餐館來(lái)了,剛一坐下,便要了一份小炒牛蛙……我妻子用一種非常懷舊的口氣說(shuō),“你打個(gè)電話問(wèn)問(wèn),她現(xiàn)在怎么不來(lái)了?是不是咱們哪地方做得不對(duì),她生氣啦?”
沒(méi)想到,一打電話才知道,方悅的手機(jī)和家里的電話全都停機(jī)。我說(shuō),“這是怎么回事呢?”
這時(shí)候,我妻子想起了方悅的哥哥,她說(shuō),“你給方長(zhǎng)貴打電話,問(wèn)問(wèn)他不就知道了。”
我一連打了幾個(gè)電話,終于找到了方長(zhǎng)貴。還是那種喉嚨很粗的京腔京韻,他說(shuō),“怎么啦,您說(shuō)。”
一問(wèn),才知道方悅結(jié)婚了,而且已經(jīng)移居日本。
“怎么著,您找她什么事兒?”
我說(shuō),“沒(méi)事兒,很長(zhǎng)時(shí)間沒(méi)聯(lián)系了,問(wèn)問(wèn)。”
放下電話,我在想,人們無(wú)論是在生活里忙忙碌碌,還是在大地上行色匆匆,其實(shí)都是在不斷地尋找歸宿。當(dāng)鄉(xiāng)下人不斷地涌入城市的時(shí)候,許多城里人已經(jīng)開(kāi)始把國(guó)外當(dāng)作他們生活的大舞臺(tái)了。
方悅杳然一去,再無(wú)消息。
時(shí)間大約過(guò)了一年,就在我差不多已經(jīng)把她忘了的時(shí)候,方悅卻突然在日本給我打來(lái)了電話。
當(dāng)時(shí)我非常驚訝。
方悅也是。
她說(shuō),“嘿,大作家,你真的不換號(hào)碼呀?”
記得我跟方悅說(shuō)過(guò)“一生兩不換”,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手機(jī)號(hào)碼。當(dāng)我把這句話重復(fù)給她的時(shí)候,電話里傳來(lái)一種久違的、銀鈴似的笑聲,她說(shuō),“什么人這是。”
她收住笑聲,告訴我說(shuō)她在一家中文書(shū)店里買(mǎi)了我一本小說(shuō),現(xiàn)在就拿在她手上,她說(shuō),“真棒!哎,你知道嗎?我特激動(dòng)!”
我說(shuō),“寫(xiě)得不好。”
對(duì)方“嘁”了一聲,說(shuō),“別謙虛了,不好能出書(shū)嗎?還賣(mài)到了日本!”
像很久沒(méi)有聯(lián)系的朋友一樣,我們聊了半天家常。方悅告訴我,她的老公是華裔日本人,也是二婚。他們同在一個(gè)旅行社做事兒。他老公帶團(tuán),她不帶,她做的是文案。老公出國(guó)后,她一個(gè)人在家沒(méi)事兒就亂看書(shū),還老是想寫(xiě)點(diǎn)東西,又怕自己不是那塊料,愣是不敢寫(xiě)。
“哎,我問(wèn)你,你們作家是不是對(duì)人和人的一些事兒特有感覺(jué)呀?”
我想了想說(shuō),“是啊,你說(shuō)得特別對(duì)!”
“真的啊!”方悅的聲音亮麗起來(lái),“我跟你說(shuō),在國(guó)內(nèi)的時(shí)候,我對(duì)什么都稀里糊涂;到了日本,我怎么對(duì)啥都特有感覺(jué)呢?最奇怪的是,有時(shí)候呆著呆著就想哭,那叫一個(gè)脆弱!”
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方悅的話還不是很理解。這幾年,沾了“作家”這一身份的光,我曾先后去過(guò)幾個(gè)國(guó)家,通過(guò)和當(dāng)?shù)匾恍┤A人的接觸與交流,才知道他們?cè)S多人想重新回到國(guó)內(nèi)生活,卻由于各種原因不能如愿。有一次去土耳其(那是個(gè)美麗的國(guó)家,那里有藍(lán)色清真寺,有藍(lán)色的地中海和愛(ài)琴海,有藍(lán)色的瓷磚拼成的古老建筑),在美麗的伊斯坦布爾,我們遇上過(guò)一位北京姑娘——準(zhǔn)確地說(shuō),她已經(jīng)不是姑娘了——兩年前,她與一個(gè)在北京語(yǔ)言大學(xué)留學(xué)的土耳其小伙子一見(jiàn)鐘情,不顧家人反對(duì),毅然與小伙子結(jié)婚并加入了土耳其國(guó)籍。僅僅過(guò)了一年,由于文化上的差異,互不適應(yīng),只好離婚。她本想回國(guó),又覺(jué)得面子上過(guò)不去,便留在那里給國(guó)內(nèi)的一家公司代理銷(xiāo)售中國(guó)大理石。那天晚上,在伊斯坦布爾的一家酒吧里,她用略帶沙啞的嗓音唱的那首憂傷的歌曲,感人至深,至今我還能記得住幾句歌詞:
還貪戀著你的風(fēng)情
誘惑著你的神秘
埋葬我的愛(ài)情
憂郁藍(lán)色的土耳其
緊跟隨著我的稚氣
逃避著我的宿命
徘徊在
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
……
我不知道方悅在日本的生活究竟怎樣。她只是在電話里告訴我,她天天寫(xiě)日記。我在想,一個(gè)對(duì)生活沒(méi)有感覺(jué)的人,肯定不會(huì)天天寫(xiě)日記的吧。
那次,方悅還要去了我的電子信箱,她說(shuō)她不會(huì)把她的日記發(fā)給我看,那都是流水賬和個(gè)人隱私。如果能寫(xiě)出點(diǎn)別的什么,她會(huì)發(fā)給我,讓我指導(dǎo)指導(dǎo)。
但三年過(guò)去了,我沒(méi)收到方悅一個(gè)字。
10
三年不是個(gè)短時(shí)間。不知不覺(jué)中,世事發(fā)生了多少變化啊。這期間,我開(kāi)的餐館早已拆遷,又開(kāi)了一家,沒(méi)多久,也拆了。我們居住的地方,也是被開(kāi)發(fā)商攆來(lái)攆去。感覺(jué)上總是在不斷地搬家。俗話說(shuō)“一搬三窮”,重要的是這種居無(wú)定所的生活,總讓我們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顛沛流離之感。那年秋天,我和妻子一咬牙,用按揭的方式買(mǎi)了一套商品房,從而把自己的身份由房客變成了城里人所說(shuō)的“業(yè)主”,終于有了一個(gè)比較穩(wěn)定的歸宿。
此后四季輪回,又是春天。
北京的春天,向來(lái)是個(gè)很好的季節(jié),溫風(fēng)和煦,柳綠桃紅。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我們居住的小區(qū)公園里散步,突然接到了一條短信:
我已回到北京。今晚如有時(shí)間,能否一塊兒吃個(gè)飯?方悅。
我立在那里長(zhǎng)時(shí)間不動(dòng),盯著手機(jī)屏上的這行小字反復(fù)看了三遍。我注意到方悅是用北京的手機(jī)號(hào)碼發(fā)的短信,她是什么時(shí)候回來(lái)的?是探親還是工作?是獨(dú)自回國(guó)還是兩個(gè)人同行?是暫時(shí)停留還是不再離開(kāi)?這些問(wèn)題在我腦子里一一滑過(guò),往壞處想,我甚至想到了方悅在國(guó)外是不是發(fā)生了婚變……但是,為了讓我們的見(jiàn)面有點(diǎn)神秘的期待,我把一切都作為暫時(shí)的懸念,不去碰它。
我只問(wèn)了她見(jiàn)面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方悅很快回復(fù):
六點(diǎn),地壇西門(mén),老地方。
我記得方悅那次在日本給我打電話時(shí)說(shuō)過(guò),出國(guó)前她就把安定門(mén)的房子賣(mài)了。不知道她為啥要把這次見(jiàn)面的地點(diǎn)定在“老地方”。是她住在了附近?還是特意去懷舊?當(dāng)然,懷舊也是一種人之常情吧。幾年前,就因?yàn)槲液头綈傇谀抢镉羞^(guò)一餐之緣,有一次路過(guò)那家餐館的時(shí)候,我曾特意進(jìn)去吃過(guò)一次飯。只是物是人非,老板、服務(wù)員,甚至店名、門(mén)臉、餐桌、菜品,全都變了。是的,在這個(gè)不斷重新組合的世界上,除了時(shí)間是永恒的,還有什么是不變的呢?從這種意義上說(shuō),方悅所說(shuō)的“老地方”,其實(shí)已經(jīng)不存在了。
從家里出發(fā)的時(shí)候,我已經(jīng)想好,這次一定由我做東。同時(shí),有一樣?xùn)|西我要還給方悅——我早知道它已經(jīng)沒(méi)用了,但在一種有意與無(wú)意的情形之下,這么多年它卻一直在我的腰上掛著——那是方悅家的鑰匙。
作者簡(jiǎn)介:
荊永鳴:男,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著有短篇小說(shuō)集《外地人》、中短篇小說(shuō)集《創(chuàng)可貼》、長(zhǎng)篇小說(shuō)《陡峭的草帽》《我們的老家》等。作品曾多次被《新華文摘》《小說(shuō)選刊》《小說(shuō)月報(bào)》《作品與爭(zhēng)鳴》《中華文學(xué)選刊》《中篇小說(shuō)選刊》等期刊轉(zhuǎn)載,同時(shí)被收入50余種作品集。曾先后榮獲《人民文學(xué)》獎(jiǎng)、《小說(shuō)選刊》獎(jiǎng)、《十月》獎(jiǎng)、《北京文學(xué)》獎(jiǎng)、《中篇小說(shuō)選刊》獎(jiǎng)、全國(guó)煤礦文學(xué)“烏金獎(jiǎng)”、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索龍嘎獎(jiǎng)”,中篇小說(shuō)《大聲呼吸》獲第四屆老舍文學(xué)獎(jiǎng)。現(xiàn)為北京市作家協(xié)會(huì)合同制作家。
責(zé)任編輯 白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