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史詩——楊佴 新水墨畫中國巡回展”作品研討會
“他的史詩
——楊佴 新水墨畫中國巡回展”作品研討會
SEMINAR ON “HIS EPIC—NATION-WIDE TOURING EXHIBITION OF YANG ERMIN’S INNOVATIVE INK WASH PAINT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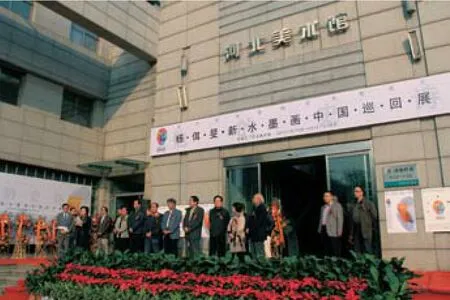
上 開幕式現場

下 河北站作品研討會
時間:2012年10月19日
16:00—19:00
地點:河北美術館學術報告廳
議題:1.當代中國水墨畫的創作困 境與觀念突破
2.色彩的運用與水墨畫的當 代性
3.中國水墨畫未來發展的可能 性與前景展望
主持:張國君 河北美術館館長
嘉賓:陶詠白、李小山、西川、鄧平 祥、馬欽忠、江黎、漢風
陶詠白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名美術評論家
我對水墨畫的關心是從近90年代開始的,以前主要關注油畫。似乎是從認識了楊佴
之后,我才開始對水墨畫產生了興趣。小山曾提出的令人振聾發聵的“中國畫窮途末路”之論,極大地刺激了我們的神經,而看到了楊佴 的作品,我就覺得水墨畫還是有前途的,中國畫還是很有發展空間的,讓我們在陰影里看到了希望。那么,針對這個議題,我先談談自己的看法。
針對水墨畫的困境,人們已然不像過去那樣焦慮了,也就是說現在對于水墨畫的研究和突破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探索成果,當然傳統的水墨畫還是占主導地位的,尤其體現在學院方面,其教學方式或許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前不久,我參加了國家畫院組織的“南北對話”畫展,整體而言,仍是老套路,基本是有名的畫家拿出以前的作品參展,并沒有看到他們畫面中多少分現代的感覺,還是徐悲鴻那一套路的人物造型。這一代人,現在大約是六七十歲左右的年紀,他們對于水墨畫的突破很困難,他們基本還是以水墨為主,色彩很少。所以我在會上向主辦方提出了一個問題——色彩哪里去了?難道就是單純的水墨嗎?色彩與水墨到底該如何認識?現在人們在水墨畫的探索中,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色彩對于水墨畫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思路沒有打開,仍然在“水墨為上”的定式思維之中,甚至中國油畫的發展也沒有色彩了,演變成了水墨的油畫。前幾年很多展覽,就是這樣。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中國本土化嗎?對此我感到困惑、憂慮。所以楊佴提出來,在當下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中,我們需要色彩,需要用色彩來表達生活,來反映時代,我特別同意他說的“我們不能把陳舊當獨特,不能把不思進取當成中國畫的常態”。如何讓中國水墨畫與世界藝術在共時性的平可上對話,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水墨畫創作的觀念的突破或者說圖式上的變化可以歸納為新寫實、新寫意、新水墨這三種類型。新寫實自然與真正的寫實有許多變化,可能是加入了一定程度的寫意;新寫意可以理解為過去的新文人畫的延伸;新水墨里面的情況就比較復雜,有很多分支,有的保持了水墨畫的材料,有的保持了水墨畫的用筆(其中書法用筆應該歸到新文人畫的范疇),有的是對現代表達形式的挪用與闡釋,楊佴 就歸于這一類,借用西方的形式,利用傳統筆法闡釋水墨畫,當然還有人完全拋開筆墨,進行觀念性的、裝置與行動類的探索。所以,我覺得楊佴 屬于林風眠系統的延續。林風眠基本上仍是用筆,但用的不是老祖宗的筆,筆筆皆變,他的線條與過去也不是一樣的,而主要是色彩的突破,林風眠是重彩、重筆、重墨,而楊佴 是半彩、半筆、半墨,中西融合得比較自然,沒有給人輕飄的感覺,而是很結實,有分量,從這一點來看,楊佴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中國水墨畫發展到現在出現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畫家,比如田黎明講究用西方的光線來進行水墨畫當代性的應用,劉慶和則是注重筆墨運用的技巧等等。從這些方面看,我個人倒是很有興趣,也抱有很大的希望,中國水墨畫有很廣闊的天空留給當代藝術家們去闡釋。由于我關注和介入楊佴 近二十年的新水墨創作過程,從他個體的發展來看,中國水墨畫仍有無限的發展空間。
李小山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館長著名藝術批評家
我現在很少參加會議,每次參加都會有種異樣的感覺,因為這類角色的扮演已經讓我厭煩了,我的聲音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接下來,我將近期在幾個會議上發表的觀點再做一次系統性的闡述。
第一,關于文化生態,這是每一個藝術家、作家所離不開的大環境,當下我們的文化生態是什么呢?表面上轟轟烈烈的熱鬧,全是過眼煙云,不要拿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說事,文化不是這樣一磚一瓦建筑起來的,它是一個自然過程。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每個畫展、每場活動,比的是什么——到場首長的級別和作品的銷售成果就是活動成功與否的指標。這嚴重扭曲了藝術的標準,學術標準可有可無,學術評價幾同于零。在這樣的生態下,藝術,真正的藝術何以立足?何以存在?
第二點,在我們的藝術領域,藝術生態對于每一個藝術家來說就是一個最大的參照系統。當下的藝術不是中國的藝術,不是北京的藝術,河北的藝術,或者保定的藝術,同樣也不是上海的藝術,南京的藝術,當下的藝術不是某一個區域的藝術,而是全球的藝術。如今,訊高度發達,信息極為通暢。我們曾經看過9·11事件的直播、伊拉克戰爭的直播,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從來沒有一場戰爭可以直播。這說明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個情態是全球化的時代,也就是說全世界變成了一個村莊,中國是村民。在談到西方為中心的時候,懷有強烈民族情緒的人會提出許多反駁,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是處于主導地位的。藝術和繪畫同樣,我們今天的藝術面臨的是西方的挑戰。
當年,我在讀研究生時提出“中國畫走到窮途末路”的觀點,憑借的只是當時能得到的少得可憐的資訊,從而發覺中國的傳統藝術、本土藝術幾百年來原地踏步、固步自封,毫無生命力可言。自80年代以來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造就了整個中國當下文化藝術的一種叫做刺激反應模式——這不只是中國的情況,倘若各位愿意,可以查閱所有非西方系統的情況,南美洲、非洲、東亞,甚至俄羅斯,都是在西方的作用下進行某種抵抗、覺醒、反思、改革等行動,中國的行為所占據的不過只是其中一個領域。

周末 紙本設色 32.2cmx56.4cm 2002年 楊佴

左 花與果 紙本設色 69cmx67cm 2010年 楊佴
我們平日經常會探討,繪畫這一類型在整個藝術系統里面已經被邊緣化了,在當下的國際大展中,在最炙手可熱的藝術家里面,純粹的畫家是很少的,這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的水墨,作為傳統藝術、本土藝術,它面臨的尷尬正在于此。我們剛剛提及林風眠、吳冠中,我特別喜歡劉驍純以前提出的一個觀點——林、吳系統,這個系統開啟了一點可能,為我們死水一潭的水墨畫創作帶來了些許光亮,這個可能就是——如果水墨畫能夠以這種類型探索下去,能否使它保持一點活力,能否使它繼續以一種藝術形態生存下去——在這一點上,楊佴 作為這一支創新隊伍里面的代表人物,他所承接的正是這一系統,或者說這個接力棒已經交到他的手里,而楊佴 帶著它可以走出多遠,以他現在的年齡,還不能斷下結論,我們要拭目以待,這是目前楊佴 等藝術家所背負的責任。
在最近階段,我和楊佴 經常探討,涉及繪畫的觀念、技法等問題。我覺得楊佴 在他的藝術實踐中已經相對成熟了,這是他為未來攀登高峰,繼續前行奠下的基礎。我想,這也是他帶給我們的信心。謝謝大家!
馬欽忠 中國美術學院公共藝術學院教授
我看當年由陶老師策劃組織的楊佴 的展覽,不論是從宏觀角度,還是具體的創作過程,那時已經說得很充分,很到位了,所以下面我想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闡述。
第一,我們經常在探討,如小山二十年前就提出中國畫走到了窮途末路等觀點,我都非常贊同,假設我們還是用原來的宣紙筆墨記錄當下的景觀,那么它在創作文化的高度和深度上,目前的時代是否還具備這種可能性?反之,是不是還有更多的空間值得我們去發揮、發展,是不是還會延續我們過去的道路去走,能走多遠?我覺得這其中有很多值得討論的點。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傳統,尤其是水墨,幾乎類似于某種宗教。評價一幅畫好與不好,是否是中國畫,將傳統的元素看得非常之重,但是如果我們把今天創造的傳統與過去的歷史相比較,又會顯得非常淺薄。所以說,抵達傳統是非常難、極為奢侈的事情。
剛剛小山提的幾點我也感觸深刻。前兩天,我在上海看到一位著名畫家去租場舉行他的專場拍賣會,目的就是告知外界這些作品都是真跡,拍的結果很好。后來,我觀察到一個現象,這位畫家一離開會場,為他作品舉牌的人也都散了。大家都明白這是行業里所說的托兒。我想這應該不是個例,反而是極為平常的,這就是當下我們藝術生態的一個縮影。
第二,從整個國際藝術來看,其實無所謂傳統,無所謂水墨,無所謂油畫,或者國畫,最傳統的技法也可以創作出非常現代的作品,最現代的媒材也可以做非常保守的事情。從這個角度,用什么媒材,用什么方式,無所謂傳統還是不傳統,關鍵是,我們對這種媒材的使用,和使用這種媒材表達的觀念、它的適當與否、以及它對這個時代精神的表達,它對人文精神的挖掘抵達了怎樣的高度,我覺得這些才應該是衡量作品的標準。
當然,傳統還是需要有人去接手的,就像中西方藝術的修復類工作,但是這些已經與主流的當代的繪畫沒有關系了,它是一種文化傳承的手段。但我們經常會把保留和創新相混淆,一方面,從媒材方面考慮,無所謂新舊;第二個方面,由于中國畫本身的復雜性,比如如何用筆,用墨,它背負太多歷史的包袱,假如說,我們將它們丟掉,換一種全新的方式,那么這一筆文化財富如何在當下體現,并產生作用?由此就帶來了第一個問題,有筆還是無筆,有墨還是無墨,現在我們仍舊在討論這些問題,當然,在這個道路上也有很多人在做,那么做的如何呢?正如之前小山所說的,如果與二十年前相比,確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是在前進還是退步,這一點是很復雜的,也很難說清。正像上個世紀初,推廣白話文的時候,許多文人志士痛心疾首,因為他們擔憂一旦啟用白話文,幾千年積淀的文言文傳統會不會就此中斷,這些文化的寶藏,我們能否繼續享用它們?現在看來漢字簡化帶來的遺留問題正在逐漸顯示出來,我想現在年輕一代不論是對繁體字還是文言文都是相當陌生的。
第三點,現在很多人探討在觀念上運用水墨,也包括外國人,水墨作為一種文化精神,水墨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閱讀方式,會給當下的視覺文化帶來怎樣的精神?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專利,我想隨著國際交流的逐漸增多,外界對于中國文化認知的加深,運用水墨這種形式探討的人會越來越多,當然不是說關注的多了就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但是這起碼會成為水墨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
我想,首先是從概念上理出了以上對于水墨的三個方面的問題,它們不是今天才做的,而是一直在反復討論的。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想到,這也是楊佴 在做他的藝術選擇的時候必須面對的背景。如何在紙上做文章,楊佴 提供了一個目前來看成績比較突出的實踐的個案,他今天仍很年輕,所以我跟小山的觀點一樣,現在不能輕易地為他下結論,我們期望楊佴 的這條色彩的探索道路,在當代環境中繼續走下去,將中國傳統的審美精神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好,謝謝大家!
鄧平祥 著名美術理論家 藝術家
我想談楊佴 畫的問題之前,針對他的畫的兩個特點先做闡述,然后再談本體問題。
一是他作為畫家是非常具有個人風格的,又是一位非常有成果的現當代意義的畫家,我為什么將個人風格與現當代意義一起談呢,我認為中國的藝術,當代和現代是不可分割的,一些西方的理論家,也有這樣的說法,現代與當代很難真正劃清界限,在中國更是這樣。因為我在做理論的同時也畫畫,很多朋友、老師經常會疑惑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有現當代的區分,為什么要強調個人性?如果與現當代藝術個性對應的話,傳統藝術就是一種比較共性化的藝術形態。如果我們就藝術談藝術,這個問題將非常難解讀。西方對于這一塊的研究要比我們透徹、深入。因此,首先你要具備個人性,然后才會有現當代性,如果撇開個人性去談現當代性,那么這個現當代性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比如說,我們要回答一個這樣的問題,20世紀人類的文明發展到如此高的程度,為什么同時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戰爭殺戮最殘酷的一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奧斯維辛……這都是駭人聽聞的,這是我們必須去追問的,只有追問才會在根本意義上理解藝術為什么要提出現代、當代以及個人性等等。為什么我們在用共產主義理論去批判所有西方理論家時,唯獨對黑格爾手下留情了,并且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黑格爾的歷史決定論,因為黑格爾在理論和思想上設計了一個模式,歷史一定是這樣發展的,現在如何決定將來如何。
正是因為20世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有如此的災難發生,在西方的思想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即任何人不能強迫別人,尤其是用公共權利強迫人接受沒有經過驗證的事物。這個時候回到藝術,我們看到藝術的力量。有些西方現當代大哲學家提出在藝術中尋找精神救贖的道路,因為藝術是最為個性和最有可能個性的東西,藝術是感性中間表現真理的東西,那么這個時候西方的藝術就一反其取得輝煌成就的古典藝術,走向了擁有極大豐富性,甚至到了令人匪夷所思這樣一種程度的現當代藝術,這就是基于前面所提的深刻的歷史決定論的背景。
藝術是最應該強調個性、自由性、感性和可能性的一種意識形態,如果藝術不強調這些,作為一個人類認知與感覺方式的最前衛的東西,那么藝術的實踐就有可能帶來某種誤區。所以我覺得在考察現當代藝術家時,強調他的個人獨特的貢獻以及個人風格學的意義,這一點是尤為重要的。那么,從這個角度看,楊佴 的藝術首先是有個性的、具備風格學意義的現當代藝術家,在此,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他的現當代性是建立在個人性基礎上的。其次,我還想談一點,從他的藝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與林風眠、吳冠中等前輩們一脈相承的藝術實踐關系,但是楊佴 區別于這兩位大師的地方在于,從心理學上看,他的內心表達走得更遠,這一點也是楊佴 藝術很重要的特質。心理學是一門具有無限可能性、豐富性,以及不可解讀性的學科。為什么要從心理學層面考察藝術家內心的自由度、存在意義呢?當下如果問年輕人對一些重大的、敏感的歷史事件的評價,很少人會有獨立完整的認識,也沒有興趣去研讀歷史材料,這說明這一代人被取消了一個指向神圣事物、指向深度價值、指向歷史價值的維度。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同小山先生剛才的發言,當下我們的精神層次、時代的脈象可以說是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了。面對這種脈象,我想有一種非常苦澀的解決方式,第一點,回到我們的起點,對事物的真實的信仰;第二點,回歸良知。為什么我會一再強調人的個性以及心理學層面的重要性,就是珍視自己的內心感覺,不要屈從于外界的壓力、誤導,而應該勇敢提出質疑。其實藝術家在社會與文化方面的作用,就是這么一點。我認為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最應該具備的品質就是真實,離開真實再談其他的事物就沒有意義了。

右 太行的早晨 紙本設色 140cmx310cm 2012年 楊佴
接下來我想談一點就是楊佴 的色彩問題,中國文人畫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壓縮、弱化色彩,難道是我們中國人的眼睛與西方不同時期大師的眼睛對外界事物的感覺不一樣嗎?自然不是的!而是我們的文化觀念使我們對色彩遲鈍了,對色彩的感覺壓抑了,所以我們的水墨發展到最后全是用墨和線來表現。20世紀的國畫大師們很多的精力是投入到色彩表達方面,將色彩與水墨結合起來,走出一條現代繪畫的新路。我覺得楊佴 雖然是林風眠、吳冠中等大師的后學,但由于其所處的時代優勢,他在某些方面,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他的色彩的表現,心理學方面的自我建構,已經超越了前者,當然,這也離不開他個人的才華。
另外,我想談一點,關于楊佴 的藝術境界,國學大家王國維說境界為上。我覺得他境界方面最大的一個特點是寧靜、靜穆,楊佴 的這種追求有某種對喧囂社會亂象的反駁。我們這個時代太躁動了,躁動在許多沒有意義的負面的事務上,缺少一種寧靜的氛圍,尤其是個人。其實,不管外界怎么喧囂,個人的寧靜還是可以找到的。這種特質在楊佴 的作品中體現的非常明顯,這是獨屬于他自己的精神法則,是由墨、線、顏色等各種元素支持的一種結構性的處理,體現的非常突出。我尤其注意到他的畫面中一些女性的表達,都是安靜的,并且這種安靜是含有某種有教養的女性的嫻靜與美麗。歷史上有個成語叫做“靜女其姝”,所謂靜女是一類有文化教養和精神品位的女性,這在這個時代是久違的。雖然描繪的是女性之美,實際上,我覺得是楊佴 對人性、對整體中國人的狀態的表達。我們真的應該安靜下來,修煉這種有尊嚴感的靜穆的品質。
最后我想再談一點,楊佴 的“拙”,畫面里完全沒有一點巧勁,而是類似于兒童的原始的藝術的無意、生澀與純然,不經意中間的經意,表面上無法中的有法,這一點給我的印象也很深。我先談到這里,謝謝大家!
江黎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教授
我與楊佴 先生相識已經十多年了,參加過他以前的展覽。今天的這場展覽讓我感覺他的作品更偏重水墨色彩,同時在他的繪畫中我看到了幾個影子:一是在中國傳統藝術系統里面的中國水墨畫和民間藝術,如年畫;同時還有西畫系統里面色彩、光影、體積等的表現語言。
在此我想說一下關于新水墨畫研究的這個點,這恐怕要從畫種的體系上追溯其源頭、傳統和發展過程。像林風眠和吳冠中兩位前輩都是結合了西方的色彩和中國畫的水墨、文人畫的意境,我認為楊佴 先生的畫也是在這個鏈條上的。從研究和發展的角度上,我希望研究單位可以將這個體系的發展整理出來,這樣,對于年輕人,對于可以被納入這個體系的藝術家,會有一個可供參考的理論依據。西方的現當代藝術基本都是追尋一些哲學依據、藝術理論,它有一套清晰的脈絡,從而有完整的藝術面貌。中國當代藝術需要尋根,不管是中國的傳統藝術還是西方藝術思潮,我想只有回歸,中國的當代藝術才有可能尋求到某種突破點,以及文化上的延續性。作為央美的教師,我很了解學生們會追求一些挑戰和革新,但是僅僅考慮如何顛覆還是淺層次的個體藝術行為,真正做學問還是要從其源頭一步一步地學習、歸納,從自身建立相應的體系。
另外一點,看楊佴 的畫讓我突然想到了塞尚,我們看他前期的畫,特別是人物比例按照當時的標準是不準確的,甚至被認為是很幼稚的,受到當時主流藝術界排斥。但塞尚就是一輩子在那里兢兢業業地研究他畫面的構圖、色彩等,成為上個世紀初西方現代藝術的鼻祖。所以正如剛才說的,楊佴 在水墨畫上的探索很有價值,他有那種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探索者也好、研究者也好、先行者也好的可貴的素質。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謝謝!
西川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著名詩人
我從另外的角度來談談我的看法。剛才看佴 的畫臨時有了一些非常明確的想法,而且這些想法彼此之間并沒有太大的關系,但這些都是他的畫帶給我的思考。
首先一個問題,如李小山先生已經提出的,文化生態問題。我自己不是研究美術的,所以我預備從外圍來談談美術的情況。美術這一事物必然與接受者發生關系,在中國當下現實中,從比如說剛才開幕式的架勢我們就可以有所體會。開幕式播放什么樣的音樂,哪些人站在前排等等,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生態。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遠一點,我想當下人們對于美術的接受是有許多層面的,比如地方上有一套官場模式的接受,它支持著一種當地的美術風氣,代表著一種對于美術的評價。——古代也有官場,古代官場支持的美術與當代官場支持的美術是不是同一種美術,是可以研究和討論的。過去中國文人舉辦“雅集”,現在可能叫做“筆會”,“雅集”和“筆會”應該有些不同吧。還有,現在畫是要被展出的,在哪里展出,被什么人贊揚或者批評,這些因素恐怕都會對美術作品的品質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還有,誰是買畫的人,買畫人的趣味是怎樣的等等。古人不會碰到美術館與出版物的問題。古代畫家是被記錄在畫論里的。所以現在的畫家與古代的畫家,他們被呈現的狀態是不一樣的。從接受者的角度入手來思考,我們既可以看到這個時代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也能看到這個時代的一個共通的審美場域,那么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下社會發達的資訊,不僅僅體現在某某事件被快速傳播上。在美術領域,以往畫家對繪畫風格的選擇,實際上機會有限,而現在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只要你留意美術,你可以看到的繪畫和古代皇帝看到的東西是沒什么區別的。在古代,皇家的收藏是地方畫家見不到的,所以那時一個地方畫家他能夠選擇的風格是很有限的,現在的畫家即使足不出戶基本上也可以通過圖片瀏覽到古今中西的藝術作品——除非作品已經丟失了。我想這對畫家的風格選擇會產生影響。我曾經看過一位清代畫家仿的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那已經是很走樣了。這說明中間經歷了許多輪的臨摹。清代這位畫家臨摹的《溪山行旅圖》,與我們看到的真跡圖像相比,已經相差太遠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圖像的傳播為畫家風格的選擇提供了廣闊的自由度。但這同時也出現一個問題:你的選擇多了,接受的美術信息多了,但你作為畫家的身份開始變得尷尬了。中國古代畫家,其實從南宋起就有這種苗頭,尤其是元明以后,文人畫家總有一種業余身份。業余身份使畫家免于成為畫匠。但到今天我們幾乎所有的畫家實際上都是專業畫家,但是專業畫家里又總有一部分人裝成業余畫家,就是說,他明明是專業畫家,但他的風格卻是業余畫家的,然后另外一部分人,他們是專業畫家,并且以專業畫家的姿態存在于世界上。我們可以以此來區分兩種畫家:你是一個專業畫家但偽裝成業余畫家,你這時候呈現出一種畫法;另外一種,你是專業畫家又繼續朝著這個專業方向走,這又是一種畫法。
剛才江黎用的一個詞我很喜歡——“研究”。我覺得在楊佴 的畫中,能夠感覺到他不偽裝成業余畫家,他是以專業畫家的姿態工作,表現出了一種研究的素質。這種研究不全是憑借他的才氣——雖然在評價藝術工作者時我們經常會用到“才華橫溢”之類的字眼,但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藝術家的工作狀態,這種工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研究狀態。在楊佴 的畫中,不論是他的色彩還是構圖,我都能看到一種研究性,這種研究性是那些偽裝成業余畫家的人所不具備的。
第三點,在剛才與朋友的交流中,我們也談到楊佴 的繪畫面貌與西方20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的關系,但楊佴同時還有一個背景,就是他在日本游學生活的經歷。我注意到他所選擇金邊款式的畫框,很顯然這不是中國傳統繪畫的裝裱方式,而是屬于西方、日本的風格。當下我們所談的現代,都被自然而然默認為西方的現代,但我覺得,除了西方的現代,佴 身上還有一種東方的現代,東方的意蘊,這也許跟他在日本生活過很多年有關系。可是,事情的復雜性在于,這一方面是優點,另一方面有可能也存在一種潛在的危險。為什么說是危險呢?東西方文化的結合這種說法,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陳詞濫調了,成為了一句空話。在有些人看來,這種結合是不可能的,這種觀點根本不成立。曾經有一位西藏朋友跟我講,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羅馬教皇有過通信來往,在交流過程中他們發現他們有相近的價值觀,尤其是在世俗層面上,比如幫助別人,解救自己等等,但他們最終落到一個地方是不一樣的,那就是喇嘛教或佛教不承認有第一推動力,但是西方是信仰上帝的,教皇堅持認為存在第一推動力。那么在這一點上,兩個貌似相近的體系實際上是走不到一起去的。另外一點,如要說起中西方之間的區別,首先是中西方的知識體系不一樣,中國的知識體系來自于亂世,它的學問根基中很大一塊是戰國諸子,但是西方乃至印度等地的知識體系并非來自于亂世。當我們想使得東西方融合的時候,就會突然發現其困難比我們可以設想的大得多,這就是說我們有可能走到一起,那另一方面我們又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還有一個危險是什么呢?假設我們可以走到一起,那么一個結果是我們走出來的是日本的東西,走出來的繪畫是日本的繪畫,走出來的書法是日本的書法,走出來的攝影是日本的攝影,走出來的建筑是日本的建筑——極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那么在這種可能性的前提下,作為一名中國藝術家,需要思考的就要比日本的藝術家多一層,也就是說,藝術既有東方的因素,又有西方的因素,我自己的因素在哪里?這個問題就比較復雜了。
還有一個問題,不局限于美術界,實際上文學界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就是當我們談起東西方的時候,我們其實忘記了,比如說,當阿拉伯人探討東西方時,他們指的是阿拉伯和西方,印度人討論東西方時,指的是印度和西方,諸如此類。每個國家在歷史上其被殖民的程度影響了其與西方之間的關系。比如一個非洲人,他的國家曾經被西方完全殖民和西化,與西方的關系就會不同于被半殖民的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這又是更復雜的一個問題,但在文化、藝術當中,這些問題我們又必須面對,這里面也同時生發出我們之前談到的接受的問題。這個時候,對于一名當代的藝術家,真的是處于種種難題之中,處在一種混沌的社會生活之中,處在東西方這樣一種微妙的關系之中,處在這種關系布下的種種危險當中。就在此時,我想,一種研究型的美術就顯得非常重要,它就是一種認真的美術實踐和試驗。我認為,藝術中倘若沒有實驗的因素,沒有向前摸索的實驗精神,沒有努力使自己區別于他人從而獲得一種可辨識度的意識,這種藝術所傳達出的基本上就只是玩的心態。所以這里我們又有了一種分類:玩的藝術和工作化的藝術。
綜上種種,佴 畫中對于色彩、構圖的實驗本身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并非美術行當的專業人士,沒有辦法判斷佴 的畫處于當下以及歷史中的具體位置,但是初看佴 的畫我就發現了他的畫具有鮮明的可辨識度,這對于藝術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了解一些別的行當的藝術家,比如音樂家、導演,他們的工作和實驗讓我意識到,在中國有一些人的的確確在為藝術做出自己的探索,也許其中大多數人走得并不遠,但是這種嘗試是有價值的。今天,我非常高興看到佴 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左 途 紙本設色 75cmx62cm 2003年 楊佴
漢風 河北省美術家協會藝術理論委員會主任
剛才在展廳看了楊佴 先生的作品,給我很深印象的是,他的作品很寧靜,這一點在當代浮躁的社會中是相當可貴的。從他的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老莊精神的影響,但是,他的作品超越了傳統和農耕文明的語境,這種超越體現在語言上和文化立場上。他持有一種現代人的心態,是站在一種都市文化層面上進行創作的,并且借鑒和吸收西方文化和日本藝術的一些因素,靈活地為己所用。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直觀感受到他擅于運用色彩,他可以將非常精美和復雜的色彩關系處理得極具中國韻味,這一點是很有難度的。
之前幾位先生也談到了當前美術界的困境,我認為,當前美術界的困境在于我們的很多藝術家的靈魂是在一種異化和異己的境遇中飄蕩,而沒有回到自己真正的內心世界。在八五美術思潮之時,我們關注的是打破傳統,尋求內在和外在的解放。那么,從今天的現實和深層意義來看,我認為,當前更為重要的是真正地回歸到自我真實的心靈世界。
我們在無數的文章里面,無數的研討會上都在強調創新,創新這個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作為一個偉大的或者優秀的畫家是一定要具備這種品質的。但是,如果忽視了真實的本體精神表現,只是極度地強調創新,其結果不但不會使我們走到西方的前面,甚至會迫使我們走向背離自我心境,背離自我立場,背離自我本真及審美意識的困境之中。我認為這種現狀,在當代中國美術界是非常典型和可怕的。當然,其中有市場化的社會大環境影響的因素,更主要的是藝術家自身沒有能夠真正理解現代精神和后現代精神。我認為,現在有一些畫家具有后現代主義的心境,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質疑的是,在中國當代政治背景、文化環境和生存境遇中,我們是否具備普遍的后現代條件和必然性?我一直認為,當下的中國仍然處于強烈的對價值的探討和追求階段,所以當代中國并不具有普遍的后現代語境。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屬于我們的審美和藝術,以及獨特而有價值的藝術批評。
只有當藝術家都回到真正自我的狀態,藝術生態才會真正合情合理并具有可持續性。只有藝術家們都能夠以自己真實的情感進行創作,那么這種文化生態才是良性的。任何一種人為的、主觀意志的、憑借想象建立的生態都是一種妄想,遲早是要坍塌的,最終還必然要回到它原始的起點狀態。我一直認為真正的美術革命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文化革命也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文化藝術的進步都是建立在對生命、對存在、對人的現實生存狀態的不斷體認和不斷改良的基礎上。是一步一步踏著前人的腳印,憑借自身非常典型的本體精神,來固化它,強化它,最后使它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審美和精神。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的本體精神非常強大,并進入一種存在層面的體認和表現的時候,其作品的能指才會得到極大的顯現和發揚,才會具有感人的力量和審美價值。
在當下的文化境遇中,我認為,我們沖出困境的唯一渠道就是我們的藝術家真正回歸到我們自身和我們真實的靈魂。一是要關注作為結果的藝術語言創新,同時,我覺得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對我們應該有所啟示。也就是說,我們在關注語言創新和結果的同時,更要關注語言創造的過程本身。只有關注過程,才有可能閃現真正具有創新意義的,并且是在本體非常享受的狀態下建立起來的自身真實的審美符號和審美體系。
我認為楊佴 的藝術探索是成功的,他的狀態是平實的,他的心是松動的,他的表現也是自在的。他的畫具有后現代的傾向,但是他沒有后現代的那種浮于表面的矯飾和虛偽的姿態,而是專注于自身審美的真實表現。我一直認為,對于當代中國美術而言,現代主義對于我們依然具有最大的借鑒意義。現代主義的那種表現性、象征性、超越性,那種對本體精神的高揚依然是我們這一代人最最缺乏的。雖然我們經歷了八五美術思潮,在那個思潮中,劉驍純、栗憲庭、殷雙喜、高名潞、彭德以及今天到場的李小山先生、鄧平祥先生、陶詠白先生都是在漩渦中心的人物,他們帶領、引導中國美術反思自身,使中國美術真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今天,我們再來反思對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解讀和借鑒,我認為仍未過時,它對我們仍有啟示意義。尤其是在中國當下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生存境遇之中,我認為這種更深刻的解讀和借鑒依然是最有價值的。
在此,我祝賀楊佴 先生的展覽圓滿成功,我也祝愿中國美術不斷實現新的超越。

右 小芳 紙本設色 40cmx32.5cm 2002年 楊佴
楊佴 新水墨畫家 美學博士
我要首先感謝各位先生的到來。這一次的研討會是臨時組織的,最初是彥鵬建議有這樣的一個環節,于是就在一周時間內邀請了在座各位,我知道很多先生是推掉了已有安排,特意從外地趕來參加的,非常感謝你們。
我作為中國人,又在國外工作、游學了近二十年,我有一點感觸,就是在經濟、科技上,我們并沒有像對待文化那樣將中西區分的如此清楚。正如李小山先生所說的當下是個信息發達的時代,其實類似這種一刀切的情況已經不可能存在了。我覺得文化藝術是人類所共有的。我看到過馮友蘭先生寫的札記,里面有這樣的論述,他說:東西方之分其實是古典與現代的區分。對此,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偉大的思想。我覺得東西方膚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人性是相近相通的,我們應該以此為基點來思考我們現在的文化。
其實在我以前的創作實踐中,我并沒有特意去梳理自己想法,后來交流增多,我開始思考自己創作實踐的出發點,應該就是基于人性的角度。我覺得我作為一名21世紀的藝術家,我們不應該做十九世紀的事情,也不應該做三百年前藝術家做過的事情,雖然我們一直在說筆墨當隨時代,說了很多年了,但是創新不應該只是一種口號,而應該落實到實踐中去。現在的我,已經越來越清晰自己所做的和要做的,就是希望可以為水墨的現代化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說這么多,謝謝各位。
(王曉晨按現場發言順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