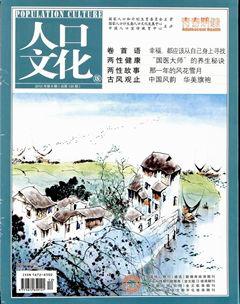婚前公證,讓我的心成了冰窖
艾一敏
相識七年
我與良友相識七年,很遺憾沒發展成眾望所歸的情侶關系。唯一原因應該就在于他不夠富有。這還是我后來在他的申辯之下改口的,我的原話是:你太窮。他說我不夠實事求是,分明是惡意打擊。
挑明了關系的發展方向,我和良友便多年相處和諧。他愛他的拜金女,我覓我的金龜婿。在我尋婿未果前,他樂意獻出他無私的愛,我心安理得享受著他的關懷,比如夏天美味的冰淇淋,冬天暖洋洋的火鍋。
良友說豪門一入深似海,你別瞎向往。保不準人家天天以淚洗面,哪有你這般自由自在。我譏笑他窮人仇富。我是不會輕易降低擇偶要求的,反正我年方二十六,還不算老。他說那我再等你幾年吧。有錢人都愛美少女,顯然那時你已條件不夠,咱們彼此將就點算了。
我呸,我討厭“將就”這個詞。人生的幸福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將就是砌不起來的,它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
蜻蜒點水
就在我尋覓得真有點心灰意冷時,在公司的一次洽談會上,陳橋及時出現,如一顆閃亮的明珠,一下子耀了我的眼。
陳橋,32歲,經營一家廣告公司,生意紅火。他的白色獅跑在眾多轎車中并不奢華卻無比顯眼。我喜歡開吉普的男人,我覺得這種男人骨子里有不羈和激情。有點錢,有事業,懂生活,這樣的男人我沒理由拒絕。所以當陳橋問我手機號碼時,我的心撞得胸膛咚咚作響。
當我把這個激動人心的好消息告訴良友時,良友很不屑地哼了一聲:女人啊,就這么幼稚!男人哪有這么容易就對你一見鐘情的!我一點都不生氣,很明顯,他這是嫉妒,試圖消減我對陳橋的萬丈熱情。我用從未有過的溫柔語氣說請他去吃火鍋,我買單,以此答謝他多年來的知遇之恩,做不成愛人,怎么著也是最好的朋友嘛。
在我與這個最好的朋友看著火鍋里香氣鼎沸剛想下筷時,我的手機歡快地唱起了歌。一瞥來電,我方寸大亂,手忙腳亂地碰翻了手邊的水杯。陳橋問我是否有空一起吃個飯,我忙說有空,連矜持一下的客套話都沒說。良友惡狠狠地瞪我。在我細致地補好妝起身欲走時,他陰陽怪氣地來了句,關鍵時刻要三思而后行。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說白了,無非就是不要輕易與人上床。
可是,很遺憾,他的這句話從我的左耳飄進沒作停留就從右耳飛了出去。和陳橋的約會讓我激情澎湃。陳橋顯然閱女人無數,他懂得如何去討女人歡心。他贊我知性美麗,說第一眼見我就覺得喜歡,我明知這些話的可信度并不很高,最后我還是神魂顛倒跟著他回了家。陳橋開始吻我時,我的手機不適時地響了起來。陳橋松開了我。不用看,我就知道一定是良友,我惱火地關了機。陳橋問是誰,我說是—個做保險的朋友,每天盯著我想讓我買什么保險,煩死了。程序突然被打斷,—下子便有些接不上去,空氣里就有了尷尬的味道。陳橋問我要不要喝點水,我訕訕地說,時間不早了,我要走了。其實我很為這句話后悔,在我站起身走到門口時,我很希望陳橋能突然拉住我的手,深情地說:留下來好不好?可是,這電視劇中的老套情節并未上演,他沒有挽留。
陳橋很多天沒再和我聯系。可我分明感到了自己對他的一些想念。
這一次的約會我們已儼然像情侶。飯吃得有些潦草,都有直奔主題的嫌疑。我并不確定陳橋的心思,但我想以自己的清白之身表明我對他的情意。當我的身體無法控制地僵硬起來時,陳橋再一次松開了我,他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他沒說下去,但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說我愿意。可是他蜻蜓點水般吻了我一下,穿起了衣服。
落荒而逃。從陳橋家出來,在冷颼颼的夜風中,我想起了這個詞。
婚事落定
良友說,他只不過當你是一場艷遇與你逢場作戲,豈敢要你清白之身?笨蛋!這讓我覺得恥辱又不甘。但不管怎樣,比起那些隨口以愛的名義占有女人身體的男人來,我還是認為陳橋不失為正人君子,我不想輕易放棄他。我想我大概愛上他了。
現在,我只有一個愿望,那就是和陳橋發生實質性的關系,成為他的女人。陳橋說我是好女孩,他說他會對我負責。負責,便是娶我吧。我這樣理解。我想我的人生終于打開了那扇渴望已久的門,門外是鋪滿陽光的幸福大道。
陳橋帶我去見了他的父母,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對畢業于國內—線大學看上去溫良謙恭的我顯然很滿意。但他們聽說我父母雙雙下崗時,他母親微蹙了—下眉頭。我偷偷問陳橋是不是他父母有根深蒂固的門第觀念,陳橋不置可否地笑著說我多想了。
我的確是多想了,很快陳橋就與我商談婚事,他的父母多年前就渴望著寬敞的客廳里能有蹣跚的孩子稚嫩的語聲,讓他們安享天倫。我說沒問題,我很愿意為你家創造這樣可愛的天使,如果你答應帶我去馬爾代夫度蜜月的話。
婚前公證
人生充滿變數,在我憧憬著未來美好的生活時,父親住院了。診斷書上“胃癌”兩字讓全家跌入了深淵。好在是早期,醫生說手術的預后還是較好的。
幾萬元的手術費用不算大,但對父母來說已是傾盡省吃儉用的所有積蓄。我的銀行卡里只有幾千塊,還有2萬元,被該死的股票套得很牢。那晚,我吞吞吐吐地問陳橋能不能借2萬塊給我,我不忍心看父母將積蓄花得一分不剩。陳橋淡淡地說了聲好,繼續專心致志看新聞報道。我囁嚅著說我股票解套了還你。他說不用,都一家人了。我如釋重負地笑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會那樣低聲下氣地與他說話,其實我也許更應該理直氣壯地與他商討,末了撒嬌地加上一句大不了咱不去馬爾代夫還不成么。我想我真沒用。
讓我感激的是良友。自從我和陳橋確定關系后,我和他便疏于聯系。那天一早他等在公司門口,一見我便將一本存折遞給我:我知道你的底細,所有的積蓄都砸在股市等待翻身呢,先借給你盡點孝道。我的雙眼瞪得想必比銅鈴還大,良友,他真是最了解我的人。存折里有4萬元。我一邊說著謝謝一邊將存折還給他,我說陳橋已經給我了。良友哦了一聲,拍拍頭說他應該想到這點的,怎么忘了。
我無法言說內心的感動。有一剎那,我失了神,將陳橋和良友合成了一個人。
父親手術很成功,他出院的第三天是我和陳橋原本約定去領結婚證的日期。那天我醒得特別早,足足花了一個小時才化了個滿意的淡妝。陳橋來接我,我美滋滋地上了車。陳橋一邊夸我特別漂亮,一邊遞給我兩張紙。他說在領證前,想和我做個婚前財產公證。那是—份協議書,上面列出了他的房產、車子和存款。我看著那張清單上龐大的財產數目,愣住了。想知道—個女人是愛你還是愛你的錢,那就去和她做婚前財產公證吧。我想起了網上看來的這句話。那么……我牽強地笑了。我說陳橋你是不相信我愛你嗎?陳橋說,這和我們的愛沒關系,現在人們都接受這個,—個程序而已。
存在即合理,我并不是不能理性地看待婚前財產公證。可是,我無端就想起了陳橋母親那天微蹙的眉頭,就有了很強烈的抵抗情緒。網上不是還有這樣的話嗎?想知道一個男人愛不愛你,那就看他肯不肯為你花錢吧。
我無法置信地瞪著眼前的男人,覺得他是那樣陌生冷漠。陳橋大概也意識到了這句話的過分,他看了我一眼,動了—下嘴唇,但最終還是什么也沒說。我的心成了冰窖。
我和陳橋沒達成協議。所以我們既沒去公證處,也沒去民政局。而且,我們的故事竟然也就這樣戛然而止,干凈利落得不可思議。
摘自10-08期《東方文化周刊》
(編輯 劉小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