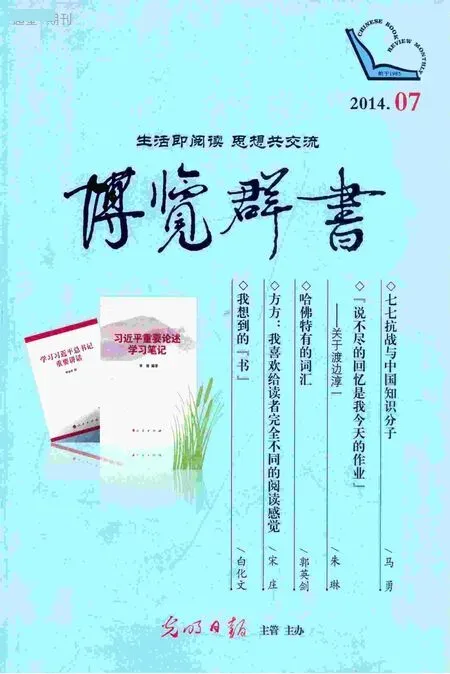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儒家憲政”之說成立嗎
○伊衛(wèi)風(fēng)
“儒家憲政”之說成立嗎
○伊衛(wèi)風(fēng)
秋風(fēng)認(rèn)為,古代政治中存在兩種傳統(tǒng),即周制傳統(tǒng)與秦制傳統(tǒng)。前者以封建制為構(gòu)架,強調(diào)君臣之間的契約關(guān)系,所謂“君臣以義而合”,君臣之間不是上下尊卑關(guān)系,有伙伴、朋友關(guān)系的含義;每一個君與他的臣組成一個共同體,在重大事務(wù)上共同決策,而規(guī)范彼此行為的就是“禮”,所以周代的治理秩序是禮治秩序,具有貴族共和的性質(zhì);在這樣的秩序下,君臣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是相互的,“禮”保證了平等,也保證人們的自由。后者是大一統(tǒng)以來的士大夫與皇權(quán)共治體制。換言之,皇帝的權(quán)力要受到來自儒生的限制,即以道統(tǒng)制約政統(tǒng),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憲政性質(zhì)。因此,“儒家向來就具有限制絕對權(quán)力的意向和精神”,它的思想中自然就蘊含著憲政的蹤跡。本文作者對秋風(fēng)的觀點持不同意見。
秋風(fēng)先生曾連續(xù)撰文討論“儒家憲政”,引起很大的爭議。為了論證這個命題,秋風(fēng)旁征博引,顯示出扎實的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令我輩敬佩。在他看來,憲政“主要關(guān)心憲制(constitution),也即權(quán)力的安排”。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憲政不只處理這個問題,還有“保障權(quán)利”的問題。作為憲政的經(jīng)典樣本,美國憲法不僅有三權(quán)分立的制度安排,更強調(diào)這種安排的目的——“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lián)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nèi)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后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相應(yīng)的憲政理論更是明確提到:基于公民同意的政治權(quán)力就是要保護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這是政治契約的基本宗旨。因為沒有權(quán)利的權(quán)力安排是獨裁的表現(xiàn),只注重權(quán)利的后果是人人都成了立法者,故而約束權(quán)力和保障權(quán)利并舉,憲政才能實現(xiàn)。從這個思路來看,所謂的“儒家憲政”不過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錯覺。
秋風(fēng)認(rèn)為儒家憲政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封建制,另一種是共治體制。在封建制下,“君臣以義而合”,說明君與臣是一種契約式的結(jié)合。他引用孔孟的話作為論據(jù),“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語)。孔孟的話能否證明封建制的儒家憲政存在呢?
一
先說封建制的問題。瞿同祖在《中國封建社會》一書中指出,大一統(tǒng)之后的中國很難稱之為“封建社會”(我們現(xiàn)在仍把秦漢以來的中國稱為“封建社會”,其貢獻要歸功于郭沫若,并深受毛澤東的推崇,然顧準(zhǔn)早就指出此中的牽強附會),而中國的封建社會以夏商周為主,西周最為典型,在宗法、階級和政治三個方面表現(xiàn)極為明顯。“分封而建”是授予封臣采邑,但這種封建關(guān)系的形成不是契約,而是靠血緣,即血緣宗法制。以血緣宗法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建立起來的國家不過是家族的擴大而已,從而生物學(xué)上的血緣關(guān)系也就決定了一個人的政治身份,所謂“血而優(yōu)則仕”,貴族恒為貴族,平民恒為平民,兩個階級是涇渭分明的。一旦有人破壞這種界限將是嚴(yán)重的僭越,所以孔子才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同的階級地位當(dāng)然會導(dǎo)致完全不同的政治前途。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與庶人在政治上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經(jīng)濟上是“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由此看來,中國的封建主義是一套相當(dāng)完善的制度。當(dāng)禮崩樂壞之后,“道術(shù)為天下裂”,王官之學(xué)失守,稷下私學(xué)興起,先秦的封建社會隨著秦始皇的統(tǒng)一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化為新型帝國,原有的制度也就隨之而解體。原來的“分封而建”為新的“郡縣制”取代;“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采邑制也由官員的俸祿制來承擔(dān);官僚的血緣世襲制也被后世的科舉取士制所替代。何懷宏認(rèn)為這是一種“選舉社會”,因為官員的產(chǎn)生不是世襲而是選舉,成了區(qū)別于先秦封建制有的根本所在。
事實上封建制的概念并非中國的概念,而是源于西歐中世紀(jì),瞿同祖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導(dǎo)言中就明確指出。通常所說的封建制度主要是指西歐中世紀(jì)的一種非常典型的社會形態(tài)。法國年鑒學(xué)派的布洛赫《封建社會》一書專門討論了“什么是封建制”。他指出西歐封建制所強調(diào)的“封疆建土”涉及的也是土地問題。一般來說,領(lǐng)主授予封臣采邑,封臣又把采邑再次分封給自己的附庸,但領(lǐng)主與附庸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法律關(guān)系,所以才有“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封臣接受領(lǐng)主的采邑,要合掌置于領(lǐng)主的雙手之中,主仆雙方以唇相吻,表示雙方的和諧和友誼。后來因基督教對世俗生活的干預(yù),封臣則要手按圣經(jīng)或圣物,甚至跪拜以表示效忠。經(jīng)過這樣的儀式,彼此之間的法律關(guān)系就形成:領(lǐng)主授予封臣采邑,封臣也要向領(lǐng)主履行相應(yīng)的義務(wù),主要是打仗(這里的打仗經(jīng)常指的是不同領(lǐng)主之間的利益爭奪)。當(dāng)封臣履行了義務(wù)之后,若沒有宣誓繼續(xù)效忠的話,那么他們之間的法律關(guān)系也就隨之而結(jié)束,封臣也就可以尋找新的領(lǐng)主宣布效忠,從而形成新的封建關(guān)系;當(dāng)然他也可以繼續(xù)效忠舊主,同樣的儀式還需履行。由此可知,領(lǐng)主與封臣之間關(guān)系的基礎(chǔ)是契約而不是血緣,這可以說是歐洲封建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布洛赫也明確地指出,“嚴(yán)格意義上的封建關(guān)系紐帶正是在血族關(guān)系不能發(fā)揮有效作用的時候才發(fā)展起來的。”(《封建社會》,商務(wù)印書館2004版,P700)
另外,封臣在戰(zhàn)爭中獲勝的話就可以獲得貴族稱號,有點像商鞅時代“軍功立國”,故而尚武又勇于冒險的騎士階層迅速崛起,一度武化之風(fēng)甚盛;在采邑之內(nèi),領(lǐng)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掌管該疆域內(nèi)的法律、行政和宗教事務(wù)。一個特別極端的例子是中世紀(jì)蘇格蘭流行的一項社會習(xí)俗——領(lǐng)主對其附庸的新娘享有“初夜權(quán)”。盡管這些弊端遭人詬病,然而封建制也為后世留下了不少的思想遺產(chǎn):領(lǐng)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精神也成為近代政治思潮中“社會契約”的淵源之一,尤其是近代憲政中的“國家的形成就是一種政治契約”與此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各自為政的領(lǐng)主彼此之間的力量角逐更為近代以來的歐洲社會民主進程早早埋下了伏筆,這些特征都與中國的封建制完全不同。雖然我們借用了西方封建制這樣一個概念,但必須清楚兩者的區(qū)別之所在。不幸的是,秋風(fēng)先生認(rèn)為中國的封建制與西方的封建制一樣,體現(xiàn)著一種契約精神。
二
退一步講,姑且認(rèn)為“君臣以義而合”體現(xiàn)了一種契約精神,但這種契約關(guān)系的雙方是“君與臣”。君是統(tǒng)治者毋庸置疑,而臣是統(tǒng)治者的助手,權(quán)力的執(zhí)行者,歸根結(jié)底還是屬于統(tǒng)治者,所以最終的契約不過是權(quán)力占有者之間分享權(quán)力的契約。孔孟確實說了君臣之間的相互尊重,可實際上君臣在權(quán)力問題上都是一家人,相互體諒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事情。關(guān)鍵是權(quán)力所指向的對象——被統(tǒng)治者在這種契約關(guān)系中并不存在,與憲政的基本精神也完全不符。
憲政的形成是“公民為了保障基本權(quán)利而達(dá)成的政治契約”。換言之,公民才是契約的主體,可是在秋風(fēng)封建制的儒家憲政關(guān)系中,統(tǒng)治者成了契約的主體,與憲政的宗旨截然相悖,這還能是一種憲政關(guān)系嗎?更進一步說,在秋風(fēng)的儒家憲政框架下,被統(tǒng)治者——普通百姓——的權(quán)利在何處得到體現(xiàn)?憲政要處理“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問題,這在封建制的語境下,就是“君與民”或者“官與民”的關(guān)系,可是在秋風(fēng)的論證中,“權(quán)利”完全被忽略。這么要害的問題只字不提,又怎么能說是一種憲政關(guān)系呢?

《中國封建社會》,瞿同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秋風(fēng)認(rèn)為“士大夫與皇權(quán)共治則是另外一種儒家憲政”,更是令人費解。他明確指出,士大夫通過教育考試而進入政府;獲得資源的控制權(quán),形成了“士人政府”;提倡“道”或“天命”的觀念等,這些對皇權(quán)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約束,所以也體現(xiàn)出一種憲政的傾向。如前所述,憲政不但處理“權(quán)力的安排”,也負(fù)責(zé)“權(quán)利的保障”問題。在共治體制上,士人對權(quán)力的約束體現(xiàn)在秋風(fēng)所說的“道”以及“天命”上,他還特別引用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學(xué)說,來證明“道”對現(xiàn)實統(tǒng)治者的制約,使得統(tǒng)治者不敢胡作非為。可是在現(xiàn)實社會中,“道”或“天命”如何能夠制約皇權(quán),具體怎樣操作,儒家沒有說法,秋風(fēng)更是沒有說法。事實上,通過觀念對權(quán)力的限制往往是士人的一廂情愿,除非所有統(tǒng)治者都是上古圣賢,敬天明神,否則用觀念來制約權(quán)力,無異于畫餅充饑。現(xiàn)實中依靠制度制約權(quán)力的典型是美國憲政。三權(quán)分立作為一種切切實實的制度,把權(quán)力的界限確定在一個明確的范圍內(nèi),同時各種權(quán)力之間相互制約以防止專制的可能。可是共治體制依靠士人的“道”來制約權(quán)力的辦法,在實踐中難以操作,于是士人就從相反的方向入手——寄希望于德行高尚的圣王出現(xiàn),他定然不會濫用權(quán)力,也會愛民如子。雖然這樣完美的人物符合士人的道德期許,可畢竟是百年不遇、千年難求的。即使有這樣的人,誰能保證他永遠(yuǎn)不會腐敗呢?所以士人通過“天命”或者“道”制約權(quán)力,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美好的烏托邦設(shè)想,但并不是所有士人的理想。
對于多數(shù)士人而言,按照社會既定的邏輯行動才是正道。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社會主流方向,士人通過教育科舉而入朝為官,他們就變成了統(tǒng)治集團的一分子,權(quán)力的附屬者,既得利益的獲得者,讓他們再去批判權(quán)力本身,無異于自毀前程,故而通過官僚儒生來約束權(quán)力基本上也落空了。當(dāng)然秋風(fēng)或許會反駁,還有追求精神獨立的儒生會“為民請命”。這一點當(dāng)然不可否認(rèn),歷史上究竟有幾個讀書人純粹追求知識而拒絕科舉?縱然有也是個案,總不能把歷史中的偶然當(dāng)作常態(tài)吧。因此共治體制中通過士人的“道”來制約權(quán)力在實踐中無法操作,往往變成了道德評價,無法制約權(quán)力濫用的問題;就士人自身來說,更是缺乏制約權(quán)力的動力,而且官僚儒生還是權(quán)力的受益者。
權(quán)力問題尚且如此,那么權(quán)利問題又會是何種命運呢?普通百姓的權(quán)利是否會得到保護?如前所述,皇帝和官僚儒生持有權(quán)力,難以制約的情形已經(jīng)毋庸置疑,而普通百姓在共治體制中有何權(quán)利,又如何被保護呢?現(xiàn)代社會中公民可以選舉代表來維護自己的權(quán)利,代議制民主或直接民主是體現(xiàn)民權(quán)的主要途徑,那么在共治體制下的民意體現(xiàn)、民權(quán)表達(dá)如何體現(xiàn)呢?有沒有一個正式的制度來保證普通百姓的權(quán)利?秋風(fēng)對此語焉不詳。事實上普通百姓在“共治體制”下幾乎成了“歷史上的失蹤者”,很難見到關(guān)于百姓權(quán)利的歷史記錄,反而經(jīng)常看到為了權(quán)利而“攔轎喊冤或赴京告御狀”,這正好說明了古代缺乏保護民權(quán)的有效途徑,百姓才冒著殺頭的風(fēng)險采取上述的舉動。由此可以看出,依靠儒生所謂的“道或天命”觀念,要么完全落,要么空陷入了道德批判;作為權(quán)力的既得利益者,官僚士人也沒有動力去制約它;普通百姓的權(quán)利保障制度更是無從說起。試問,作為憲政基石的兩個要旨——限制權(quán)力和保障權(quán)利——在共治體制下都無法實現(xiàn),儒家憲政還能成立嗎?
三
當(dāng)然憲政本身也有歷史,存在古典憲政和現(xiàn)代憲政之分。古典憲政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好生活”,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專門討論“幸福的城邦”問題,它不僅涉及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的問題,更包含美德教化等問題;現(xiàn)代憲政則主要約束權(quán)力以防止侵害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對后一個問題完全放棄了,這是進步還是退步姑且不論。從秋風(fēng)的論證來看,他所界定的憲政顯然是屬于后者。要論證古代中國就有現(xiàn)代憲政的因素,且不說這里的時空錯位,只著眼于憲政本身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儒家憲政的說法不過是“直把杭州作汴州”。
若“用觀念制約權(quán)力”在現(xiàn)實中真能發(fā)揮作用的話,那么人類所有的烏托邦都可以變成現(xiàn)實,理想國中的哲學(xué)王或儒家的“內(nèi)圣外王”早都把人類帶入了美好的社會。然而現(xiàn)實告訴我們,那些都是烏托邦,因為現(xiàn)實有現(xiàn)實的邏輯。僅就“權(quán)力制約”而言,歷史上確實存在一種切實可行的制度。自從大一統(tǒng)之后,中國政治的架構(gòu)發(fā)生了變化,原本屬于服務(wù)于皇帝私人生活的人員經(jīng)歷了“外部化”過程,從皇帝的私人隨從變成了具有公共職能的官員,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組織結(jié)構(gòu),也就有了“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權(quán)力格局。皇帝統(tǒng)領(lǐng)王室,而宰相領(lǐng)導(dǎo)政府;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依賴。皇帝要依靠宰相來治理天下,而宰相則借助皇帝表達(dá)政令的正當(dāng)性。皇帝不能為所欲為,宰相也不是有恃無恐,最為典型的表現(xiàn)是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皇帝發(fā)布命令,須先由中書省起草,然后交由門下省審議,通過之后交給皇帝,用紅筆橫批,最后由尚書省按照兵、刑、禮、吏、戶、工各部門的具體分工執(zhí)行。皇帝如果想要走后門給某人封官,即沒有經(jīng)過中書門下兩省,自行起草命令,然后直接交給尚書省執(zhí)行。自知沒有經(jīng)過合法程序,所以皇帝不敢用“紅筆橫批”,而改用墨筆斜批,意思是讓尚書省馬虎執(zhí)行,這樣得來的官因沒有經(jīng)過正常的途徑,所以被稱為“斜封官”,在官場中是受到輕視的。從這套權(quán)力的運行規(guī)則來看,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相互制約有制度性保障的。不幸的是,明代廢除了宰相,政府失去了領(lǐng)導(dǎo),那么對皇權(quán)的制約也就不存在了,相應(yīng)的制度基礎(chǔ)也就沒有了。要說古代社會是專制權(quán)力不受制約,那么明代則是典型。由此可以看出,制約權(quán)力的制度性安排比起儒家的觀念約束更為切實可行,然而傳統(tǒng)對百姓權(quán)利的保護方面一直處于缺失的狀態(tài),故而與現(xiàn)代憲政的含義相差甚遠(yuǎn),更與儒家憲政扯不上關(guān)系。
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
(本文編輯 謝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