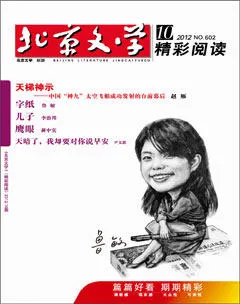我的自由
屈指算來,從在報刊上發(fā)表第一篇作品開始,至今已經(jīng)逾50個年頭。詩歌、散文、雜文、報告文學(xué)均有所涉獵,只是從未發(fā)表過小說。
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似乎都有文學(xué)情結(jié)。“喜愛文學(xué)”是許多人年輕時的共同特征。文學(xué)為我打開了透視生活的窗子。上大學(xué)時和參加工作以后,瀏覽了古今中外大量文學(xué)作品。欣賞的眼界高了,“動手”的欲望反而受到抑制,小說創(chuàng)作一直看得比較高深,未敢輕易介入。近20年,多與新聞體裁打交道,消息、通訊、特寫等等倒是積累了不少,創(chuàng)作有文采的文學(xué)作品比例不高。這也算是自己難以釋懷的一個“心結(jié)”。聊以安慰的是,對文學(xué)的喜愛,使自己對當(dāng)代文學(xué)一直保持關(guān)注,特別是幾位喜愛的作家,他們每有新作,總會找來拜讀,不時會有自己“試試筆”的愿望萌動。
真正觸動自己的是《北京文學(xué)》創(chuàng)刊60年特刊。我比較喜歡收集這種創(chuàng)刊多少周年的特刊,因為這種特刊一般編者下工夫都很大,不光有歷史厚重感,其中的作品也會精挑細(xì)選。這期特刊果然讓我一讀難以釋卷,鐵凝的《春風(fēng)夜》、崔曼莉的《求職游戲》都很有味道。尤其是擅寫農(nóng)村、農(nóng)民題材的北京作家劉慶邦的《丹青索》,將筆墨指向畫壇,短篇容量卻不小,讀來敬佩不已。暗暗思忖,如果自己寫一篇反映畫家生活的小說會怎樣?
有了這個念頭,便多日揮之不去。幾經(jīng)琢磨,確定讓自己經(jīng)受一次挑戰(zhàn),寫一個以畫鷹見長的畫家故事——《鷹眼》。因為工作關(guān)系,常常能夠接觸一些畫家朋友,平時為熏陶自己的“修養(yǎng)”,喜歡觀畫展、看畫廊,畫家的生活模式、情趣愛好,乃至逸聞趣事,多有目睹、耳聞。況且,實(shí)際上畫家并不生活在真空里,必然打上當(dāng)今社會烙印,許多人情世故是相通的。這讓我對駕馭這個題材增添了一點(diǎn)信心。
選擇“鷹眼”為題,是因為鷹眼之犀利、睿智,明察秋毫,在各種動物中異常突出。畫家能掌握畫鷹精髓,讓鷹眼生動起來,絕非等閑之輩。但貪欲往往會蒙蔽雙眼,迷亂內(nèi)心,自以為春風(fēng)得意,樂享桃紅柳綠,不知不覺中也許早入他人圈套。不是鷹眼不明,實(shí)在是總有叵測人心。寫新聞常期望有“打眼”的視覺效果,玩收藏卻忌諱“打眼”,畫家賣畫被“打眼”則將是“致命的”。畫壇交易,水深莫測,買賣雙方動心眼、耍手腕、設(shè)圈套,都可以有看點(diǎn),比較容易“出戲”。以自己的想象完成一次畫家采風(fēng)故事,小河溝翻船,鷹讓雞“鴿眼”,算不上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充其量算個游走畫壇的“騙術(shù)曝光”吧。結(jié)尾處,畫家已然恢復(fù)自由,但新的誘惑仍在,歌廳舞榭,酒綠燈紅,畫家的筆浸上錢欲色彩,還真說不好能畫出什么樣的佳作還是劣品,遭遇什么樣的是非曲折,有“鷹眼”般的洞察,也未必看透。
寫小說畢竟初學(xué)乍練,對繪畫藝術(shù)的了解過去尚屬淺嘗輒止,基本構(gòu)思完成,匆忙“惡補(bǔ)”研讀繪畫典籍、新知。擔(dān)心寫人敘事中處處露怯,但似乎仍難以完全避免。感謝《北京文學(xué)》讓我實(shí)現(xiàn)一個多年的文學(xué)夢想,但愿將來能夠?qū)懙煤眯膶W(xué)夢能夠不斷延續(xù),結(jié)出更成熟的果實(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