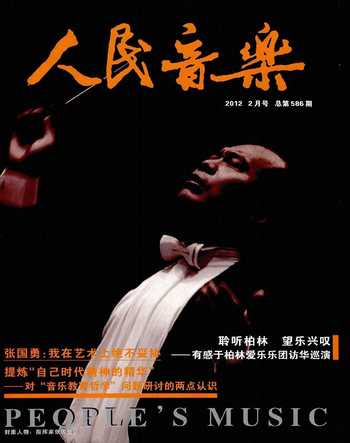楚劇《大別山人》音樂創作述評
序言
現代楚劇《大別山人》是第十二屆文華獎獲獎劇目。該劇的]出十分感人,無疑,音樂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楚劇音樂的發展更多體現在對既有傳統的傳承和保護上。像以《大別山人》這樣的現代題材為基礎,又在力求在創作上著意出新且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楚劇音樂卻不多見。
該劇的作曲者李道國,是一位有追求且較為勤奮的中年作曲家。他不僅具有較深厚的中國傳統音樂功底,通曉楚劇音樂的聲腔板式,而且也學習過西方作曲技術理論“四大件”。同時,他還有著長期在戲曲團體與編劇、導]、]員一起合作的工作經歷。他曾為京劇、漢劇、楚劇、黃梅戲、隴劇等多個劇種作曲,因此,近年來他在戲曲音樂創作方面成績斐然。
楚劇《大別山人》的音樂創作,既有楚劇音樂風味,又動人動聽。以下從音樂的戲劇性、音樂的整體性和音樂的創造性三方面來談談對其音樂創作的看法。
一、音樂的戲劇性
戲劇性,是戲曲音樂的重要特點之一。其基本特征有兩點,一是表現人物性格;一是表現矛盾沖突。在表現人物方面,該劇作者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如劇中的男女主人公王福和桂英都以男女迓腔為主,以體現典型的楚劇音樂風格。性格潑辣的臘妹,由于其特定人物身份(四川籍),作者采用了楚劇高腔和川劇高腔結合的做法。如例1:
(譜例選自“湖北省地方戲曲藝術劇院樂團用譜”,下同)
憨哥是一位憨厚可愛且說話有些“口吃”的農村青年,作者選擇根據鄂北民歌改編的《如今唱的是幸福歌》為素材。如例2:
大媽是劇中一位長者,鑒于楚劇目前尚無專用的老旦腔,作者選用了“應山腔”(亦稱“站花墻”調),用以體現對其他女性唱腔的區別。如例3:
總之,對于這樣一個人物較多且性格各異的大型現代戲,作曲者在不同人物的腔調運用上,采用了“依人選曲”的方法。也正因為是“依人選曲”,所以為該劇音樂的戲劇性提供了較好的基礎。聆聽不同性格的唱腔,讓聽眾不僅從視覺上,而且也從聽覺上感知到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此外,在表現戲劇矛盾方面,該劇的音樂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開場幕后伴唱“送郎當紅軍”的依依不舍與王福、桂英揭蓋頭的熱烈喜慶;第二場王福、桂英重逢時的悲喜交加與第四場桂英給憨哥療傷時的款款深情;還有第五場王福、桂英、憨哥之間的情感高潮等等,作曲者均充分運用了音樂的情感表現功能,與劇情的發展變化緊密配合。或為伴唱、對唱,或為獨唱、齊唱;或為全奏,或為獨奏;或為委婉纏綿的慢板,或為緊張激烈的快板等等。
二、音樂的整體性
從全劇音樂來觀察,《大別山人》的音樂在整體性上也為我們做出了成功地嘗試。所謂整體性,是指該劇音樂在按戲劇性要求完成各類不同人物的唱腔設計、表現劇情矛盾沖突的同時,在風格上體現出來的總體特征。
我們知道,在戲曲音樂創作中存在著既對立又統一的兩種因素,即表現因素與邏輯因素①。戲曲音樂發展至今,在歷經其唱腔體制的“單曲反復”、“多曲聯綴”、“單腔板式變化”、“多腔板式變化”等變化之后,已進入現代戲曲音樂時期②。對楚劇而言,由于這一時期音樂的創作成分逐漸增多,表現因素日漸增強,于是在創作中常見的一個突出問題便是:不少劇目的唱段單獨拿出來都非常精彩,但全劇音樂的材料運用過多,因而顯得缺乏統一感,缺乏整體性。究其原因,是作者對全劇音樂材料的安排缺乏理性思考,在音樂創作構思中缺少邏輯因素的緣故。聆聽《大別山人》的音樂,可以看出作曲家的總體安排和理性思考。其基本特點是,在全劇音樂材料的安排上注重統一因素的運用。該劇的統一因素就是“送郎當紅軍”這一幕后伴唱的基本曲調及其種種變化。例4為該劇主題歌:
一方面,“送郎當紅軍”作為主題歌貫穿全劇;另一方面,該主題歌的各種基本素材,或融入劇中人的各種唱腔之中,或融入前奏、間奏和過場音樂之中。全劇音樂既有發展變化,又有高度統一的整體感。特別是劇終以后,“送郎當紅軍”的旋律還在觀眾的耳旁回響。例5即為將主題歌音調融入主人公王福唱腔中的實例:
對這種現代戲曲音樂創作中“主題貫穿”的做法,人們往往褒貶不一。該曲作者究竟是受京劇“樣板戲”的影響,還是直接受瓦格納樂劇“主導動機”貫穿的影響?目前筆者尚未考證。然而,當戲曲音樂的創作成分日益增多,且原有曲調基本框架日漸模糊的時候,作曲者在創作中注重對全劇音樂材料統一性的選擇,是戲曲音樂唱腔體制發展的歷史規律所至③。
三、音樂的創造性
《大別山人》的第三個突出特點,體現在音樂的創造性上。在舉國上下都在倡導保護傳統文化的語境中,談楚劇音樂的創造性是否有些不合時宜?對此,竊以為應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來看待之。也就是說,楚劇音樂的發展,也要注意其自身風格的多樣性④。我們應用平等、相對的觀念來看待戲曲音樂(包括楚劇音樂)的保護和發展。一方面,我們要加大保護傳統的力度;另一方面,我們還須注意其在新時期的發展與創造。《大別山人》的音樂創作,在對楚劇音樂的發展上有如下幾點可圈可點:
其一,對字腔關系的適當突破。傳統楚劇唱腔的特點是朗誦性較強而抒情性不足,如何使楚劇音樂既有楚劇風格,又優美動聽,是歷代楚劇音樂作曲家孜孜以求的課題。以往的作品在旋律美化上所作的探索,主要體現為對語言聲調的自然延伸。然而,過分拘泥于方言聲調,對旋律的美化也是一種束縛⑤。因此,該劇的作曲家在創作時,嘗試對唱腔的字腔關系進行了一定的發展,以追求旋律的雅化與美化。
其二,吸收湖北民歌等外來因素。如《大別山人》的主題歌“送郎當紅軍”,其素材就出自同名湖北監利民歌;憨哥的唱腔,也系吸收劉正維先生根據湖北應山民歌編曲的《如今唱的是幸福歌》創作而成等等。誠然,吸收外來因素豐富楚劇音樂并非《大別山人》的首創。但是,如何將外來因素與楚劇的傳統音調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既有新鮮感,又流暢自如,卻是不易解決的問題。無疑,《大別山人》的作曲者在此方面的嘗試是成功的。
余論:幾點思考
聆聽《大別山人》的音樂,引發筆者對一些相關問題的思考。茲作余論如下:
第一,如何看待戲曲音樂的“作曲式”創作方式。
為什么我們要召開這樣一個學術研討會?為什么要為一個成長中的中年作曲家的作品進行研討?竊以為與戲曲音樂尤其是楚劇音樂在當代的窘境,與戲曲音樂創作人才的匱乏等方面原因有關。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為了補回“文革”的損失,我們將戲曲音樂建設的重心移至恢復傳統、保護傳統上面來,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做法。但是,其中遮蔽了一個被我們忽略的問題,這便是對戲曲音樂在當代如何發展缺少思考。尤其是對戲曲音樂的“作曲式”⑥創作方式及其在當代戲曲音樂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認識不足。如今,《大別山人》音樂創作的成功,充分說明了這一創作方式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作曲式”的創作方式是當代戲曲音樂發展的重要途經之一。
第二,如何看待地方劇種發展中的風格問題。
《大別山人》的音樂創作,是否距離傳統的楚劇風格遠了一些?或者說,像這樣的大型現代楚劇,其音樂創作能否保持其地方性品格?保持其濃厚的生活氣息?這是一個不可不考慮的問題。對此,我們需要弄清什么是地方性品格?比如楚劇的地方風格究竟是什么?以楚劇迓腔為例,是以早期一唱眾和鑼鼓伴奏的“哦呵腔”為準呢?還是以1930年代李百川先生清新活潑的唱腔為準?抑或是以1950年代關嘯彬先生如泣如訴的唱腔為準?這些問題恐怕目前還沒有一個共識。理論上講,既能保持地方風格又能表現現代生活自然是最佳選擇。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楚劇音樂的風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劇種風格的日漸淡化和劇目風格的日益強化,已成為20世紀以來戲曲音樂發展的基本趨勢⑦。根據當代“可持續發展”理念和文化保護政策,地方劇種(或楚劇音樂)的地方性品格,主要從博物館式的保存和活態傳承的早期傳統劇目中來體現。而在表現大型現代題材的劇目中,在發展和保持問題上是難以兩全的。
①一部戲的音樂必須通過感性使人得到感染,即劇中人的喜、怒、哀、樂以及全劇的矛盾沖突均要盡可能地體現——這是戲曲音樂的表現因素。同時,又不能脫離理性的約束,即全劇音樂的冷、熱、張、弛以及材料的統一與對比要布局得當——這又是戲曲音樂的邏輯因素。詳參蔡際洲《戲曲音樂的表現因素與邏輯因素——關于全劇音樂材料構成規律的探討》,《黃鐘》1992年第3期。
②這里特指1949年以后,由專業音樂工作者參與“戲改”以來產生的,以表現現代題材為主的戲曲音樂。
③蔡際洲《戲曲音樂的表現因素與邏輯因素——關于全劇音樂材料構成規律的探討》,《黃鐘》1992年第3期。
④蔡際洲《楚劇音樂的可持續發展》,《戲劇之家》2010年第8期。
⑤蔡際洲《“依字行腔”另面觀》,《楚天劇論》1987年第2期。
⑥中國音樂學院董維松先生曾將戲曲音樂的創作方式總結為“套腔式”、“編曲式”、“作曲式”三種。第一種套腔式,是指傳統的創腔方式。無須作曲家動手,有經驗的]員拿起劇本即可]唱。這種方式是保留和傳承傳統唱腔的重要途經,也是眾多傳統劇目得以延續的重要方式。第二種編曲式,這種創作方式對傳統唱腔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但這種改革以基本保留原聲腔的基本格局為限。也就是說,盡管某些地方改動了,但原有曲調的基本框架不變,人們還可以聽出是某劇的某種腔調。第三種作曲式,這是受現代京劇音樂創作的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創作方式。其特點是創作的成分較之編曲式更多,作曲家多運用某劇種音樂的素材和音調進行創作,原有曲調的基本框架較為淡化。但是,人們還可聽出是某劇種的基本風格。
⑦蔡際洲《當代戲曲音樂的歷史進程與發展趨向》,《中國音樂學》1994年第1期。
(本文系根據2010年10月17日在“楚劇《大別山人》暨李道國音樂作品研討會”上的發言稿整理而成)
蔡際洲武漢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
(責任編輯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