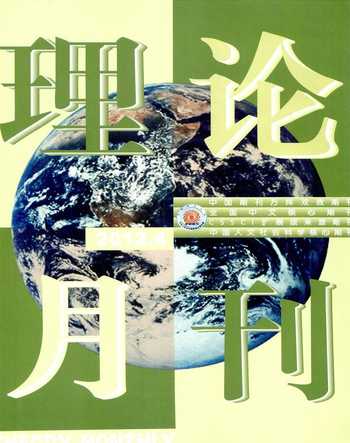信任危機與中國人的異常行為
彭大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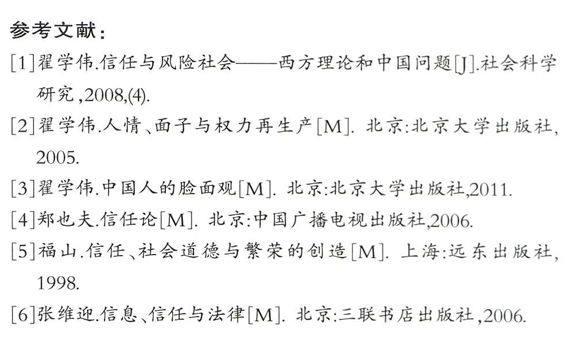
摘要:社會轉型會引致個體或群體行為的變化,這些變化或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或對社會的發展形成阻滯。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因此,中國人的社會行為必將發生一系列的改變。文章基于四個個案描述了中國人異常行為,指出人際信任危機是產生異常行為的根本原因。而人際信任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中國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人際信任機制中的內在約束松弛,而外在約束尚未建立這一事實。因而,如何在社會轉型中,重建信任機制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信任;信任機制;異常行為
中圖分類號:C912.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4-0152-04
一、中國人的異常行為:若干個案
異常行為是一個經過比較才有意義的概念。在含義上,它與正常行為相對。判斷某個行為是否為異常行為,參照物的選定非常重要。我們從兩個維度上來選定參照物,其一,從縱向的時間維度(或者說歷史比較)出發,用當前的行為與傳統中國人的行為進行比較。其二,從橫向維度,即同時代的中國人中處于不同群體的人的行為進行比較。無論是哪個維度上來衡量,下面四個案例中的行為都應歸為異常行為的行列。
案例一:在上海浦東機場,留日的兒子為了學費之事與母爭執,未果,兒子遂刀刺母親,母親受傷倒地,圍觀者甚眾,無一人伸出援手,最后竟然是一名外國游客現場施救,并最終將這位可憐的母親送往醫院。(新民網,2011)
案例二:中國富人的海外移民熱潮。一度移民海外,成了富人的不二選擇。中國的富人在國內如魚得水,生活的好不瀟灑,為何要移民國外?(中國青年報,2011)
案例三:中國人在國外豪購行為常見諸報端。但令人不解的是,海外歸國人士,通常在國外豪購茅臺酒和中華煙,究其原因,一些購買者表示,從美國購買茅臺不僅價格便宜,而且絕少有假酒,質量有保證。(中國新聞網,2011)
案例四:日本九級大地震,使得內地罕見的“搶鹽熱”一度達到沸點。(聯合早報,2011)
上述案例均是新近發生的一些事件,此類在傳統社會里都是不曾遇見的事件經常能在我們生活中看到或聽到。那么是什么導致了中國人的這種異常行為?這種行為具有普遍性還是特殊性?(即針對不同的文化群體,是否都有相同的影響?)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妨來逐個分析一下個案本身。案例一的焦點在于在人流甚多的中國機場,面對受傷的中國人,中國的旁觀者無一人伸出援手,反而是一個外國游客在現場施救。這說明了什么?中國人很冷漠?中國人喪失了助人為樂的精神?顯然,這些都不能滿意地對此作出回答。案例二中說的是中國富人熱衷移民國外的事。難道中國富人不夠愛國?國外的月亮比中國圓?這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實際也并非問題的實質。倒是案例三中,我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中國人這種海外購物熱潮乃源于一個簡單原因,即中國出口海外的東西是真的,且價格便宜。反過來說,國內銷售同樣品牌的物品有很多是假貨,且價格比海外的要高。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國內銷售的國貨為何有售假的風險?為什么銷往海外的商品價格更便宜?這些問題都無法輕易地能找到答案。案例四中描述的“搶鹽”事件,且最終引發了一種輿論恐慌,原因何在?是老百姓愚昧還是老百姓安全感缺失呢?
通過對上述原因的追問和思考,我們發現這些行為都和信任一詞存在著關聯。案例一是對陌生人的不信任,案例二是對社會體系不信任,案例三是對行業組織的行為不信任,案例四,社會體系不信任導致的安全感缺失。在分別討論個體的人際信任和社會體系信任之前,有必要厘清信任來源以及信任危機的產生根源。
二、信任含義與產生的基礎
(一)信任的含義及其特征
“信任”這一概念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到來而凸顯出社會意義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它看成是現代性的產物(翟學偉,2008)。然而,不同的時期和文化環境中,對信任的理解卻難以獲得統一。悉數西方學者對信任一詞所作的論述,大致是從兩個維度拓展概念的含義。其一,認為信任是聯結個體之間互動關系的一種心理期待。例如,羅特(J.Rotter,1976)認為信任是個體對另一個人的言詞、承諾及口頭或書面的陳述的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賴茲曼(L.Wrightsman,1974)把信任看做個體特有的對他人的誠意、善意及可信任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而在薩波爾(C.Sabel,1993)那里信任是交往雙方對于兩人都不會利用對方的易受攻擊性的相互信心。其二,認為信任是一種使個體間互動或社會關系得以良性運行的一種方法。社會學家大多都認同這一看法。如社會學家科爾曼在他的理性選擇理論中涉及對信任的論述。他認為信任是致力于在風險中追求最大化功利的有目的的行為,是社會資本的形式,可以減少社會監督與懲罰的成本(科爾曼,1974)。德國社會學家盧曼更是把信任看成是一種“化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一種社會機制。經濟學家阿羅說“信任是經濟交換的有效的潤滑劑”,這與盧曼對信任的理解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暫不去評論西方學者對信任理解的貢獻和局限性,且把視野轉向中國人對信任的理解。盡管前文已經指出,信任的含義是伴隨現代性而凸顯出來的,這并不表明,在現代化以前的中國人沒有“信任”的同義詞。甚至相反,在西方學者對信任討論之前,我們就已經出現了與“信任”含義相同的詞。例如,在古漢語里,“信”“義”等就具有與信任相似之意。《說文》中,“信”指從人言。它包含的意義甚廣,這里擇要羅列其部分含義:(1)書信、消息,(2)使者(發信臣),(3)憑據、符契,(4)誠實,(5)信用,(6)聽憑,(7)信任等。在古代漢語中一個“信”可以包辦這些意思,讀者可從具體語境中體會其實際含義。無獨有偶,“義”在古漢語里也有相似的含義,在《論語》中有“信近乎義,言可復也”“子日: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等傳達的便是此意。然而,“信任”在詞源學上并不是特指今天所傳達的含義,而是“相信并任用之”的意思。如《史記·蒙恬列傳》:“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南史·荀伯玉傳》:“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元陳以仁《存孝打虎》楔子:“唐僖宗信任田令孜等,貪財好賄。人民失散,四野饑荒”等。而信任在今天則特指人際交往中的一種單向關系,與“相信”同義。比如說“他信任你”,實際表達的是“他對你的一種單向關系”,至于你“信不信他”則在“信任”里是找不到的證據。無論是西方還是在中國,信任一詞含義,都具有隨時空而變化特點。想要建立一個一致的概念恐怕為時尚早,但我們可以基于對“信任”在中西方語境中不同的理解,按其共同點做一統括也尚無不可。
綜合中西方對信任含義的理解,以下幾點可以概括其共同之處:(1)在社會行動(互動)的日常經驗、約定俗成的規范基礎上,對他人的一種主觀愿望。無論是在西方學者那里。還是中國人那里,信任首先是一種主觀愿望。而作出這
一主觀愿望的則依賴社會交往過程中經驗規則、約定俗成的習慣等。(2)具有一定時空秩序的特征。即信任具有一定的時間差和空間聯系的特征。時間差是指“行動和兌現較之諾言和約定必然是置后的,言與行,承諾與兌現之間存在著時間差”(鄭也夫,2001)。空間聯系是指人與人交往的場景。傳統社會是“面對面”交往的社會,這種面對面的交往便具有了空間特征。如吉登斯所言,現代社會行動中“時空脫域”頻繁發生,信任的空間特性便極大地拓寬了。因此,這種空間秩序需要特殊外在約束來維持信任的生成。例如,互聯網上的商業交易靠“法律法規”的外在約束來得以維持。(3)風險性。這一特點是承接前面兩個特點而來的必然結果。如前所述,信任表達的是主觀愿望,那么這種主觀愿望立基的前提一旦被違背或被忽略,必然使得這種主觀愿望難以達成。而信任的時間差和“脫域”的存在,加劇了這種不平衡,使得行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增強。這也正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信任問題之所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如鄭也夫(2001)所言“具備了確定性,就不存在風險與應對風險的這一特定方式了,也就不叫信任了。”(4)具有特定的社會功能。無論西方社會還是中國社會,信任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我認為對此最為簡潔的概括可能要算盧曼了。他把信任看做是“化約復雜性的一種社會機制”不僅把信任一詞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說得很明白,同時也指明了“信任”本身便是為建立“社會秩序”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如我前面所說。信任一詞的含義具有時代性,其含義并非一成不變。與之相伴隨的特征也不甚枚舉,但我認為,基于中西方學者對信任的理解而概括出來的上述四個特點是最為基本的,也構成了本文對信任進行討論的基礎。
(二)信任產生的基礎
承認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對信任含義理解上的共同之處,并不意味著我贊同用西方學者構建的信任理論對中國的現實解釋的正確性。相反,我認為中國和西方在信任的含義理解上雖有共同之處,但二者產生的基礎卻并不相同。用基于不同基礎上建立的理論解釋具有文化差異的社會事實,必然也是不可取的。為了進一步論述的方便,我們尚需要回過頭來。討論一下西方學者對“信任”的理解的局限性。局限性之一是受西方方法論上所持有的“二元論”的影響。進而把“信任”也進行了二元區分。“信任”只和“不信任”相對,排除了第三種可能性。這一局限性,構成了其西方理論對中國事實解釋上的困難。例如,中國人在行動的時候,有時候很難確切地區分是信任還是不信任。而且這種信任關系會隨著外部條件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例如,大街上一老太跌倒了,你決定該不該上去扶一把的時候,實際上難以確定你是“不信任”還是“信任”這個老太。當你上前看的時候,你發現她正是你的鄰居“王大媽”,你會毫不猶豫地“攙扶”她。概言之,二元對立的分類難對此一情形中的信任關系予以解釋。局限之二是,信任只產生于個體的人際交往過程中。從西方學者對信任含義的理解中,我們不難看出,信任主要產生于個體交往行動中,這種促動力來自三個預期:一是心理預期,即認為信任會換來對信任的回報。二是文化預期,即對相同文化理解上獲得一致性的可能性高。三是預設了對違背信任行動的懲罰機制的存在。正是這三個方面的預設構成了西方信任的基礎。而回過頭來反觀中國信任的產生。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信任最早是產生于“親緣關系”之上。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社會中,甚至可以不用“信任”來概括。而用其它詞語可以取代之。例如朋友之間的“信”,君臣之間的“忠義”等就表達了同等的含義。在重視血緣關系的傳統農業社會里,要建立非親緣關系之上的“信任”關系,唯有用“忠信”等同于“孝親”(翟學偉,2008)。“熟人社會”是建立信任關系的次一級場所,它可以看做是對親緣關系的拓展。因為在傳統農業社會里,熟人社會多數是依親緣關系而建立的,此時的熟人關系、地緣關系與親緣關系往往是重疊的。由此,我們看出中國農業社會里所建立的“信任”關系,是沒有外在約束的,它只依賴其交往中的內在文化規定性(如三綱五常)。熟人社會的“信任”關系之所以可靠,是因為熟人社會空間特征的局限性,即違背“信任”的后果會導致其無法在該社會中生存,因而無需外在的強制性規定。
至此,我們已經把中國和西方信任產生的基礎之不同做了一個簡單的對比。在今天中國發生的社會事件中,我們大約看出中國人的信任結構與西方學者所描述的信任結構有區別。但是我們也不能僅憑此就斷定西方的信任理論就完全不適合于解釋中國的社會事實。我認為,伴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社會處于急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這一過程所呈現出來的景象,可以看成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碰撞所產生的后果。完全抹去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用西方現代社會理論來解釋中國社會事實是不可取的,同樣的道理,完全摒棄西方理論的有意啟發,僅從中國傳統文化視角來解釋信任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是不可取的。
三、信任生成與信任危機
除了信任產生必須具備的基礎外,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構成信任產生的當然前提,如果沒有互動,信任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里的主體可以是個人、群體也可以是組織甚至是社會系統。有了互動、有了內在或外在的約束規則,實際上也就具備信任的基本條件了。我把人們在互動中信任的產生稱之為信任的生成。信任生成只是信任存在過程中的首要步驟,而最終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是使得這種信任得以維持下去。如何才能維持下去呢?這就需要有對信任基礎的外在或內在約束違背行為實施懲罰,即建立懲罰規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之所以信任能夠持續不斷,本質上并不是因為血親關系或熟人關系的緣故,而是在血親或熟人關系基礎上所生成的人們普遍遵循的道德規范與倫理的約束,以及人們對偶爾違背這些規則人的懲罰。懲罰的形式可以是無形的道德譴責,也可以是有形的體罰。群體的譴責和輿論的壓力往往使得“犯規者”難以在這樣一個社會里同別人交往下去。這種懲罰規則的存在強化了信任機制。使得信任在社會關系結構不改變的前提下,得到永續。西方社會的情況又如何呢?我們在信任基礎一節中,闡述了西方信任的基礎中存在心理預期、文化預期和懲罰機制。其中。心理預期和文化預期來源于社會上的主流價值觀,比如西方的宗教信仰,而懲罰機制則是法律法規和道德譴責。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的信任生成中的外在性約束(即法律法規)和內在性約束(主流價值觀)都構成了必要的前提。而約束本身的被認可和懲罰機制的存在必然也會強化信任,使之在社會互動中得以維續。
從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信任的生成過程看,內在約束和外在約束既構成了信任的前提又是信任得以維續的保證,這在現代信任系統中是不可或缺的,否則信任就會出現問題,產生信任危機。基于圖1的信任機制,我把信任危機分成兩種。一是信任在一次互動完成后即宣告終止。即信任難以持續的問題。一次性交往過程中,人們往往因私利心驅使,產生違背約束規則的行為出現(經濟學中稱為一次性博
弈)。這種行為往往導致信任難以維續。例如,南京的彭宇事件便屬此類,其后果導致后來者難以對陌生人賦予信任。案例一也部分地源于此一原因。二是信任產生的基礎“薄弱”,使得信任生成出現問題,當無法產生出信任時,信任的持續問題就更不存在了。什么情況下會導致信任無法產生?首要的原因當屬信任基礎的缺失。在社會轉型期,這種缺失尤為突出。當一種舊的價值觀“土崩瓦解”之時,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建立起來,信任的基礎處于“真空”狀態中,因而無法產生出信任。另外,當信任維持成為問題時,往往也會削弱信任生成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講,信任缺失也可能是信任難以維系所產生的一個結果。總而言之,信任危機的出現是信任機制中某一個或幾個環節出現問題所引起的。因而,對中國當下所出現的信任問題的討論也應該從信任機制人手。
四、社會轉型與中國的信任危機
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里,信任機制有幾個重要的特點:其一,人際互動的范圍狹窄,一般只限于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熟人社會里。其二,信任產生自然是以血緣、親緣或者是擴展的親緣關系為基礎。所謂擴展的親緣關系是指人們把熟人關系或者是朋友的關系一并納入親緣的范疇。例如,中國人把朋友稱呼為“兄弟”便有此意。其三,信任關系的約束以內在的倫理觀為主,外在約束(法律法規)為輔。所以傳統的社會又被稱為禮俗社會。然而。在中國導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發生了急劇轉型,信任的基礎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信任的影響也自然凸顯出來。我們從社會轉型的框架中,大致看到了對中國當下信任影響的必然性。然而,要細究其中影響路徑,我們尚需要清楚與農耕社會比較,中國社會轉型中都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社會轉型是伴隨工業化、城市化而來,因而首要的變化便是主體間的互動范圍的擴展,即從熟人社會擴展到了陌生人社會。這一變化構成了當下中國信任問題的“導火索”。從中我們看到,互動范圍從熟人群體轉移到陌生人群體的時候,互動所產生信任的基礎實際上已經部分地被消解了。熟人社會的倫理本位在陌生交往群體中無法構成共同的基礎,這樣內在約束所引發的懲罰機制也形同虛設。另外,從熟人擴展到陌生人交往群體本身,實質上也同步削弱了人們對內在機制的懲罰規則遵從,使得(互動中)一次性“博弈”中違背規則的可能性加大,其后果必然使得信任難以維續而產生信任危機。社會轉型期的第二個重要的影響是觀念滯后于現實。這個事實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西方其他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也出現過。從理論上而言,面對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新問題,我們的法律法規還沒有來得及改變以應付這樣的問題。基于此,我們通常斷言,信任產生的重要基礎之一的外在約束規則沒有建立起來,可能構成中國當下信任危機的另一原因。這一觀點既合乎邏輯也與許多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但我認為,在中國的情況可能并非完全如此。根據實際情況出臺或修改法律法規的數量和頻率,中國可能是處于世界前列。特別是地方法規的出臺更是“神速”,因為沒有那么多民主程序的制約,憑官員“拍腦袋”便可制定出新規。如此高的頻率出臺規定以應付新出現的事物,故而規定的“滯后性”所造成的影響應該很小。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即中國不缺少法律法規,而是有法律法規而不遵守的問題(翟學偉,2004)。換句話說,社會轉型一方面使得構成信任基礎的內在價值觀不適用于陌生群體的交往,另一方面法律法規的約束力也并未比傳統社會有所增強。兩個原因結合起來,并導致人際間的信任缺失和信任難以維續問題,即中國當下的信任危機。
社會轉型帶來人口流動性增強,強化了人際互動中選擇一次性博弈違背約束的可能性,進而影響信任生成與維續。那么,對于一種長久交往下去的互動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換句話說,對于那些流動頻率非常低的人,會選擇怎樣的策略來建立和維持互動中的信任呢?我認為會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在群體成員可以選擇的情況下,行動者會選擇熟人社會中有血緣、親緣、地緣關系的人作為成員。例如,農民工外出務工群體,往往以親緣或地緣(老鄉)結伴而行,并在駐地形成小團體,這時候信任的聯結基礎是牢固的。另一種可能是。在互動成員不能選擇的情況下,努力建構一種“準親緣關系”(或者說擴展了的親緣關系),內在約束規則也便依照原有的親緣價值觀來建立并很快取得認同。中國人所謂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便是證據。換句話說,行動者在人際頻繁互動中,一旦不能成功地建立起這種準親緣關系網絡,便無法建立新的信任基礎,從而使得人際互動和交往變得異常困難。限于篇幅,此處不再展開討論。簡而言之,在頻繁交往的群體中,信任建立的基礎再次退回到熟人社會所建立的價值倫理上來。
五、對案例的再思考
對具體案例進行再分析之前,尚需要解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文中開始部分所提出來的人際信任和系統信任的問題。之所以在此處要對這兩個信任予以討論是因為,其一,厘清二者的關系便于案例分析,其二是兩個信任并不完全相同。人際信任機制問題,前文已經詳細討論過,此處不再贅述,本部分只對系統信任予以分析。我從狹義上把個人對社會制度系統的信任稱之為系統信任,它與個人或群體的信任是有區別的。其區別主要在于:制度系統自身便構成了信任的重要前提。它由規則構成,為行動者提供信息,是行動的基礎,同時也對行動者起到型塑作用。個人之所以信任制度系統,是因為制度系統對任何個體都將具有一致性。“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對此最好的解讀。然而,一旦制度系統因人而異時,便使得制度系統本身的約束力下降,同時使得人們對制度系統信任度降低,這便形成了系統危機。如果要細究制度系統為何會因人而異時,我認為“中國人的關系觀”在其中起著關鍵的作用。中國人的關系觀和臉面觀往往使得制度系統的約束力形同虛設,從而就形成了翟學偉教授所說的,在你沒有“關系”的時候,制度就具有效力,而當你有“關系”時,制度對你就形同虛設。久而久之,制度系統不僅在體制外成員中的公信力下降,而且體制內的人(規則的運作者)也不能相信制度能夠給他帶來“長治久安”,因而制度信任危機帶來的社會后果具有普遍性。回到“富人海外移民熱”的案例中來,我們看到富人紛紛移居海外,目的何在?富人不夠愛國嗎?顯然都不是問題的答案。真實的原因可能是來自于他們對制度系統不夠信任,他們不信任制度系統能保證其財產私有權“不可逾越”,甚至還有可能如其他評論者所說的,富人可能更擔憂通過直接或間接操控制度所獲得的財富,會在未來制度系統“不穩定”時遭遇風險。如果說“富人海外移民熱”不足以說明是制度系統危機所致,那么中國人在海外豪購國貨的行為便使得國人對制度系統的信任危機暴露無疑。在同一個國度生產同樣的物品,在國外市場上不但沒有贗品,而且價格低廉。我們且不去討論涉及市場定價問題的國際市場賣價低的原因,那么國內市場充斥贗品,應該作何解釋?如果說制度系統能“一視同仁”地把出口貨和內銷物品同等看待,還會有國內市場充斥贗品的事情發生嗎?無論是“富人海外移民熱”還是“國外豪購國貨”行為,實際都是發生在中國的富人階層,或者至少是中國的中產階層。如果說他們因深諳社會體制系統運作之道,而采取的一種規避風險的策略行為,那么普通老百姓“搶鹽事件”又說明什么呢?顯然不是老百姓的“愚”,它折射出來的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缺失,“搶鹽”是一種無奈之舉。“安全感缺失”背后顯然還是對體制系統的不信任。如果他們相信體制有足夠的能力來保證他們的生存權,他們是不會作出這等近乎愚昧的瘋狂之舉。所幸的是中國政府部分及時告知真相并采取行動,才使得事態不曾擴大。
概而言之,當前中國人的許多異常行為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本身可能多少會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但其背后所隱含的許多社會必然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這些個案所折射出來的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便是其中之一,中國目前正處于向工業化、城市化轉型的重要時期,如何引導人們在互動中重獲信任的“陽光和雨露”,將是社會和諧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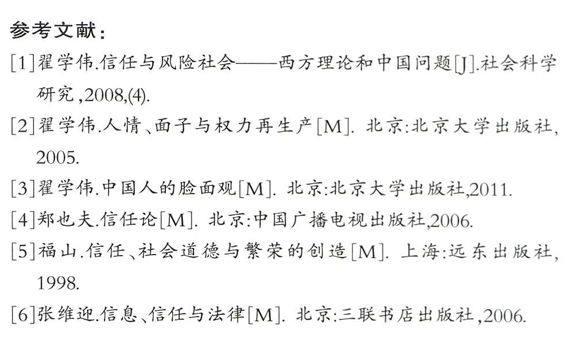
責任編輯楊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