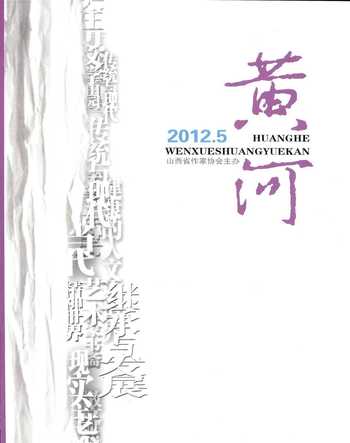讀宋雜錄六則
蔡潤田
避諱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種特別的風俗,即在民國之前,凡書寫或言說都要避免直接寫出或說出君父尊親的名字,必須用到相關文字時,則以同音或同義字替本字,或者用原字而省缺筆畫以避之,是為“避諱”。據說,其俗始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就中,對于孔子及當代帝王之名眾所共諱,稱公諱。人之避父祖之名,則稱家諱。
在宋之問詩文中看到屬于“公諱”的有:
(一)“代業京華里,遠投魑魅鄉”(見《全唐詩》第一函第十冊宋之問卷;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下同)。此聯見于《桂州三月三》詩中。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世”為“代”。“世業”,世代相傳的事業。如《資治通鑒》卷五十六:“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之問這一聯說,本來世世代代都在京城做事,可如今自己卻被貶到這常有山神水怪出沒的邊遠荒涼之地。
(二)“賢相稱邦杰,清流舉代推”。此聯見于《范陽王挽詞二首(其一)》。“舉代”:舉世,整個人世,普天下。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舉世混濁,而我獨清。”此處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世”為“代”。這一聯,之問稱贊追贈為相的范陽王是國中英杰,其德行高潔負有名望,受到天下人的推崇。
(三)“昔者巨浸橫流,下人交喪”。此句見于《祭禹廟文》。“下人”:即下民,百姓,人民。如《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此處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改“民”為“人”。這句話意思是:以前大水泛濫成災,老百姓處處遭殃。
(四)宋之問有些詩是奉武后(曾自立為武周皇帝)和中宗之命寫的,這些詩的題目都綴以“應制”二字。如《幸少林寺應制》、《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等。
這“制”字就是避武后名字“曌”的。皇帝命令,稱詔或制。因為武則天,名武曌(音zhao,同照,武則天為自己造的字。另據《資治通鑒》卷二0四記載:為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為武則天選的字,意指日月當空),“詔”與“曌”同音,武則天規定只能用“制”。奉皇帝命寫詩不說“應詔”而說“應制”。施蟄存先生說:“‘應詔和‘應制本來沒有區別,但武則天規定用‘制字,不用‘詔字,故武后以后都用‘應制而不用‘應詔。”(《唐詩百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關于避諱,歷史上施行情況并不完全一致。據我有限的閱覽,制約施行的大抵有三種因素:一曰禮制(定式);二曰法令;三曰習尚。就禮制層面說,《禮記·曲禮上》:“二名不偏諱。”鄭玄注:“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作為一種禮制規定,凡兩個字都與尊親相同的名字,只選擇其中一個字予以避諱就行了。不必兩個字都一一避諱。但這種禮制實際上大都未能實行,實際通行的是“偏諱”,即每個字都避諱。甚至法令都無濟于事。
《舊唐書·太宗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并不須諱。”唐太宗意識到因“避諱”給人們閱讀典籍帶來的麻煩和混亂,剛登上皇位就立下這個法令,并進而指出“世民兩字不連續者,并不須諱”,看來很開明。“據此,唐以前兩字兼避,已成風俗,至太宗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時二名仍偏諱。《日知錄》廿三謂‘高宗永徽初,已改民部為戶部,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閆若璩謂太原晉祠有唐太宗御制碑,碑陰載當時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勣,已去世字。是唐太宗時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陳垣《史諱舉例》第四十四)這里,顧炎武說太原考據家閆若璩已發現在太原晉祠,太宗自己立的碑就對自己的名字施行 “避諱”了,這與他“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并不須諱”的政令顯然自相矛盾、有些出爾反爾。“可見,法令為一事,習尚又為一事也。”(陳垣《史諱舉例》第七十六)
按陳垣先生舉“唐諱例”,其中:
太宗高祖子世民 世改為代,或為系,從世之字改從云,或改從曳。民改為人,或甿,從民之字改從氏。
……
武后曌詔改為制,李重照改重潤。(筆者按:李重潤為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之孫,唐中宗李顯和韋皇后長子)(陳垣《史諱舉例》第七十六)
太宗當初出于保護文化典籍的考慮,為避免典籍“廢闕”(缺漏),免生“訛異”,詔令“二名不偏諱”,但自己就施行不力,別人依然我行我素,照樣“避諱”。究其原因,想來,這畢竟是維護皇家面子的事,令是下了,雖不是作秀,也不必太認真的。所以,“避諱”者自不會追究責任。而不“避諱”者,也順理成章,無可非議。
大概就是這模棱兩可的原因吧,宋之問有時避諱有時不避諱。在《始安秋日》詩中有句云:“世業事黃老,妙年孤隱淪。”這里說世代都崇尚黃老之學,自己年輕時候獨自過著隱逸生活。其間,卻沒有避這個“世”字。宋之問因為再度遭貶有意犯諱、以發泄對李唐宗室的不滿嗎?以之問的畏縮,諒他不敢。只是避與不避當時并非大問題,也不會招致禍患的。事實正是如此。太宗李世民自己也是有時避諱,有時不避諱的。他在李世勣的名字上施行“避諱”,在虞世南的名字上就沒“避諱”。在他的詔書中稱“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所以,后唐明宗李嗣源說太宗“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臣南,官有‘民部(按高宗時改為‘戶部)靡聞曲諱,止禁連呼”(參見《日知錄》卷二十三)。“據此,則唐時諱法,制令甚寬。……非如宋之淳熙文書令,廣避嫌名;清之乾隆字貫案,罪至梟首也。”(《史諱舉例》第七十六)看來各朝諱法寬嚴不一,唐代比宋、清寬得多了。
才子、才子氣
同一題材在不同作者筆下,往往會呈現出不同的思想格調,這種情況在一些古代同題詩中時有所見。讀宋之問的《息夫人》一詩,聯想到杜牧、袁枚有關吟詠息夫人的詩作,就有這種感受。尤其是三人同為才子型詩人,其詩作韻味何以大異其趣,個中緣由值得玩味。
息夫人 (即息媯),春秋時息國國君夫人,又稱桃花夫人。據《左傳·莊公十四年》載:因蔡哀侯向楚王稱贊了息夫人的美貌,導致楚王興師滅息。息夫人被擄進楚宮,后來生二子,即堵敖與成王。但她郁郁寡歡,始終不說話。楚王追問其故,她道答:“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又《烈女傳》卷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其妻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
息夫人的不幸遭際及她無言的抗議,在舊時一向被傳為美談。唐時還有祭祀她的“桃花夫人廟”。后人多有詠息夫人的詩文,就我有限的閱讀,除以上三位才子之外,還有唐王維《息夫人》,劉長卿《過桃花夫人廟》,羅隱《息夫人廟》,宋錢惟演《無題三首(其一)》;清鄧孝威《題息夫人廟》,洪亮吉《題息夫人廟》,孫廷銓《詠息夫人》。
這里,僅就上述三才子的詩略事申說,看該如何評價它們的高下優劣。而這,恐怕首先須有個評判標準問題。然而,文無定法,筆無極詣,詩無達詁。繩墨法度是很難確定的。不過,以愚之見,大略說來,詩文高下,就主觀條件講,至少有兩條:一為器識涵養,一為才氣性情。二者孰闕孰贍,其作品便會有或深或淺、或文或質、或淳或漓的差殊。
有關息夫人的這個歷史故實,宋之問、杜牧、袁枚雖都賦詩題詠,卻也因器識、才情的秉持不同,所表現的情感、境界自又不同。
宋之問《息夫人》:
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
仍為泉下骨,不作楚王嬪。
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
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
宋之問《息夫人》全用《列女傳》之說。之問系初唐才子,一向媚附權貴,品行無足稱道。但對息夫人的吟詠,筆調看似平淡,卻也寄寓著深切同情。并無逞才使氣、乖情悖理之嫌。其識見可謂公允,氣度不失淳厚。
杜牧、袁枚的詩都典出《左傳》。
杜牧《題桃花夫人廟》云:
細腰宮里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
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細腰宮”即“楚宮”,是根據“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傳說翻造的。這一句間接指斥楚王的荒淫。“金谷”,即金谷園,乃晉代豪富石崇的名園。石崇有樂妓綠珠,權貴孫秀求綠珠不得,遂矯詔收崇下獄。石崇臨捕時對綠珠嘆道:“我今為爾得罪。”綠珠回答:“當效死于君前”,遂墜樓而死。這首詩,以綠珠之死而反襯息夫人之不死,自是意有褒貶。不過在字面上卻還不露痕跡。清趙翼《甌北詩話》說:“以綠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刺,尤得風人之旨耳。”寓褒貶于無形,寫得辭微旨婉。這是杜牧的妙處。但是“至竟息亡緣底事?”這一詰問與下句互文,弦外之音是說,息亡是因為息夫人的美色,這就不足為訓。到底息亡是因為什么?說穿了,是因為楚國的強暴,息國的軟弱。美貌,又何罪之有!詩藝、才情為識見所累,于此可見一斑。傅庚生先生說:“牧之矜才,往往失于輕佻。輕佻則意淺,意淺則瀕于漓薄矣”(《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雅鄭與淳漓》)。
現在來看清袁枚《詠綠珠》言及息夫人的詩句:
人生一死談何易,看得分明勝丈夫。
猶記息姬歸楚日,下樓還要侍兒扶。
這詩仿佛演繹杜牧詩意而來。前兩句盛贊綠珠殉節不必說了,后面描摹、嘲諷息夫人的兩句,命意、見識自不能與宋之問的詩意淳厚相比。單就藝術表現而言,也不如杜牧的含蓄蘊藉。
袁枚無疑是一大才子。向來才子型的文人大都風發凌厲、心裁別出。鑒于前人對息姬多所同情的態度和杜牧寓諷于婉的詩藝,袁枚自是不甘落入前人窠臼。于是,求新求異,便懸擬出息姬“下樓還要侍兒扶”的矯柔造作之態,從而,極盡揶揄之能事。其筆意不可謂不尖新。然而,生二千載下,以如此尖刻的筆調嘲諷一介“生時蒙辱,死后赍恨”的弱女子,實在有失公允而未免澆薄了。
袁枚《雁宕山卓筆峰》詩云:“孤峰卓立久離塵,四面風雪自有神,絕峙通天一枝筆,請看依傍是何人!”此詩看似狀寫山峰,實為自況。卓然不群,絕少依傍,確是才子文人的可貴處。但,逞才過甚,失去蓄勢,就會顯出才子們的負面氣息——浮薄與詭異。袁枚詠息夫人詩就有此病。錢鐘書先生說:袁枚“論東坡語較平允,然‘有才無情、多趣少韻適可自評。”談到袁枚批評 “東坡、山谷俱少情韻。藏園、歐北兩才子詩斗險爭新”時,錢先生說他“蓋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亦拙。”(《談藝錄(六二)》)
袁枚愛“斗險爭新”,貫以浮薄小慧自圣,另有佐證。《隨園詩話》云:“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日:‘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固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囅然。”乍聽,這話確乎雄辯,不能不為袁枚機敏的辯才所折服。然而細味其旨,就覺得很可疑,難道為了“后世之名”就可以將自己的身價系乎一妓女的名下,借以標榜嗎?境界如此,實在不好恭維。雖出語新異,小巧小慧而已(參見《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雅鄭與淳漓》)。
對這位才氣橫溢的大才子,筆者絕無全盤否定之意。限于識見,這里只是就事論事,覺得他矜才、尚奇,有時就“聰明反被聰明誤”了。至于他文學上的總體成就和影響,豈敢妄贊一辭!
作為對三位才子同題詩(按指題材相近)及相關議論的一則讀書筆記,本文不過是想說明這樣一點意思,即文人的長處、短處相伏相倚;才情、器識不可偏廢。有學有識,無才無情,不免腐儒氣;饒于才情,乏乎識見,又難免才子氣;而才、識俱無,就只有俗人氣了。腐儒氣不好,俗人氣尤其要不得。才子氣呢?看來亦未必佳。清代詞學家陳延焯《自雨齋詞話》有云:“無論作詩作詞,不可有腐儒氣,不可有俗人氣,不可有才子氣。人第知腐儒氣、俗人氣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尖巧新穎,病在輕薄;發揮暴露,病在淺盡。腐儒氣,俗人氣,人猶望而厭之;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故得病最深。”
宋之問、杜牧、袁枚同為才子,然而,由于在同一問題上所顯示的器識不同,其詩其人的境界就大有差殊,就這一點說,宋之問淳厚,雖系才子而無才子氣;杜牧略顯刻薄,等而下之;袁枚逞才使性,尖刻漓薄,而盡顯才子氣,“得病最深”。
逍遙不是適性
“愿與道林近,在意逍遙篇。”這是宋之問在越州長史任上所作《湖中別鑒上人》一詩中的開頭兩句。此處之問以支遁(道林)喻越州的鑒上人(僧人)。意思是說愿意與像支道林這樣的高僧過從,領略逍遙的真諦。這里,之問把道林與逍遙篇并提,其實是在推崇道林,說自己賞識道林對莊子《逍遙游》的釋義。
關于道林其人,據記載,支遁,字道林。東晉高僧、名士。世稱支公,也稱林公,本姓關。陳留(今河南開封市)人,或說河東林慮(今河南林縣)人。約生于晉愍帝建興二年(公元314年),卒于廢帝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享年五十三歲。他初隱余杭山,二十五歲出家,他雖為釋氏而于“章句或有所遺”。當時名流謝安、王羲之都與支遁過從甚密。后于剡縣(今浙江省嵊縣)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余、常隨稟學”。晉哀帝時應詔進京,居東安寺講道,三年后回剡而卒(參見《高僧傳》卷四)。他精通佛理,有多種佛學著作。好談玄理,注《莊子·逍遙游》。但著述大都亡佚。筆者所見有限,其生平、學說主要保留在《高僧傳》、《大小品對比要抄序》、《莊子集釋》和《世說新語》中。尤其后者,劉義慶直接說到與劉孝標注中提到支遁處加起來有五十多處。
宋之問為什么“在意《逍遙》篇”,在諸多注釋莊子的著作中如此看重支遁對莊子《逍遙游》的注釋呢?其釋義有何新穎獨到之處?
支遁的注已佚。關于逍遙的釋義無從窺其全豹,人們大抵只能從上述有關著述中勾稽其要旨。但有一點,是明白的,即他為《逍遙游》作注的動機是因為不滿于西晉向秀(公元227年——280年)和郭象(公元253年——312年)的《莊子注》中的逍遙義。在表示不滿的同時也直接道出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逍遙不是適性。
向、郭都是魏晉玄學發展中的重要人物。向秀有《難養生論》(與嵇康《養生論》的辯難文)、《思舊賦》(憑吊舊友嵇康文)傳世,郭象有《莊子注》傳世。
《世說新語·文學》三十二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鉆味,而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于二家之表,立異義于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二百二十頁)這是說《莊子·逍遙游》向來就是個難以詮釋的課題。眾賢達名士所能鉆研體味到的意蘊都不能超出向秀、郭象兩家的義理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與人談及《逍遙游》,竟別具只眼,超越向、郭,其闡發的新意都是此前一些名流所不曾領略到的。所以,后來人們在解說莊子《逍遙游》時便都采納了支遁所闡發的義理。
那么,郭象與支遁對《逍遙游》各有怎樣的解釋,二者有何不同?“支理”何以受到追捧?筆者不學,決非這篇札記能道其詳。不過,撮要言之,或許可以透過如下記載窺其梗概。
《世說新語·文學》三十二劉孝標注曰:“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茍當其分,逍遙一也。”(《世說新語簽疏》第二百二十頁)
向、郭認為,大鵬高飛九萬尺,尺鷃只低飛于榆木檀木之間,雖有大小的差別,但是都能各自縱任其本性。如果都正好適合各自的性分,則逍遙是一樣的。郭象對《逍遙游》的題解說得更明白:“夫大小雖殊,而放于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其間哉!”(《莊子集釋·逍遙游第一》見世界書局印行《諸子集成》)這里,郭象強調只要“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就是了,至于大鳥小鳥,是勝是輸就不必“曲與生說”了。所以說“茍足于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余矣。”(同上)“照郭象看,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以‘自性為根據,……所以事物‘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就這點看,……‘安命就是‘順性。”(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二百八十三頁)易言之,適性亦即逍遙。
然而,支遁并不這樣認為。南朝梁代慧皎《高僧傳》卷四《支遁傳》:“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按:此人名與《世說新語》所記不同,或許當時二人都在場,二書所記各有側重)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于是退而注《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嘆服。”
關于桀跖,一說桀跖即夏桀和柳下跖的并稱。泛指兇惡殘暴的人。《荀子·榮辱》:“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淮南子·說山訓》:“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貍,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一說桀跖,又名柳下跖,原名展雄,相傳是當時賢臣柳下惠的弟弟,為魯孝公的兒子公子展的后裔,因以展為姓。系戰國、春秋之際奴隸起義領袖。在先秦古籍中被誣為“盜跖”和“桀跖”。
這里,支遁因襲舊說,以桀跖為邪惡。說桀跖那樣兇惡殘暴的人他們也是適性而為的,難道也算是逍遙嗎!所以他說:“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游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于糗糧,絕觴爵于醪醴哉?茍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世說新語簽疏》第二百二十頁。并見于《莊子集釋》)
這里,支遁在《逍遙論》中說,所謂逍遙,是講“至人”的精神狀態。莊子闡發這方面的大道理,而以大鵬與尺鶠的寓言來說明。大鵬生活的范圍遼闊廣大,所以在身體之外無所謂適應與否的問題;尺鷃生活在低近處而嗤笑在高遠處的大鵬,是由于內心的驕傲。“至人”隨順萬物的本性并且有很高的興味,游歷無窮而不受約束,駕馭萬物而不執著于萬物。這樣就可以悠然而不會心為物役,迷惑不會產生,達到不疾而速,優游自得而無所不適。這就是逍遙的境界。如果人所有的欲望都與所能得到的相當,并滿足于所能得到的欲望,快樂得有似天然本性,這就如同饑餓的人得到一頓飽餐,口渴的人得到一次痛飲一樣,豈不是有點干糧就忘掉了豐盛的祭品,有了口水喝就拒絕了濃醇的美酒嗎?如果不是最高境界的滿足,難道可稱其為逍遙嗎?
支遁在此明確提出:所謂“逍遙”,是“至人”的精神狀態。并不是任何人所有的精神狀態都可以稱為逍遙的;這種逍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至高境界的“至足”;并不是“有欲當其所足”的“茍足”, 即并不是不管什么欲望,得到滿足就是逍遙。“此向、郭之注所未盡。”(同上)是直接針對向、郭“各適性以為逍遙”的。
陳寅恪先生說:“郭象舊義原出于人倫鑒識之才性論。故以‘事呈其能及‘極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適為言。林公窺見其隱,乃舉桀跖性惡之例,以破大小適性之說。然則其人‘才藻新奇,神悟機發(世說新語品藻類郗嘉賓問謝太傅條注引支遁傳),實超絕同時之流輩。”(《逍遙游向郭義及支遁義探源》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89頁)
無怪乎宋之問“愿與道林近,在意逍遙篇”了。
不向俗人說
宋之問在武后當政初期,曾寫過一首騷體詩(或曰樂府詩),題為《冬宵引贈司馬承禎》。詩曰:
河有冰兮山有雪,
北戶墐(以泥涂塞)兮行人絕。
獨坐山中兮對松月,
懷美人(友人)兮屢盈缺。
明月的的寒潭中,
青松幽幽吟徑風。
此情不向俗人說,
愛而不見恨無窮。
這首詩是寫給他的好友司馬承禎的。之問早年向道,寓居嵩山時,與司馬承禎同師事道士潘師正。與司馬也可謂師兄弟了。大約后來兩人不在一處,見面的機會很少吧,之問寫了這首景色清幽、情感深摯的懷人詩。詩意大體明白,無須辭費。就中,我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句:“此情不向俗人說”。這“不向俗人說”頗耐尋味。于之問,何為“俗人”?在他人,通常指什么人?對此,我想就見聞所及,迻錄如左,略事申說。拉拉雜雜,不過是些所謂“獺祭”“叢脞”之類的雜碎堆積而已。
首先,說到俗人,須先釋“俗”。《釋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至于“俗人”,通常似乎釋義如下:
1.庸俗的人;低俗的人。《荀子·儒效》:“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
2.一般人,普通人;百姓,民眾。《老子》:“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3.佛教、道教指未出家的世俗之人,與出家人相對。東晉法顯《佛國記》:“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 宋代洪邁《夷堅甲志·僧為人女》:“汝為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惓惓,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為董氏子矣。”魯迅《華蓋集題記》:“在和尚是好運……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
以上,是對俗人的三種釋義。但從佛、道觀點看,教里教外,出處有別,和尚、道士而外,不論雅士抑或凡夫,百姓抑或宰相,都是俗人。即是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出家人和俗人兩種人。但實際上,“俗”不特與佛、道,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在儒學傳統中亦與“雅”相對。《周禮·天官》:“不雅曰俗”。職此,推及社會人群,俗人而外,也便有雅人。而雅、俗則構成價值判斷,意有褒貶,是可軒輊的。而且,單就雅和俗來說,雅有高雅、典雅、儒雅、俊雅、清雅、優雅、和雅、大雅等種種人,似乎各有特征、卻無高下,大抵都含褒義。俗則不然,凡俗、流俗、低俗、粗俗、庸俗、鄙俗、惡俗等層次中人,不惟彼此有程度、性質的不同,大凡曰“俗”,都含不同程度的貶義。惟其如此,歷史上,不論文人雅士還是仕宦中人,賢與不肖,只要稱他者為“俗人”,一般都有清高自重、不屑為伍的意味。賢達、名士、才子、士大夫者流有這個派頭,一些勢利小人也以此自圣。正因為這樣,這“不向俗人說”出自不同人之口,或自重,或自詡,或刺人,或諷世,或揚己抑人甚至榮己而辱人,其意味是不盡相同的。
就宋之問來說,詩中言說的對象為道士司馬承禎,俗人當泛指未出家修行的普通人。但普通人與道士價值取向、生存方式或有不同,卻難以抑揚褒貶。而且之問詩中所勾勒的情境無關道家宏旨,常人可以領略。不必強調只對道士司馬,不向普通人說。所以,這里“不向俗人說”之“俗人”,就不是一般普通人,而是帶有不屑與譚的貶義了。但是,之問何人?在武后和中宗朝,他本可以憑自己的非凡才具,有個安定而榮耀的生活和身份的。他卻名利熏心,附炎趨勢,夤緣幸進,甚至給武則天的嬖臣“捧溺器”,行徑如此鄙俗,也還要大言“不向俗人說”,這就嫌矯情,有些崇己而抑人的味道,也多少有點才子氣的張狂。而且效仿雅人口吻,也別有作秀和“無疾而顰”的嫌疑。
同樣的話,出自另外一些人之口,就覺得信實而得體的多了。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說自己遭受宮刑還忍辱負重寫作《史記》。這番苦衷,只能說給富于超越意識的具有大智慧的人,一般世俗之人是不可理解的。這里,固然有自尊,也未始沒有刺人或憤世嫉俗的意味。想到司馬遷的身世、遭際,這話就不為夸飾。
有些人并非出于“孤憤”,毋寧說是自重自賞,自標高潔,也說這樣的話。黃庭堅《寄題安福李令愛竹堂》:“淵明喜種菊,子猷喜種竹,托物雖自殊,心期俱不俗,……富貴于我如浮云,安可一日無此君。人言愛竹有何好,此中難為俗人道”。在《書贈俞清老》中還說:“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這里的“難為俗人言”云云,是談他與李令、俞清老在脫俗境界方面的會心、相得,是自尊自賞,自標高潔。其間,惟以俗人襯托自己之雅潔,未必措意于貶抑。俗人猶言普通人。又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瓠子河》:“ 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側城南注。”這里俗人亦即百姓,就純粹是個中性概念了。
自然,也有言及“俗人”而帶貶義或略作針砭,謂其低俗或庸俗的。《后漢書·張衡傳》:“(衡)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紅樓夢》第三二回:“寶玉道:‘罷!罷!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并不愿和這些人來往。”魯迅 《南腔北調集·論翻印木刻》:“中國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說不出他以為好的畫的內容來,俗人卻非問內容不可。”
不消說,稱他人為“俗”,有話“不向俗人說”者,至少須自身先得避免俗氣,須不俗或脫俗。而要脫俗,就得旨趣淡泊一些,別汲汲于功名利祿,別太在乎世俗價值。“于世俗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黃庭堅《書枯木道士賦后》贊李長倩)。這說來容易,做到卻不易。尤其如我儕血肉之軀、凡夫俗子是很難脫盡俗人味的。但難歸難,還是應在俗世中力求少些俗人氣。渾渾噩噩,完全隨流從俗是可怕的。黃庭堅云:“士生于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書嵇叔夜詩與侄榎》)蘇軾《于潛僧綠筠軒》亦云:“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人生活的雅致不容易。跌入“欲壑”,俗起來就很難收拾。
不過,俗與不俗,重在內心修養,并非刻意或時時掛在臉上。有人問黃庭堅“不俗”該是什么樣子(“或問不俗之狀”)黃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書嵇叔夜詩與侄榎》)不俗的人日常生活與普通人沒有什么不同,在面臨重大考驗的關鍵時刻志向就顯出來了。士人在生活中超脫還是入世,剛強還是柔順,僅憑一次關乎大節的行為是很難全看清楚的,但他的俗與不俗都以這一事關“大節” 中的表現來裁斷。黃庭堅認為平素可以同世人和光同塵,重要的是要有不俗的內在心志。“俗里光塵合,胸中涇渭分”(《次韻答王慎中》)。這與老子“常寬于物,不削于人”的涵容心態,與莊子超脫恣縱又不睥睨萬物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莊子·天下》有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于萬物,不譴(拘泥)是非,以與世俗處。”生活中的道家,如何行藏出處、待人接物,庶乎可知大概了。
雅俗問題多半已成為歷史話題。古今異勢,觀念異趣。如今,日常生活中,俗與不俗已界限模糊,很難判斷。對此,有所軒輊已屬不易,若再求雅,更近諷刺了。
猿、猿聲
讀宋之問的詩,看到若干詠猿或猿聲的詩句。頗也引起我的一些聯想。
這里,不妨先對猿這種動物略事申說。
2010年秋,筆者曾到黃河沿岸的垣曲縣境游覽。在該縣參觀有關猿的新發現的展覽。據云:1994年,中美科學家來到山西省垣曲縣考察。在這里,曾發現了中國科學史上第一塊始新世哺乳動物化石。1995年5月,他們在黃河北岸寨里時,發現了眾多的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靈長類動物特征的猿類化石,主要是牙齒化石和頜骨化石,并且命名為“世紀曙猿”。另據考證,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萬年以前。專家認為,世紀曙猿的發現,推翻了人類起源于非洲的論斷,并且把類人猿出現的時間向前推進了1000萬年。
參觀了垣曲博物館 “世紀曙猿”遺址的介紹,似乎使我對這種動物感受更直接、深切。不過,筆者對猿感興趣倒不在其起源,而是勾起我對猿的“文學形象”、尤其是對古代詩歌中“猿”的意象的聯想。
在動物學意義上,猿為哺乳動物,是靈長目動物的總稱。這種動物在我國文化典籍中多有記載。我國古代字書中對這種動物的相關闡釋大致是這樣的:
《爾雅·釋獸》:“猱猿擅援”。郝懿行《爾雅義疏》引《玉篇》:“猿似獼猴而大,能嘯。”郝又云:“按陸機以長臂為猨”。《說文》:“蝯善援,禺屬。”按:經查,蝯、猨、猿。一字異體。“蝯”較古,“猨”、“猿”是晚近出的俗字。
有關典故,如:
貉逾汶則死。——《考工記·總目》。注:“貉或為猨。謂善緣木之猨也。”
毋教猱升木。——《詩·小雅·角弓》。傳:“猱,猨屬。”
猿狙之便自山林來。——《莊子·天地》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戰國策》
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漢·董仲舒《春秋繁露》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的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里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按即“斷腸猿”)。——《世說新語·黜免》
又如:猿猴獻果(指將人的四肢在胸前捆在一起的姿勢;京劇《謝瑤環》來俊臣的酷刑中即有此一招兒)猿狖(猿猴);猿眩(猿臨懸崖而目眩。極言險峻);猿臂(臂長如猿,運用自如,亦比喻攻守自如的作戰形勢)等。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猿”常出現在古代詩人的筆下,尤以“猿聲”見著。我在讀宋之問詩作時,發現至少有如下幾處:
猿躩時能嘯,鳶飛莫敢鳴。(《入瀧州江》)
沓障連夜猿,平沙覆陽雁。(《自湘源之潭州衡山縣》)
破顏看鵲喜,拭淚聽猿啼。(《發端州出入西江》)
泛舟依雁渚,投館聽猿鳴。(《發滕州》)
鳥游溪寂寂,猿嘯嶺娟娟。(《下桂州龍目灘》)
猿飲排虛上,禽驚掠水飛。(《早入清遠系》)。
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宿清遠峽山寺》)
其實,不自初唐始。魏晉南北朝以來,就有詠“猿”的詩歌。(而詠巫山猿的似乎更多。可能此地多猿)如: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引漁歌。
在唐代,人們耳熟能詳的,如: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早發白帝城》
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里長。——王昌齡《送魏二》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劉長卿《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杜甫《登高》
為什么古代詩人詩作多“猿聲”,以致成為古典詩歌特有意象呢?縱觀這些詩文作品,恐怕與猿在典籍中所記載的特性分不開的。其一,作為人類的祖先,與人類有密切的親緣關系。其智能、靈性有相通相近處,故以猿鳴喻人情。其二、猿擅嘯、聲哀。叫聲凄切,悲涼凄清,象征憂愁幽思。《山海經·南山經》載:“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校木,多白猿。”(“發爽之山多白猿”)晉郭璞注:“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嗚,其聲哀。” 《水經注》在記述三峽時引用《荊州記》等地記所載,曾先后三次提到了三峽的猿:“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也”,“此峽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凄異。”詩中之“猿”,大都取“有靈性”與“其聲哀”“凄異”這兩層意思。劉鶚說:“猿猴之為物,跳擲于深林,厭飽乎梨栗,至逸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有靈性也。”(《老殘游記·自敘》)就此,猿的叫聲,成了古代詩人們表達悲哀、傷感的特有意象。這是與今人的感受和表達方式所不同的。當然,也有例外。李白《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則突破以前詠猿時的哀愁、悲傷的氛圍,將歡悅的心緒和浪漫的情凋融入三峽兩岸不斷啼叫的猿聲之中。成為三峽詠猿詩的另類經典之作,傳誦千古。再則,若非與鳴聲連屬,單獨用“猿”字,則可能別有意涵,如宋之問如上的“看心欲定猿”,其“猿”字蓋謂人心邪僻,有貶義。《維摩詰經·香基佛品》:“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法制御其心,乃可調服。”之問此句,意即在此,與表達傷感無關。
緣何樂道王子喬
在唐才子“西河(今山西汾陽)宋之問”的詩作中多所道及王子喬。那么王子喬哪路神仙?何許人也?據《列仙傳》和《歷世真仙體道通鑒》載:王子喬,周靈王(公元前571——前545在位)太子,字子晉,或名晉,字子喬。幼好道,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今河南境內)之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修煉三十年后受書“桐柏真人”。一天,對山中的柏良說:“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在河南)山巔。”果然,那天他乘白鶴落在山嶺上,人們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他“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列仙傳》說人們為他在嵩高山立了祠廟。并有贊詞云:“妙哉王子,神游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宋之問何以對這樣一個由人而神的仙人津津樂道呢?
據史書記載,宋之問青年時代師事著名道士潘師正,與其弟子司馬承禎、韓法昭及隱士田游巖等交游,出入道觀,日后詩文中屢屢提及神仙類人物,容或有其道家人物熏染和信仰問題。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簡單,言在此,意在彼, 詩中的“王子喬”是別有所指的。題為《王子喬》的詩作其旨趣就是如此。
且看其詩《王子喬》——或曰長短句:“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騎云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人衣。”
那么,這首詩究竟為誰而作,是何背景?《資治通鑒》卷二0六記載這樣一件事:久視元年(公元700年)六月,武則天“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昌宗飲博嘲謔。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原來,宋之問是以王子喬比擬、美化張昌宗呢。這里的 “諸武”即武則天侄子武三思、武承嗣等武氏宗親。張昌宗何許也?之問何以要如此美化此人呢?現在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被武后寵愛,被武、宋追捧的神秘人物吧。
據有關記載,張昌宗,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由武后女兒太平公主推薦,與其兄張易之同入侍宮中,為武則天男寵。其為定州義豐(今河北安國)人,行六。美姿容,人稱六郎美如蓮花。覲見武則天時他們“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武則天見后“甚悅”,封昌宗為云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即貼身侍衛將領,封易之為司馬少卿,不數日又進拜昌宗為銀青光祿大夫,配給侍從。從此,二張儼若王侯,每天隨武皇早朝,皇帝聽政完畢,就在后宮陪侍女皇。二張那時的受寵程度可以從當時權貴們對其吹捧來說明。當時權傾一時的武承嗣等人都甘為二張“候其門庭,爭執鞭轡”;甚至武三思還吹捧張昌宗是“王子晉后身”;當有人贊揚張昌宗之美“面似蓮花”時,宰相楊思禮卻諂媚道“乃蓮花似六郎”;甚至太子李顯、太平公主等人還兩次上表請封張昌宗為王,最后因為不合制度,武則天“乃賜爵鄴國公”。長安元年(公元701年),皇太子李顯的兒子邵王李重潤、女兒永泰公主及其丈夫魏王武廷基暗地里議論二張專政,被二張知道告于武則天,武則天竟然“皆逼令自殺”。因一點小事而逼殺孫子女和孫女婿,可見二張受女皇寵愛之深。武則天為安置二張等寵臣還特意于圣歷二年(公元699年)設立一個新機構控鶴府,以易之兄弟為控鶴監內供奉,后又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又以易之為奉宸令。
張昌宗與兄易之專權亂政,時人側目。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則天病,崔玄暐、張柬之等人率羽林兵以謀叛罪誅之。昌宗粗能屬文,其應詔和詩,多為宋之問、閻朝隱所代作。武則天以其丑聲外聞,欲以美事掩其跡,詔撰《三教珠英》,令昌宗主之。昌宗乃引文學之士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兩《唐書》均著錄其領銜之《三教珠英》并《目》一三一三卷,為唐代規模最大之類書,今已佚。《全唐詩》卷八○錄存其詩三首。生平事跡見《舊唐書》卷七八、《新唐書》卷一○四《張行成傳》附。
關于宋之問作詩美化張昌宗一事大約發生在武后朝證圣元年(公元695年)以后。本年二月,武則天的男寵薛懷義失寵被殺,太平公主將自己的男寵張昌宗送給母親解悶。從此,張昌宗張易之兄弟就成為武則天最心愛的侍寢男寵,每天都跟隨在女皇的身邊,張昌宗是個男寵,但并不是繡花枕頭。他出身名門,精通音律,容貌俊美,也工于心計。對于現在的人來說,張六郎昌宗遠遠不如他的五哥張易之出名。但是在則天一朝的宮廷中,張昌宗才是最出色的美男。武則天和所有的帝王一樣都追求長生登仙之術,她很羨慕傳說中的周靈王太子姬晉(即王子喬),這位王子喬傳說擅吹笙作鳳鳴,后隨浮丘公登仙而去,成仙后還乘白鶴現于緱山,人稱“升仙太子”。武則天曾經為這位升仙太子題寫過碑文。于是馬屁應運而生。武三思想討姑媽的歡心,便將她最羨慕和最心愛的人扯到一起,說:“我以為六郎之美,已非凡世所能有,他一定是王子喬轉世。”武則天很歡迎這個比喻,下令造鶴麾并制木鶴,將張昌宗打扮成她心目中的王子喬模樣,果然仿若神仙中人。后來宮中游宴賞蓮,馬屁又誦道:“六郎似蓮花。”誰知高手還在后面,宰相楊再思的發言更勝一籌:“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雖是馬屁,但也足以證明張昌宗的美色非同凡響,始能先動太平公主,再動武則天,又在傳說中被選為打動上官婉兒的人物。但宋之問賦詩“美之”絕非僅因為張昌宗的美色,主要是緣于張宗昌那炙手可熱的權勢,而這,正是之問一入宮廷就諂附張氏兄弟,并在后來受牽連被貶謫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