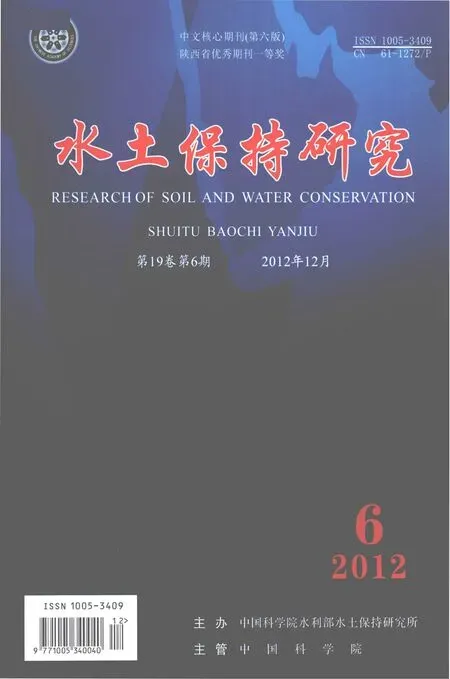河流生態修復研究進展
楊俊鵬,王鐵良,范昊明,蘇子龍
(1.沈陽農業大學 高等職業技術學院,沈陽110866;2.沈陽農業大學 水利學院,沈陽110866)
河流生態系統具有十分豐富的生物資源和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長期以來,人們為了滿足泄洪、排澇、航運、灌溉等要求,過多地使用混凝土等硬質材料進行水利工程建設和河道整治,結果導致河流長度縮短,河道遭到分割,淺灘和深潭消失,沿河的洪泛平原和濕地消失,河流兩岸的植被減少[1]。同時,人類將生產和生活產生的大量污染物排入河流中,造成水質惡化。此外,人類無節制地使用河流淡水資源、開發其生物資源,造成河水干涸、動植物減少。以上種種人類活動都對河流生態系統造成了脅迫,導致其生境惡化,生物多樣性減少,從而造成河流生態系統的破壞。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態環保意識不斷提高,對“人水和諧發展”的要求越來越高。保護水資源、修復河流生態系統已引起生態、環保、水利等多方面的關注,國內外對河流生態修復理論、應用技術的研究和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2]。我國擁有大量的河流資源,但多數遭到破壞,進行河流生態修復的研究對我國水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河流生態系統的影響因素
河流生態系統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水文條件、流域氣候、河流地貌、河流的水力特性和水質等。它們之間相互作用,是河流生態系統生境的組成要素。其中,水文條件和流域氣候主要是在流域的尺度上對河流生態系統的生態過程和系統的結構、功能造成影響,而河流地貌、河流的水力特性以及水質則主要在河流廊道和河段這樣相對較小的尺度上發揮作用[3]。
水文條件對河流生態系統具有主動性、驅動性作用,除了對河流環境景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外,還對河流生物群落的構成和生物過程有著重要影響。水文條件包括河流的水量、流量和水文過程。其中,水量和流量對河流地貌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們的變化對河流中物質、能量、信息以及生物之間的傳遞和遷移具有重要的意義。豐華麗等[4]研究表明,水量和徑流量的減少是河流生態系統退化的關鍵因素,嚴重時甚至會導致不可逆的生態退化。較為激烈的水文過程(例如驟然漲落的洪水)能夠將河流與河灘動態地聯結起來,促進水生與陸生生物之間的能量交換和物質循環。Poff等[5]認為水文條件是一種調節河流生態系統完整性和多樣性的控制變量,水量、流量和水文過程任何一項的改變都會引起河流生態系統的變化。流域氣候主要通過降雨和溫度對河流生境進行影響。流域氣候與河流生物群落的生物構成、生物過程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降雨會導致河流的水文條件發生改變,從而影響河流生境;在溫度較低時,河流生態系統的能量交換和物質循環將會減弱。同時,河流生態系統也反作用于流域氣候,造成局部小氣候的改變。生命系統與非生命系統之間存在依存與耦合關系。河流生物群落依附不同的河流地貌生存發展,并與河流地貌相互影響;同時,良好的河流地貌景觀格局使河流與洪泛灘區、湖泊、水塘和濕地之間保持良好的連通性,為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暢通提供了物理保障[3]。河流的水力特性在較小的尺度上(如河段、河流廊道)上影響著河流環境景觀的形成,并且使河流中的生物質和礦物質得以運移和傳遞,為水生生物提供棲息地并輸送營養物質。不同的水生生物都對應有相適宜的水力特性[3],它的改變將會對水生生物造成影響。水質是判斷河流生態系統是否健康的直接指標之一,良好的水質是維持河流生態系統多樣性、完整性以及其生態功能的基本條件,水質的惡化將導致嚴重的生態退化。
2 人類活動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
人類活動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使其整體性、連續性等特點遭到破壞,往往造成河流生態環境的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服務功能降低,甚至造成不可逆的生態退化。這種脅迫主要有傳統水利工程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污染物的排放對河流的污染、引水量過大、沿河的農業、漁業生產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等。
2.1 傳統水利工程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
傳統水利工程(大壩、河道硬化等)的修建對河流原有的水文條件、河流地貌以及河流的水力特性造成嚴重的影響,破壞了河流生態系統本身的特性,從而造成了其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例如大壩的修建,將河流分割開來,破壞了河流的連續性,使河流上游形成高位水頭、下游流量減少,中斷了大壩上下游能量、物質和信息的傳遞,造成河流原有生境的改變,而生物群落和生境具有統一性,導致河流生物群落的棲息和遷徙規律受到影響[6],最終使生物群落的多樣性降低。再如河道硬化整治,由于對河道采取截彎取直和大量采用混凝土等硬質材料,一方面改變了河流地貌和河流的水力特性,破壞了河流的開放性和多樣性,使原來蜿蜒的河道變得順直,河水流速加快,阻礙了河流與河岸之間的交換、地表水與地下水之間的聯系,改變了水域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7],造成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退化;另一方面,致使河流原有景觀遭到破壞,河道形狀幾何規則化,變得十分單調,降低了河流生態系統的景觀服務功能。
2.2 污染物排放對河流的污染
人類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向河流排入大量污染物質,如果其數量超過河流生態系統的自凈能力,將導致水質變壞(如水體富營養化、水體中含有大量的懸浮顆粒物等),直接對河流生態系統造成破壞(如水生生物大量死亡等),降低其淡水供應等生態服務功能。另外,由人類活動引起的硫化氣體的大量排放,導致酸雨的形成,也會間接造成河流水質的惡化。
2.3 引水量過大
隨著社會的發展,工農業以及人類的生活引用了大量的河水,但是每條河流的循環水量是有限的[8]。無限制的引用河水,使河流生態系統的水量低于生態需水量的下限,將導致原有河流生態系統結構的破壞,生態服務功能的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甚至造成河水干涸,整個河流生態系統的徹底毀滅。
2.4 沿河的農、漁業活動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
沿河的農業活動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主要表現在對河灘的開墾和耕作。由于土地肥沃,人們加大了對河灘、湖岸、河邊濕地的開墾。大量的開墾造田使河灘、湖岸及河邊濕地原有的天然植被受到嚴重破壞,水文條件、河流地貌及水力特性均隨之發生改變,導致河灘、湖岸土地以及河灘濕地的退化,減少河灘本來擁有的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降低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如河灘濕地對河流水質的凈化作用等)。此外,河灘的開墾還會造成水土流失,在河灘田地中大量使用農藥,會對河流水質造成新的污染。而漁業活動則會造成河流中的經濟魚種受到過分的捕撈,破壞了原有的食物鏈,導致河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受損。
3 河流生態修復的概念和任務
有關河流生態修復的概念在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我國學者任海和彭少麟[9]將其定義為:重建河流系統干擾前的結構與功能及有關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特征,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2003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做出有關“河流生態恢復”的定義:河流恢復是這樣一種環境保護行動,其目的是促使河流系統恢復到較為自然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河流系統具有可持續特征,并可提高生態系統價值和生物多樣性。我國學者董哲仁[10]在此基礎上將其定義為:河流生態修復是指通過適度人工干預,促進河流生態系統恢復到較為自然狀態的過程,在這種狀態下河流生態系統具有可持續性,并可提高生態系統價值和生物多樣性。這些概念都突出了人工干預和自然恢復的結合,但其分歧在于對河流生態系統修復的程度上,前者是對原有河流生態系統的重建,而后兩者則是不追求完全恢復原有河流系統,而是達到一個相對較為自然的狀態。學術界有關河流生態修復的任務雖然表述不一,但內涵基本相同:一是水質、水文條件的改善,使水量高于最小生態需水量,生境得到恢復;二是河流生態系統空間結構(河流地貌),及河流的連續性和開放性的恢復,以及河道縱向的蜿蜒性和橫向斷面的多樣性;三是對生物種群的恢復,通過對生境的改善使生物的多樣性得到提高。
4 河流生態修復理論研究
自德國學者Seifen[11]提出“近自然河溪治理”的概念后,河流生態修復得到了蓬勃發展。20世紀60年代起,西歐和北美的發達國家將生態學原理運用于工程實踐中,開展有關河道生態修復的相關實驗研究,并逐步運用于實踐。Vannote等[12]在更早的時候提出河流連續體(River Continuum Concept,RCC)的概念,指出河流網絡從河流源頭起,到下屬各級河流流域是一個連續的、流動的整體系統,河流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與流域具有統一性。同時RCC還概括了沿河縱向有機物數量的時空變化、生物群落的結構和資源的分配,使得河流生態系統特征能夠得到預測[13]。但是RCC描述的是沒有受到干擾的河流生態系統,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董哲仁等[14]提出“水文—生物—生態功能河流連續體”概念,其內涵是:以河流水文—水力學過程空間連續性,生物群落結構空間連續性,營養物質流和能量流空間連續性,信息流空間連續性為要素的河流連續體模型;同時,考慮水文、生物及河流生態系統演變和進化的動態特征,建立相應的時間坐標和尺度。這些概念指出了河流生態修復的重點和時空尺度,構成了研究人類活動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脅迫機理和河流生態修復的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開展了河流健康、河流生態需水量、河流生態修復的尺度和機理的研究,以及修復方法技術的研究。
4.1 河流健康
河流健康的研究可為河流的生態修復提供相關的標準,是河流管理工作的依據。學術界對河流健康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但總體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單純從河流生態系統出發,Richard等[15]認為河流健康是指河流生態系統完整、生態條件良好。這種定義適合未受人類活動干擾的河流,但是當前多數河流不可避免地與人類社會相聯系,所以另外一類定義將人類的價值涵蓋其中,強調了河流對社會生態服務的特征。夏自強和郭文獻[16]在總結前人相關概念的基礎上,提出河流健康為既能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同時又能維持其對人類社會提供的各種服務功能。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健康河流委員會(Healthy River Commission)將健康河流定義為:與其環境、社會和經濟特征相適應,能夠支持社會所希望的河流的生態系統、經濟行為和社會功能的河流為健康河流[17]。目前,多數學者采用第二類定義。
對河流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河流健康的評價上。國外較早開展了相關研究,并立足于實際情況,建立起采用不同指標體系和標準的河流健康評價方法。目前,國外采用的評價方法可分為生物評價法和綜合指標法兩類。其中,生物評價法是基于生物對河流環境變化的反應來對河流健康進行評價,澳大利亞采用的AusRivAS模型就是將大型無脊椎動物作為指示物種,對其生活狀況進行監測,并將其作為評價指標與期望值相比較得出評價結果[18]。但是當所評測河流缺乏指示物種時,該方法則不能有效地做出評價。而綜合指標法綜合了物理、化學、生境、生物等多方面因素,能夠反映不同尺度的信息,綜合指標法將成為未來河流健康評價的主要發展方向。常用的是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制定的河流狀況指數法(ISC),該法通過對河流的水文、河流物理狀態、岸邊帶、水質和水域生物5個方面的現狀與原始狀況相比較進行健康評價[18]。我國學者也較為傾向于綜合指標法,高永勝等[19]在考慮了社會需求的滿足程度和維持河流自身生命需要的基礎上建立了河流健康生命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包括地貌結構、社會經濟功能、生態功能3個方面的16項指標,并選擇分層二元對比專家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但是綜合評價法也存在指標過于繁雜、某些指標的監測成本較高、評價速度慢等缺點,尚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4.2 河流生態需水量
河流生態需水量是河流生態修復的重要依據,使河流水量滿足生態需水量要求也是河流生態修復的重點之一。河流生態需水量是指在特定生態保護目標下,維持特定時空范圍內的河流生態系統水分平衡所需要的總水量[20]。國外對河流生態需水量的研究開展的較早,并已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體系,目前,相關研究已擴展了尺度,將生態需水量的研究與其他生態系統以及人類社會聯系起來,并從河流生物群落所需的水動力學、水質要求等多個方面開展研究,并廣泛地應用于河流的生態修復和管理之中。Acreman等[21]研究表明,河流的生態需水量應立足于河流自身,滿足河流生物對水的質、量、水動力等多方面需求,同時,還要充分考慮到人類社會的需求。Arthington和Pusey[22]通過對澳大利亞全國河流水資源分配進行分析,提出應通過對水流(包括水質、流態等)的保護和修復來保證生態需水。我國河流生態需水量研究則側重于解決水資源短缺危機、河流生態修復等方面。倪晉仁等[23]將河流生態需水量分為:河流水污染防治用水、河流生態用水、河流輸沙用水、河口區生境用水以及河流景觀與娛樂環境用水。王偉等[24]對灤河典型水庫群聯合調度影響區(潘家口水庫、大黑汀水庫至灤河河口)的最小、適宜、理想三個等級的生態需水量進行了計算,為灤河下游的生態修復提供依據。常用的計算方法有水文學法、水力學法、棲息地法、整體法。這些方法在國內結合應用背景進行了改造,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4.3 河流生態修復的尺度和機理
河流生態修復的尺度和機理研究有助于確定河流生態修復的規劃、原則以及所采用的修復方法。目前對河流修復的理論研究多集中于流域尺度,董哲仁[10]通過分析水文過程與生態過程的耦合特征,論證了流域尺度是編制河流生態修復規劃的適宜尺度,以流域尺度進行河流生態修復規劃更能反映生態系統整體性特征。也有學者提出應針對不同的時空尺度特點進行針對性的研究,趙彥偉和楊志峰[25]探討了河流生態修復的時空尺度,將時間尺度分為短、中、長和極長四個尺度,將空間尺度分為區域、流域、河流廊道和河段4個尺度,指出在修復過程中應根據不同的時空特點,確定重點內容和方向。
在河流生態修復機理研究方面,李睿華等[26]研究了美人蕉、香根草和荊三棱3種水生植物改善河水水質的機理和效果,指出河道修復中植物對提高河流自凈能力、改善流域局部小氣候有重要的作用。滑麗萍等[27]研究了河湖底泥的生物修復方法,并對其機理進行了闡述。高甲榮等[28]對采用扦插、生物墊和梢捆3種土壤生物工程措施進行河流岸坡治理的北京懷九河—渡河段的穩固岸坡效果進行了調查觀測,分析了其加固機理。Pedersen等[29]通過對Skjern River的生境、大型植物和大型無脊椎動物在2000年(修復前)和2003年(修復后)的兩次調查觀測,分析了生物群落的恢復機理,指出生態修復使生境變得豐富多樣,極大地促進了生物群落的增長,并指出生物群落將會隨著河流形態的穩定而持續發展。Nakano等[30]對日本北部的Shibetsu River的生態修復進行了調查研究,探討了大型無脊椎動物種群的恢復機理,指出重塑的蜿蜒河道為大型無脊椎動物創造了兩種主要的生境:穩固的河床邊緣生境和在河道彎曲處形成的樹木的生境,這兩種生境有利于大型無脊椎動物的發展。鄭天柱等[31]應用生態工程學理論進行河道生態恢復機理的探討,指出滿足河流生態需水量是缺水地區恢復河流生態的關鍵。楊海軍等[32]對河岸生態系統恢復過程中自組織機理進行了初步研究。綜合目前國內外研究情況,關于河流恢復機理的研究尚屬于初步階段,一些機理尚不清楚,還有待深入研究,例如河岸生態系統在恢復過程中對水生生物群落的影響等問題。
4.4 河流生態修復模型
河流生態修復模型可有效地為河流生態修復的規劃和決策提供參考和指導,也是近年來國際上研究的熱點之一。國外較早地開展了該方面的研究,并相繼建立了一些模型,為河流的生態修復服務。例如基于GIS技術建立的生境適宜指數模型(HIS,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33],將其結合河流水力模型可有效地預測水生生物的適宜生境的參數(如水深、流速等),可為河流生境的修復提供參考,但該模型在遇到復雜河道時部分參數的預測與標準值不符。又如模擬大壩拆除后河流中沉積物運動和河床穩定性的模型[34],它可以對大壩拆除后河流中沉積物的重新分配及河床的穩定性進行預測,包括大壩拆除時期和拆除后的4a恢復時期,但是該模型未考慮河流對河床的沖刷。另外還有計算水流動力的模型(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35],該模型被廣泛應用于確定水流運動參數,以滿足生態水利工程的需要,并可結合其他生態學模型模擬恢復過程,為河流的生態修復服務。有關綜合模型的報道較少,Bockelmann等[36]在2003年針對英國的Afon Morlais河的一段長約3km的蜿蜒片段開發了生態恢復模型,此模型集合該河流片段的水力、土層、生態參數建立而成,可以對河流的恢復進行預測,但由于各條河流的狀況不同,因此該模型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不能得到廣泛的應用。我國的河流生態修復模型尚處于起步階段,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葉飛等[37]通過原位樣方觀測和室內水情模擬實驗,開發了岸邊帶植被演替模型,該模型耦合了全局基于連續性模式的水動力模塊和局部基于元胞自動機模式的植被演替模塊,但是該模型由于缺乏對水溫、濁度等因素的考慮,具有局限性。我國在綜合模型的方面尚處于概念理論階段,相關報道較少。綜合上述文獻,當前國內外對河流生態修復模型的研究多集中于對部分的模擬,并且這些模型考慮的影響因素不全面,只能對一些理想狀態下的情況進行模擬,具有局限性;由于河流生態恢復機理尚不明確,所以對于綜合模型的報道較少,已開發出的綜合模型還不完善,有待進一步研究。
5 河流生態修復的方法
目前,河流的生態修復方法主要用于對河流地貌和水質的修復,常用的修復方法有:
(1)水利工程設施的拆除。由于水利工程會對河流生態系統構成脅迫,人們在進行河流的生態修復時會通過拆壩、拆除混凝土河道等措施降低水利工程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
(2)河岸帶的修復。河岸帶位于水陸交錯地帶,是河流水生生態系統和陸地生態系統之間能量、物質和信息交換的重要過渡帶。因此,河岸帶的修復對河流生態系統的修復具有重要的意義。常采用后撤堤防、建造生態護坡以及修復或建造河岸濕地等方法進行河岸帶的修復,可有效提高生物多樣性和防治水土流失。李小平和張利權[38]在上海浦東機場鎮河岸帶中采用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濕生植物進行修復,10個月后發現土壤剪切力和生物多樣性都得到了明顯改善。
(3)河道的修復。對河道的修復主要是在縱向上修復河道自然蜿蜒的形態,趙進勇等[39]總結了修復蜿蜒形態的四種方法:復制干擾前的蜿蜒模式法、參考附近未受干擾河段模式法、自然恢復法和通過對受干擾河流進行系統評價和分析的系統分析法。但由于河流都具有獨特性,因而復制法和參考法都具有特殊性,不適合所有河道;自然恢復法的歷史較長;系統分析法能夠綜合多方因素模擬河流的蜿蜒形態,較為適用。河道修復在橫向上是修復河道斷面的多樣性,同時注意深潭—淺灘的創建。另外還可以通過建造橡膠壩、小型水堰等方法來改善河道內的局部地貌形態。美國從1990年開始的基西米河生態修復工程,通過改變上游水庫的運行方式、修建攔河壩抬高水位以恢復兩岸濕地和回填渠化河道、恢復其自然蜿蜒狀態等方式,達到河流生態修復的目的[40]。
(4)控制入河污染物。水質是河流生態系統的重要影響因素和生境要素,對河流生態系統的健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結合河岸濕地、生態河道的生態治污等防治污水方式的同時,還應加強對各類入河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以減少水污染,修復河流水質。
6 建議
我國幅員遼闊,擁有大量的河流,但是由于人為或自然原因,大部分河流生態系統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因此,加強對未受干擾河流的保護和對已受破壞河流進行生態修復已刻不容緩。從目前國內研究情況來看,河流的生態修復雖取得一定成就,但仍處于探索階段,針對我國實際情況提出以下發展建議:(1)在根據不同尺度進行河流生態修復工程的規劃和建設的同時,應注意結合河流所在區域的其它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以助于更大尺度范圍內的生態建設;(2)當前大多的研究和工程實踐偏重于河流水質的改善,今后應加強對河流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修復的研究和實踐;(3)加強對河流生態修復標準的研究,盡快確立起修復標準,為河流生態修復提供依據;(4)應綜合修復方法、河流健康評價體系、生態需水量以及修復標準等多個方面,構建起一套完整的河流生態修復模型,來指導具體工程建設,并對已修復河流進行監測、管理;(5)河流恢復歷時較長,但在修復工程結束后缺乏長期監測,建議應進行針對生態護坡、生物多樣性恢復、流域小氣候等的長期觀測。
[1] 王薇,李傳奇.河流廊道與生態修復[J].水利水電技術,2003,34(9):56-58.
[2] 孫東亞,趙進勇,董哲仁.流域尺度的河流生態修復[J].水利水電技術,2005,36(5):11-14.
[3] 董哲仁.河流生態系統研究的理論框架[J].水利學報,2009,40(2):129-137.
[4] 豐華麗,陳敏建,王立群.河流生態新系統特征及流量變化的生態效應[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12(6):59-62.
[5] Poff N L,Allan J D,Bain M B,et al.The natural flow regime:a new paradigm for riverin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J].Bio-Science,1997,47:769-784.
[6] 王東勝,譚紅武.人類活動對河流生態系統的影響[J].科學技術與工程,2004,4(4):299-320.
[7] 董哲仁.水利工程對生態系統的脅迫[J].水利水電技術,2003,34(7):1-5.
[8] 艾學山,王先甲.打造健康河流維持可持續發展[J].國土資源科技管理,2007,24(3):60-65.
[9] 任海,彭少麟.恢復生態學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10] 董哲仁.河流生態修復的尺度格局和模型[J].水利學報,2006,37(12):1476-1481.
[11] Seifert A.Naturnaeherer wasserbau[J].Deutsche Wasserwirtschaft,1983,33(12):361-365.
[12] Vannote R L.The river continuum concept[J].Can.J.Fish.Aqua.Sci.,1980,37:130-137.
[13] 蔡慶華,唐濤,劉建康.河流生態學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J].應用生態學報,2003,14(9):1573-1577.
[14] 董哲仁,孫東亞,彭靜.河流生態修復理論技術及其應用[J].水利水電技術,2009,40(1):4-10.
[15] Richard H N,Charles P H.Monitoring river health[J].Hydrobiologia,2000,435:5-17.
[16] 夏自強,郭文獻.河流健康研究進展與前瞻[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8,17(2):252-256.
[17] Halse S A,Scanlon M D,Cocking J S,et al.Factors affecting river health and its assessment over broad geographic ranges:the Western Australian experience[J].Environ.Monit.Assess.,2007,134(2):161-175.
[18] Ladson A R,White L J,Doolan J A,et al.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n Index of Stream Condition for waterway management in Australia[J].Freshwater Biology,1999,41(2):453-468.
[19] 高永勝,王浩,王芳.河流健康生命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水科學進展,2007,18(2):252-257.
[20] 占車生,夏軍,豐華麗,等.河流生態系統合理生態用水比例的確定[J].中山大學學報,2005,44(2):121-124.
[21] Acreman M,Dunbar M J.Defining environmental river flow requirements-a review [J]. Hydr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2004,8(5):861-876.
[22] Arthington A H,Pusey B J.Flow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in australian rivers[J].Riv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03,19(5):377-395.
[23] 倪晉仁,崔樹彬,李天宏,等.論河流生態環境需水[J].水利學報,2002,9(9):14-20.
[24] 王偉,楊曉華,王銀堂.灤河下游河道生態需水量[J].水科學進展,2009,20(4):560-566.
[25] 趙彥偉,楊志峰.河流生態修復的時空尺度探討[J].水土保持學報,2005,19(3):196-200.
[26] 李睿華,管云濤,何苗,等.用美人蕉、香根草、荊三棱植物帶處理受污染河水[J].清華大學學報,2006,46(3):366-370.
[27] 滑麗萍,郝紅,李貴寶,等.河湖底泥的生物修復研究進展[J].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學報,2005,3(2):124-129.
[28] 高甲榮,劉瑛,Hanspeter Rauch.土壤生物工程在北京河流生態恢復中的應用研究[J].水土保持學報,2008,22(3):152-157.
[29] Pedersen M L,Friberg N,Skriver J,et al.Restoration of Skjern River and its valley-short-term effects on river habitats,macrophytes and macroinvertebrates[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7,30(2):145-156.
[30] Nakano D,Nagayama S,Kawaguchi Y,et al.River restoration for macroinvertebrate communities in lowland river:insights from restoration of the Shibetsu River,north Japan[J].Landscape Ecol Eng.,2008,4(1):63-68.
[31] 鄭天柱,周建仁,王超.污染河道的生態恢復機理研究[J].環境科學,2002,23(12):115-117.
[32] 楊海軍,內田泰三,盛連喜,等.受損河岸生態系統修復研究進展[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36(1):95-100.
[33] Gillenwater D,Granata T,Zika U.GIS-based modeling of spawning habitat suitability for walleye in the Sandusky River,Ohio,and implications for dam removal and river restoration[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6,28(3):311-323.
[34] Konrad C P.Simulating the recovery of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and river-bed stability in response to dam removal on the Elwha River,Washington[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9,35(7):1104-1115.
[35] Daraio J A,Weber L J,Newton T J,et al.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nd ecological models applied to juvenile freshwater mussel dispersal in the Upper Mississippi River[J].Ecological Modelling,2010,221(2):201-214.
[36] Bockelmann B N,Fenrich E K,Lin B,et al.Development of an ecohydraulics model for stream and river restoration[J].Ecological Engineering,2004,22(4):227-235.
[37] 葉飛,陳求穩,吳世勇,等.空間顯式模型模擬河流岸邊帶植被在水庫運行作用下的演替[J].生態學報,2008,28(6):2604-2613.
[38] 李小平,張利權.上壤生物工程在河道坡岸生態修復中應用與效果[J].應用生態學報,2006,17(9):l705-1710.
[39] 趙進勇,孫東亞,董哲仁.河流地貌多樣性修復方法[J].水利水電技術,2007,38(2):77-83.
[40] 吳保生,陳洪剛,馬吉明.美國基西米河生態修復工程的經驗[J].水利學報,2005,36(4):473-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