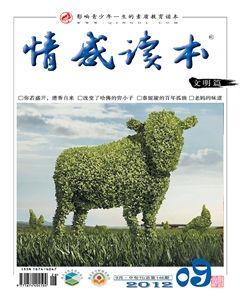路
佚名
修路
吞下幾塊點心、幾枚柑橘作為午飯后,王柏林又揮起了鋤頭和鐵鏟。在他眼前,連片的茂密雜草一叢叢倒下。而在他身后,一條人行便道清晰地顯露出來。
這位重慶市云陽縣盤龍鎮(zhèn)親睦村的老人已經(jīng)78歲了,他總是帶著干糧,扛著修路的工具,出現(xiàn)在山間小道和鄉(xiāng)村公路上。鋤草、挖土、搬石頭修補。3年間,他義務整修出的人行便道達到18公里。
親睦村山高坡陡,與云陽新縣城隔江相望。雖然村里有了“村村通”,但大多數(shù)村民沒有交通工具,還得走人行便道去鎮(zhèn)上趕集。荒草隨著歲月瘋長,磚石也在風雨中老去,村里僅有的幾條人行便道漸漸無法通行了,人們?nèi)ユ?zhèn)上得繞十幾公里的路。
王柏林是從哪一天開始修路的,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了。每天,他頂著寬檐的大草帽在清晨7點出發(fā),一直忙到下午5點回家。走到道路需要修補的地方,老人便馬上開始工作。他揮動鋤頭,動作嫻熟,平均一個小時能整修出好幾米路來。
“看到學生娃娃從這里去呀來的,都要走這條路,還有很多老年人和上來搞爬山運動的……修了路好走一些。”王柏林平靜地說起修路的初衷。
經(jīng)過整修,曾經(jīng)荒廢的人行便道如今連通起5個村莊和兩個鄉(xiāng)鎮(zhèn),重新熱鬧起來。村民和游客們走在平整的道路上面,心里開懷又感激。
有的人把自己當成金子,生怕被埋沒;而有的人甘愿做泥土,鋪在人們腳下。有后者的存在,便知路在何方。
指路
河南人劉貴軍“北漂”10年了。在北京豐臺區(qū)正陽大橋附近,他有個不起眼的廢品攤。和所有的廢品攤看上去差不多,大捆的硬紙殼和無數(shù)瓶瓶罐罐堆滿了一輛卡車。但特別的是,一臺報廢的小面包車靠在卡車旁邊,車頭用油漆刷著5個大字:“指路臺”、“義務”。
有時會有汽車停下來,里面的人搖下車窗大聲喊:“豐臺醫(yī)院怎么走?”也有人下了車直沖他走過來:“師傅,西道口你知道不?”他便帶著濃重的河南鄉(xiāng)音,耐心地用普通話為他們講解。
“前面右拐,看到紅綠燈再左拐就是了!”說起附近的大小地方,劉貴軍想都不用想,張口就來。
7年前,劉貴軍剛到正陽大橋擺攤收廢品,就發(fā)現(xiàn)每天看攤10個小時,能遇上50個人向他問路。很快,他把義務指路當成自己的副業(yè)。后來受到交通廣播臺的啟發(fā),他還給“小面包”的車頭刷上了字。這樣,不僅迷路的人老遠就能看見他,也更方便張口求助。
按照一天50人次粗略計算,一年下來,劉貴軍能為上萬人指路。有記者想采訪他,他擺擺手:“我這不叫事兒,動動嘴而已,有啥好寫的!”
有時候,他會遇到一些豪車,司機坐在車里,打聽清楚后便一踩油門揚長而去,留給他濃濃的尾氣味兒。不過,這兩年他也漸漸發(fā)現(xiàn),喜歡說“謝謝”的人越來越多,5年前大概有3成,現(xiàn)在能達到6成了。
自認為是弱勢群體的劉貴軍說,他一直很珍惜幫助別人的機會,那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心滿意足。
歸路
沙漠里可沒有義務指路人,特別是在地球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當賴立坤發(fā)現(xiàn)自己在那里迷路時,幾乎絕望了。
去年11月,這個廣東順德人騎著自行車從家鄉(xiāng)出發(fā),一個多月里,他成功穿越了英、法等國。然而,今年2月的突尼斯之旅卻讓他陷入了沙漠的包圍。
那天下午,賴立坤記錯了路線,往前走,樹木越來越少,沙土越來越多;往回走,原來的三岔路變成了五岔路。他打開手電筒查看地圖,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走在沙漠的邊緣。
天色漸暗,賴立坤打開手機,電話不通。他又打開求救用的熒光棒,可是茫茫沙漠,一點光亮何其微弱。野狼、饑餓、恐怖分子……賴立坤的腦中,所有最可怕的元素連環(huán)閃現(xiàn)。在黑暗中,一輛破舊汽車緩緩駛來,兩名男子將他塞進了車,他們說什么,賴立坤一點兒也聽不懂。
“就算是綁架也好過死在沙漠里,”在車上,賴立坤逮住機會,一口氣向20多名身在國內(nèi)的友人發(fā)送短信求救,“我在非洲突尼斯……找不到中國人……我冷餓至極,請救我。”
信號的另一頭,一場緊急救援的行動立刻開始。順德區(qū)容桂派出所啟動應急機制,與中國外交部溝通后,和中國駐突尼斯的外交人員取得了聯(lián)系,終于接通了賴立坤的電話。聽到熟悉的粵語鄉(xiāng)音,他的眼淚馬上就下來了。
其實,帶他走的人壓根兒不是什么綁架者,而是好心人。他們帶賴立坤去了附近的村莊,還把他安置在一戶人家。
有時候,你看不見那條通往家的路,但你可以試著相信,在語言和交通工具都無法到達的地方,也有著溫暖的燈火。
摘自《現(xiàn)代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