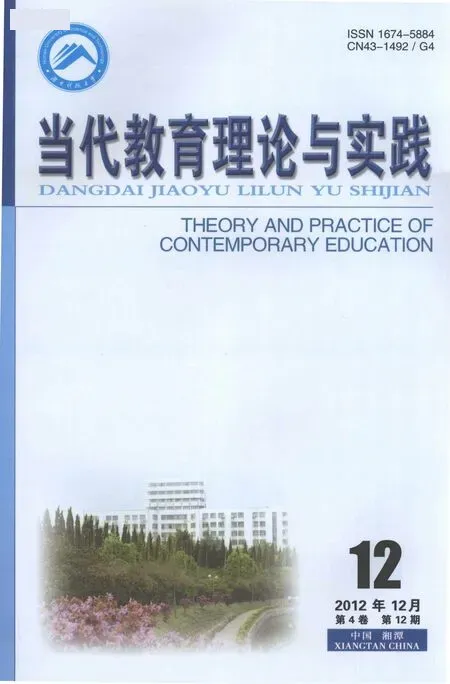從弗氏精神分析學說看《每個人》的后現(xiàn)代主義生活*
邱能生
(華僑大學廈門工學院,福建廈門361021)
一
菲利普·羅斯是當代美國文壇頗受爭議而又極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是繼馬拉默德、艾·巴·辛格和索爾·貝婁之后的又一位美國猶太文學作家。羅斯于1933年3月19日出生于新澤西州紐瓦克市一個猶太家庭,童年和少年時代在紐瓦克的猶太區(qū)度過,青年時代先后在紐瓦克學校、拉瓦斯大學接受正規(guī)教育,1954年畢業(yè)于賓西法尼亞州巴克內爾大學,次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他的作品曾多次獲獎,其中短篇小說《信仰的辯護者》(Defender of the Faith)1960年獲歐·亨利故事競賽獎(O.Henry Prize Contest)、小說《再見吧,哥倫布》(Goodbye,Columbus)1966年獲美國全國圖書獎、《遺產》(Patrimony)1991年獲全國書評家協(xié)會獎、《夏洛克戰(zhàn)役》(Operation Shylock)1993年獲福克納獎、《薩巴斯劇院》(Sabbath’s Theater)1995年獲全國圖書獎、《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8年獲普利策小說獎。自從1959年發(fā)表第一部短篇小說《再見,哥倫布》以來,菲利普·羅斯就一直是美國當代文壇一位倍受爭議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風格多樣、主題選材廣泛,其中以性愛和猶太人生活為主題的小說引起了批評界普遍的爭論。
二
《每個人》(Everyman)是菲利普·羅斯2006年剛剛推出的第27部作品。羅斯先生說這本小說的構思開始于前諾貝爾獎得主索爾·貝婁的死亡與疾病——當時索爾·貝婁從芝加哥搬到了波士頓,就住在離羅斯非常近的地方。“我本該非常清楚索爾·貝婁就要去世這件事的,因為他當時已經89歲了,但他的死還是讓我難以接受,我開始寫這本書是在他落葬的那一天。那天我從墓地回來,就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羅斯先生是這樣回憶的,“如果你夠幸運,你的祖父母會在你成年后去世,比方說在你上大學以后。而我的祖父母是在我讀小學時去世的。如果你夠幸運的話,你的父母會一直活到你50歲左右;如果你非常幸運,那他們會活到你60左右,而你的孩子們,當然,決不會死在你的前頭。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這是一種合約。但在這個合約中,沒有你朋友的份額,所以當他們死去時,會讓人非常震驚。”[1]羅斯的作品自傳性較強,寫盡了一生的滄桑之后,在這部新作里他著力于探討死亡的意義。作者安排他在死后來回顧自己的一生,在他看來人的一生只不過是肉體不斷受到病痛折磨,身體機能每況愈下而最終走向墳墓的過程。他不信教,也沒有什么信仰,死亡就是生命的結束,抽象的精神道德根本不存在。人在本質上是非理性的,無法解釋的,人在欲望的控制下生活,欲望讓人充滿活力,也一步步把人推向死亡。本文旨在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來分析小說《每個人》(Everyman)的人物性格,并進而探討小說的死亡主題和性主題。
三
《每個人》是講述關于死亡的事。故事始于墓地,終于手術臺。小說的無名主人公的一生都是在死亡的威脅和病痛的折磨中度過的。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使用了一些后現(xiàn)代主義的手法:小說的無名主人公在第一章中已經死了,但到了第二章他又會復活,然后從他的視角來回顧自己的一生,把故事重新再講一遍。這樣,讀者從這一“倒望遠鏡”中看到的就是大量關于衰老、疾病和死亡的描寫。
《每個人》的標題和主題都取材于中世紀的一部道德劇。兩部作品在劇情結構和主題上都有類似之處,它們探討的也都是死亡,但結果卻大相徑庭。劇本中的主人公在自己的大限之日面對上帝,回顧自己的一生,發(fā)現(xiàn)無論是朋友、家庭還是財富、美貌和知識都毫無意義,這些世俗的追求在你死后都會拋棄你。最后他發(fā)現(xiàn)只有通過行善、懺悔和謹慎為人才能獲得拯救。劇本的道德寓意非常的明顯:具體的世俗追求毫無意義,只有抽象的精神道德才能超越一切。羅斯小說中的無名主人公在小說的開頭也已經死去,然后由他來回顧人生。在這里他所面對的不是上帝,而是讀者。在他看來,抽象的精神追求沒有意義,人在這個世界上所能抓住的只有具體的實物,死后所擁有的也就是自己骨骸的托身之處——墓穴,死亡是人生的終點,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上帝,也沒有來世。“宗教只不過是一種謊言,這他在很早以前就意識到了,所有那些宗教所宣揚的道義都是騙人的蠢話。”[2]人的一生是在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脅中度過的。在小說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著力描寫了主人公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和病痛對他的折磨:二戰(zhàn)期間,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開始感到死亡帶來的恐懼。當他走在澤西島的海灘上時,心中有種莫名的恐懼,擔心溺死的水手會沖上岸來纏住他的腿。9歲的時候他因疝氣要做個手術,在醫(yī)院的病房里親眼目睹了對面床位的男孩在半夜死去的過程。他是如此的害怕以至于當他第一次看到外科醫(yī)生“穿著外科手術袍和戴著白色的面具”時認為他可能不是史密斯醫(yī)生了,而是“一個剛剛走進來而不知是誰的人,他拿起刀要把我變成一個女孩子。”[2]30多歲時他身體健壯,事業(yè)有成,但他卻時時感到死亡的暗示。外出度假,他害怕到海邊去散步,因為那時他能感到死亡的威脅在不斷逼近。羅斯這樣寫到“他心態(tài)正常,并不走極端,為什么在這樣的年齡會不斷受到死亡威脅的折磨了?他現(xiàn)在離最后的大限還長著啊!”[2]生命在這里再次向我們展示了它的不確定性,人在本質上是不理性的,無法解釋的。
接著,小說向我們講述了他71歲時的經歷。他經歷了一系列的外科手術:血管肉瘤切除、頸動脈擴張、心臟起博器安裝。“時間已經把他的身體轉變成一個儲存人造機械的儲藏室,以防他身體最終倒坍。”[2]他離開了朋友、自己的三個妻子和三個孩子,一個人獨自在海邊的療養(yǎng)村里居住。回憶起自己的一生,除了少年時的一段美好時光之外,在他腦海中的都是關于急癥、手術臺和醫(yī)療救助方面的回憶。他已感到死亡正悄悄地向他走來。他的這些感覺在看著朋友們一個一個死去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強烈了,他逐漸意識到“老年不是一場戰(zhàn)斗,而是一場屠殺。”[2]當他透過這些事實,透過他所居住的療養(yǎng)村和他老年時開辦的美術課程,他發(fā)現(xiàn)他的一生實際上就是三個婚禮和一場葬禮。
小說最后描述了主人公到墓地去觀察一位挖墓人的實際工作內容:他要知道墓穴是怎么挖的,里面是怎么回事,因為那些就是他死后的實實在在的全部所有。一切最終歸結于冰冷的實際存在物,生的過程中對所有抽象意義的探討都是徒勞的。生活如果有意義的話,應該只能歸于對具體事物的把握,舍此之外,并無其他。“羅斯致力于刻畫那些執(zhí)意要在美國社會中尋找某種有意義的行為方式的人物,不管那個社會是多么的荒誕。但是,幾乎所有的男女主人翁,都是一些徹底的失敗者,除了毀滅性的行為方式外,他們一無所獲。”[3]這樣,在《每個人》中,羅斯以蒼涼的筆調完成了對中世紀那部同名劇作的戲仿,凸現(xiàn)的主題十分悲觀:“生是肉身欲望日漸消減的過程,死則是身體殘骸埋葬于墳墓之中。生死都沒有意義。”[4]
四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認為人格結構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層面構成。本我:指人類精神中最底層和原始獸性的東西,類似無意識,是人類精神活動的力量源泉,以“快樂原則”追求滿足,不考慮現(xiàn)實環(huán)境,無所謂善惡對錯。構成本我的主要是“性力”,弗洛伊德稱之為“力比多”(Libido),這種本能驅使人去尋找快樂,尤其是性快樂。自我:由認識和理智過程構成,它是精神的感覺器官,感受外部刺激,也感受內心活動。它在現(xiàn)實原則的條件下,控制本我的活動,以便在現(xiàn)實的條件下滿足本我的欲望需求。超我:是社會力量在人心理中的代表,指的是人從兒童時期培養(yǎng)起來的社會對他的影響,包括社會道德和行為準則,它無意識地起作用,是人類結構中最后的保障文明發(fā)展的層次[5]。
潛意識的內容是那些為人類社會、倫理道德、宗教所不容許的、原始野蠻的、目無道德法紀的動物性本能沖動,以及出生后被壓抑的欲望,往往是經歷的濃縮品,是幼童期的經驗、欲望和動機的沉淀物。潛意識是最活躍、最不安分守己的分子,它們千方百計地想表現(xiàn)出來。但由于社會禮教、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社會標準的作用,意識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發(fā)揮著它的威力,控制著潛意識繼續(xù)留在最底層,不允許其表現(xiàn)和滿足。
羅斯在這部小說中除了叩問死亡之外,他的另一個主題是性。性力是人潛意識的內容,是人潛在的欲望,它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表現(xiàn)出來。性力一方面使人的生活充滿活力和激情;另一方面又因為其內容是違背倫理道德和宗教而不為人所接受,所以往往又會給人帶來無比的痛苦。小說的無名主人公在死后回顧自己的一生,發(fā)現(xiàn)自己一生主要都是活在性的矛盾中。一方面性給他帶來的刺激是無法避免的,在欲望面前他毫無辦法。但另一方面,性又使他家庭破裂,妻離子散,臨到終年一個人生活在療養(yǎng)村里,倍受疾病和孤獨的折磨和煎熬。為了使自己的后半生不至于在精神錯亂中度過,在性力的驅使下他離開了他的第一個家庭,給他的兩個兒子造成了傷害。他的這兩個兒子為此以后再也沒有原諒他,他們甚至罵他是“可惡的雜種(you wicked bastards!)”“愚蠢的色鬼(you silly fucker)”[2]。這件事情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痛。后來他為自己辯解:事情會不同嗎?如果我不這樣做,事情會不同嗎?我會比現(xiàn)在更不孤獨嗎?也許會!但這就是我所做的!我現(xiàn)在已經是71歲了。這就是我!我就這樣了!在這里他在為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權利在爭辯。他應該得到原諒。他沒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人在根本上是被潛在的性力牽著走的。
的確,欲望就象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他的生活有了色彩,另一方面又徹底地毀了他。盡管他很清楚Marete,一位年輕模特的吸引力和追求她會有什么結果,盡管他也不糊涂,心地也不壞并且也有對家庭的責任感,但是他還是無法擺脫欲望的控制并且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他知道“他生命中的這次最瘋狂的冒險可能會使他失去一切”[2]也還是沒有用。他一直深愛的第二個妻子菲比(phoebe)也是一直對他關心倍至的妻子因為他的背叛最終離開了他,從此以后他的日子就只能在病痛的折磨和孤獨中度過了。他的第三次婚姻很快也破裂了,晚年只能一個人在凄涼的療養(yǎng)村中度過。即便如此,他也無法控制自己去勾搭一個在海灘上跑步的年輕女人。在這里羅斯似乎要告訴我們,人本質上是非理性的,人的欲望無法被壓制。不管自己意識有多么的清楚,它都要想辦法表現(xiàn)出來。羅斯用一種蒼涼的筆調告訴我們: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救藥的。
五
但是羅斯在小說里對他的主人公并不是毫無同情心的,也不是完全不相信愛情有忠貞的一面的。雖然他一生倍受疾病的折磨和親人的遺棄,但還是可以從他的女兒南希的愛中找到一些安慰。南希并沒有因為他欺騙她的母親而恨他,她不僅原諒了他,而且一直期望她的父母親能和好。在他晚年的時候南希總是想辦法找時間去陪他,并在他死后精心地安排和組織他的葬禮。在這里羅斯似乎借用南希這個角色表達對他主人公的同情,他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是普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把握自己的行為的。人在外部環(huán)境和內在性力的驅動下,似乎很難不犯錯,對于這樣的一個生活的失敗者我們理應給予一定的理解和同情。
“閱讀羅斯的文學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世界是破碎的、荒誕的,人在本質上是非理性的,是無法解釋的、不可靠的、不可信的,道貌岸然的外表后面也許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動機。他的小說描繪、展示出當代美國社會中各種復雜心態(tài)的人物,他們中許多人是生活的失敗者。”[6]羅斯在《每個人》中描寫的這個無名主人公就是這么一個心態(tài)復雜,行為動機漂浮不定的失敗者,他的思想行為就象他所生活的社會一樣荒誕。然而以“每個人”荒誕的一生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是他上一輩人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小說中羅斯精心描寫了一段“每個人”兒時美好的家庭生活場景,這段已逝的猶太人家庭生活是“每個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兒時的他家庭幸福,他在父母和哥哥的關愛下快樂健康地成長。他家里在1953年開了一家珠寶店,他喜歡擺弄店里的那些舊手表和珠寶器械,這些東西培養(yǎng)了他對藝術的追求。然而兒時對藝術的夢想待到成年后,在物欲橫流、荒誕不羈的社會的影響下便逐漸地抹去了,轉而從事更加實際的廣告工作。兒時他們把訂婚戒指和結婚戒指賣給了當?shù)氐娜彝ィ麄兌己退母改敢粯佣寄軐ψ约夯橐龊蛺矍楸3种艺\。然而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的他回憶那段時光,卻怎么也不能理解他們是怎么能避免各種誘惑和選擇而一輩子相愛地生活在一起而不會出現(xiàn)背叛。在這里作者似乎想要從上一輩人的生活中來尋找當代人生活問題的答案,借用兩代人生活的對比來批判當代失衡的社會:信仰缺失、物欲膨脹,人們在支離破碎的社會中隨波逐流。
[1]秦小孟.當代美國文學概述及作品選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2]Philip Roth.Everyman[M].New York:random House,inc.2006.
[3]W B Fleishmann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Co.1971.
[4]楊衛(wèi)東.死者對人生的回顧:菲利普·羅斯的新作《每個人》[J].外國文學評論,2006(3).
[5]朱立元,李 鈞.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上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6]金 明.菲利普·羅斯作品中的后現(xiàn)代主義色彩[J].當代外國文學,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