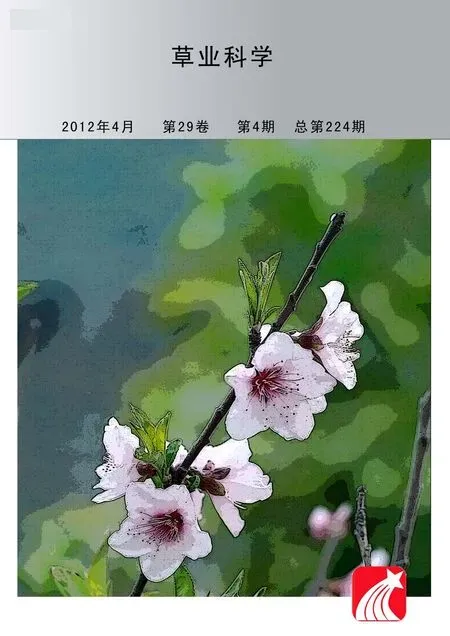低碳農業研究進展
魏 斌,張靈菲,葛慶征,張衛國,江小雷
(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科技學院 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730020)
2003年,英國政府在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低碳經濟”[1],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讓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關注。遏制氣候變暖、拯救地球家園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每個國家、民族和個人都應該本著對全人類負責的態度,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都應該責無旁貸地行動起來,轉變傳統的消費模式、發展方式和價值觀念,走低碳發展的道路,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2]。低碳意味著環保、節能減排,意味著傳統產業結構的調整、能源結構的優化和低碳產業的發展,意味著生產、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
1 低碳農業的概念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經濟模式[3-5]。低碳經濟形式上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質上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低碳經濟的本質就是通過產業部門的協作努力,最大可能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實現溫室氣體與經濟發展的“脫鉤”。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經歷了原始農業階段、傳統農業階段和現代工業化農業階段,而以能源、機械、化肥、農藥等投入要素為基礎的現代工業化農業過程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發展低碳農業勢在必行。通過發展低碳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得以減少,進而發揮農業在發展低碳經濟中的作用,以此實現現代農業由高碳農業向低碳農業的轉型。
低碳農業是低碳經濟的一個重要領域,是低碳經濟在農業發展中的實現形式。低碳農業是指在農業生產、經營中排放最少的溫室氣體,同時獲得整個社會最大效益的技術,即:通過提高農業的碳匯能力和減弱農業的碳源能力,實現農業源溫室氣體凈排放不斷減少的目標。發展低碳農業除了秉承低碳經濟的內涵之外,要突出資源高效利用、綠色產品開發、發展生態經濟,還要突出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固碳減排,其關鍵在于提高農業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同時降低農業發展對生態系統碳循環的影響,維持生物圈的碳平衡[6-8]。低碳農業即生物多樣性農業[9-10],是為維護全球生態安全、改善全球氣候條件而在農業領域推廣節能減排技術、開發生物質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新型農業[11-12],是一種全新的以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為基礎的現代綠色農業經濟發展模式[13]。它不僅提倡少施化肥、農藥,進行高效的農業生產,而且更注重農業生產整體過程中能耗的減少和低碳的排放。
低碳農業是相對于當前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現代工業化農業而提出的新型農業[14]。現代工業化農業生產過程中,化肥農藥的廣泛使用,農膜農具的隨意廢棄,機械運作的大量排放,無一不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行為。低碳農業旨在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開發并使用生物農藥,恢復生物多樣性;減少化肥的施用,進行高效綠色的生產,保護生態環境;優化能源結構,發展新型和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節能減排,遏制全球氣候變暖。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估計,低碳農業系統可以抵消約80%的因農業過程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無需生產工業化肥,每年可為世界節省1%的石油能源,而不再使用這些化肥還能降低30%的農業排放[15]。資源與環境是農業生產的自然基礎,資源匱乏、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等現實困惑都要求人們必須發展低碳農業。低碳農業的本質是生態農業經濟,建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有利于緩解資源貧乏的壓力,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16]。
2 低碳農業發展現狀
根據《哥本哈根協議》,世界各國陸續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或通報了2020年的減排目標。其中挪威承諾的減排幅度最大,目標是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30%~40%;美國承諾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日本承諾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10%~20%;俄羅斯承諾到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25%;中國承諾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將單位GDP的CO2排放量減少40%~45%;印度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20%~25%[17]。為實現這些目標,各國不僅在工業上做出了重大改革和調整,而且對農業也給予了空前的重視和關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新近指出,對地球大氣最近250多年觀察表明,溫室氣體主要來源于化石燃料、土地開發和農業生產3個方面,而且農業過程占總排放量的1/3左右,其中約25%為CO[18]。2
農業是處于環境與發展沖突最前沿的一個基礎產業[19],它既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其本身也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影響[20]。對此,世界各國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開展了各種形式的低碳農業發展模式。印度克什米爾地區開展的自適應農業模式,不但可以減少農業投入和生產成本,提高農用地生產力,還可以減緩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21];美國和加拿大倡導的固碳農業,不僅可固定大氣中的CO2和CH4,減少土壤碳的投入,而且還有利于提高生產力[22-23];以奶業聞名于世的新西蘭,采用家庭式季節性有機放牧模式,機械和能源投入相對較少,極大地節約了生產成本,高效低碳,使其奶制品出口達90%,奶產業躋身于世界前列[24];南美諸如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國,廣泛建立種植園,生產木材,以生物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同時也減輕因造紙等行業對熱帶雨林的破壞,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5];以色列是世界上水和耕地資源最匱乏的國家之一,但其采用先進的理念、管理和技術,開展節水農業和精致農業,不僅自給自足,其農產品還出口其他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資源節約型農業的典范[26];墨西哥低碳農業發展的研究認為,生物燃料的利用是農業部門對低碳的最大貢獻[27]。之外,還有研究表明,與農業相關的減排,主要來自于反芻動物CH4排放量的減少,其次為水稻(Oryza sativa)的CH4排放和化肥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更有學者[28-30]提出,發展低碳經濟既是技術經濟問題,還是制度與體制問題。
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未來能源需求的膨脹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面臨巨大壓力[31]。我國不僅是世界上農業氣象災害多發地區,各類自然災害連年不斷,農業生產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而且也是一個人均耕地資源占有少、農業經濟不發達、適應能力非常有限的國家。現代農業的高投入、高能耗,雖然可大幅提高產量,但代價沉重,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四大危機”:環境污染危害、農產品殘毒危害、受能源制約的危害、農業不可持續發展的危害。據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信息通報》統計數據顯示[32],“我國每年生產農用化學品、化學種植業、化學畜禽水產養殖業折合消耗標準煤1.4億t,相當于排放CO212.54億t,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34.32%。”面對這一嚴峻形勢,在“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以保障經濟發展為核心,以節約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為重點,以科學技術進步為支撐,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新的貢獻”的指導思想下,制定了“通過繼續推廣低排放的高產水稻品種和半旱式栽培技術,采用科學灌溉技術,研究開發優良反芻動物品種技術和規模化飼養管理技術,加強對動物糞便、廢水和固體廢棄物的管理,加大沼氣利用力度等措施,努力控制CH4排放增長速度;通過繼續實施植樹造林、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資源保護、農田基本建設等政策措施和重點工程建設,努力實現森林覆蓋率達到20%,力爭實現碳匯數量比2005年增加約0.5億t CO2”的農業溫室氣體控制目標[33]。據此目標,開展了以“節能減排,恢復生態”為核心的低碳農業發展模式。通過發展資源能源節約替代、集約復合種養、生態旅游、高效減災及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等多種低碳型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以及免耕、節水、增施有機肥、病蟲害生物防治、新型農作物育種等技術措施的推進,實現農業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突破,增加科技對農業發展的貢獻率和比較效益,應對未來我國農業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34]。
3 草地生態系統中的碳
草業科學是研究草地農業生態系統的科學,草業是農業的一種特殊形態。它涵蓋了從草地資源到草地農業生產的草地農業的生態與生產的全過程的理論和技術,是大農業科學的一個分支[35]。草地生態系統作為全球分布最廣的生態類型,是農業自然自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能量流通與物質循環對全球氣候變化具有重大影響[36-37]。草地擁有強大的碳匯功能,草地對土壤碳匯的影響主要通過增加土壤碳庫和植被碳庫來實現。草地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大氣中的CO2固定并將其以有機物的形式儲存在植被和土壤中,對于固碳減排,緩解全球氣候變化有重要貢獻[38]。因此,發展低碳農業不能忽視草地生態系統中碳的作用。據德國全球變化咨詢委員會(WBGU)估計[39],全球陸地生態系統的碳儲量有46%在森林中,23%在熱帶和溫帶草原中。世界永久性草地面積為24億hm2,約為全球陸地總面積的1/5[40],我國擁有各類天然草原近4億hm2,約占國土面積的41.7%[41]。根據IPCC[42]的報告,草地固碳量為1.3t·hm-2·a-1,以此推算,我國草地每年可固碳約5.2億t,折合CO219億t,可抵消我國全年CO2排放總量的30%[43]。草地碳匯不僅功能強,而且還擁有自己的特色。據Post等[44]對全球草原生態系統碳儲量所做的估算,平均碳儲量約為569.6Pg,其中植被層為72.9Pg,土壤層為496.6 Pg。Ni[45]應用碳密度法并結合相關調查數據對我國草原碳儲量進行了估算,數據顯示,我國草原總碳儲量為44.09Pg,其中植被層為3.06Pg,土壤層為41.03Pg,即地下部分的碳儲量遠大于地上部分,說明草原生態系統與森林等其他陸地生態系統不同,沒有固定而明顯的地上碳庫,所固定的碳絕大部分貯存于地下土壤中[46-47]。這就意味著,當遭遇火災等大規模毀滅性災害時,草原生態系統釋放到大氣中的碳僅為其固定的碳的很少一部分,遠小于其他陸地生態系統。這是草原生態系統碳匯的一大特色,也是草地生態系統實現固碳減排的一大優勢。
草地生態系統碳循環過程主要包括碳素的輸入,地上、地下生物量中的碳固定,土壤中有機碳的貯存,土壤呼吸作用(包括土壤微生物呼吸、活根系呼吸和土壤動物呼吸等生態過程)中碳的排放等環節。此過程受氣候變化及人類活動的極大影響。在各種陸地生態系統中氣候變化將首先對草地生態系統產生影響,其中降水和溫度季節配置方式的潛在變化對草地生物學過程(如植物生產力、養分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產生的影響比各氣候要素總量的變化更加重大。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對草地碳循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作為碳素輸入主要途徑的初級生產力主要取決于溫度和降水量的大小及其季節配置。因此,溫度和降水量,尤其是其季節配置方式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到草地初級生產力的規模和碳素輸入量的水平。溫度和降水量是造成土壤有機質分解速率的主要因素,氣候變化又會對草地土壤中碳素的貯量產生重大影響,這對于整個碳循環而言尤為重要[48]。
氣候變暖增加草地土壤水分蒸發,促進植物蒸騰作用[49-50],加劇草地退化,由此產生的水分脅迫降低植被的固碳能力,從而導致草地生產力下降[51]。降水增加則改善土壤的水分供給條件,增強光合速率,從而提高生產力,增加固碳量。人類活動如草地開墾、過度放牧、火燒等對草地碳循環過程有明顯的影響。草地開墾主要導致土壤中有機碳的大量損失。研究表明[52-53],草地開墾為農田后會損失掉土壤中碳素總量的30%~50%,大量損失發生在開墾后的最初幾年,20年后趨于穩定。放牧是最常見的草地利用形式,也是人類對草地施加的最為廣泛的干預方法。過度放牧是天然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草地退化導致生產力下降和土壤有機碳減少;過度放牧可促進草地土壤的呼吸作用,從而加速碳素由土壤向大氣中的釋放。就全世界草地而言,在過度放牧下地上凈初級生產力中僅有20%~50%能夠以凋落物和糞便的形式歸還土壤[54]。降低牧壓、退牧還草、草原圍欄、禁牧休牧輪牧等保護性管理措施能有效遏制草地退化,逐步提高草地固碳能力[55-56]。
4 結語
低碳農業是農業發展歷史上的又一次革命。低碳農業不僅是一個是理論體系,也是一個技術體系,更是一種思想。盡管我國在低碳農業領域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從實踐的范圍來看,都不夠深入。尚存在農業生產方式不盡合理、低碳意識有待提高、理論創新緩慢、發展模式有待豐富的問題;低碳技術滯后,新型技術有待研發等問題尚待解決。此外,我國草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研究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現有的研究雖然為農業生態系統碳循環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與低碳農業實踐的結合并不十分緊密,有關碳循環的研究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因此,要確保低碳農業的順利發展,需要切實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政府的主導作用、技術的支撐作用和國際合作的橋梁作用。我國要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探索發展低碳農業的模式和思路。發展低碳農業不僅是我國農業本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選擇。所以,應當把發展低碳農業作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內容,從而深化對低碳經濟的認識,并完善低碳經濟的體系,進而為我國順利實現高碳農業向低碳農業的轉型奠定堅實的基礎。
[1]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Energy white paper,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R].London:TSO,2003.
[2] 孫翠花.中國低碳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J].世博直線,2010(5):34-35.
[3] 張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國:地位、挑戰與戰略[J].中國人口與資源與環境,2008,18(3):0001-0007.
[4] 李明賢.我國低碳農業發展的技術鎖定與替代策略[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1(2):1-11.
[5] 賀順奎.低碳農業: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J].貴陽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5(3):39-41.
[6] 李志萌.我國低碳農業發展探討[J].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3(4):22-25.
[7] 季學明,季學生,林建永.我國經濟轉型與發展低碳農業的宏觀思考[J].農業展望,2010,41(9):21-26.
[8] 黃璜.我國低碳農業發展現狀與對策[J].作物研究,2010,24(4):0215-0217.
[9] 孔箐鋅,靳佩貞.低碳背景下的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思考[J].中國農學通報,2010,26(21):297-300.
[10] Niggli U,Flieβbach A,Hepperly P,et al.Low green-house gas agriculture: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otential of sustainable farming systems[R].Rome:High-Level Conference on World Food Security,2008.
[11] 李曉燕,王彬彬.四川發展低碳農業的必然性和途徑[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103-106.
[12] Balat M,Balat H.Recent trends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ethanol fuel[J].Applied Energy,2009,86:2273-2282.
[13] 孫超.關于低碳農業的幾點思[J].農業經濟,2010(8):23-24.
[14] 楊中柱.發展我國低碳農業的思考[J].作物研究,2010,24(4):252-257.
[15] 朱小雯.氣候變化威脅糧食安全,低碳農業應運興起[J].農村經濟與科技,2009(10):57-58.
[16] 王昀.低碳農業經濟略論[J].中國農業信息,2008(8):12-15.
[17] 鄭爽.《哥本哈根協議》現狀與氣候談判前景[J].中國能源,2010,32(4):19-23.
[18] 曾以禹,陳衛洪,李小軍.國外發展低碳農業的做法及其啟示[J].世界農業,2010(10):59-63.
[19] 駱世明.中國多樣的生態農業技術體系[J].自然資源學報,1995,10(3):225-231.
[20] Lippert C,Krimly T,Aurbacher J.A Ricardi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in Germany[J].Climatic Change,2009,97(3):593-610.
[21] Bangroo S A,Kirmani N A,Ali T,et al.Adapting agriculture for enhancing eco-efficiency through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gro-ecosystem [J].Researc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2011,2(1):164-169.
[22] Morgan J A,Follett R F,Allen L H,et al.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gricultural l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2010,65(1):6A-13A.
[23] Bolinder M A,Janzen H H,Gregorich E G,et al.An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annual carbon inputs to soil for common agricultural crops in Canada[J].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7,118:29-42.
[24] Rosin C,Campbell H.Beyond bifurcation:Examining the convention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New Zealand[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9,25:35-47.
[25] Yevich R,Logan J A.An assessment of biofuel use and burning of agricultural wast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2003,17(4):1095-1135.
[26] Roman L M,Maas F D.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to Israel’s agriculture[J].Israel Agriculture,1980(4):1-4.
[27] Johnson T M,Alatorre C,Romo Z,et al.Low-carbon development for Mexico[M].Washington DC: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0.
[28] Simon S,Wiegmann K.Modelling sustainable bioenergy potentials from agriculture for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J].Biomass and Bioenergy,2009,33:603-609.
[29] Walker K J,Preston C D,Boon C R.Fifty years of change in an area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plant trait responses to habitat modification and conservation,Bedfordshire,England[J].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009,18(13):3597-3613.
[30] McHenry M P.Agricultural bio-char production,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and farm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Western Australia:Certainty,uncertainty and risk[J].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9,129:1-7.
[31] 唐海明,湯文光,肖小平.中國農田固碳減排發展現狀及其戰略對策[J].生態環境學報,2010,19(7):1755-1759.
[32]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信息通報[R].2004.
[33]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R].2007.
[34] 趙其國,錢海燕.低碳經濟與農業發展思考[J].生態環境學報,2009,18(5):1609-1614.
[35] 任繼周.草地農業生態系統通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6] 鐘華平,樊江文,于貴瑞.草地生態系統碳蓄積的研究進展[J].草業科學,2005,22(1):4-11.
[37] 周濤,史培軍.土地利用變化對中國土壤碳儲量變化的間接影響[J].地球科學進展,2006,21(2):138-143.
[38] Schimel D S,House J I,Hibbard K A,et al.Recent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carbon exchange by terrestrial ecosystems[J].Nature,2001,414:1669-1721.
[39] WBGU Special Report.The accounting of biological sinks and source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A step forwards or backward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1998.
[40] Scurlock J M O,Hall D O.The global carbon sink:a grassland perspective[J].Global Change Biology,1998(4):229-233.
[41]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畜牧獸醫司,全國畜牧獸醫總站.中國草地資源[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42] IPCC.The Scientific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43] 劉加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決不能忽視草原的重大作用[J].草地學報,2010,18(1):01-04.
[44] Post W M,Peng T H,Emanual W R,et al.The global carbon cycle[J].American Scientist,1990,78:310-326.
[45] Ni J.Carbon storage in grasslands of China[J].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2002,50:205-218.
[46] 章力建,劉帥.保護草原——增強草原碳匯功能[J].中國草地學報,2010,32(2):1-5.
[47] 閆玉春,唐海萍,常瑞英.長期開墾與放牧對內蒙古典型草原地下碳截存的影響[J].環境科學,2008,29(5):1388-1393.
[48] Suttie J M,Reynolds S G,Batello C.Grasslands of the World[R].Rome:FAO,2005:1-16.
[49] Huntington T G.Evidence for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lobal water cycle:Review and synthesis[J].Journal of Hydrology,2006,319:83-95.
[50] Wan S,Luo Y,Wallace L L.Changes in microclomate induced by experimental warming and clipping in tallgrass rairie[J].Global Change Biology,2002,8:754-768.
[51] 李鎮清,劉振國,陳佐忠,等.中國典型草原區氣候變化及其對生產力的影響[J].草業學報,2003,12(1):4-10.
[52] Canadell J G.Land use effects on terrestrial carbon sources and sinks[J].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2002,45:1-9.
[53] Yao M K,Angui P K T,KonatéS,et al.Effects of land use type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dynamics in Mid-West C?te d’Ivoire[J].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2010,40(2):211-222.
[54] Ingram L J,Stahl P D,Schuman G E,et al.Grazing impacts on soil carbon and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a mixed-grass ecosystem[J].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2008,72(4):939-948.
[55] 華娟,趙世偉,張揚,等.云霧山草原區不同植被恢復階段土壤團聚體活性有機碳分布特征[J].生態學報,2009,29(9):4613-4619.
[56] He N P,Yu Q,Wu L,et al.Carbon and nitrogen store and storage potential as affected by land use in a Leymus chinensis grassland of Northern China[J].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2008,40:2952-2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