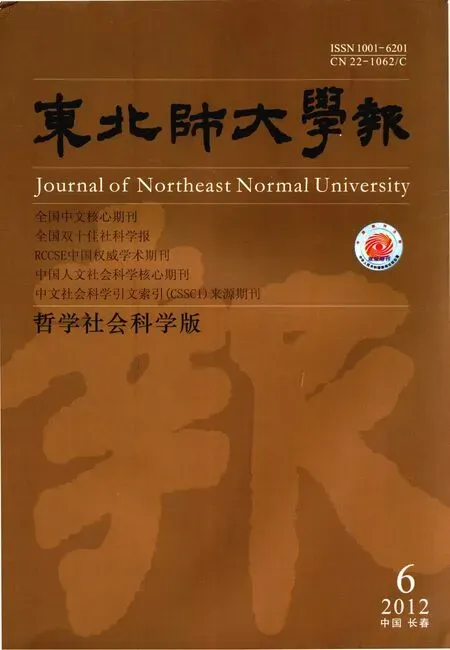英國19世紀小說中“慈善”一詞的語義轉換研究
龍瑞翠,王立河
(1.燕山大學外語學院,河北 秦皇島066004;2.東北財經大學 國際商務外語學院,遼寧 大連116000)
工業革命使轉型性成為19世紀英國社會主要特征,各種思想、概念內涵發生著急劇變換。小說作為該時期比其他任何有關人類經驗的記載都更深刻、更早捕捉到問題意識的“史書”[1],以私語化的“小敘事”撕開所謂正史的宏大敘事表層,先鋒地書寫壓迫在人們心頭的、對這些轉換的復雜體驗。作為19世紀英國社會論爭焦點[2]的“慈善”也不例外地成為小說的書寫對象。在其中我們能清晰認知到“慈善”概念語義內涵的轉換過程。
一
作為基督教國家,英國慈善傳統源遠流長。但19世紀之前,慈善話語主要發生在鄉村世界,且主要基于《伊麗莎白濟貧法》(1601)和《斯品漢姆萊法》(1796)的封建家長制話語模式。在該模式中,經常會有某些地主、貴族把慈善當成身份義務,為彰顯其高貴身份與仁慈,對教區內窮人布施,這一個別特征被不斷重復化、類型化,形成群體性特征,即地主貴族喜歡對窮人布施,這一群體性征的高重復性實踐促使其被語言化、背景化成為特征詞匯——慈善,進而被語用法“固化”[3],即只要“慈善”一詞被激活,話語雙方就會自動形成歸約性認知框架:任何貴族都可能、應該會對窮人施行慈善,并促生有效救助結果。狄更斯作為該時期最強力文化代言人在20多年小說創作中一直不懈闡釋著這一默認性框架推理。以其最全面、成熟探討慈善真意的《遠大前程》(又譯《孤星血淚》)為例,雖然19世紀中期英國已進入典型工業社會,但在農村,傳統慈善文化認知框架依然留存在人們的認知思維中。村民們都期望能和地主貴族郝薇香拉上關系,以獲其資助。皮普萬幸蒙召,村民一片嘩然,都認為她一定是要資助他了。這一群體認知促使年幼的皮普產生極其主觀的心理預設:自己就是那個蒙獲資助的幸運兒。基于這一心理圖景,他在聆聽、解讀郝薇香的話語時充滿了受恩的期待與趨向性,并默認性推理對方也完全是為此目的。因此在接收、理解她的話語時只能聽見想聽的,并在其后處理與她有關的所有信息時都極具偏向性。
然而自19世紀初始,貴族階級經濟、政治地位不斷下滑,文化絕對統治地位也不斷受到威脅與挑戰。而城市化的全速推進又使大量鄉村居民涌入都市尋找更高的自我感與話語權力。傳統慈善話語模式迅速解體,家長制慈善語義漸失其在社會話語詞匯群中所具有的意義實在,呈現出“實詞虛化”的狀態——郝薇香的行動及其話語效果就隱喻了該弱化過程。雖然她已“從肉體到靈魂,從內心到外表,稀里嘩啦一古腦兒都垮掉了”[4]47,然而正是這一敗落貴族卻因“慈善”而在無聲中主宰了包括皮普、艾斯黛拉在內很多人的命運。雖然她收養孤兒艾斯黛拉的初衷不無慈善意味,卻又耽于舊日情仇,使之成為自己復仇的犧牲品,從而扭曲了慣常貴族為彰顯自我仁慈品性與身份對窮人施與恩惠的涵義。雖然最后她痛悔前行,但傷害已經造成,她不僅改變不了受惠者的命運,甚至還使之陷入萬劫深淵。如果說這一慈善災難并非其本意,那她為一己之私而有意誘導皮普深陷誤讀泥潭則實屬惡意的非慈善之舉。我們知道語義本身具有方向性映射特征,讀者正是通過這一特征最終整合成新心理空間,獲得對抽象或未知事物的識解。因而當具有方向性映射特征的傳統慈善語義再遭遇“話語發出者”郝薇香的有意誤導,皮普必然對其話語產生先在性預設心理空間,并偏差性識解這些話語,從而深信是她資助他成為上等人,并深陷其中幾喪本性。基于此,我們說,傳統大家長制慈善語義已發生極大弱化:郝薇香試圖實踐傳統慈善語義而施行的慈善事實已無法像曾經那樣產生事實救助作用,而其通過語義識解的有意誤導所營造的慈善救助虛幻卻又如此諷刺地令人迷失自我。
事實上社會人群對慈善語義默認性推理所導致的錯位識解不僅影響其對貴族階級施行慈善的偏執性心理期待,還促使他們在可能情況下極力模仿貴族的慈善話語與行為以確證自己的社會身份。例如很多中產階級出身、一心向上爬的人物都極力模仿貴族慈善行為以贏得社會身份認可。其中一項就是參加、舉辦各種義賣會等,進行慈善攀比,以彰顯自己的仁慈。換言之,慈善已成為一種身份話語符號。這一符號化在薩克雷的《名利場》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富商奧斯本雖然本性冷酷無情,卻經常舉家到最有名的圣·保羅教堂探望孤兒,因為慈善施舍是一種身份高貴、賢德仁慈的象征,只要能提升身份,英國商人絕不會沒有錢使[5];貪婪、吝嗇的別德太太為了博得賢德夫人的美譽,經常參加各種義賣會;吝嗇的小畢脫通過資助各種慈善事業來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鋪路。基于此我們說,雖然傳統封建大家長制慈善語義已經被“實詞虛化”,然而在其徹底消失之前,還會通過各種形式重新組合、分布、轉移等語義弱化方式影響著語域內人群對慈善的認知與思考方式。
二
傳統慈善語義的“實詞虛化”必然意味著新語義實體的產生:隨著中產階級社會地位提升,功利主義慈善語義日益由邊緣義走向中心義,從附庸變成主人,實現其“虛詞實化”的過程。具體而言,這一轉換至少涉及三個范疇。
其一,利益交換日益成為慈善語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商業價值觀對傳統封建家長制及宗教文化價值觀的鯨吞蠶食,人們一直篤信的通向幸福之路的信條崩解[6]。人們不再相信傳統貴族階級為彰顯身份的無償救助以及基督教傳統中施恩莫望報所帶來的幸福感,轉而相信只有互惠的“慈善”才能帶來幸福。在《遠大前程》中,大部分人物身上都能找到這一慈善闡釋。皮普的姐姐是小說中第一個以這一特征出場的人物。在中產階級功利主義慈善語義日居中心的語境之中生存,其對慈善的認知、期待、施行都基于功利主義互惠的心理空間。因而她時時強調自己的慈善之心,甚至還把撫養親生弟弟當成一種為慈善之故的行為,而不是因為他是親弟弟,認為并時常強調自己行慈善應該獲得回報。如果說《遠大前程》中慈善施為者所期待的回報還具有模糊不確定性,那么到《苔絲》,慈善已變成施為者換取直接、赤裸裸利益的手段:杜伯維爾兩次對孤立無援的苔絲伸出援手施行“慈善”,均以極度自私的功利主義——滿足自我欲望為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
其二,以工具理性手段對“泛化人”施行慈善成為社會慈善語義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泛化人”即將慈善對象“人”進行簡單化處理,當成標準化一的群體、空洞的抽象符碼,而忽略了人作為個體存在的具體需求與價值。這尤其體現在以功利主義為信條的“慈善事業”中。工業革命使中產階級憑借機器的無限力量占據政治經濟的主流地位,因而他們中很多人都堅信機器規則——工具技術性、機構化、職業化、數據化等定然也能使他們迅速獲取文化主流地位。于是一種建基于機器信條之上的唯理主義慈善事業應運而生以取代傳統強調貴族品德的“窮人慈善”[7],實現密爾所說的“使所有人看起來都差不多,并用相同的標準和準則來規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8]1。因而該時期出現了杰里比和佩蒂格(《荒涼山莊》)、莎吳塞唐(《名利場》)等大批慈善職業者。但他們從根本上說卻是“偽”慈善者,因為他們未能真正走進貧民世界,了解貧民真正所需,而是篤信只要簡單機械地分發報紙、書刊、傳單等給貧民窟的工人、流浪者、因窮困潦倒而行竊的犯人等,便能幫助窮人解脫困境,實現社會和諧。然而這一過度注重形式、追求速度,將慈善對象抽象化為沉默、機械接受指令的群體的慈善事業從根本上缺失了靈魂對靈魂的呵護,因而注定是要失敗的——該時期小說及各種公允的社會調查報告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只有像《瑪麗·巴頓》中的礦場老監工那樣多年如一日地實質性幫助難民、改過自新的犯人的慈善者才是真正的慈善者,其慈善行為才能真正產生效用。
其三,以工具理性為手段對具體人施行有效慈善救助成為部分中產階級人群眼中慈善語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尤其體現在狄更斯后期小說對中產階級功利主義慈善內涵(尤其是工具理性在維護、實施慈善時的有效性)的反思中。這一反思最鮮明體現在他對新興技術中產階級慈善話語的處理中。《遠大前程》中的律師賈格斯是典型的技術中產階級新貴,對技術極其嚴謹,對待嫌疑犯,他不會像別人一樣充滿偏見,而是極力追求證據。雖然他外表看來極其冷酷無情,總是竭力撇清自己的人性溫情面,強調自己接案子是為了錢,可是他在巴索落木圍場的言語卻無聲地表明,他在盡自己最大能力保護窮人免受非正義的傷害。而且看著許多孩子因為社會慈善施為無效而被迫犯罪,走向人生的毀滅,他極度痛心疾首,一旦有機會便毫不猶豫地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人脈搭救他們,是他使艾斯黛拉——也許還有其他很多孩子不至流落街頭乃至餓死,是他收留了神志失常的茉莉,讓她不至流離失所。可以說,在他冷酷的面具下是一顆珍貴的菩薩心腸。
三
這一時期的慈善語義不僅呈現出“實詞虛化”、“虛詞實化”的語義轉換狀態,而且由于社會語境的變化還延擴出新的語義層面:既包括舊有語義的新變體,也包括全新語義的進入。
首先,取傳統家長制慈善與新興功利主義慈善各自之所長形成的家庭式“安靜”慈善成為該時期慈善語義的重要部分。我們知道,語義的產生其實是一個程式編碼的過程,這一編碼決定了讀者對該語義關聯概念陳述的闡釋,因而“當這一程式編碼所拘囿或導向的言語闡釋達到一定頻率時”[9],它就會“自動覆蓋其他層面,乃至成為唯一的可解碼語義”[10]。因此,隨著原本處于邊緣的成分即中產階級功利主義慈善語義成分進入范疇,并被不斷重復使用,成為人們自動接收的語義成分,從而覆蓋語義原有組成成分尤其是核心成分——家長制慈善語義。但這不等于說舊有慈善語義成分的徹底消失,而是可能通過重新范疇化,最終融于另一范疇,這便是廣為該時期作家接受、宣揚的家庭式“安靜”慈善語義成分的進入。正是由于洞悉了家長制慈善的非功利性與松散無效性、功利主義慈善的有效性與情感冷漠,無論是穿梭于上流社會的薩克雷、自幼失母的夏洛蒂還是偏于宗教的里德等都在其小說中一遍遍地渴望、呼喚著源自家庭的、安靜有效的慈善救助。因此有了《簡·愛》中細膩描畫收留簡的林間小屋的溫暖壁爐與溫馨氣氛,《名利場》中沉靜但樂善好施且不亂施救助的杜賓等。對于狄更斯這樣自小缺失家庭溫暖的作家而言更是如此。從他最初的《博茲札記》、《霧都孤兒》,到《圣誕頌歌》、《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乃至未完之作《艾德溫·德魯德之謎》,我們都能看到他對溫暖壁爐與溫馨家庭生活式慈善救助的情有獨鐘。因此他讓喬(《遠大前程》)收養孤兒皮普,并用自己溫暖、有力的臂膀使皮普能安然在溫暖壁爐旁長大,使久受城市商業文化之病的皮普得以康復,讓飽嘗人間滄桑的馬格韋契在生命末端體味“兒子”皮普的呵護;塑造溫柔的埃斯特(《荒涼山莊》),通過她將城市帶回到以人為本位的鄉村莊園,用人性的良知和心靈的力量去溫暖、減輕飽嘗人間滄桑的喬的苦難。總言之,雖然這些小說中還羅列了眾多其他慈善內涵,然而通觀全局,作家無一例外地都將家庭式“安靜”慈善置于其他語義層之上,將之塑為慈善的靈魂,因為它既具有明顯有效性,又閃爍著人性的光芒。
其次,全新語義“海外慈善”進入該時期慈善語義內涵中。所謂海外慈善涵括了慈善的海外輸出與來自海外的慈善。這一時期,英國社會熱衷于海外慈善,各種以海外慈善為名頭的慈善基金、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英國作為一個強國,雖然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卻已迅速變得富裕強大起來,因而“誰要是懷疑我們的東西不是天下第一,我們的人不是蓋世無雙,誰就是大逆不道”[4]125。因此在國內施行慈善早已過時,施行海外慈善以“拯救”更多需要拯救的人才是當務之急。這一思想與狄更斯等人所極力宣揚的家庭式“安靜”慈善思想內涵是嚴重相左的,因而必然為小說家們所輕視,乃至為他們所百般嘲諷——如《荒涼山莊》、《名利場》、《月亮寶石》、《黑暗的心》等將之稱為不切實際的、望遠鏡里的慈善。然而生活在一個“無限浪漫的時代”[11],作家對海外世界又不可避免地充滿了浪漫主義情懷,因此又極度渴望“來自海外的”、拯救工業英國于沉淪境地的慈善,如《老古玩店》中千呼萬喚終究還是遲來的海歸紳士。而在《遠大前程》中,正是殖民地這片“純凈之土”滌盡了倫敦帶給人們的骯臟,獲得了重生。馬格韋契還有他的大洋洲東家就是這樣獲得重生的:在殖民地,他們不再是社會渣滓,而是成為混得很不錯的體面人,并有了實現慈善“反哺”的機會——從海外對英國國內施行慈善。由此,海外殖民地成了拯救英國的恩主。然而皮普與施恩者馬格韋契在話語權上的顛倒,以及馬格韋契被捕、財產被沒收導致其慈善施為結束也表明:雖然慈善行為與話語的發出者源自殖民地,但真正支配話語權的依然是英國本土。
總言之,社會的急劇轉型使19世紀英國小說慈善語義發生劇烈轉換:傳統家長制慈善由實體詞變成符號代碼,而原本處于邊緣的中產階級功利主義慈善語義日益演變為社會慈善語義的主流范疇,承載著社會慈善的實體含義。但由于中產階級是一個正在形成并不斷調整階級內部階層構成的新興階級,其作為一個階級的價值觀念內涵也在不斷調整中,因而呈現出階級內部慈善語義的多重性,甚至在階級內部對于同一慈善語義也可能持矛盾態度。與此同時,殖民發展所帶來的全球共生影響還為慈善一詞帶來新的語義層面:涵括了對海外施行慈善與來自海外的慈善救助。而透過這一語義轉換,我們可以瞥見的是作者深邃的歷史意識:他們從精神實質上對歷史真實的把握,對傳統文化、工業文明中諸種文化價值觀的深刻反思,對“從混亂中建構起新文明秩序”[12]的渴望與努力。
[1]R.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3:191.
[2]F.Christianson.Philanthropy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Fiction[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7:12.
[3]P.Hopper & E.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35.
[4]狄更斯.孤星血淚[M].王科一,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5]薩克雷.名利場[M].楊必,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152.
[6]N.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M].New York:Viking Penguin,1998:198.
[7]M.Roberts.Head versus Heart[A].Edited by H.Cunningham &J.Innes.Charity,Philanthropy and Reform[C].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66.
[8]J.Mill.From On Liberty[A].Edited by M.H.Abram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The Victorian Age[C].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Inc,2000:1155.
[9]R.LaPolla.Why Languages Differ[A].Edited by D.Bradley,etc.Language Variation[C].Canberra:Pacific Linguistic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3:135.
[10]S.Nicolle.A Relevance Theory Perspective on Grammaticalization[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8,9(1):23.
[11]B.Disraeli.Introduction[A].Edited by M.H.Abram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The Victorian Age[C].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Inc,2000:1049.
[12]S.Marcus.Dickens from Pickwick to Dombe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