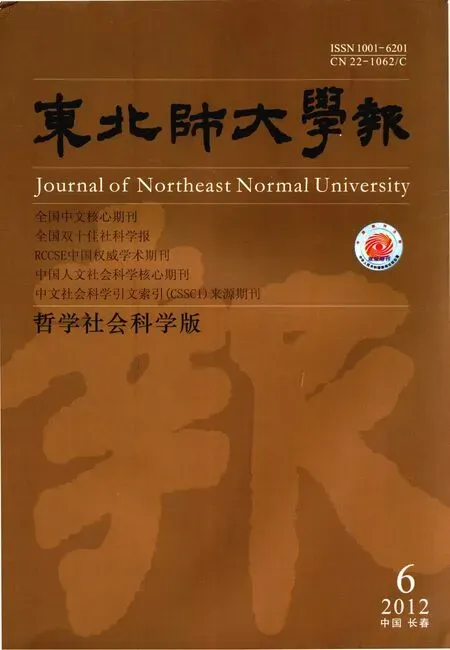歷史小說《紅王妃》的別樣性
劉國清,崔秀范
(1.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2.東北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由于明確宣稱要秉承“現實主義”風格,對實驗小說毫無興趣[1],英國當代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曾被認為是當代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一面旗幟。雖然德拉布爾“對現代主義的實驗技巧和主觀表達持否定態度”[2],但她沒能將傳統的現實主義風格堅持到底。在明確表示將堅持現實主義風格之后沒過兩年,她的第5部小說《瀑布》(1969)就放棄了“寧可尾隨一個偉大的傳統”的立場而投入“一個新潮流”中,“《瀑布》是一部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反傳統的小說。”“它糅合了傳統主義和實驗主義,讓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替敘述。”[3]2101980年面世的小說《中年》出現了非線性敘事。這種非傳統的敘事使《中年》頗像一只萬花筒,將倫敦不同地區的眾多人物在一天內的生活以紀實體小說的形式走馬燈似的拋給讀者,小說從一個鏡頭猛地轉向另一個鏡頭,從一個人物快速轉到另一個人物,令讀者目不暇接,對讀者想象力構成巨大挑戰。這種既有現實主義風格,又有現代小說技巧的小說被英國當代小說家和文學理論家大衛·洛奇冠以“后現實主義”小說的稱謂。不過,在推出《紅王妃》之前,雖然德拉布爾現實主義小說中有了越來越多的現代主義甚至后現代主義的成分,但其小說并沒有偏離現實主義小說太遠。《紅王妃》很是不同。盡管評論界認為這是一部歷史小說,但作者本人卻予以否認:“這不是一部歷史小說”,而是“一部風格別樣的小說。”[4]《紅王妃》究竟是不是歷史小說,它的別樣性又體現在何處?
一
在《曼布克獎與當今英國歷史小說熱》一文中,筆者指出了獲英國曼布克獎歷史小說的六大特征[5],其實這也是自上世紀60年代復興的英國歷史小說的特征。無疑,曼布克獎推動了英國當代歷史小說的發展,但當代英國歷史小說的迅猛發展有其自身的原因,曼布克獎只是為其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展示平臺而已。作為歷史小說的故鄉,英國有著深厚的歷史小說土壤,既有創作傳統,也有很大的讀者群。對大英帝國往昔輝煌的懷戀,帝國崩解后來自前殖民地作家對殖民統治的反思,對一戰、二戰殘酷與血腥的歷史反思,新歷史主義興起而引發的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對“小說之死”進行回擊而進行的小說實驗,以及尋找傳達人性關懷理念載體的文學實踐,所有這些因素促發了當代英國歷史小說的復興與輝煌。《紅王妃》正是在這股潮流下孕育而生的。
不知是德拉布爾在故弄玄虛,還是連她自己也難以給這部心愛之作歸類或定類,《紅王妃》無疑是一部雜糅之作,這從小說的整體布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小說分為三部分:古代篇(165頁)、現代篇(148頁)、后現代篇(36頁)。它兼具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還有后現代主義的特征,但主體還是歷史小說。《紅王妃》古代篇講述了18世紀朝鮮獻敬王后洪玉英(Hyegyong Hong)的宮廷生活經歷,占了小說近一半的篇幅;現代篇講述了被王妃附體的英國女學者芭芭拉·霍利威爾博士到韓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期間的經歷,其中最主要的是與學術權威荷蘭學者占·范喬斯特先生的交往經歷;后現代篇則是芭芭拉為完成占·范喬斯特先生的遺愿與范喬斯特的太太維維卡共同培育領養的中國女孩陳建依的故事。它既有依據所謂正史的歷史敘述,也有豐富的歷史想象;既有對歷史的透視,又有強烈的現實的人文關懷;既有對異域人性的關照,又有對本土生存的思考。雖然《紅王妃》的現代篇和后現代篇直接講述王妃及當時歷史的部分極少,但這兩部分卻都與王妃,確切地說,是與王妃鬼魂的意愿有關,因而也難以撇清與這段朝鮮宮廷史的瓜葛。《紅王妃》自然應列入歷史小說之列。可作者為什么拒絕承認自己創作的《紅王妃》是歷史小說?
上世紀60年代英國歷史小說開始復興,但由于長期以來學界一直將歷史小說歸入通俗文學之列而缺少對其創作藝術的重視與研究,德拉布爾不希望自己的《紅王妃》劃入歷史小說之列,就是不想讓《紅王妃》落入眾多歷史小說在文學批評界曾經歷過的命運。雖然在英國文學史上鮮有歷史小說劃入文學經典,但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興起而今繁盛不衰的英國歷史小說不僅聲勢浩大,而且與傳統的歷史小說有著很大的不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股英國歷史小說熱潮中的很多歷史小說理應劃入嚴肅文學之列。這不僅可以從這些歷史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上加以佐證,更可以從最具指標性的曼布克獎得到確認。素有英國文學晴雨表的曼布克獎自創設以來一直以推介最優秀的嚴肅小說為己任,其評選的獨立性、公平與公正性為其贏得了極佳的口碑,有“英語文學界的諾貝爾文學獎”之譽。在曼布克獎42年的評選史上,共有16部歷史小說獲獎,占總獲獎量的三分之一還強,這充分說明了當代英國歷史小說在當代英國嚴肅文學領域的特殊分量和顯著地位。當然,也有反對聲音,認為歷史小說屢獲殊榮,是英聯邦文壇的不幸,但這種指責既沒有阻擋住英國歷史小說屢獲大獎,而且也不公允,是傳統的偏見在作怪,因為此英國歷史小說非彼英國歷史小說,不能總是帶著一副老眼鏡去看問題。隨著英國當代歷史小說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重視與研究,德拉布爾雖然沒有撤回自己過去的聲明,但她已默認,或者說已變相承認《紅王妃》是一部歷史小說。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當被問及是否還否認《紅王妃》是一部歷史小說時,德拉布爾雖未給予正面回答,但她卻談到,《紅王妃》主要直接選用朝鮮紅王妃歷史回憶錄和大量相關的朝鮮歷史文獻,而且她還特別提到,雖然《紅王妃》有虛構的成分,尤其是虛構了一些宮廷生活情節,“但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物。”[6]德拉布爾的回答完全可以看作是她認可了學界對《紅王妃》是歷史小說的定位。
二
但《紅王妃》絕非是一般的歷史小說,它是作者苦心孤詣的實驗之作。德拉布爾雖然曾發誓堅守文學傳統,但她并沒有因循守舊,而是既善于繼承傳統,又勇于創新。自《瀑布》開始,德拉布爾就沒有停止過藝術創新的探索步伐。1993年德拉布爾和丈夫,英國著名傳記作家邁克爾·霍爾羅伊德,以及英國當代杰出小說家多麗絲·萊辛一起訪華的一次座談會上,德拉布爾坦誠,她不再堅持最初宣稱的堅守傳統的立場:“我現在不那么看了。我認為,文學創作既要從傳統中吸取營養,也要有創新。因此,也就不能只跟在傳統后面……”[3]208有評論認為,《紅王妃》中的知識分子人物讓人想起作者的姐姐拜厄特的代表作《占有》,場景有些像美裔加拿大當代作家卡羅爾·希爾茲的《相當傳統的女人》,作品中有收養的亞裔孩童這頗似美國當代作家安·泰勒的《通往美國之路》,在敘事處理上與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有相近之處[7]191-4。
雖然《紅王妃》目前已被認為是一部歷史小說,但同時也被認為是一部“后現代之作,是元小說”[7]191。元小說是后現代主義文學的一部分[8],“是后現代主義文學中與黑色幽默相映成輝的另一藝術景觀。”[9]396戴維·洛奇早就注意到了德拉布爾高超的元小說敘述技巧。他曾以德拉布爾的《黃金王國》為例簡單扼要地評析了她在小說敘述上應用元小說敘述技巧所表現出的駕馭能力。德拉布爾熟諳元小說之道,她在應用元小說藝術上已經非常嫻熟,拿捏得當:“德拉布爾采用的此類元小說式點綴,在數量上并沒有多得以至于從根本上打亂小說意欲在一個虛構的故事里,以巨細靡遺、令人信服并滿足傳統要求的手法來審視當代社會里許多知識女性的命運這個任務。”[10]248
不過,小說《紅王妃》與一般的元小說又迥然有異,因為它除正文的三部分外,有序、跋,還有致謝、資料來源說明,甚至還列出了參考書目。小說正文外的這種安排使小說顯得特別另類,似乎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部學術著作。但這些應統一看做是小說《紅王妃》的有機組成部分,因為正是這些部分透漏給我們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是在用這些手段告訴讀者,小說《紅王妃》是如何創作出來的。曾幾何時,“文學之死”,“小說之死”不絕于耳,但正如英國當代著名的小說家福爾斯所認識到的那樣,不管是“文學之死”,還是“小說之死”,死的不是其自身,而是其原有的形式。當代文學一直在探索,在不斷的進行著文學實驗,元小說就是其中之一。元小說被認為是“關于小說的小說”,也就是洛奇所言的“關注小說的身份及其創作過程的小說”。《紅王妃》不僅在正文中不斷地提醒讀者該小說的創作過程,而且序、跋、致謝、資料來源說明,以及參考書目的功能也是在提示告知讀者小說的創作過程,只是這些正文之外的部分與眾不同而已。《紅王妃》無疑是一部元小說。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元小說,因為在《紅王妃》中,歷史不僅是作者展示思想理念的舞臺,也是她表演其高超的元小說藝術技巧的平臺。《紅王妃》是一部歷史元小說的杰作,德拉布爾所言的別樣性就在其中。
三
雖然元小說作為一個術語“首次出現在美國小說家兼批評家廉·H·伽斯的論著《小說與生活中的形式中》”[8]396,但學界普遍認為英國是元小說的故鄉,而斯泰恩的《項狄傳》是元小說的開山之作。在當代英國文壇元小說藝術已在歷史小說中施展魅力,當今英國出現了一批歷史元小說作品,拜厄特的《占有》被公認為是歷史元小說。事實上,早在1972年出版的約翰·伯格的小說《G》同樣是一部歷史元小說。盡管《G》的副標題特意用了“小說”二字來提示其虛構性,但由于作品大量使用歷史文獻,《G》顯得不象是小說,至少不象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小說主人公大談其作為作家的責任與義務,而且談及自己在敘述故事、設計情節、刻畫人物等方面所遇到的技術難題,這無疑是在與讀者進行交流和切磋,因而具有明顯的歷史元小說特征。
歷史元小說在歷史小說中加入評論,引導或迫使讀者參與到同小說寫作有關的美學或哲學的討論中來[11]。《紅王妃》不僅通過加上正文之外的序、跋、致謝、資料來源說明以及參考書目這種結構性的策略暗示小說的創作過程,更重要的是,小說正文中通過諸多手段提示小說的創作過程并與讀者展開交流,因而具有鮮明的元小說特征。對于歷史元小說,作為同時也是文學評論家的德拉布爾應該不會陌生,更何況當代英國小說界姊妹花的姐姐拜爾特的小說《占有》(國內譯為《隱之書》)就是引起歐美文學界轟動的公認的歷史元小說之作。盡管《紅王妃》與《占有》有著諸多不同,但卻具備了歷史元小說的所有要件,因而可以說《紅王妃》是德拉布爾小說實驗的成功之作,是一部可以與《占有》比肩的歷史元小說。
德拉布爾只是用“別樣”二字來給自己的小說貼上頗有些玄虛的標簽,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文學界鮮有自我評斷自己作品的先例,德拉布爾也不便逾規;二是即使自己知道《紅王妃》應劃入歷史元小說之列也不愿作聲,因為不甘落人后的德拉布爾連同胞姐姐拜厄特都視為自己文壇上的對手,不愿屈居其下。當代英國文壇姊妹花拜厄特和德拉布爾素來不睦,一是德拉布爾曾公開對母親頗有抱怨,這令拜厄特很氣惱;二是姐妹倆在文學創作上誰也不服誰,都在暗中角力。兩姐妹佳作頻出,其中不能說沒有雙方角力的功勞。德拉布爾的小說《紅王妃》與其姊拜厄特的小說《占有》同歸入歷史元小說之列,這可能會令德拉布爾有些不舒服,但一個是寫異域的古代宮廷悲劇史,一個是寫本土維多利亞時代一段未被人知的羅曼史,卻各有優長,是花開兩朵,朵朵鮮艷迷人,芬芳斗艷。評論界曾把《占有》視為一部魔書,維多利亞時代與后現代社會時空交錯,相隔百年的愛情故事并置,小說中穿插大量的童話和神話,詩歌、書信和日記等非小說題材應有盡有,形成文中文,愛情傳奇、偵探故事、荒誕神話、校園喜劇、歷險故事、哥特小說等體裁無所不包。拜厄特因此不僅享譽英倫,而且譽滿全球,似乎英國當代作家鮮能出其右。雖然難以斷言《紅王妃》能出其右,但可說它與《占有》在伯仲間。《紅王妃》以其特有的鬼魂敘事使小說得以在古代、現代和后現代三個階段縱橫馳騁,實現了時空間的自由穿越,并且既可利用第一人稱,又可利用第三人稱敘事,騰轉挪移,游刃有余。而正文之外的序、跋、致謝、資料來源說明以及參考書目這種結構性的巧思妙設不僅給人以學術性的肅穆感,也給人以一種歷史的厚重感和莊嚴感。這些正是這部歷史元小說的超拔之處,也是德拉布爾本人所言的小說別樣性之所在,或者說至少是《紅王妃》別樣性的重要元素。
[1]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304-305.
[2]Knutsen,Karen Patrick.Leaving Dr.Leavis a Farewell to the Great Tradition?Margret Drabble's The Gate of Ivory[J].English Studies,1996(6):579.
[3]張中載.看《瀑布》——德萊布爾的實驗性小說[C]//當代英國文學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
[4]瑪格麗特·德拉布爾.紅王妃[M].楊榮鑫,譯.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序):1-2.
[5]劉國清.曼布克獎與當今英國歷史小說熱[J].外國文學動態,2010(6):48-49.
[6]Interview with Margaret Drabble.http://www.harcourtbooks.com/authorinterviews/bookinterview_Drabble.asp.
[7]Stovel,Foster.Margret Drabble:The Red Queen[J].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2007(34).
[8]洪雪花.《一個悲傷的女人》的女性主義解讀[J].延邊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6):102.
[9]劉象愚,楊恒達,曾艷兵.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M].盧麗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11]劉國清,石愛霞.歷史之維、印第安神話與隱喻[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