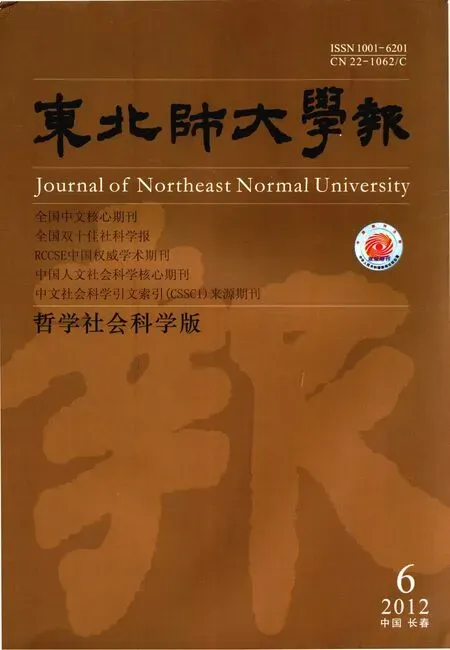翻譯的悖論和詩學意識
丁啟紅,羅潤田
(成都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禮記·王制》篇載:“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緹,北方曰譯”。“寄”、“象”、“狄緹”、“譯”都是當時對翻譯人員的不同稱呼,漢以后漸統一為“譯”,而至少從南北朝起“翻譯”二字便開始連用,既可指人也可指事。從信息語際轉換的角度來看,當語際交際中因語言的障礙而導致信息的發送和接收必須有交際中介人(即譯者)的介入時,翻譯即出現。凡翻譯活動均涉及原發信息、中介人和經過中介人用譯入語處理過的信息的接收者。人類語言的特殊復雜性導致通過翻譯而進行的言語信息交流活動有其間接性和對中介人的依賴性。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強烈地依賴于中介人,另一方面必然要對中介人的作用做出反映和評價。因此,對中介人如何發揮作用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翻譯研究的重心或中心,翻譯策略和翻譯標準的研究之所以永生常新則有了必然的根源。
一、翻譯即信息的語際轉換——經驗論的缺陷
大多數翻譯教科書所遵循的翻譯概念從信息語際轉換的角度出發,認為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在保持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外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的過程。按照這個解釋,信息與載體既被割裂開來,對信息的忠實即“信”自然就成了譯者努力追求的目標,于是闡釋學(hermeneutics)登場;然而,既然信息接收者是譯者的服務對象,那么不考慮他們的反應,翻譯豈不無的放矢?于是“讀者反應論”即“接受美學論”應運而生。雙方都因此而演繹出了一整套理論來規范實踐,但是這兩種由實踐提出問題再回到實踐中去尋找答案而演繹出來的理論因對研究對象的自取其便的割裂走上了一條經驗主義的理路。嚴復的“信、達、雅”三字翻譯標準眾所周知,但他本人從經驗出發也意識到了絕對的信是難以達到的,他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1]。“難”是因為翻譯承受著來自語言與文化的多重張力,使得信度和效度如何調和的矛盾突出,給譯者造成極大的困惑和難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提出的應是“信、達、雅”三難說,而不僅是翻譯標準,這樣的理解更彰顯出嚴氏理論的偉大時代功績。但是,譯事之難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個問題超出了經驗論的范疇,要找出“難”的終極原因必須借助先驗的科學論,即比較語言學、比較文化學和現代詩學。
二、翻譯的語言與文化悖論
(一)翻譯的語言悖論
人類不同語言之間的異同是由語言的性質決定的。同的一面指向可譯性,可分相對可譯性和絕對可譯性;異的一面指向不可譯性,亦分為相對不可譯性和絕對不可譯性。
語言的共同性體現在人類語言所共有的等級體系(hierarchy):音素—音節—語素—單詞—習語與搭配—句子—語篇。從無意義的單位到有意義的單位,語言的共同性由小到大等級過渡。音節、語素和單詞有時合而為一,如單音節詞。這個體系表明,似乎連貫的言語線性流是由離散的單位構成的,這些離散的單位由小到大,構成了一個等級體系,于是語言表現出有限手段的無限應用的創造性,這決定了句子與語篇層面上詞語的調遣組合方式的無限性,因而能夠任意表達無盡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語言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人類語言共同具有的開放性是可譯性的終極原因。反觀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則寓于特定語言的獨特性(uniqueness),同樣體現在這個等級體系中。不同語言在其等級體系的每一個層面都會有差異,但是差異性在各層面上是由大到小遞增的,在其大端即句、段層面差異很小,在語篇層面有時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但差異在有限手段的詞、語層面開始劇增,雙語轉換時極易產生意義與其表達形式的不對等。語言手段的有限性使得語言又成了一個封閉的體系,語言手段的封閉性則是不可譯性的終極原因。
愛倫·坡在《睡谷傳奇》中寫的一個小句“…in his mind,he completely carried away the palm from the parson”,直譯派可能譯成“在他頭腦中,他干干脆脆地把象征勝利與榮譽的棕櫚枝從牧師頭上拿走了”,意譯派則可能譯成“他簡直覺得自己比牧師還了不起”,二者用不同方式解釋了原意。原句中用了一個換喻詞(palm是棕櫚枝,象征勝利或榮譽),又巧用了頭韻,但譯文都沒有把它們保留下來,這不是譯者的無能,而是語言本身的獨特性所決定的。由于譯入語的文化欠缺(不能從棕櫚枝聯想到勝利與榮譽)和語音系統的差別(英語的頭韻多半是漢語沒有的),原語文本中的意與形的和諧統一美不能在譯入語文本中得到體現。
(二)翻譯的社會文化悖論
翻譯中涉及語言差異的問題還有一個側面,這就是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因素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中所造成的文化欠缺以及語言中包含的文化特異 意 義 (culturally idiosyncratic meanings)。中國人和英美人都認為狐貍是狡猾的動物,因此英語的an old fox和漢語的“一只老狐貍”無論字面意義和指稱意義都恰好一致;但是中國人不會像英美人那樣用貓去比喻心地惡毒的女人,因此,把She is a cat.譯成“她是個包藏禍心的女人”,只是譯了指稱意義而沒有保留形象,從信息傳譯上講信度有了,但從風格上講效度則與原文不匹配。隱喻格大多是民族文化的一種替身,替身出場,真身遁跡,觀者不知就里,得有人指點迷津才行,這個人就是譯者;但是戲在替身身上,一旦替身退去,真身登場,戲味全失。錢先生用補償法在翻譯《毛澤東選集》時把“三個臭皮匠,湊成個諸葛亮”譯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to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既保留了替身,又點明了真身,且保存了源語的和諧優美,堪謂佳譯。
翻譯的語言與文化悖論表明,可譯性與不可譯性都是相對的概念。首先,絕對可譯與絕對不可譯都是極端的概念,實例也罕見。從意義與風格全部原樣保存,即意、神、形兼似的意義上講,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的絕對可譯性很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有度的區分,完全的“信”則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但從完成語言符號的類似社會功能,達到相應的語用目的的意義上講,絕對不可譯性也很小。其次,相對可譯和相對不可譯是相通的,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沒有截然的界限而言。承認語際轉換中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并存,就把理解和解釋也拉入了翻譯的范疇。翻譯往往流于解釋,這樣的說法看似無奈,其實是必然的。如果改“流于”為“就是”,解釋作為手段就登上了翻譯理論的大雅之堂,問題只在于解釋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別,是否具有與原作一樣甚至勝出原作的藝術效果。奈達的“對等說”三易其表述方式。最后改定為“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提出的功能對等的原則之一是:如果拘守字面意義的譯文可能引起指稱意義的誤解時,必須對譯文做一些變動,詞語上的或是句法上的變動皆可[2]。既然詞語與句法均可變,解釋就成了正法。
三、中介人即調停者
關于信息與言語形式的關系問題,在具有審美價值的作品翻譯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朱光潛先生說:“藝術是有生命的東西”[3]。一切有藝術生命的語言產物都是形(言語形式)和體(思想內容)的和諧統一體。中國傳統文論歷來主張文質合一,體用合一。認為意(言語所載的信息)與辭(言語形式)的關系是“本與末”、“實與藝”或“內與外”的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和諧的統一體。因此,文學翻譯的本質就是用譯入語文本還原源語文本信息與言語形式的和諧統一,使原作的藝術生命得以再生。這就意味著:第一,譯作的“信”必須包括既忠實于原作的信息,又忠于原作的文體與風格;第二,譯作必須具有與原作一樣的審美價值。但是,由于語言學上的和社會文化學上的諸多困難,可譯性常常是打了折扣的,譯作難以百分之百還原于原作。所謂的“還原”只能是近似的,而一旦達到了足夠的近似,在審美價值上近于原作的便是合格的譯品。優于原作的則是更佳的譯品,Some shops invite crime by making it easy to take goods.的譯文“有些商店貨物擺放不嚴,無異于開門揖盜。”就符合漢語遣詞造句的習慣,用“開門揖盜”譯by短語可算發揮了譯入語優勢,但絕不是沒有語義學上的根據。原句中crime是上義詞,其實際含義是它的下義詞stealing或robbery,等于譯入語的“盜”,因此用這個成語翻譯invite crime恰合原意,且更形象生動。
翻譯活動承受著來自語言差異、文化差異、時代懸隔等因素造成的多重異向張力,要達到用譯入語文本還原源語文本信息與言語形式的和諧統一,優秀的中介人肩負著忠于原作、讀者和藝術的三重責任,不可能把某一種傾向貫徹到底。嚴復先生所譯的《天演論》有三點是公認的:一是它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貢獻,二是它文字的優美,三是它“略虧于信”[4]。美譯難信,信譯難美。佛經翻譯的中堅時代據梁啟超總結是自晚漢迄盛唐約六百年,先后分三個時期,與之對應的譯品特點是:一、未熟的直譯,二、未熟的意譯,三、以玄奘為代表的“直譯與意譯,圓滿調和”,達到了“道之極軌”[5]。梁氏的結論和佛經史家的“古譯”、“舊譯”及“今譯”的時期劃分和譯作評價是一致的。這些史實表明,在人類文化交流史上產生過影響的優秀譯作都不是單一取向的,尤其一代代譯經師嘔心瀝血,歷經數百年而不輟,成就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最為壯觀的佛經翻譯。由此看來,注重原作文本的文本主體論和注重接受美學效應的讀者反映論從各自立場出發都有道理,兩方面的研究也都很有價值,但如果走到極端,互相排斥,要求中介人只擇其一,就不利于對翻譯實踐的指導。作為跨文化的語際交際中介人,譯者應做且能做的就是居中調停,取得原作與譯入語讀者都能接受的最佳妥協與折中,還原作品的藝術生命力,求得信度與效度的和諧統一。
四、文學翻譯家的詩學意識
綜上所述,討論翻譯逃脫不了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語言學與社會文化學悖論對翻譯活動的制約作用,也逃脫不了文學文本是具有藝術生命的信息內容與言語形式的和諧統一體這個先決條件對翻譯活動的制約作用,前者導出的結論是信有度的區分,所謂忠實只是一個理想化的追求目標;后者則表明信亦不單指信息而言,也必然與文體風格有關,這自然意味著作為中介人的文學翻譯家必須具有強烈的文體風格意識自覺,亦即詩學意識自覺。
西方現代“詩學”(poetics)利用該詞的詞源擴大了概念的外延,使之涵蓋了一切的語言藝術創作樣式,稱詩學即“文學的科學”(science of literature)。從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法國結構主義到最近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都企圖找出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普遍屬性即“文學性”(literariness),亦即構成具體文本的基礎的普遍適應法則,或曰文學的“本質”(essence)[6]。當代西方詩學深受語言學的影響,引入了“突出”(foregrounding,又譯“前景化”)等概念,又表明詩學與文體風格學(stylistics)是相通的,因此文學翻譯家的文體風格意識亦可稱之為詩學意識。
林語堂說:“文章之美,不在質而在體。體之問題即藝術的中心問題。”[7]“體”即文體風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就是語言的“變異”等產生的得到“突出”的言語形式。凡藝術必貴“推陳出新”,語言藝術自不例外。“文貴奇、變、高、遠”、“文章之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語不驚人死不休”等可算作“突出”說、“文學性”之類的精妙解說了。既然文學的言語形式決定著作品的藝術生命.那么風格傳譯便成為中介人關注的中心,換言之對風格的高度關注就是文學翻譯家的詩學意識自覺。
“突出”是西方詩學與文體風格學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中介人通過對語言常規(norms)的變異等手段使其言語形式具有文學性,從而轉移讀者的注意力更多地去注意“是怎樣說的”而非“說的是什么”,于是,與以傳遞信息為主旨的非文學語言相比,文學語言便具有了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因此,由于文學文本的信息內容與言語形式的不可分離性,文學語言便具有了雙重作用:表達符號意義(semiotic meanings)和完成詩學功能(poetic functions)。此時,我們可以再返回到經驗中來考察文學翻譯家的詩學意識自覺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首先,經驗告訴我們當雙語的符號意義和詩學功能大致能夠求得對等的統一時,譯入語就應盡可能忠實地照搬源語的言語形式,這時忠實地傳譯原作的藝術表現形式就是最佳地還原原作的信息與形式的和諧統一藝術生命。這樣做需要引進外來表達形式,造成譯入語文體與語法的變化,語言的開放性使之成為可能并創造出無盡的意義,因此翻譯的功用之一就是在吸納外來文化的同時引進外來表達法,自然豐富和增強譯入語的表現力。
但是,語言的等級體系中的封閉性使得雙語的符號意義和詩學功能難以處處達到對等的統一,完全的對等統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當不可求時,文學翻譯家只好求助于對原作風格的總體把握,通過譯入語的再創作來還原原作的信息與形式的和諧統一,以保存原作的藝術生命。譯事之難正在于符號意義與詩學功能難以求得雙語的對等統一。祝慶英對“By Jove,she has taste!”exclaimed Henry lynn.(Jane Eyre)的翻譯為:“嗬,她還挑肥揀瘦呢!”亨利·利恩嚷道。讀起來絲毫沒有讀翻譯作品的感覺,就是原文語義的譯入語解釋,我們可稱之為“棄形存魂”的譯法。通過這樣處理,原作的妙處就借譯入語“投胎轉世”傳遞給了讀者。
高明的文學翻譯家在雙語中難以求得符號意義與詩學功能的對等統一時,能夠自覺以強烈的詩學意識,通過對譯入語的再創作從而變語言學意義上的不可譯為詩學意義上的可譯。在文學閱讀中,人類與生俱來的獵奇心理和探奇覽勝的驚喜與愉悅則表現在對語言藝術之美的探索中感受到了強烈的藝術震撼。簡言之,詩學意識是中介人對原作藝術生命和讀者所負的責任,作者的藝術追求和讀者的審美期待是趨向一致的,當語言的符號意義和詩學功能一并納入中介人的視野時,文學翻譯家經過真正意義上的藝術經營后一定會為譯入語的文化藝術寶庫增添新的財富,實現世界多元文化的互補與共享。
[1]嚴復(譯).天演論[Z].北京:譯林出版社,2011.
[2]Nida.E.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3:125.
[3]朱光潛.詩論(朱立元導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0.
[4]賀麟.嚴復的翻譯[C]//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153.
[5]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C]//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57-62.
[6]Fowler R.A Dictionary of Modem Critical Terms[Z].New York:Routledge & Regan Paul Inc,1987:184.
[7]林語堂.論翻譯[C]//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