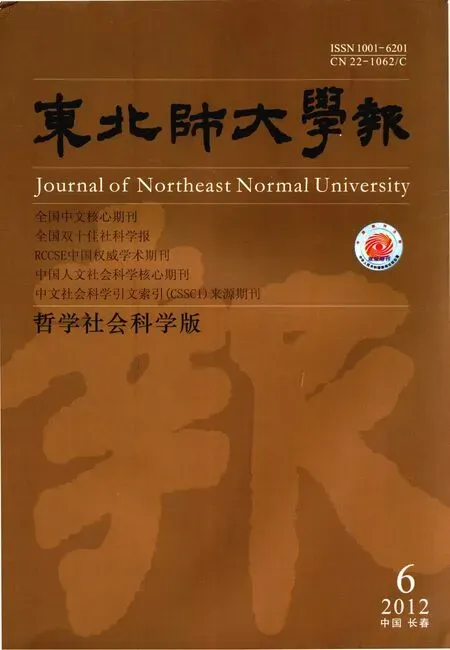論北魏宗室階層的文化參與及角色嬗變
劉 軍
(吉林大學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長春 130012)
北魏宗室專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體后裔,他們是北魏政權賴以存在的根基和骨干。身為天潢貴胄,北魏宗室不僅在政治和社會層面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深受華夏文明的感召,積極投身各類文化事業,在中古的文化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往的研究側重分析宗室成員氣質類型的轉變,著力捕捉其文士化的趨勢和線索,代表性成果有孫同勛《拓拔氏的漢化》、何德章《北魏遷洛后鮮卑貴族的文士化》和王永平《墓志所見北魏后期遷洛鮮卑皇族集團之雅化》等,但較少關注宗室成員參與文化活動及與之連帶的角色認知的改易。筆者認為,由此切入能夠更形象地反映北魏宗室階層日新月異的精神面貌與生存狀態,更生動地詮釋包括宗室在內整個胡人貴族實現漢化、文士化的歷史進程。
一、北魏宗室階層參與的文化活動
北魏宗室高居統治集團金字塔的尖頂,是獨一無二的特權階層,他們可以享受最充分的文化資源;作為帝國權力的主宰,他們在精神世界尋求蛻變的外部壓力和內在動力也最為強勁。這就決定了宗室階層的文化參與無論數量還是內涵都必然超越其他胡人勛貴。北魏宗室以現實具體的文化活動為媒介擴展自身的影響力,主要有下列表現。
(一)接受官、私教育
北魏宗室要提升知識素養,適應全新的統治形勢,接受嚴格、正規的學校教育勢在必行,而中原地區已有的教育系統為其創造了便利條件。漢族傳統教育分官學和私學兩個部分,它們都被用來教導宗室子弟,只不過二者在不同時期所占的比重有所差別,大抵以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遷都為界,此前以官學為主,后來私學取而代之。北魏前期一度禁絕私學,《魏書·太武帝紀下》載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庚戌詔曰:“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這樣,宗室貴胄就只能進入官辦的太學讀書。中書省治下的中書學(后更名國子學)同為培養宗室子弟的重要園地,《元暉墓志》:“(元暉)太和中始自國子生辟司徒參軍事。”[1]110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執政的馮太后又開皇宗學,“于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專門教導皇子皇孫[2]533。官辦學校因有朝廷鼎力扶植,條件優越、師資雄厚,大批學術精英匯聚于此,這對于宗室提高文化素養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盡管存在種種禁錮,但中原的私學傳統從未真正停歇,擺脫官學之陳腐,投奔名師求學的宗室亦不在少數,如尚書左仆射元贊便是大儒常爽的高足[2]1848。北魏洛陽時代,私學蔚為大觀,“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2]1842。宗室教育更多地選擇棄官從私,如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順,自幼師從樂安陳豐,習學王羲之《小學篇》[2]481;中山王元英諸子追隨大儒劉蘭學習儒家經典[2]1851。中古私學乃學術之中心[3]20,其較官學擁有底蘊深厚、學風扎實、教法靈活等優勢,因此北魏后期私學逐漸取代官學成為訓導宗室的重鎮。
(二)參加宮廷文化活動
北魏宮廷很早便延聘漢族名士,為皇帝施政出謀劃策,久而久之,北魏宮廷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濃郁的人文氛圍,對胡人貴族文化價值取向的成型起到了關鍵的導向作用。宗室成員是北魏宮廷文化活動重要的參與者,自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可以憑借特殊的身份入直禁中、侍書伴讀,和皇帝一道享受文化盛宴。《元彝墓志》:“孝明皇帝春秋年富沖,敦上庠之學,廣延宗英,搜揚俊乂。王(元彝)以文宣世子,幼緝美譽,參茲妙簡,入為侍書。”[1]226可見,侍書多選年少的宗室才俊。后來稱帝的元子攸亦在其列,他“幼侍肅宗書于禁內”[2]255。類似的事例還有元邵“年十八,為侍書”[1]221;元譚“還除直閣將軍,延內侍書”[1]229;元悛“年七歲召為國子學生,即引入侍書”[1]231;元湛“乃引入侍書”[1]356。宮中還時常設壇講學,為宗室傳授知識。如孝武帝永熙三年(534),“于顯陽殿講《禮》,詔(李)郁執經,解說不窮,群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2]1179。皇帝一時興起,甚至親登講壇,與宗室坐而論道。如道武帝“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祗肅”[2]383。孝文帝為推行家族制改革,在清徽堂為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詳諸皇弟講解漢族喪服[2]573。宣武帝也取法先皇,在式乾殿為眾兄弟解讀《孝經》[2]203。此類講讀活動有助于宗室增長見聞,拓寬信息來源。北魏宮廷效仿名士風范,頻繁舉行文化意蘊深刻的飲宴,宗室貴族是其常客。酒席之上,賓主雙方把盞言歡、直抒胸臆,充分沐浴六朝的文化新風。典型的事例是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在皇信堂宴請有服宗親,席間令宗室賦詩言志,“特令(元)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2]464。后數年,又于洛陽清徽堂游園宴飲,孝文帝酒酣之際作詩與宗室應和[2]572。我們知道,中古士人飲宴不圖口腹之快,而是專為詩、為禮進行的儀式象征[4]13。在這樣的宴會中,宗室不僅可以接受漢文化的熏陶,而且充分展示了自身的風采,使其品位旨趣更加靠攏漢族士夫。
(三)與漢人士族切磋交往
中古士人重結交、善標榜,志趣相投者往往結成相對閉塞的社交圈。北魏宗室在入主中原后,深感為漢族士人接納的重要性,于是嘗試借助文化平臺融入這個特殊的群體。加之北魏優待宗室,給予其充裕的生存空間,使之能夠自由地開展社交活動。當時宗室廣交名流,以營聲譽。《魏書·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楨傳附熙傳》:“(元熙)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后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于河梁,賦詩告別。”同書《孝文五王·京兆王愉傳》:“(元)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又《道武七王·京兆王黎傳附羅傳》:“(元)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賓客,從游青土。”交往的過程中伴隨著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宗室可向漢族士人咨詢請教。如安豐王元延明“每有疑滯,恒就(李)琰之辨析,自以為不及也”[2]1728。雙方亦可平等地爭執辯難。如在揚州刺史王肅的餞行酒宴上,宗室“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楊)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2]1291。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宗室和士人間舉行的私宴,《洛陽伽藍記·城西·法云寺》對此有過生動的描述:“(元)彧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游后園。僚采成群,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并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郄焉。”類似的還有《元湛墓志》:“嘉辰節慶,光風冏月,必延王孫,命公子,曲宴竹林,賦詩暢志。”[1]239《元顯墓志》:“及春日停郊,秋月臨牖。庭吟蟋蟀,援響綿蠻,籍茲賞會,良朋萃止,式敦宴醑,載言行樂,江南既唱,豫北且行,詩賦去來,高談往復,蕭然自得,忘情彼我。”[1]360較之宮廷公宴,宗室私宴不受禮法羈絆,顯得歡快活潑,賓主雙方在飲酒之余,游園賞月、吟詩作賦,其雅趣與江左時尚完全合拍。
(四)投身典籍的收藏、校勘活動
北魏朝廷十分重視古代典籍的收藏和整理工作,宗室憑借特殊的地位,在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時最負盛名的宗室藏書家非安豐王元延明莫屬,《魏書·文成五王·安豐王猛傳附延明傳》:“(元)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余卷。”足見宗室藏書數量之巨。且嗜書如命者大有人在,同書《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傳附順傳》載,宗室元順死后,“家徒四壁,無物斂尸,止有書數千卷而已”。此事得到《元順墓志》的印證,其銘曰:“嘗無擔石之儲,唯有書數千卷。”[1]223又《元茂墓志》贊墓主元茂有“家無一帛,書有萬篋”;“家無寸縑,書有盈帙”之語[1]163。正是對書籍的這般癡狂,才成就了北魏宗室的藏書事業。還有很多宗室熱衷于典籍的校勘、整理工作,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到的元延明,他曾計劃利用豐富的私人藏書,“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2]1955。元延明的這項工作是對中古禮樂制度的重大創舉,相關成果為后世所沿襲[5]314。他還對皇家藏書進行了系統的考訂和校對,《元延明墓志》載其任秘書監、中書令時,“或外典圖書,或內掌絲綍。……又監校御書。時明皇則天,留心古學,以臺閣文字,訛偽尚繁,民間遺逸,第錄未謹。公以向歆之博物,固讎校之所歸,殺青自理,簡漆斯正”[1]287。付出過相同努力的還有宗室元璨,《元璨墓志》云:“擢秘書佐郎。時尋有敕,專綜東觀,墳經大序,部帙載章,所進遺漏,緝增史續。”[1]152藏書、校書活動既是對宗室文化修養的綜合考核,也為其施展才華提供了場所。
(五)從事著述活動
著述是精神產品的制造過程,屬于高級的文化活動。隨著北魏宗室知識水準的不斷提升,他們也開始從事創作,這代表著宗室階層趨于漢化的全新動向和最高成就。宗室成果最豐者當屬文學方面,傳世的詩賦文章不勝枚舉,對此已有專門研究[6],茲不贅述。我們將集中考察宗室在經史等傳統學術領域的建樹。北魏治國奉儒家經典為圭臬,于是就有宗室根據自身感悟對經義重新加以詮釋和演繹。如孝明帝時,主政的清河王元懌“典經義注”,親纂《孝經解詁》[2]766。安豐王元延明在此方面可謂著作等身,《隋書·經籍志》著錄其作有《毛詩誼府》三卷,《三禮宗略》二十卷;未見《隋志》的還有《五經宗略》、《詩禮別義》、《九章》、《器準》等[2]530。史學也是宗室著述的主陣地,彭城王元勰有感于時政之艱難,著《要略》三十卷,“撰自古帝王賢達至于魏世子孫”[2]582。元順撰《帝錄》二十卷[2]485,屬于同類著作。又元孚“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告誡胡太后女主干政的危害[2]424。再有清河王元懌遭權臣元叉構陷拘禁,為表明心跡,“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2]592。中古時期,為適應門閥制度的發展,譜牒之學方興未艾,北魏宗室亦涉足于此,濟陰王元暉業“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室錄》,四十卷”[2]448。據考證,此書是北魏宗正寺所藏皇族玉牒的翻版[7],日后魏收修《魏書·宗室列傳》便以其為底本[8]487。由此可知,北魏宗室的經史著述服務于政治,以致用為目標,明顯帶有河北學術艱深務實的烙印。
(六)參加宗教活動
北魏時期,佛教興盛,宗室階層是最虔誠的信徒團體之一,他們廣泛參加宗教活動,從中汲取異域文化的養料。當時皇族內部以皇帝和太后為首,競相召集僧尼,舉行講經活動,宗室則為座上客。《魏書·宣武帝紀》:“(宣武帝)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與之研討的就有清河王元懌。《元懌墓志》:“(帝)每與王談玄剖義,日晏忘疲。”[1]172二人癡迷忘我之狀不難想見。太后駕旁專設侍講席位,為其演說佛法[9]。《洛陽伽藍記·城內·胡統寺》:“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于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胡)太后說法。”《魏書·劉昶傳附劉輝傳》載,駙馬劉輝與妻蘭陵長公主不睦,“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于靈太后”。說明宗女常受太后邀請入宮聽講。宗室亦可聚眾講經,如元叉“尤精釋義,招集緇徒,日盈數百。講論疑滯,研賾是非,以燭嗣日,怡然自得”[1]183。再如陳留王元景皓“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并進京師大德超、光、脡、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10]237。需要注意的是,北魏宗室大多擁有雄厚的財力,正是他們的喜好與支持,才使佛法得以廣為流傳。
總括以上,北魏入主中原后,宗室階層急速趨向漢化,這不僅表現為自身氣質面貌的轉變,更主要的則是他們對中原既有文化活動的廣泛參與和向六朝時尚旨趣的主動接近。通過梳理文獻,我們發現,北魏宗室主要參加官私教育、宮廷文化、士人社交、典籍整理與收藏、著書立說和佛教講經。通過這些文化活動,宗室階層對待漢文化的心理隔閡漸趨消融,華夷之森嚴壁壘隨之不攻自破。
二、北魏宗室階層文化角色的嬗變
與北魏宗室階層參與文化活動連帶的便是他們的文化角色問題,也就是在文化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及作用,這是衡量該階層整體進化程度和發展速度的有效基準。傳統觀點基于北魏宗室脫胎于草原游牧氏族、野蠻落后的事實,先入為主地將其限定在消極被動的受眾或客體位置上,片面強調其作為“學習者”的一面,這與歷史事實存在較大的差距。實際上,隨著浸染漢文化日深,以及自身素質的蛻變,至遲于孝文帝太和改制之際,宗室階層獨立自覺的文化心態就已經開始萌動。受此驅策,他們對于文化活動的平等介入和主體角色產生了迫切的需求。這是研究中古北方民族史、文化史無法回避的問題。對此,前文間或有所表露,例如宗室成員以主體姿態召集、參加士人宴飲,并充分展示學識和風采;宗室進行藏書、校勘和著述活動等。下面我們將補充一些資料,動態地追蹤宗室文化角色變遷的軌跡。
首先,在教育領域。北魏《魏書·景魏十二王中·任城王云傳附順傳》:“(元順)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可見,元順已經廣收門徒,聚眾講學。宗室一改單純受教的形象,經明行修者招收徒眾、授業解惑,完成了由“學習者”向“傳播人”的重大轉變。《魏書·樂志》:“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如前所述,元延明深諳典籍,堪稱宗室翹楚,對王朝的禮樂制度貢獻甚巨,文中提到的信都芳不僅是他的學術助手,也是他的弟子。元延明在宮廷教育中也據有主導地位,其墓志文曰:“少時高祖垂嘆,以為終能致遠,遂翻為國師,郁成朝棟。既業冠一時,道高百辟,授經侍講,琢磨圣躬。”[1]289元延明既貴為“國師”,則皇室成員俱在其教授之列。又《元頊墓志》:“明帝春秋方富,敦悅墳典,命為侍學。王執經禁內,起予金華。”[1]290可見,墓主元頊也曾擔負過帝師重任。以上事例充分證明,宗室具備了獨立傳播漢文化的能力,其知識層次已今非昔比。
其次,宗室人物開始主持某些重大禮儀活動。禮儀是中原文明的精粹,北魏建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國家儀禮幾乎為漢族士人所壟斷。可隨著知識、閱歷的積累,愈來愈多的宗室開始躋身這一神圣殿堂,且能與漢族宿儒就核心問題一較高下。如臨淮王元彧“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2]419。安豐王元延明奉敕監修金石[2]530。又《魏書·祖瑩傳》:“初,莊帝末,爾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祖)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宗室元孚是修復禮樂工作的總負責之一,他成果顯著,“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嘆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2]428。輿服也是禮儀制度的重要環節,清河王元懌于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奏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5]238。這套服飾體系為北齊所沿用,具有開創意義。為逝者議定謚號屬于喪禮的范疇,北魏后期,多有宗室主管此事,如彭城王元勰上孝文帝謚[2]577;太常卿元脩和少卿元端議于忠謚[2]746;太常少卿元端與給事黃門侍郎元纂定羊祉謚[2]1924。在莊嚴肅穆的禮儀活動中,宗室也時常扮演主角,為士人所矚目。如元彝在孝明帝正光二年(521)舉行的國學釋奠大典上出任執經,此乃主持儀式之首席,非德高望重、才學優異者不能擔當[11]。總之,國家禮儀盡管帶有政治色彩,但究其實質還是一種文化行為,宗室能夠搶占學術高地、小試牛刀,必然要以深厚的知識儲備和良好的個人修養為先決條件。
再次,長久以來,宗室貴族被排斥在士人社交圈之外,漢族士人在政治上盡管臣服,但內心深處對異族統治者的鄙夷和敵視一時難以消除,太武帝時崔浩國史獄事件便是雙方矛盾的總爆發[12]152。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緊張關系的緩和,宗室與士人逐漸打破堅冰,在文化層面開啟了溝通的大門。至洛陽時代,漢化浪潮已勢不可擋,宗室與士人間相互了解、彼此尊重,最終水乳交融,形成了胡漢文士濟濟一堂的空前盛況。憑借不懈的努力,宗室終于為漢族士人所吸納,成為其平等交往之一分子。宗室大多禮賢下士,《魏書·盧玄傳》載,范陽大族盧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后來之冠,諸父并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盧元明“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其間不乏感人至深的場景,史載,南陽人馮亮“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凈,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2]1931。元英與馮亮肝膽相照,足證宗室精英在漢人名士心目中已有一席之地,這是雙方深入接觸的有利前提。
宗室身上閃現的亮點往往能夠得到名士的認同和欣賞。如臨淮王元彧“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金蟬曜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復道。觀者忘疲,莫不嘆服”[10]201。其氣質風貌儼然漢族士夫,因而大受贊許。宗室中的少年英才還會博得名士的特別青睞,獲贈帶有預測性質的評語,從而聲名鵲起,實乃東漢末年清議傳統之延續。如元孚“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2]424。元子孝“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后生領袖,必此人也’”[2]442。又元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2]449。這些評語都源自司徒崔光之口,崔光出自“四姓”之首清河崔氏,是漢人士族的總代表,他的舉動表明宗室已在士人的關注視野之內。進而言之,宗室既然成為評議的對象,也就意味著士人社交圈準入資格的獲得。
我們還注意到,漢人士族總是將具備某些共同特質的宗室人物歸并起來加以品評和比較。《魏書·太武五王·臨淮王譚傳附彧傳》:“(元彧)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瑯,未若濟南備圓方。’”同書《文成五王·安豐王猛傳附延明傳》:“(元延明)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并以才學令望有名于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兩則史料相互照應,說明元延明、元熙、元彧三人構成了相對完整的士人小群體。《元延明墓志》卻說:“惟與故任城王澄、中山王熙、東平王略,竹林為志,藝尚相懽。故太傅崔光、太常劉芳,雖春秋異時,亦雅相推揖。”[1]289可見,元延明、元熙又與元澄、元略聚集,自比竹林七賢。然而,無論何種組合,宗室雅士總是以群體的方式活動應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群體與東漢黨錮之際士流互相標榜結成的所謂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諸名目類似,乃士人自覺意識之反映[13]259。該現象的出現與宗室獨立的主體性文化角色的塑造緊密相關,標志著他們正式成為士人階層的有機組成部分。
以上可見,遷都洛陽后,北魏宗室的精神世界煥然一新。經過長期的磨合,宗室實現了與士林精英圈的平等對接,完成了由文化客體向文化主體的歷史跨越。其主體角色日益鞏固,突出表現為收徒講學、主持國家儀禮和獲得漢族文士的認可等方面。
三、余 論
從北魏立國到覆滅一個半世紀的短暫時間里,拓跋宗室的文化素養和氣質面貌發生了根本的飛躍,漢化及文士化乃大勢所趨。征服民族的這種變化驗證了恩格斯《反杜林論》中的經典論斷:“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早期皇室對漢文化懵懂無知,道武帝曾幼稚地詢問朝臣:“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2]789毗陵王拓跋順入宮聽講黃老之道,竟然“坐寐欠伸,不顧而唾”[2]383。區區百年之后,皇室人物無不自命文士風流。杰出代表是孝文帝,他“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2]187。又《元欽墓志》:“(元欽)秋臺引月,春帳來風,琴吐新聲,觴流芳味,高談天人之初,清言萬物之際,雖林下七子,不足稱奇。”[1]250《元斌墓志》:“(元斌)心棲事外,恒角巾私圃,偃臥林潮,望秋月而賦篇,臨春風而舉酌,流連談賞,左右琴書。”[1]140這種文化心理的質變消弭了胡漢隔閡,是中古時期民族融合的核心內容和主要動力[14]。形象地表現在文學領域,膾炙人口的狩獵詩在游牧民族粗獷的風格之上又融入了漢文化的典雅[15]。拓跋宗室的文化變革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必然以現實的文化參與為契機,以具體的溝通交流為途徑,以完成主體性角色轉變為導向。這才是探討拓跋宗室及胡人勛貴文士化問題的基點。綜合上文,我們發現宗室通過接受正規、系統的學校教育實現啟蒙,充分吸收宮廷學術的養料,積極搭建與漢人士族的對話平臺,廣泛參與藏書、校勘、著述、研討等文化活動,在文化實踐中學習、提升自身的素質修養。在此過程中,宗室精英憑借長期不懈的努力變被動為主動,逐漸為漢人士夫所接受,成為文士社交圈的平等主體,標志著其文化角色的正式轉變。拓跋宗室之所以棄武從文,是環境外因帶動內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眾所周知,中古時代是門閥士族的天下,士族不僅左右政局的走向,也引領著社會風尚。游牧民族統治中原的最佳方法不是武力迫服,而是化身士族的一部分,與之分享國家。而文化作為士族的旗幟,自然成為拓跋宗室改弦更張、接近士族的首要舉措。簡而言之,熱衷文化事業、打造主體形象乃拓跋鞏固政權的有效手段。
以北魏宗室為代表,考察中古北方胡人貴族的漢化和文士化進程是重要的學術命題,相關材料豐富,研究手法各異。現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宗室文化類型的分析上,內容包括知識水平、個性素養、文化心態和價值取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學者孫同勛先生,首創數量統計法對宗室氣質類型的量化分析,指出宗室中武將所占的比例由開國伊始的54%銳減至孝文帝以后的38%,揭示了宗室文士化的總體趨勢[16]73。此類研究盡管極為必要,但限于瑣碎的個案考證,不可避免地存在拘謹刻板,流于平面化的缺陷,窒息了文化史應有的生動性。眾所周知,人是社會的動物,只有在人際互動中方能實現自我價值。鑒于此,筆者試圖引入身份角色論,著重論述北魏宗室參與文化活動的情況,尤其是其文化主體地位的形成,以此管窺宗室在文化領域發揮的作用。較之文化類型分析,身份角色論不僅還文化史鮮活、立體之本來面目,而且更契合“文士”作為文化活動組織者、精神財富創造者、思想理念捍衛者的本體特質。可以說,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全景展示北魏宗室的文士化問題。這是本文在方法論層面的探索,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1]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2]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4]黃亞卓.漢魏六朝公宴詩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5]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6]周建江.北魏皇室文學述論[J].西北師大學報:哲社版,1993(5):33-38.
[7]劉軍.論鮮卑拓跋氏族群結構的演變[J].內蒙古社會科學,2011(1):43-47.
[8]李百藥.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9]劉軍.北朝侍講制度考述[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0(6):99-102.
[10]楊衒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劉軍.北朝釋奠禮考論[J].史學月刊,2012(1):35-41.
[12]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A].金明館叢稿初編[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1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4]劉國石.北朝時期少數民族貴族的漢文化修養[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66-70.
[15]李炳海.民族融合與中國古代狩獵詩的中興[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5):67-73.
[16]孫同勛.拓拔氏的漢化及其他——北魏史論文集[M].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