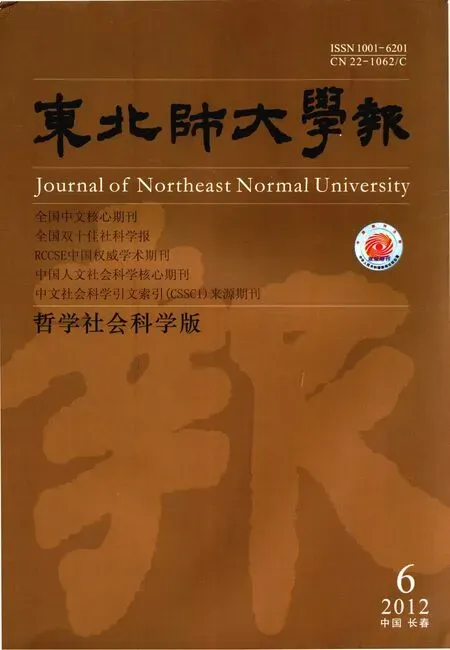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四書”經典結構形成過程的思想史考察
董灝智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在被納入“四書”經典結構之前,早已流傳于世近千年之久。關鍵的是,四者的身份與地位也各不相同。從篇幅上看,《大學》與《中庸》甚至都不能被視為著作,它們被收入《禮記》中而隨之流傳,在唐代中期之前,單獨關注過二者的人幾乎微乎其微。而相較于“學庸”的落寞,“語孟”則榮膺殊榮。在漢文帝時,《論語》、《孟子》被立于學官、置“傳記博士”,但旋即被“五經博士”所替代。至東漢時,《論語》由“傳”升格為“經”,《孟子》雖仍屬“傳記”,但在《漢書·藝文志》中已被降為“諸子”。“語孟”二書一升一降的結局,也奠定了二書在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間的不同地位。據《經義考》,這一時期的“論語注解”約有七十余種,而對《孟子》的注釋之作僅有晉人綦毋邃的《孟子注》(九卷),“孟學”一度中衰。這一情況直至唐代中葉才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觀,即《大學》和《中庸》被從《禮記》中擷取出來而獨立成書,后與《論語》和《孟子》合稱為“四書”。這一過程中思想脈絡的演變對“四書”經典結構形成的影響,將是本文闡述的重點內容。
一、發軔期:韓愈的“道統論”與李翱的“復性說”
一般認為,唐宋之際是中國學術的重要分水嶺。早年,“唐宋變革論”曾在國內外學界擁有強勢的話語。毋庸置疑的是,唐宋之際的思想變化實為劇烈,一種不同于漢唐儒學的“新儒學”開始在唐代中葉發軔,并在宋代盛行,這種“新儒學”就是后來的“理學”。重要的是,“四書”經典結構的開端也始自于此,韓愈為重要開端人物。在他生活的年代,佛教依舊盛行于官方與民間,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相比之下,傳統儒學的衰微傾向則日漸明顯,但儒學維護倫理綱常的終極目標是佛教難以企及的。所以,在此大背景下,韓愈及其弟子李翱開啟了以“復興儒學”來“排斥佛教”的新思路。在此過程中,湮沒千載的《孟子》、《大學》、《中庸》卻先后被發掘出來,使它們被后人重新審視,而這三者恰是組成“四書”的重要部分。
韓愈接過前輩學人排佛的大纛,繼續批判佛教。但與他人不同,韓愈仿照佛教的“佛統”為儒學建構“道統”以期對抗佛教。在他看來,佛教與老、莊之學一樣,皆為“異端邪說”,而儒學之道才是正道,即“原道”,它與佛、老之道互相沖突,互為水火,二者道不相同,勢不兩立。關鍵的是,儒學之道也有薪火相傳的“道統”:“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1],但在孔子死后,繼“先王之道”者僅孟子而已,而孟子死后,荀子與揚雄二人未能傳其道,“先王之道”最終降為“楊、墨、老、佛”之流。所以,韓愈在中國思想上的重要意義,就在于他發現了古圣先王前后相繼的“道統”,在使孟子的地位扶搖直上的同時,還促使了《孟子》一書的升格。韓愈的“道統論”上承楊綰奏請“把《論語》、《孝經》、《孟子》集為一經”的上疏,下啟皮日休的“尊孟”之舉,構成了《孟子》由“子”升“經”的重要一環。不寧唯是,《禮記》中的“大學之道”也在韓愈的著作中得到凸顯。其撰《原道》所引的“傳曰部分”正是《大學》中的主要內容。雖然,后來朱熹對于韓愈舉《大學》只引到“誠意”處而不說“致知在格物”,頗有微詞,但不可否認的是,韓愈卻是首次將《大學》中的主體部分提煉出來,并指出儒學的“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是“將以有為也”,這完全不同于佛教的“治心”,儒學的“修心”是為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佛教的“治心”卻是去君臣、人倫之道,二者是有本質的區別。由此可知,韓愈以儒學的“正心”來排斥佛學的“治心”。在這一過程中,《大學》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說,韓愈的“排佛論”在客觀上促使了《孟子》的升格和《大學》的新生,但其排佛的論調與前人相比無甚特別之處,所以,其弟子李翱雖繼承了韓愈“以儒排佛”的方法,卻與其師不同的是,他并未將視野局限于儒學內部,而是先從佛教入手,“過其門”而“入其室”,找出儒學對于佛教的劣勢,然后補之不足。在李翱看來,“佛法之所言者,列御寇、莊周所言詳矣”,其“所言者”即是“性命之學”,這在其《復性書》有跡可尋[2]。也就是說,佛教的內涵與老莊等人的道家思想無異,其核心之處就在性命之學,而儒家也有“性命之學”,只是在戰國后期湮沒無音。儒家講“性命之學”的重要著作是《禮記》中《中庸》。李翱從相對于“佛性”的“人性”入手,作《復性書》三篇,其顯然為《中庸》的注疏,一如歐陽修所云:“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3]1049《復性書》的首句為“人之所以為圣人者,性也”,很明顯,此處“人皆有成圣人的本性”是借用了禪宗“見性成佛”的說法,而李翱與禪僧的交往又多見諸史籍,故李翱將禪宗的說教方式引入儒學中,提出“復性成圣”的方法論,這樣一來,儒學與佛學的終極追求也就相差無幾。從這一意義上說,李翱以儒者身份的“援佛入儒”,既豐富了儒學,又打擊了佛教,可謂一舉兩得。重要的是,源自于先秦儒家“性命之學”的復性之說也有前后相承的“道統”可尋:孔子以之傳于顏回、子路、曾子,后子思得之而作《中庸》四十七篇,并將此傳之孟子;孟子之后由其弟子公孫丑、萬章等人傳之。后因“焚書坑儒”,作為“性命之書”的《中庸》雖未被毀,但此道廢缺,遂淪為莊、列、老、釋之流,而李翱的《復性書》正是發現了湮沒已久的“性命之學”,并將之傳世,故其言“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所以,李翱也認為自己注解的獨特在于:“(前人)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而這一轉變,對后來的宋儒影響頗多,他們對《中庸》的新認識正是經由《復性書》而形成的。
不難看出,韓愈的“道統論”,不僅使“孔孟”取代了“周孔”,還勾勒出孔孟之間的傳承脈絡,而李翱的《復性書》,則對孟子之后、被人們忽視已久的“天道”、“性命”、“心性”之說進行了重建,他們二人從思想上完成了“四書”形成的第一步。
二、醞釀期:“學庸”新詮與“語孟”并稱
至北宋,理學家們承繼了韓愈、李翱二人復興儒學的使命。他們比韓、李更向前一大步,不止借用佛教的用語及思想,還借用道家、道教的說法,為孔孟儒學彌補缺環,將其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即“將倫理提高為本體”。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選中了先秦儒學內闡述天命、心性等“形而上”之論較多的《易傳》、《中庸》、《孟子》等書,并在前人的基礎上,因其需要對它們進行了重新詮釋,尤其是對《中庸》的新詮與《大學》的改定。因為“四書經典結構的核心”不在“語孟”,而是在“學庸”。
對于《中庸》,自李翱賦予了它不同于前人的新詮釋以來,宋代理學家踵事增華,對《中庸》進行了新的詮釋與發揮,這一過程是從周敦頤開始的,繼之張載、二程,后集大成于朱熹。而他們對《中庸》的詮釋卻有著雙重目的:一方面,他們通過對《中庸》“關鍵詞、句”的新解而構筑了理學體系;另一方面,又置《中庸》于其理學思想內進行解讀,二者則是相輔相成、交融一體。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庸》被“理學化”的過程,恰是理學“宇宙本體論”的建構過程,而此“形而上”理論的建構,卻是在貫穿“天道”與“人道”的視域內,從“性即天道”(即“天命之謂性”)的立場出發,為“形而下”的倫理之教(人道),找到宇宙論的本體根據,也就是從“倫理學”到“宇宙論”的“形而下”與“形而上”的合一過程。在周敦頤、張載、二程等北宋理學家的視閾內,《中庸》與《易傳》是他們建構其思想理論的重要依據。周敦頤最先將二者合一,并用《易傳》解《中庸》,為“性與天道”賦予了更高的本體——“太極”。同時,他還把《中庸》的“誠”與《易傳》的“乾元”結合起來,解釋了天道運行會滋生萬物、天道變化而使萬物各得其稟賦的原因。而當“誠體”落實到“人道”時,它是仁、義、禮、智、信之本,孝悌忠順之源,在這一點上,“誠”又是仁義禮智等儒學重要概念的“本體”。所以說,周敦頤對《中庸》的闡發,尤其是對“性命天道”的本體論層面的發揮,雖然未改變《中庸》文本,但其內涵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與鄭玄的注解相比,更為明顯。誠如楊儒賓所言:“鄭玄的注解永遠沒有超越的心體、性體、道體這一回事……李翱、周敦頤出來了,他們認為《中庸》該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重要典籍,所以《中庸》就變成了與每個人的終極關懷以及宇宙的終極實相相關的典籍。”[4]與周敦頤相比,張載則在《中庸》的詮釋中賦予了“太虛之氣”的新說,這才真正形成了儒學自身的、而不是借用老佛之學的“本體論”。這種唯實的“本體”,即“太虛之氣”,正是產生萬物的根源,由此,《中庸》中的“天”、“性”、“道”和“教”等內容,因張載的“氣論”、“性論”而發生了改變,《中庸》一書的“理學”傾向便越來越明顯了。相較于張載,二程則將“天理”的意涵添加到《中庸》新詮之內。二人對《中庸》可謂推崇備至,尤其是程頤,稱《中庸》為“孔門傳授心法”,這是自《中庸》成書千余年來,對其最高的評價,《中庸》為子思之作的說法,正源于此。同時,“中庸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它經二程兄弟發明以來,千載不傳之秘由此而明于天下,世人皆可學而至矣,而非高遠難行之說。并且,《二程粹言》有言:“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這意味著,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即“天理”、“理”或“道”,它既為“本體”,又為“準則”。這樣,《中庸》首句的“天”、“性”、“道”之間的關系便因“理”而有了新意。這意味著,從周敦頤、到張載、再到二程,他們在為倫理道德層面建立“形而上”的本體依據的過程中,《中庸》被賦予了新解:《中庸》先言性,再言學,再言王道,“形而上”與“形而下”層面在《中庸》中實現了新的融合,完成了《中庸》的理學化改造。
《大學》單本的流傳過程與《中庸》有所不同,在唐代之前,并無單本的《大學》獨自流傳。據《四庫全書總目》載:“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為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也就是說,最早對單行本《大學》進行注解的是司馬光,清人朱彝尊在《經義考》中闡述《大學》發展史時,首提的就是司馬光的《大學講義》[5]443。但是,《大學》受到重視并被納入“四書經典結構”之中,卻是始自二程。對二程而言,他們承繼了宋初學者的“疑經惑古”風氣,對《大學》不僅是詮釋發揮,還改訂《大學》原文。二程不再奉“經傳文本”為金科玉律,在賦予《大學》新解的過程中,先進行的是調整《大學》原文的次序。在二程看來,《大學》不單是“孔氏遺書”(程顥語)、“孔子之遺言”(程頤語),還是入德之門、修身之關鍵,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但《禮記》中的《大學》原文卻“先后失序”,有違“大學本旨”,由現存的《明道先生改正大學》和《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可窺測出二程對《禮記·大學》內容的調整與更改。關鍵的是,二程對《大學》的用力絕不止如此,更體現在發揮《大學》的微言大義,尤其是程頤,還對《大學》原文有三處更改,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是把首句中的“在親民”改為“在新民”。不寧唯是,在《大學》原本中,對八條目的詳解是從解“誠意”開始的,但對“格物”與“至知”卻未有詳論,程頤則把其學說關鍵的“窮理”貫穿于“格物”與“致知”之中,這使《大學》中不曾解釋的格物、致知便因程頤的解釋,一躍而成為“修身之根本”與“大學之道”的“本始”。
所以,程頤為《大學》“格物致知論”所補充的“格物窮理”之新說,不但《大學》原文未曾闡述,即使韓愈的《原道》,也是止于“誠意”,絲毫未提及“格物致知”,而程頤卻“發前人千載所未發”。這一說法,不止是對《大學》微言大義的闡發,還將個人的“修齊治平”與宇宙萬物之本體的“理”相連。尤為重要的是,“格物窮理”也被程頤賦予了“本體論”的意義。因而,包含了“三綱領”與“八條目”的“大學之道”,上接“天理”,下啟“成圣”,其對個人而言的重要意義由此而凸顯出來。那么,經二程的改造而發揮的《大學》,其重要的地位自是其他儒學典籍所難以企及的,此皆二程之功也。
至于《論語》和《孟子》二書,在宋代之前,二者的地位是非對等的。自韓愈以來,雖有《孟子》升經的提議,但卻沒有結果。到了北宋,在《孟子》地位日漸上升的同時,一股“疑孟”、“非孟”的思潮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除了不認同孟子的某些觀點之外,最主要的是由批判孟子而反對王安石變法,尤其是孟子的不尊周王說,這誠如黃俊杰所言:“如果抽掉北宋王安石變法以后所引起的權力關系的重組這個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背景,那么,宋代知識分子或儒者爭辯孟子政治思想的原因及其意義,就顯得晦而不彰,甚至難以掌握。”[6]17然而,在張載、二程等理學家的視閾內,卻將二者作一體觀瞻。這是宋代理學家與其他儒者的不同之處。對張載而言,《論語》、《孟子》二書為見圣人之窗口,“要見圣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于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7]272。所以,王夫之評張載之學為:“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8]82同時,其作《正蒙》一書,正是效法孟子之“撥亂反正”而辟佛老之說。而在二程的思想體系內,不但視《語》《孟》為一體,甚至置二者于“六經”之上。《二程粹言·論書篇》有載:“于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9]1024程頤更進一步說道:“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與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知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圣人之意見矣。”[9]322而天下之書眾多,如何由讀書而明圣人之經旨?這還是要先從《論語》、《孟子》二書入手,“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圣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9]205非但如此,二書還在張載、二程等人的視域內,被賦予了新解,他們皆有專門注解的《論語》和《孟子》的著作,雖然大部分散佚,但從現存的吉光片羽中仍可窺測出他們通過對“語孟”二書中關鍵字、詞、句的新詮,即完成了二書的理學化改造。
至此,在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理學家構筑思想體系的過程中,《中庸》、《大學》、《孟子》、《論語》的性質發生了改變。雖然,正是由于“四書”的出現,才凸顯了這一過程的重要,但反過來看,如果沒有這一過程,恐怕就不會有后來“四書”經典結構的登場。
三、形成期:朱熹對“學庸語孟”的詮釋與合并
《宋史·道學傳》載:“(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又載“(程頤)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10]據此,有學者認為,“四書經典結構”在二程的視域內已經形成,更有人認為,在張載的學說中已有“四書結構”。雖然,二程與張載在“四書”經典結構形成過程中,實有奠基之功,尤其是二程對《大學》與《中庸》的表章,但若說“四書”在他們的思想中已經形成,恐怕是有可商榷之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書類一》載:“論語、孟子,舊各為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11]1其中,“淳熙”為南宋孝宗的年號(1174-1189),這期間即為朱熹完成《四書章句集注》的時間。同時,《經義考》內的“四書”首載的就是朱熹的《四書語類》,所以說,“四書體系”的正式形成,完全是出自南宋理學大家朱熹之手,尤其是他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重新詮釋,才有后來“四書”之規模,甚至可以說,朱熹在中國學術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四書”的建構。
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卒于慶元六年(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他生活的時代已是南渡之后的宋朝,因統治者的需要,理學由北宋時期的民間學術一變為官方支持的學說,在此大背景下,朱熹接受了理學的啟蒙,并且與程頤一脈的學人有著直接的關聯。縱觀朱熹一生,其學問、思想與“四書”關聯極深。考諸朱熹的學術歷程,他在5歲時,首先接觸到的蒙學讀物即是“語孟”二書,在他逝世之前,仍在修訂《大學》。而朱熹之所以重要,更在于他集理學之大成,在繼承張載、二程的學說的基礎上,將理學推向巔峰,這也是理學又稱為朱子學的原因。在此過程中,朱熹對《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進行了新詮釋,并且,他的“理一分殊”、“理先氣后”、“心統性情”、“主敬涵養”和“格物窮理”等重要命題,也在詮釋“四書”的過程中得到了彰顯。這意味著,朱熹與張載、二程一樣,在其思想體系內賦予儒學經典以新解。他先后著有《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孟子集解》、《論孟精義》、《大學集解》、《中庸集說》、《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后四者即是朱熹《四書集注》的組成內容。《論語要義》、《孟子集解》、《論孟精義》、《大學集解》、《中庸集說》等書就是朱熹一番考辨、取舍的結果,經40年之積累,最終刊刻成書。由此可折射出他對“學庸語孟”四書的用力之勤、用功之深,誠如宋儒李性傳所言:“是四書者,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遺蘊。”[12]3而與他人不同,朱熹對“四書”的詮釋雖以“己意”解之,但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通過對前人注釋的詳細考辨,這里既有理學家又有漢儒,朱熹是訓詁與義理并重,漢學與宋學的特征在朱熹身上交錯顯現,這也是朱熹的“遠邁前人”之處。
接下來的問題是,朱熹為什么會把“語孟學庸”融為一體,并提出“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此孟子,次中庸”的說法?首先,朱熹和其他理學家一樣,承繼了韓愈的“道統說”,并進一步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是古圣先賢相傳的“心法”,從堯到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淵、曾子,皆傳此法并照之行事。至子思時,邪說驟興,他懼此“道”失傳而作《中庸》,以昭之后學,尤其是將其傳給孟子。所以,朱熹在《讀書法》中反復強調《中庸》的重要位置,將其置之于后。其次,朱熹作為理學家,“理”是其核心思想,而“如何窮理”則構成了其思想展開邏輯。在二程的影響下,朱熹接過了他們“格物窮理”的大纛,自然也特別重視《大學》一書,因為其中有“格物致知”之說。朱熹曾言:“某于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于大學亦然”,可見,《大學》在朱熹視域內的地位,而朱熹對《大學》的詮釋,也是從改定章序開始的,這與二程的做法十分相似。更為關鍵的是,朱熹一方面把《大學》分為經、傳兩部分,一方面又據程頤之意補上“格物致知”的內容。同時,朱熹對《大學》的重視,還與宋初以來的“疑古惑經”思潮有直接關聯。因為,經書的權威地位喪失了,人們沒有可信任的經典書籍,所以在朱熹的視閾內,特別強調“格物窮理”,朱熹解之為:“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再次,朱熹延續了二程的“孔孟”及“語孟”一體的做法。在《讀論語孟子法》中,“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等關鍵說法皆源自二程,這一點毋庸置疑。最后,朱熹融“學庸語孟”于一體,并論其順序為《大學》、《論語》、《孟子》和《中庸》,這是因為:“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后,方宜讀之。”[12]249這意味著,朱熹主要是從方法論的層面構筑了“四書經典結構”,將此“四者”視為求學問道的次序,而若不是經過長久研習,是很難得出以上結論的。所以說,“四書經典結構”出自朱熹之手,“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禮記中,注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于諸子,及趙岐注后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實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注,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而行而舊說盡廢矣。于是四子者與六經并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5]541更為重要的是,“理一分殊”、“理先氣后”、“心統性情”、“主敬涵養”和“格物窮理”等重要命題,也在朱熹詮釋“四書”的過程中得到了發揮,使先秦儒學中的重要命題被“理學化”,誠如黃俊杰所說:“朱子畢生理會《四書》,并通過以‘體’‘用’以及‘理’‘氣’等概念為核心之哲學系統,賦《四書》以新解,就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代表作。”[13]所以說,朱熹《四書集注》的完成與刊刻,標志著“四書經典結構”的正式形成。關于《四書集注》的刊刻時間,本文仍以束景南的考證為主,朱熹生前《四書集注》編集合刻凡五次,分別是淳熙九年(1182),淳熙十一二年(1184-1185),淳熙十三四年(1186-1187),紹熙三年(1192),慶元五年(1199)[14]。
雖然如此,但“四書”走進千家萬戶而成為中國士人的必讀之書,卻是在朱熹的《四書集注》變成了科舉考試的“參考書目”之后,也就是“四書”的官學化,卻是從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開始的[15],使“四書”在元明清三朝取得了和“五經”一樣的重要地位[16]。不寧唯是,還出現了眾多的“四書”注解,僅據朱彝尊的《經義考》來看,其所收錄的《論語》等單書及“四書”成書以來至清代康熙之前,不同時期的眾多學者對它們的研究專著,《論語》類371種,《孟子》類150種,《中庸》類160種,《大學》類178種,“中庸大學”類71種,“四書”類334種,以上內容包羅萬象,從注疏、到釋義、再到考證,甚至還包括辨疑、講錄等,由此可凸顯出“四書”在元明清時期的影響力。
[1]屈守元,等.韓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2665.
[2]董誥,等.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6434.
[3]李逸安.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4]楊儒賓.《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歷程——從性命之書的觀點立論[J].臺大歷史學報,1999(24):29-66.
[5]朱彝尊.經義考[M].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6]黃俊杰.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M].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7]章錫琛.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
[8]王夫之.張子正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程頤,程顥.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1]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97.
[12]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黃俊杰.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辨證[M].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4.
[14]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7:628.
[15]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2018.
[16]韓東育.“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內情[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