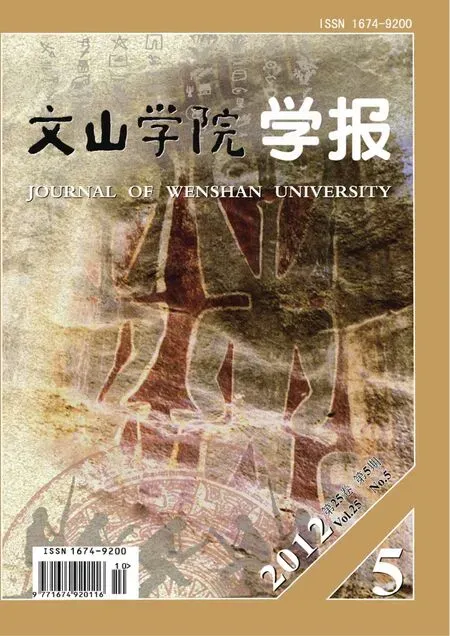試論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社會控制功能
洪 涵
(云南行政學院 法學教研部,云南 昆明 650111)
廣義地說,“社會控制”是指通過社會力量使人們遵從社會規范、維持社會秩序的過程。云南各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多種對超自然存在物、超自然力的信仰及儀式,以功能主義視角觀之,它們是一定時空條件下的社會設置,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承擔著社會控制的功能。
一、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種類
人們一般將具有嚴格的組織、教義、儀式、活動場所、神職人員的信仰形式稱為制度性宗教或人為宗教,而將與之相對的,教義、組織人員、活動場所、儀式活動都比較松散的信仰形式稱為原始宗教。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云南各民族形成了多種對超自然存在物、超自然力的信仰:
(一)自然崇拜
在先民的生活里,強大的自然力帶來的旦夕福禍,常使他們敬畏不已。在不能將之制服之際,只有寄希望與之修好,于是山、地、雷、電、火等自然物質、現象逐漸被人類視為“神”或“鬼”而受到膜拜。例如傳統上,云南佤族祭奉的最大神就是山神鹿埃姆和鹿埃松。
(二)動植物崇拜
動植物既是人類的生產資料、生活同伴,也可能傷害人類,各民族于是也將各種想象加在動植物身上。如云南藏族、摩梭人、普米族都有松樹崇拜,布朗族則有專門的祭竹鼠儀式。
(三)圖騰崇拜
“圖騰”本是美洲印第安人鄂吉布瓦語“totem”的音譯,意為“他的親族”, “圖騰”崇拜一般與族群劃分相聯。在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納西族、怒族均有崇拜虎的現象,以虎來命族名,認為虎是祖先、狩獵不獵虎,舉行大事時要擇“虎”日等等。
(四)祖先、靈魂、鬼魂崇拜
對夢、昏、死亡、疾病等現象的困惑,對先人、英雄的崇拜追思,促使先民產生了靈魂觀念,同時還基于血緣感情并加以功利主義的想象,認為祖先的靈魂一般是善的,能夠保佑生者。而陌生人的鬼魂則可能作祟為惡,應該敬而遠之。如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云南某些地區居民的甕棺葬中就有專門為不死的靈魂提供出入的小孔,表明當時的這些居民已有了復雜的靈魂不死觀念。[1](P18)
(五)巫術
人們企圖借助某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通過一定的儀式對預期目標施加影響或者加以控制的活動一般被稱為巫術。[2](P364)如怒江傈僳族相信有一種能致人死亡的“殺魂”巫術,如果路遇某人后生病,就是被該人“殺”了“魂”。[3](P216)
(六)禁忌
很多民族都有為避免招致不好的后果或懲罰,而規定、遵守一些行為規則,禁止同“神圣”或“不潔”的事物接近的禁忌。如云南哈尼族就禁忌牲畜上房屋、母雞學公雞叫。
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種類多樣、關系復雜,不過總結來看,它們都是通過一系列“儀式”得以表達,通過一系列“神話”得到詮釋的,其中,“對超自然存在以至于宇宙存在的信念假設部分”,就是信仰;“表達甚而實踐這些信念的行動”,就是儀式。[4](P219)一方面,人們口耳相傳了種種言說與神話,替各種信仰找出解釋的理由,構成一個滿足人類求知愿望的系統,另一方面人們還普遍采用祭祀、祈禱、舞蹈、歌唱等形式來表達這些信仰。
二、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社會控制功能
人類學的功能主義視角,主張研究、揭示社會有機體中各種社會設置、文化因子的“功能”。以功能主義視角觀之,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在傳統社會中承擔著如下社會控制功能:
(一)穩定社會主體
原始宗教信仰可以安撫個體心靈,使個人確定性地歸屬于某個集體:
1.安定、撫慰個體心靈
信仰一般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們所進行的一種自我調適,它幫助人們將現實中的種種不確定神秘化,使各種社會存在在人的主觀意識中“有序”而不“動蕩”。如面對生老病死,許多民族都相信死者靈魂不滅,常由巫師手持刀、矛或木棍開路,為死者舉行“送魂”儀式,讓其與祖先歡聚。通過此類儀式,安撫了生者的內心,使個人得到了關于生死、意外的解釋,通過穩定社會個體,進而實現社會有序。
2.劃分社會群體,促進族群認同
在初民社會,地域分割性明顯、群體依賴性強,對生產、生活資源的爭奪往往以群體為單位,所以劃分群體,在群體內進行合作,群體外或競爭或合作,穩定社會成員的分布,使個人歸屬于某個集體,是社會控制的基礎。云南民族傳統社會經常借用原始宗教的途徑來劃分群體及其“勢力”范圍,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1)通過圖騰、借助神話。如云南怒江白族《氏族來源的傳說》解釋了白族熊、虎、蛇、鼠四個氏族的來源,并分配了他們的居住地——蘭坪、怒江、瀘水①。這種基于動物圖騰所作的群體劃分,既強調了幾個支系的同源及團結,又對他們各自的地域范圍、自然資源進行了確認、分配。
(2)通過設立并祭祀寨門、寨心、寨樁的形式。寨門、寨心、寨樁是承擔著群體劃分功能的建筑文化,如云南愛尼人的傳統寨門分坑瑪(前門、大門)、坑止(后門)、坑丈(側門)三種,每年三四月份,全村成年男子要在祭司“追瑪”的指揮下舉行祭寨門儀式。[5](P179-185)又如傣族、布朗族、阿昌族、拉祜族的寨子也有以某些建筑物或設施為標志的“寨心”,以強化“寨子”的存在。
(3)通過崇拜守護神。如傣族把有共同血緣和歷史關系的許多村寨組成的片區稱為“勐”,每個勐有勐神一至幾名,他們一般是建勐時的英雄或首領,用專門的祭祀勐神的儀式,祭祀期間全勐要停止生產活動二至三天。祭祀時還要統一服裝,通往其它村寨的路口要插上樹枝“封路”。[3](P323)
(二)形成公共執事組織,集中行使公共權力
沒有公共決策、管理組織及首領,社會秩序會發生紊亂,云南傣族《咋雷蛇曼蛇勐》、哈尼族《三種能人》等文學作品都反映了這一道理②。各民族還基于原始信仰,形成社區的首領、公共執事組織,管理公共事務:
1.用神裁或神裁與原始民主相結合的方式
如布朗族的“召曼”(村社頭人)是通過在神廟里抽簽產生的,他們認為這是本寨寨神“再曼”選擇的頭人。[6](P71-72)又如基諾族認為,祭司、鐵匠的產生是“鬼女”看上了人間的某個人,而來挑逗,被選中的人會得到種種預兆,見到預兆后要去求卜,若被卜證實,就要與鬼女結婚,然后擔任祭司或鐵匠。[7](P800)
2.直接以神的名義宣布
一些首領、執事人員的產生直接被以神的名義指定。如歷史上云南傣族過“開門節”時,最高頭人要按程序分封或加封各頭人,并對百姓說:“當著佛的面,把你們喜歡的人,擁護的人加封了,你們要好好聽他的話,要你們做什么就做什么。”被封的人面對佛像念讀任職誓詞,念畢,將其燒為灰放入杯內,當眾一飲而盡,以表示對封建領主和佛主的無限忠誠。[8](P135)
3.神職人員轉變為世俗首領
弗雷澤曾在其著作《金枝》中分析了一些民族所共有的由“祭司”發展到兼行首領、祭司權力的“首領”,再到“祭司”、“首領”分離的歷史過程。[9](P48-49)云南民族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例子,如彝族畢摩就是源于父系氏族公社時代的祭司和酋長,直至唐、宋時期,祭司仍由酋長兼任,到忽必烈平大理國,將原有酋長/祭司任命為土司、土官后,一種叫“奚婆”的祭司才從奴隸主、封建主集團中分裂出來,清朝改土歸流后,進一步發展為專司宗教職事的畢摩。[1](P214-215)
首領及公共執事組織產生后,各民族往往還通過各種禁忌、神話來強化首領、公共組織的權威。如愛尼人推選“龍巴頭”,要求其家中“清凈”,“清凈”指的是家中沒有六指、雙胞胎,家人健在、沒有未婚先孕,辦事公道等。又如昆明彝族撒尼人祭天選舉會長、祭司、執事人員時,凡行為不端、重婚納妾、當年家中有產婦及喪事者均不得當選。
(三)形成行為規范,調整社會關系
許多民族傳統信仰,在觀念上是唯心的,但在行為上,卻是唯物的,信仰,把神與人類生產生活秩序聯系在了一起。
在生產秩序方面,云南許多農耕民族在砍地、燒地、播種、收獲、裝倉時都有祭祀儀式,這些儀式,安排了生產秩序,灌輸了生產常識。如哈尼族每當陽春三月,無論男女老少只要第一次聽到布谷鳥叫,都要報一聲“我聽見了”,并要在多數人都聽到布谷鳥叫聲后,約定一個屬羊的日子,向布谷鳥獻祭,以求五谷豐登、六畜興旺。[3](P328)
在生活秩序方面,云南各族在誕生、成年、婚姻、喪葬等方面都有一些超自然信仰及儀式。如瑤族男子“度戒”,要經翻云臺、上刀梯、踩火磚等考驗,還要由度師傳授宗教儀禮,背誦宗教經典和本民族、家族歷史。度過戒后才能正式成為“盤王”的子孫,列入家譜名冊,同時說明男子已進入成人階段,有了參加村社各種社會活動的權力和婚戀的資格。[10](P101-119)
(四)懲罰越軌行為,解決糾紛,救濟權利
在生產生活中,基于信仰,人們自覺維護“規范”,社會得以有序。倘若出現違反規范的越軌行為,源自信仰的強制力會對之進行制裁:
1.直接提出以超自然制裁力為后盾的行為規范
“超自然也經常(雖然并不是一直)嚴密地監視著活人的道德行為。而且人們也常常把習慣規則和程序附會成天神的旨意,使其更具約束力而帶有終極、絕對與神圣之名。”[11](P368)如納西東巴經典中常提到“犢姆”一詞,意為做事的規矩、程式。“犢”為可以做的事,公眾認可的事宜,“莫犢”則為不可以為之事。再如哈尼族的《神和人的家譜》,也談到最大的天神俄瑪在創造兒孫時,覺得應該先造“規矩”和“禮節”,沒有他們,神殿都會被“鬧翻掉”,所以首先生了“瑪白”和“煙似”這兩個“規矩” 姑娘和“禮節”姑娘。[12](P65)
2.糾紛解決及權利救濟制度
(1)神判。在云南許多民族歷史上都曾有過撈油湯、占卜等神判方式。如阿昌族發生是非之爭難分涇渭時,就約定地點,找來公證人,由當事者同時點燃大小、長短相同的兩支燭,以誰的燭燃燒時間長為有理。[6](P83-84)
(2)通過祭祀、巫術。許多民族在驅鬼儀式中都要驅逐“口舌鬼”。如景頗族在木腦縱歌中要由三個“董薩”念“木宋鬼”(即“口舌鬼”),據說這類鬼有30多個,它們會使人們生病惹禍、吵架斗毆,必須殺牛祭獻。[13](P85)蘭坪維西的那馬人用“活人鬼”來稱呼活著的某些女人的魂魄,每個村子中的幾個嘴快、心丑的女人都可能被視為“活人鬼”,在祭鬼時,要念她們的名字。[14](P416)
三、原始宗教信仰承擔社會控制功能的特點
云南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承擔著社會控制的功能,其特點有:
(一)自發性、內化性
傳統信仰的產生,不是精心設計的結果,它們源于人類的情感和心理活動,也源于人類的現實社會生活。這些信仰通過儀式、神話的反復強調,形成一種固定化模式,每一個新的個體在社會化進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著它們的模塑。
(二)神、人、自然秩序的合一性
原始宗教信仰,以鬼、神的邏輯來解釋整個宇宙、整個世界,將神、人、自然秩序合為一體。世俗公共執事組織的活動、人們的行為規范都以神的名義來進行、來發布,社會控制通過這種“合一性”得以實現。
(三)微觀、宏觀調控相結合
從微觀來看,原始信仰雖然提供了一些行為規范,但這些規范還是有些雜亂、混沌、含糊不清。原始信仰的社會控制功能主要還是體現在調適社會主體心理、劃分社會群體、加強社會團結這些宏觀層面上。
(四)調控結果的超驗性
原始信仰發揮社會控制功能的“后果”,往往是非理性的、超驗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不了了之
當事人可能基于神秘的信仰,安慰自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還可以通過詛咒、發誓等形式,給自己憤憤不平的心態予緩沖。雖然這種糾紛解決方式可能只是放空炮,非正義方得不到現實的制裁,但卻可以緩解矛盾,為社會減壓。并且當一個人在菜園中咒罵、對著竹籬笆念念有詞,以求蔬菜等不被偷盜之際,周圍的觀眾,將再一次感受、重溫共同行為規范。
2.讓當事人如“驚弓之鳥”
“是鬼魂、幻影、幽靈造成的雖無根據但有益處的恐懼,它使得冷酷無情的惡棍和亡命暴徒膽戰心驚。”[15](P109)神秘的信仰憑借著神靈的詭異,使當事者可能基于對超自然力制裁的恐懼而出來承擔責任,甚至因被嚇而曲打成招。如云南怒江傈僳族就有過因畏懼撈開水而自殺的事件。[6](P4)
3.基于概率得到某種不一定符合實質正義的“后果”
傳統社會有限的物質技術條件,難以確保實體正義的真正實現,神秘信仰之下的種種定分止爭的期望,可能會基于概率得到某種“說法”。如撈油鍋的結果可能單方受傷也可能雙方受傷或雙方都不受傷,出現前種情況,則糾紛可以得到解釋,后兩種情況則需要其它解釋,如可以解釋為此次主持者的咒語無效,也可以解釋為雙方都是無辜的等等。雖然“神的旨意”不客觀、不科學,但事實上卻有助于冷卻矛盾。
4.將偶然性事件視為“應驗”的表現
將偶然性事件視為“應驗”的表現,既可能是認識上的錯誤,也可能是基于現實生活中的某種“必然”而得出的“推定”。例如傈僳族的“殺魂”之說,之所以會將路上偶遇的“某人”確認為“嫌疑人”,多是基于生活經驗。就如普里查德分析阿贊德人請示毒藥神諭一樣,他們總是從平時有過矛盾的人當中一一列出“嫌疑人”的候選名單。[16](P123)
社會有序離不開社會控制,社會控制的方式與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關聯。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在血緣、地緣、族緣密切聯系的小型社會中形成和存在,這種小型社會有同質的文化背景,容易形成集體意識,便于實現社會控制。在傳統簡單社會向現代復雜社會變遷過程中,原有的社會控制方式也將逐步發生變遷。現代社會應該根據復雜社會的特質及現實需要,構建、完善適宜的社會控制方式,維護社會穩定。
注釋:
① 故事說的是,一場洪水災難后,剩下的兩兄妹得到神的旨意成親,他們先后生下五個女兒,大姑娘嫁給熊,發展成一個大氏族,住在蘭坪一帶,叫熊氏族;二姑娘和老虎成親,后代叫虎氏族,居住在怒江地區,即勒墨人;三姑娘嫁給青蛇,生兩兄弟,兩兄弟又生子,有的說怒族話,有的說傈僳話,他們是蛇氏族;四姑娘嫁給老鼠,他們帶著孩子在瀘水居住,后代為鼠氏族;五姑娘和毛毛蟲結婚,婚后被毛毛蟲嚇死,沒有后代,所以也就沒有毛蟲氏族。參見呂大吉、何耀華:《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白族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頁。
② 傣族《咋雷蛇曼蛇勐》說的是“盤巴”時代、“賴盤賴乃”時代,首領沙羅、桑木底分別認為人類社會要有序都得有“頭”。哈尼族《三種能人》講的是官人、祭司、匠人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參見王松、王思寧:《傣族佛教與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3頁;李少軍:《詩性的智慧——哈尼族傳統哲學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27頁。
[1]呂大吉,何耀華.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彝族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2]莊孔韶.人類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郭恩九.云南文化藝術詞典[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4]李亦園.文化與修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5]楊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護和祈愿[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6]夏之乾.神判[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7]呂大吉,何耀華.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基諾族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8]王松,王思寧.傣族佛教與傣族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9][英]J.G.弗雷澤.金枝[M].徐育新等譯.劉魁立審校.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10]趙廷光.瑤族祖先崇拜與瑤族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
[11][美]基辛.文化人類學[M].張恭啟,于嘉云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
[12]李少軍.詩性的智慧——哈尼族傳統哲學思想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3]劉稚,秦榕.宗教與民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14]呂大吉,何耀華.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白族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15][英]J.G.弗雷澤.魔鬼的律師——為迷信辯護[M].閻云翔,龔小夏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16][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