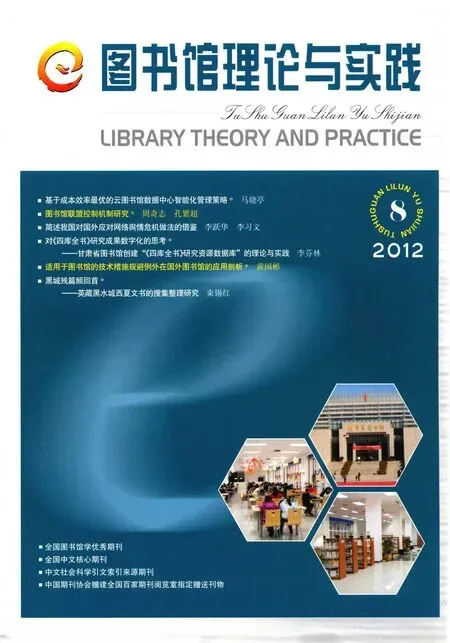試論花兒分類的歷史與現狀
●李 瑋(寧夏群眾藝術館,銀川 750001)
20余年前筆者在西北第一民族學院音樂系讀本科時,系里把花兒列入民族民間音樂課的教學內容之一,曾請已故的老花兒研究家劉尚仁先生講授過花兒課。劉先生雖然簡略地介紹了甘肅臨夏地區盛傳的河州花兒和洮岷花兒的基本情況,但這個具有獨特民族地域色彩的歌種,引起了筆者的極大興趣,從此開始留心學習閱覽有關花兒的介紹性、研究性文章和專著。
筆者畢業后分配到寧夏群眾藝術館文藝部工作。為發展建設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社會文化藝術,寧夏也把花兒列為熱門課題,從上世紀90年代起,由寧夏群藝館牽頭,西北五省區協辦的“沙湖杯西部民歌(花兒)大賽,”每兩年舉辦一屆,使我們這些只有一時一地的課堂講座知識、沒有田野實際考察積累的后學者,大開眼界,增添了學識。原來除了甘肅的河州花兒、洮岷花兒之外,還有寧夏花兒、青海花兒、新疆花兒及漢、回、撒拉、東鄉、保安、裕固、土、藏、東干等民族的花兒。各地區、各民族中傳唱的花兒(有的又稱為少年、干花兒、山花兒、山曲子、山歌、花兒號子、花兒小曲……)有的曲同詞異,有的詞同曲異,有的詞曲皆不同,有的曲詞又大同小異。對于這種千百年來以甘、寧、青為中心,在西北五省區及其周邊的川北、內蒙西部(甚至西亞東干族和中亞回族移民中)廣泛傳唱演繹的統稱為花兒的歌種,如何正確地分類?怎樣從音樂和文學等方面認識區分它們的共性與個性特征?帶著這些問題,筆者開始了進一步學習、考察的歷程。[1]
一 中國的民歌采風制度與民歌保護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我國周代開始建立了搜集民間歌謠的方法與制度,這主要是統治者用來考查民間習俗、社會風尚和政令得失的一種措施。《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漢書·藝文志》稱:“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由于采集的對象主要是“風”(民歌、民謠),因此又稱為采風。除了觀民風之外,“公卿和列士”還要借重于民歌的音樂文學格式,加工創作歌頌統治者文治武功的“頌”歌和表現當時社會風情的“雅歌”。所以《詩經》應是西周—春秋時期的古代歌曲總集,“風”基本上是北方各地的民歌,即所謂的“十五國(諸候國) 風”,“大雅”與“小雅”是貴族和士大夫借重“風”的音樂體裁格式填詞創作的“雅歌”(藝術歌曲),“頌”是他們為頌揚統治者文治武功的“頌歌”(多為宮廷慶典禮儀用的儀式歌曲)。《史記·孔子世家》說:“詩三百篇,孔子皆能弦歌之”。可見當時孔子興辦教育時,所設置的六門課程(六藝)之二的“樂”,主要教唱的就是這些古代的經典歌曲,才有了《詩經》的稱謂。《春秋左傳》記載:“吳季札在魯國觀賞樂舞,所奏音樂的次序基本上與《詩經》編次相同”。這說明了古代宮廷慶典儀禮樂舞,是由宮廷樂師樂工用《詩經》編創演繹的。[2]
楊蔭瀏先生在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認為“風”和“雅”有各種不同的曲式,有些一個曲調重復幾遍后,用副歌作為尾聲,有些一個曲調前面用副歌作為引子,還有些一個曲調在重復中作換頭的變化,還有兩個曲調各自重復作有規則或不規則的交織變化等等。乾隆時期敕撰的《詩經樂譜》,為古代詩樂中規模最大,收譜最多的刊本。所收曲調略同于歷代詩樂,多為一字一音的古代歌曲的主要特征。筆者所以不厭其煩拿《詩經》作為本文的導引,因為其一民歌是一切音樂最早的源頭和基礎,世界各國各地都是如此。其二是我國最早開始編輯論述古代民歌和藝術歌曲時,就開始了科學的分類與體裁、形態、音樂特點的分析。其三是在文字沒有形成以前,民歌是“感于心而形于聲”的一種呼喊與聲腔,是無詞的空歌,音樂界稱之為“腔民歌”。各地區、各民族傳承至今的勞動號子和山歌中,多保留著古老的腔民歌的痕跡。文字形成以后,人們逐漸把即興呼喊出的聲腔加以組織,演化成一句、二句、三句、四句等各種形式的音調、曲調或音響組合等,并填入含有語義性的詞句,就形成了“調民歌”(曲牌、曲調、小曲、鑼鼓詞)。人們在實用時可根據表達內容和情感的需要,依譜輾轉填詞創作,也可根據需要加上樂器或裝飾的服飾道具,合著音樂節奏邊舞邊唱。[3]
中國最早的一部音樂理論專著《樂記》,對詩、樂、舞同源共生和聲、音、樂的不同含意作過簡練又確切的解釋:“感于物而動,故形與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以言為本,以聲為用,言之不足,則歌詠之,歌詠之不足,則手舞之足蹈之也”。由上可見,中國對音樂的形成與發展的解釋,與歐洲是不同的,歐洲人認為音樂是上界的語言,是古希臘掌管文藝科學的女神繆斯創造和賜給人間的,所以以女神的名字“Music”來為音樂命名,象征音樂是最美最純的天籟,有令人心曠神怡的功能。這種解釋只能引起人對美的向往和追求,但卻是不確切、不完整的。在中國漢語中,聲、音、樂三個詞雖同為表達音樂的詞語但卻有不同的含意,“聲”泛指包括天籟、地籟、人籟在內的一切聲響,其中也包括各種噪聲;“音”指有秩序,有條理、有組織的音調與音響組合(曲牌、小調);“樂”專指詩、樂、舞三種因素混為一體,尚未分化的古代樂舞。這些樂舞是上古時代各民族部落的群眾,在漫長的生存斗爭中逐漸創造發展起來的。例如講述歷史傳說的敘事歌,慶典儀禮時用的儀式歌,迎來送往的問答歌,談情說愛時唱的情歌,各種勞動生活中唱的漁歌、牧歌、船歌、夯歌、農事歌等。各種各樣的民歌都與各種具體的社會生活活動密切結合在一起,由于其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和可塑性特點,才能夠廣泛流傳,代代傳承,發展演繹,經久不衰。[4]
其次民歌是人民大眾口頭創作、代代傳衍的活態文化,它包含著音樂(歌)和文學(歌詞)兩個相輔相成的組成部分,按現代通行的按不同音樂體裁分類的方法,把民歌分為勞動號子、山歌、小調三大類,花兒一般都是歸入山歌類的一種歌種。20世紀以前中國還沒有民歌、詩歌這類稱謂,古代一直沿用的有歌、詩、謠、辭、曲、令、調、樂、引等稱謂,這是因為中國古代音樂(歌)和文學(詩詞)一直是同源共生、相輔相成的孿生姐妹,都是采用依譜填詞、依調度曲作歌的方法創作演繹而成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西方比較文化學和科學的分類方法傳入我國,才開始將人民大眾口頭創作輾輾填詞的勞動號子、山歌、小調統稱為“民歌”,把文人依譜度曲填詞創作的詩詞稱為“協樂文學”或詩歌。歌詞嚴格的說是詩歌的分支,唐以后把詩、詞、曲、令等依譜度曲填詞創作演唱的詩歌稱為詩余,把講究平仄對仗、聲韻格律的,供科舉考試和創作、欣賞、對答、朗讀的純文學的律詩、古體詩才當作是正規的詩歌。所以歌詞和詩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兩者雖有許多共同之處,卻也有截然不同的特性。歌詞兼有歌與詩的特性和品格,雖然在填詞作歌時也要講究語言的精煉、準確、生動、通俗、言簡意賅、韻律和諧,但這些文學上的特征是通過樂節、樂句、曲調、節拍、音樂特殊表情法來體現的。[5]
二 不同歷史時期的花兒采錄收集與研究開發
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視采集民歌的活動,歷代統治者都建立過樂署、樂府、梨園等專門的音樂機構,從軍、從政、從文、從藝的官員大都經過嚴格的科舉制度的培訓考試,一般都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藝術修養,他們在任或離職后,都兼有采風采詩向統治者進獻民族民間樂舞百戲的習慣。歷代統治者采集民歌民謠的制度和舉措,除了解民風民俗,考正制度的正誤得失之外,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打造宮廷官府盛大排場的禮樂和供上層社會宴享娛樂的樂舞百戲。博大精深豐厚的中國傳統音樂、詩詞、說唱、戲曲、雜技、百戲……就是在不斷地采集、加工、演繹、改編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積淀起來的。
歷代的方志、典籍、歌集、樂書、樂譜中,如《詩經》《樂府》《楚詞》《宋詞》《元曲》及明清時匯編的《山歌集》《神奇秘譜》《白雪遺音》《霓裳續譜》《納書楹曲譜》等,雖然查不出有關花兒的論述和曲譜文字的記載,但從民歌一脈相傳的特性來說,我們卻可以從“十五國風”和“秦隴樂府”中找出與花兒有聯系的信息和痕跡。民間花兒唱詞中唱的“留下少年的孔圣人”“張良留下的唱山歌”,“花兒是誰最先唱,西天取經的孫悟空”……,民間歌手為表明花兒的古老,把花兒與喜歡編歌、唱歌的古人聯系起來,盡管這只是杜撰的傳說不能作為信史。甘、青一帶傳衍至今的氏族社會聚眾唱歌野合的“花兒會”,以及歷代在甘寧青一帶從政參軍的文人學士,在考察民俗民風的記述詩作中,提到花兒的詞句也有不少,這些歷來都是花兒研究家們作為探索花兒源流的依據反復引用過,這里不再一一贅述。
上世紀20—40年代,陸續有不少獨具慧眼、青睞喜愛花兒的研究家們采錄收集花兒歌詞并編出專集出版,為這種長期在西北民族民間自然傳承的具有獨特風格色彩的民歌俗曲能登上大雅之堂被國內外了解賞識,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23年我國地質學界的前輩袁復禮教授在甘寧一帶搞地質調查時,曾將采錄的花兒歌詞30余首整理出來并寫了介紹性文章,以《甘肅的歌謠——話兒》為標題,發表在“五四”新文化中心——北京大學創辦的《歌謠》專刊上,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北大教授鄭振繹、朱自清等在編寫講授中國文學時,多次引用花兒歌詞作為論述介紹中國傳統歌謠的例證;張亞雄先生是最早收集研究花兒(歌詞)的學者之一,他1936年前后陸續在甘肅、四川等地的報刊上發表采錄收集的花兒歌詞及論述介紹花兒的短文,后匯編成《花兒集》一書于20世紀40年代初期出版;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1929年任甘肅者通志局副總編纂的慕少堂先生,以他為首編纂的西北地方史巨著—《甘寧青史略》,在《副卷之五·歌謠匯選》中,選編了百余首民國初期甘、寧一帶地方武裝拉桿子造反、燒殺搶掠時編唱的花兒歌詞,還附有一首常用的隴山花兒曲調——《打老鄉歌》。[6]
早期的花兒研究家們從人文學和民俗學的角度,對花兒的源流、傳播、文學格式、民俗價值和藝術特點等,進行過卓有成效的探討和研究。如認為花兒是勞動大眾的心聲傾吐,是他們“任性而為,沖口而道,亳無掩飾,其得意處,正其本色……”,是“情動于中則歌詠外發,番漢所謳,借抒胸臆……”,認為隴山花兒的特征是“一人獨唱,誰為顧曲之周郎,三句一疊,酷似跳月之苗俗”。認為花兒繼承發揚了《詩經·國風》中的賦、比、興手法,“畢竟其中多比興,松崖評語(指清吳鎮詩‘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正相宜……”,“其詞雖不雅,而體兼比興,置之三百篇中,可與鄭衛諸詩并垂不朽矣”。“……然民間花兒,茍精其術,亦可致遏云響谷之妙,一豈古之伊涼調乎?”他們當時就開始注意到了“音調是花兒最要緊的,花兒的靈魂完全寄托在音調上面。……但編樂譜是專門的學術,花兒又浩如海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生吞活剝地抄來許多歌詞,沒有活的音調來輔助它,終久是干枝葉了……”。“夫歌曲之美,三分附著于字句組合,七分寄托于音調的仰揚高下,抄寫記錄歌曲,只抄寫一小部分姿首,大半神魂天韻捉它不住。比如采集標本,把一朵牽牛和一只蝴蝶,生吞活剝地粘夾起來,結果是一片桔草和一只干蝴蝶,有什么天然的美妙神韻呢?”在前輩的啟示下,被譽為“西北民歌之王”的著名音樂家王洛賓和著名電影音樂作曲家、原重慶國立音樂學院教授王云階等,首開全面記錄花兒曲譜之先。據有關文論中記述,王洛賓記錄的甘寧青花兒曲譜很多,除散見于三、四十年代編輯的花兒專集和期刊外(多未署名),其他均已散失,唯一保留下來的是上述《甘寧青史略·歌謠副卷》中的《打老鄉調》和在寧夏廣為傳唱的六盤山回族山花兒《眼淚花花兒把心淹了》。王云階教授為了給40年代著名影片《塞上風云》配曲,到青海深入生活時,曾記錄了三十余首花兒曲調,完成配曲任務后,將記錄的花兒曲調編入教材或在報刊上發表,引起當時國統區音樂界的很大興趣,馬思聰、陳田鶴等作曲家曾將其改編成重唱、合唱歌曲在教學或音樂會上演出,創立了用花兒音調創作歌曲器樂曲之先。王云階記錄的花兒曲調1951曾結集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山丹花》,這是我國早期唯一結集出版的花兒曲調選集。這些先行者早期的收集研究活動,為花兒音樂的收集、整理、傳播、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給學術界留下了一些珍貴的資料,起到了承先啟后的作用。[7]
三 花兒收集整理與研究開發的繁榮昌盛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經受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薰陶的老一輩文藝家的倡導帶動下,花兒音樂的收集、整理、開發、利用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可喜局面,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65年以前,北京、上海及西北諸省區出版社出版的花兒和選有花兒曲調歌詞的選集約有百余種之多,用花兒令調整理、改編、創作的歌曲、器樂曲、舞蹈、歌劇、舞劇、歌舞劇、影視音樂作品更是多不勝數。花兒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山歌野曲,象出土明珠珍寶一樣,沐浴著和煦的春風,登上了新中國的藝術殿堂,受到國內外普遍的關注和贊賞。更為可喜的是,這一時期花兒曲譜文詞的記錄整理,開始走了嚴謹正規,對音準、節奏、表情、速度、句式結構、調性調式及方言聲韻、唱法類別等,一般都開始注意進行標記和注解。尤其是把土生土長的花兒歌手請進文藝團體和音樂學府,用當時盛行的磁帶錄音技術,準確的把他們的原生態演唱錄制下來或復制成唱片出版發行。如中國唱片社1954年前開歷史之先河,出版了西北花兒王朱仲錄演唱的花兒曲令唱片,西北各地區廣播電視臺和電影制片廠或文藝團體,都保存有一些早期采風調查時的民間歌手的現場演唱錄音,這些珍貴的、不可再得的經典文獻資料,曾為花兒音樂歌詞的整理研究和開發利用發揮過應有的作用,也為《中國民間歌曲集成》西北五省區卷的進一步普查選編打下了一定基礎。[8]
雖然花兒在毀滅文化的“十年浩劫”中遭到過無情的摧殘,但正象花兒唱詞中所唱的“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子拿來頭割下,不死時還是這個唱法”。“任憑你有遮天手,難封世上唱歌口……”。粉碎四人幫后,花兒的演唱活動、采錄整理、研究開發等又恢復了勃勃生機。尤其是1979年始,由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音協有關協會發起并主辦的全面搶救收集民族民間文化藝術遺產、編纂10部文藝集成志書的浩大工程,各集成志書以省、市、自治區分別組織領導機構和普查編輯班子,在深入基層,全面普查收集音、譜、圖、文、象資料的基礎上,分別選編立卷,由全國編委會和總編輯部三審定稿、統一驗收出版。1999年經國務院批準,將修筑新文化長城、編纂十部文藝集成志書的工程,列入“六五”——“八五”期間藝術科學系列的重點科研項目,成立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實施,并專門下文規定審定驗收出版經費由國家財政統一安排解決,普查編選經費由各級財政部門予以保證,各集成志書總編輯部與出版單位統一制定了普查編纂的規范體例和要求,使民族民間文藝的采錄、整理、選編、審定、出版等工作全面步入規范嚴謹的新歷程。
四 新時期以來花兒的整理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1980年以前,花兒的調查研究處于分散自由狀態,且范圍狹小,調查研究方法不夠科學細致,因而,各省區學者和愛好者都以個人調查收集所得作一般的介紹論述,對花兒的源流、類別、音樂文學特征等進行單一簡略的分析研究,因此產生許多不必要的爭議。就拿花兒的源流、名稱和分類來說,早期的調查研究多局限于甘肅境內,河州花兒和洮岷花兒被視為是正宗本源,其他的都是支流或傳入者。這明顯是不符合各民族各地區花兒生成傳衍的歷史與實際狀況。更何況河州花兒并不能完全涵蓋其他花兒類型的歷史和形態,洮岷花兒只是在洮岷兩地花兒會上演唱的與河洲花兒不同類型的高腔山歌,在其他有傳統花兒會或新型花兒會的省區是不傳唱和流行的。[10]
民歌集成西北五省區的普查選編,以現行政區劃和民族、歌種音樂體裁分類的方法,雖對各省區、各民族中長期傳衍的民歌歌種首次進行了統一規范,但忽視了民歌生存傳衍的生態環境和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百人百調、千人千腔、十唱九不同的實際情況,對一些兼有山歌、小曲甚至勞動號子特征的混生型花兒都劃入同一類型歌種,而且各類相互重復的曲令論述太多,把一個跨省區、跨民族甚至跨國界、廣泛傳唱并約定俗成統一稱為花兒的各具形態特征的歌種,按一種規范和類型來歸類分析,從人文學、民俗學和比較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的角度來說,是不夠科學和不符合花兒生存傳播的實際狀況的。
在民歌集成普查選編的同時,中央和有關省區的民族音樂學家,在充分了解和掌握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上,用國際通用的人類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念和方法,提出共同文化區和獨特色彩片的理論,把花兒民歌和其他音樂文化的分類研究,引入科學化、規范化、附合歷史發展實際的新的高度。20世紀80年代初,武漢音樂學院教授楊匡民先生首先提出湖北民歌色彩區的概念,隨后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苗晶、喬建中二位研究員撰寫了《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劃分》,他們應是我國音樂界最早提出按地域文化的不同色彩進行音樂分類的學者。緊接著甘肅師大音樂系教授赴西北五省區對各地傳唱的花兒進行調研后,撰寫了《花兒的體系與流派》,青海藝術學術院張谷密教授撰寫了《論花兒的旋法特點及藝術規律》,青海藝術館周娟姑撰寫了《花兒音樂的民族地區特點》,寧夏民族藝術研究所劉同生研究員撰寫了《花兒的音樂與文學》,這幾篇論文都以比較文化學和民族音樂學的觀念和方法,從宏觀的共同文化區和微觀的獨特色彩片入手,對各地區、各民族統稱為花兒歌種的生成發展和類別形態以及不同的演唱審美習慣等,進行了綜合的分析論述。這種先按地域分、再按民族和不同類型分的科學分類方法,在民歌集成甘、寧、青等卷的概述、分述中也得到了共識和體現。
比較文化學和民族音樂學實用的科學分類法,是音樂學家在研究過程中采用的手段、方法、渠道、途徑和特有工具、它可以促進研究家們的思維方法趨于科學化、規范化、多樣化,使研究者的主體認識與研究對象的客觀實際與規律和諧一致,從而開拓和體現出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廣度。21世紀以來,用新的視點和方法,全方位、多學科、從宏觀和微觀多種角度研究花兒已成為一種時尚,出現了許多具有一定深度、廣度和學術價值的專著和論文。其中關于花兒的分類已突破原來的兩分法、四分法、六分法等局限。現就個人學習研究所得,分別簡述如下:
(一)在共同文化區廣泛傳唱的同類型花兒,多數學者稱為河湟花兒(又名少年、話兒、山歌、野曲、干花兒、山花兒、花兒小曲、花兒號子、回回調、漢族耶爾、回族耶兒……)
按傳唱流行地域可分為:
1、甘肅河州花兒:包括東鄉花兒、西鄉花兒、南路花兒、北路花兒、隴西、隴中、隴南花兒、蘭州花兒、河西、張液、武威花兒、平涼花兒等。
2、青海花兒(青海少年):包括東部農耕區傳唱的河型花兒,西部農牧區傳唱的羌藏味河湟型花兒等。
3、寧夏花兒:包括西海固地區、銀南、銀北、銀川、鹽池及現內蒙西部一帶流傳的河湟型花兒。
4、新疆花兒:包括昌吉、焉耆花兒等回族聚居地流傳的河湟型花兒。
5、陜西西北部花兒:包括寶雞地區、陜北、陜川邊境一帶流傳的河湟型花兒,又稱為涇渭花兒。
6、西亞吉爾斯、哈薩克斯坦東干族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7、港澳、臺地區西北人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8、東南亞各國西北移民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按傳唱民族可分為:
1、漢族花兒:包括陜、甘、寧、青、新、港、澳、臺及境外西北漢族移民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2、回族花兒:包括陜、甘、寧、青、新、港、澳、臺、西蒙、川北及境外西北回族移民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3、東鄉族花兒:甘肅臨夏及寧夏海原等地東鄉族人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4、撒拉族花兒:青海循化新疆伊犁等地撒拉族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5、保安族花兒:甘肅積石山一帶保安族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
6、土族花兒:青海互助、大通、民和等地土族人中傳唱的羌藏味河湟花兒。
7、裕固族花兒:甘肅南部及酒泉一帶裕固族中傳唱的河湟型花兒。可分為漢族耶爾與回族耶爾、裕固族耶爾(耶爾:裕固族稱令調為耶爾)三種。
8、藏族花兒:甘肅、青海兩省藏族中流傳的羌藏味河湟型花兒。
(二)在共同文化區內局部地區生成傳唱的不同類型與色彩的花兒
1、洮岷花兒:以前在研討花兒時,學者們經常用清代賜宮返故里的臨洮人吳鎮的詩句“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作依據,把花兒的生成與傳播與花兒會聯系起來,其實吳鎮這兩句詩描述的是與廣泛傳唱的河湟花兒不同類型的洮岷花兒。
洮岷花兒是一種專門在古洮洲和岷州兩地花兒會上即興對歌、談情野合時唱的山歌。據郭沫若《釋“祖”、“妣”》考證,在名山勝地或桑間濮上聚眾對歌野合,是一些古老民族自古傳承的休憩娛樂、繁衍子孫后代的傳統習俗。甘、青兩地至今仍保持著著這種原始氏族社會的風俗,與古氐羌族長期在這一帶活動生息、融合轉化有一定的傳承關系。
洮岷花兒分為南北兩路,南路為岷縣卓尼一帶花兒會上演唱的《阿歐令》(又名扎刀令),北路為臨洮蓮花山花兒會上演唱的《蓮花山令》,兩者都是一字對一音,一句主腔自由重復后接一句合腔的古“相合歌”的演唱方式。一種腔調即興填詞對歌和七字句單字尾等特點,與廣泛傳唱的河湟花兒格律結構雖有一定的交融關系,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
2、羌藏花兒:青海的花兒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借騾大會或農貿集市之機,聚眾唱歌娛樂休憩的新花兒會,一種是與洮岷花兒會形式內涵大致相同的古老花兒會。后者在樂都瞿曇寺,民和峽門松山灣、互助、丹麻、大通老爺山等地都有花兒會。參加者多為信仰佛、道、喇嘛教的土族、藏族或當地漢族人(與洮岷一帶的漢人一樣,多為宋元時期歸化的氐羌人,史稱土番)。也是借朝山祈福祈雨求子之機,游山逛景、對歌聯姻、交友娛樂,演唱的多為帶有濃厚羌藏味的花兒調子,當地人多稱為“少年”。因其令調文詞民族化、地方化的痕跡比較為鮮明,甘、青兩省的花兒研究家們曾將其列為河湟花兒的四大流派之一,稱其為青海牧區羌藏花兒或民和土族少年。
3、撒拉族、保安族花兒:這是以青海循化和甘肅臨夏大河家及新疆伊犁一帶撒拉族、保安族聚居地流傳的花兒,這兩個民族都是性格勇武開朗、能歌善舞的民族,他們在傳唱河湟花兒的過程中,用本民族的傳統音調和藏族“拉伊”(情歌)的音調,創新發展了許多調式韻味獨特、夾有大量民族語言的令調。因而,甘青兩省的花兒研究家們將其列為河湟花兒的四大流派之一,稱為撒拉保安花兒。
4、六盤山回族山花兒:隴山(六盤山)地區,是我國遠古文化的發祥地之一,為古代匈奴、氐、羌等部族游牧繁衍之地。殷商時封為周之屬地,周文王聯合羌胡部族滅商后入主中原,封為屬國,出現了“弦誦早聞周禮樂,羌胡今著漢衣冠”的時代。春秋戰國時為先秦的屬地,因不服管理作亂犯上,為秦所滅,《史記·秦本紀》對此有所記述,《詩經·小雅》中記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獨獫狁(犬戎)于襄”。“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古原州,即今寧夏固原地區)”。歷史上稱其為“秦隴文化區”或“隴山文化片”。《甘寧青史略·副卷》為隴山花兒作序時說:“……自胡樂代起,夏聲浸微,中原曲調分為兩派,南曲多吳音,北曲雜胡戎……。一人獨唱,誰為顧曲之周郎,三句一疊,酷似跳月之苗俗,論者比之山歌,然任性而為,沖口而出,其得意處,正其本色也”。
由唐至元,回回人陸續落藉于這一帶囤墾牧養,至明代已發展成“回七漢三”,“沿絲綢之路沿線,千里之地盡悉回莊”的格局。回回人入鄉隨俗,吸收融合漢族文化,在傳承發展隴山花兒的過程中,兼收并蓄河湟花兒、信天游、蒙漢小曲和伊斯蘭音調等多種成份,將其打造成為具有鮮明民族地域特色、音調豐富、曲式多樣的新型花兒品種。1981年卜湯鐺文教授來寧調查后,將其列為花兒四大流派的兩種,命名為西海固花兒、隴中花兒。1984年民歌集成寧夏卷選編時將其統一稱為回族山花兒,與河湟花兒并列選編入卷。2002年非遺保護工程啟動后,又進行了多方調查考證,因這種類型的花兒以寧夏六盤山(古稱隴山)為中心,在隴山周邊回漢族中都有傳唱(卜湯鐺文四分法中分出的隴中花兒與其屬同一種類型),因而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花兒歌種——六盤山回族山花兒,單獨列項上報,經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審定后,列為國家級首批重點保護項目。
花兒的科學分類,促進了花兒研究的科學化、規范化、多樣化,使研究者的主體認識與客觀實體緊密相連,和諧一致,從而開拓和體現出研究成果逐步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以上論述均為個人學習研究的心得,在撰寫過程中學習、參考、摘引了大量文獻資料,不妥之處,衷心希望專家學者賜教指正。
[1]劉同生主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寧夏卷[M].北京:音樂出版社,1991.
[2]莊壯主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甘肅卷[M].北京:音樂出版社,1993.
[3]黃榮恩主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青海卷[M].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0.
[4]周吉主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新疆卷[M].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0.
[5]塞上樂譚—劉同生音樂文論選集[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6]馮光鈺.花兒為什么總是這樣紅[M]//王沛主編.中國花兒曲令全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
[7]喬建中.花兒的民族屬性及其他[M]//王沛主編.中國花兒曲令全集.蘭州:甘肅人發出版社,2007.
[8]王沛.讓花兒永遠歌唱[M]//《中國花兒曲令全集》概述.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