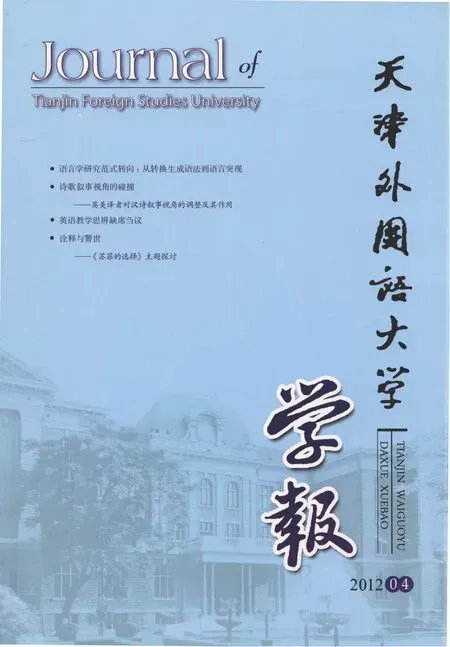多元族裔身份的自由追尋與建構—— 解讀《夢娜在希望之鄉》中的女兒形象
劉 哲
(天津外國語大學 基礎課教學部,天津 300204)
一、引言
美國華裔文學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和奮斗過程:從早期對美國文化和主流社會的臣服和無奈,到抵抗和破除美國白人社會對中國文化和習俗的歧視與偏見的覺醒,再到反映中美文化沖突與融合過程中自我價值與身份的思考與困惑,直至重新定位自我、尋找自身價值、尋求多種文化間相互溝通的再覺醒。
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那些出生、成長在美國的華裔或多或少接受了美國主流文化的價值取向,他們中的一些人試圖通過摒棄中國傳統文化來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也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看作是美國人。一些人部分地接受中國文化部分地接受美國主流文化,期望實現二者的完美結合;還有一些人選擇成為其他少數族裔并最終建構起多元的、跨文化的族裔身份,比如,任璧蓮小說中的主人公夢娜所作出的選擇。
《夢娜在希望之鄉》是任璧蓮繼《典型的美國佬》之后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該作品入選了《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小說并被《洛杉磯時報》評為1996年度十佳圖書。小說延續了《典型的美國佬》中張家的故事,通過描述拉爾夫和海倫的女兒——夢娜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的成長經歷,展現了第二代美國華裔女孩對多元族裔身份的追尋和建構,反映了任璧蓮“對美國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數民族之間的聯系和發展,以及對民族身份不定性的獨特見解”(程愛民等,2010: 42)。
二、 夢娜自我身份的追尋
1 掙脫束縛——夢娜對華裔文化的拒絕
作為美國華裔的后代,夢娜對華裔文化的認同經歷了“炫耀—拒絕—認同”的曲折過程。根據Phinney的少數族裔青少年建構文化身份所經歷的“三段式”理論,夢娜在混沌原初階段雖然清楚自己的華裔身份,但是她對中華文化的了解都來自父母,并不是自己探尋所得。特別是當他們一家搬到比較富裕的猶太社區居住時,由于猶太鄰居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菜肴的極大興趣,夢娜也受到大家的歡迎并被視為中國菜的“專家”,受邀品嘗猶太主婦們做的中國菜。夢娜到處炫耀自己是“正宗的華人”,說明她對自己的族裔身份已經有了很強的意識,然而炫耀自己的中國性并不意味著夢娜對自己華裔身份的認同。
伴隨著夢娜的成長,她開始“厭煩當華人了”(p.29)。這主要緣于夢娜和父母特別是與母親海倫之間的矛盾。夢娜的母親海倫是第一代美國華裔,她在青年時代移民來到美國,經過與丈夫拉爾夫的艱苦創業,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擁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進入美國中產階級,成為“典型的美國佬”。這是很多第一代華裔美國人的“成功之路”。因此,海倫期望自己的女兒們也能夠按照她所設計的藍圖來實踐自己的人生和實現自己的價值。但是作為出生在美國的第二代華裔美國人,夢娜深受美國價值觀和文化的浸染,她對自己的人生,自我的身份有著不同的追求——在美國,她有自由成為任何她想成為的人,在美國,“你要以什么身份出現都可以”(p.14)。因此,當夢娜決定做美國猶太人的時候,母女間便爆發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
“你怎么可以成為猶太人?中國人從來不干這種事情。”
“那么我想我肯定不是中國人。”(p.45)
在海倫看來,“女兒的職責是聽從,而不是拿她所謂的偉大想法來煩她的媽媽”。而夢娜則認為,她“不僅僅是一個女兒”,她“還是一個人”(p.221)。西方的人文價值觀認為,“人的本質核心是‘自由’。一方面,人的心靈具有一種反對束縛和反抗限制的本能沖動,是一個個體的人在內心深處體現出的在特定歷史和現實關系中(文化中)對‘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它也是人類或絕大多數人(由個體組成的群體)把握和駕馭這種關系的‘自由’。反對一切對個人的或人類的精神上、肉體上的束縛”(劉建軍,1998:21)。而美國更是一個崇尚自由精神的國家,夢娜認為:“美國人就意味著成為你想成為的人”,美國人就意味著自由與獨立。因此,當以母親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束縛了夢娜對自我身份探尋的自由時,夢娜本能地對中國文化和華裔身份產生了抗拒心理,從而決然否定了自己的華裔身份。
2 追尋自由——夢娜對猶太文化的認同
母女之間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差異,使夢娜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的差別,面對無法調和的矛盾,夢娜選擇皈依猶太教,做一名猶太人。猶太文化和猶太教為夢娜開辟了多元族裔身份的追尋之路。
夢娜之所以選擇做猶太人,首先是因為在美國,各少數族裔之間的地位差別很大,猶太人在社會中有較高的地位。猶太人是“美國夢”的化身、成功的“模范少數族裔”。作為弱勢族裔中的一員,夢娜自然期望成為最優秀的少數族裔中的一分子,從而獲得他人的認同。賽義德(Said,2002:177)曾說:“流散者總是感到一種迫切的需要,那就是通過選擇成為一種成功意識形態的信仰者或者一個成功民族的成員來重塑他們殘缺的人生。”
夢娜居住在猶太社區,在與猶太鄰居和朋友相處的過程中,在學習猶太教義、接受猶太文化的過程中,她發現猶太教與猶太文化中的某些核心思想與價值觀與自己在成長階段的個人價值取向是相契合的,這更加堅定了夢娜選擇猶太文化身份的決心。例如,猶太文化崇尚自由精神,信仰的自由是猶太教所堅定捍衛的原則。它教導每一個人都擁有按照自己的靈魂表達自己意愿的權利。而這些恰恰是夢娜從自己的華裔父母那里所無法獲得的。夢娜的父母成長于傳統的中華文化環境,遵從儒家思想,以儒家的禮來教育子女。傳統禮教確立了父母在家庭里擁有絕對權威的地位,子女只需無條件的服從,沒有選擇的自由。相比之下,以自由精神為核心的猶太教與猶太文化更容易獲得夢娜的認同。通過成為猶太人,夢娜可以實現自我表達、自我選擇的愿望。她希望像霍拉威茨拉比所教導的那樣,能夠決定自己的信仰,自由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和想要做的事情。因為黑人阿爾弗雷德事件母女間的矛盾終于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致使夢娜最后離家出走,奔向自由。
她感覺好似站在時間的最前端。在她身后,沒有歷史,在她之前——一切都在這里,多么傲慢啊!好像你沒有母親!好像你是在空氣中誕生的。她能夠聽見海倫的聲音。然而夢娜感覺到——什么東西在體內張開,如同火車站一樣廣闊,伴隨著閃亮的光芒流動著。(p.189)
夢娜離家出走,掙脫父母的束縛,如同猶太人不堪忍受埃及法老的奴役,在摩西的帶領下出走埃及,走向心中的自由之地迦南。迦南之于猶太人,如同多元的美國社會之于夢娜,從此,夢娜獲得了對自己族裔身份探尋與建構的自由。
在夢娜對自己多元族裔身份的探尋階段,猶太教中的自由主義精神猶如一盞明燈,為夢娜指點方向,同時,也為夢娜建構多元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社會人類學認為,“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類文化的綿續”,宗教與文化的緊密聯系使得兩者之間的界限往往難以劃分。威爾·赫伯格曾指出,現在的宗教不再與那些教會活動或神學價值體系聯系在一起,更多的是指個人的認同和群體的同化(李國正,2004:150)。對夢娜來說,猶太教中的自由、平等、抗爭、包容等信條都具有極大的魅力,她對猶太文化的全情投入,對猶太民族的認同以及對華裔文化的拒絕,都體現了她對文化身份的自由追尋以及為實現各種文化間的對話與交流所作出的抗爭。
在猶太教自由探索精神的鼓勵下,夢娜開始對各種文化進行審視與思考并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族裔文化與主流文化的獨特見解。她精辟地總結出幾種文化間的差異:“猶太人寄希望于今生今世,天主教徒寄希望于天堂,中國人則寄希望于后代。”(p.231)由此可見,夢娜強烈地意識到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下,只有承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才能不被完全同化并保持獨立自由的文化身份。夢娜不僅認同自己的少數族裔身份,而且認為華裔應該像猶太人那樣“認清楚自己是誰,不要白費功夫試圖成為白人……要意識到自己就是少數民族”(p.137)。有學者認為,“猶太民族成為模范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也因為他們是文化同化下仍致力于肯定自己的族裔性的代表”(尹曉煌,2000:193)。不可否認,夢娜對于多元文化的態度正是她對猶太文化探尋和認同的結果。“猶太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在歷史上,它從未要求思想和信仰上的整齊劃一,唯一強調的是對一些共同基本原則的篤信和遵行。”(胡浩,2011:75)猶太教中對不同觀點的包容、對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觀能動性的尊重為夢娜建構多元族裔身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三、夢娜多元族裔身份的建構
夢娜先前對于華裔文化的拒絕主要緣于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矛盾,但是隨著夢娜對各種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思考,她發現自己的感覺越來越接近霍拉威茨拉比所預言的“你越是猶太人,就越是中國人”。在很多情況下,她的行為和想法都不自覺地體現出中華文化對她的影響。夢娜繼承了某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比如,她為人謙遜,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等等。夢娜對自我身份的追尋仿佛又回到了起點。然而,夢娜對中華文化的回歸恰恰印證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文化雜合理論。夢娜建構多元族裔身份的過程同樣經歷了“否認、商討和雜合的過程”,只不過夢娜對猶太身份的選擇與認同使得這個過程更具復雜性,她不得不在三重文化間進行文化轉化并尋找到一個平衡點進行文化間的商討,最終建構一個雜合的文化身份——猶太教華裔美國人。通過夢娜的經歷,作者期望揭示的是在多元文化趨勢下,美國社會的各種族裔和文化間的關系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對于美國的少數族裔來說,他們所要“超出”的可能不僅僅是“第三空間”。
離家多年之后,夢娜與母親的重歸于好,預示著夢娜對華裔文化身份的認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她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構。不同于黃玉雪式的“模范少數族裔”,也不同于譚恩美式的融合中美文化的邊緣人。夢娜所追尋的是一個在多元文化身份間自由轉化的美國人。正如她所說的:“這是個自由的國家,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去禮拜堂。事實上,我要是愿意,我也能去清真寺。”(p.248)夢娜在嫁給猶太人賽斯之后,把自己的名字改為Changowitz,象征著自己的身份是猶太教華裔美國人。她還把自己的女兒起名為I0,表明“自我”的身份在出生后只是0,它的內容是需要每個人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不斷選擇、不斷建構的。由此可見,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變,它會超越空間、時間、歷史和文化,進行不斷地轉化,是建構在許多不同且往往交叉的話語、行為和狀態中的多元組合(Hall,1996:4)。這也正是任璧蓮想要在她的作品中展現的一種理想的族裔本質:不同族裔齊聚一堂,任何族裔成員都是美國這個大家庭的一分子,各族裔平等相處、兼容并包。每個美國人都有自我族裔身份的選擇權。正如任璧蓮在一次訪談中所說的:“我們相互接觸,然后從各自那里學到東西,這是很奇妙的事。這并不是放棄我們自己的根,我們只是學得更多,并允許這些事改變我們的生活。”
作為第二代美國華裔,夢娜的身份觀已經超越了以她父母為代表的第一代美國華裔。在面對文化身份的困惑時,夢娜沒有盲目地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也沒有機械地試圖將母國文化與主流文化相融合,而是積極地探索一種更能夠體現自我的途徑。夢娜對猶太教的皈依既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又受到了美國歷史文化的影響。因為在美國社會所確立的以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新教)為核心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宗教信仰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宗教和身份認同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任壁蓮一直希望能夠像猶太裔美國作家馬拉默德和貝婁一樣成為美國作家,而不只是美國華裔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跨越少數族裔的樊籬,被主流社會所接受。在小說中將宗教信仰問題納入族裔身份建構的主題中,體現了作家探討美國社會問題,塑造具有美國性的人物形象的創作追求,同時也反映了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新動態。
四、結語
作為第二代美國華裔女性作家,任璧蓮在《夢娜在希望之鄉》中塑造了一個在美國多元文化語境中尋找自我、建構自我的女性形象。夢娜所建構的文化身份超越了傳統的族裔界限,超越了東西方文化沖突與融合的身份觀,追尋的是一種各個族裔間彼此平等、相互融合的族裔關系,建構的是一個自由的、多元的文化身份。這也反映了任璧蓮頗具后現代主義色彩的身份觀:在美國多元文化背景下,一個人的族裔身份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的,而是后天養成具有流變性和雜合性特征的。
[1]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Routledge,1994.
[2]Elliot,E.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3]Hall,S.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A].In S.Hall & P.du Gay (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C].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4-17.
[4]Jen,G.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M].New York: Alfred A.Knopf,1996.
[5]Ling,A.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 Routledge,1990.
[6]Phinney,J.S.Ethnic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M].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3.
[7]Said,E.W.Ref l 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8]Santrock,J.W.Adolescence[M].New York: McGraw Hill Companies Inc.,2005.
[9]程愛民等.20世紀美國華裔小說研究[M].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0]方紅.雜交主義與非殖民化進程中的文化兩難[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2):48-53.
[11]胡浩.論猶太文化的自由精神[J].河南社會科學,2011,(1): 74-76.
[12]金莉等.20世紀美國女性小說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3]李國正.自由精神的文學思考[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149-151.
[14]劉建喜.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文化身份建構——論米勒的《祖先游戲》[J].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1,(3): 69-75.
[15]蒲若茜.族裔經驗與文化想象: 華裔美國小說典型母題研究[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6]張瓊.從族裔聲音到經典文學——美國華裔文學的文學性研究及主體反思[M].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