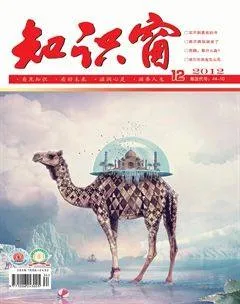講壇大學里怎么讀書
楊玉圣
大學生得讀書,就像工人得做工、農民得種地、歌星得唱歌、演員得演戲、教師得教書、官員得開會一樣,天經地義。
讀大學,讀什么書?作為學生,當然首先得讀專業書,但這絕不意味著滿足于僅僅讀教材。教材,讀其中一本有代表性的,也就夠了,因為目前的絕大多數教材都是東拼西湊之作,乏善可陳。
讀什么?讀本專業的名家名著,讀原版的名著,特別是非專業的跨學科的古今中外的經典著作。初讀,也許味同嚼蠟;讀不懂,沒有關系,因為有些經典注定是讓大多數人讀不懂的。從囫圇吞棗到一知半解,從不懂到讀懂,乃至讀透,是一個循環往復、甘苦與共、苦盡甘來的復雜過程,一言難盡。
讀書,除了汲取知識、學養,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問題。帶著問題,再去讀書,用比較的視角,用批判性的思維,嘗試著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就是研究性地讀書。讀書讀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會養成一種學術的判斷力,從而才有可能融會貫通,有所發現,進而推陳出新。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把知識內化為修養,而且還要把知識轉化為智慧,從而為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奠定扎扎實實的理論、學術和知識上的堅實基礎。
在大學里,分數的意義已經不再像在中學里那樣是學生的“命根子”了。為分數而學習的大學生,一定是舍棄了博覽群書的取向、自由探索的過程,基本上是圍繞著教材、講義或者教室打轉轉。這樣,與其說是讀大學,不如說是讀高四、高五、高六、高七。尤其在綜合性大學還不會讀書的話,大學算是白讀了。
作為家長,同時也是身為有25年教齡的大學老師,我從未在分數上要求過兒子楊肯。從大一一個學年的情況看,除了必修課和自己本專業的課外,楊肯還選修了王希教授、閻步克教授等主講的歷史類課程,并旁聽了賀衛方教授的課,這使我感到特別欣慰。盡管作為文科生在“高等數學”這門頭痛的必修課上僅得了可憐的70分,但楊肯仍然在選修課、專業課上成績優異,一個學年下來,在“牛人”濟濟的北大法學院160位同學中,排在60名左右。我覺得,這已經相當不錯了。何況,在過去的一年,楊肯還一直主動參加各種社團活動,攝影,拍片、策劃、剪輯、導演、設計,并在《中國青年報》《散文百家》和《律師文摘》上發表了3篇習作。凡此種種,可能比高分數更有意義。
大二可能是4年大學生活中最自在的兩個學期:度過了大一新生的好奇與興奮,逐漸適應了大學生活的環境、節奏與方法,心態回歸正常,思維開始活躍,有可能進入讀書與學習的自由狀態,從而可以在修習專業課的同時,結合課業開始自由地閱讀、思考和寫作。我很欣慰的一點是,從這個學期開始,楊肯有意識地主動親近經典,把閱讀《利維坦》《政府論》《聯邦黨人文集》和《通向奴役之路》提上了日程。邁出這一步,可能就是大學讀書生活的一個新起點,也意味著,迎接知識上的新挑戰、學術上的新機遇。同時,我還期望楊肯能夠在認真讀書的基礎上,沉潛下來,精讀、思考、比較,力求有所心得,并寫出學術性的讀書報告。因為,寫作是大學生的另一個基本的素養。
我總是跟我的學生講,讀大學,不在于讀什么專業,而在于是否能學好,其中關鍵是學方法,因為一旦學會了方法,即可觸類旁通。就文科大學生而言,最重要的技藝有二:其一是“說”,其二是“寫”;能說,會寫,能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識水準、綜合素質和學術修養。如果一個文科生讀了4年大學,到頭來,連“說”和“寫”這兩關都過不了,大學就白讀了,無形之中,4年就浪費了。
作為過來人,我還想特別提醒一點的是,與電腦、網絡適當保持距離。電腦也好,網絡也罷,一言以蔽之,無非就是工具而已;如果反過來,一天到晚抱著電腦,電腦和網絡就異化成我們的“主人”了。如此一來,久而久之,除了對視力的嚴重損害外,包括頸椎、腰椎,早晚得出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