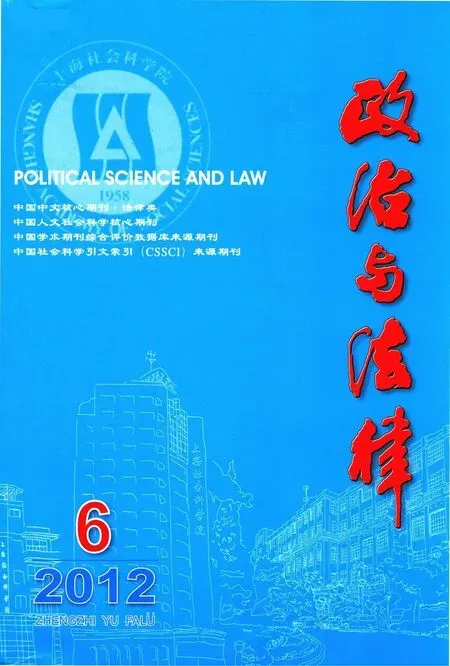賠償該如何影響量刑*
王瑞君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山東威海264209)
一、賠償影響量刑的相關規定及制度設計分析
我國刑法第36條將賠償損失與刑罰作為并列的責任后果加以規定,第37條將“賠償損失”作為非刑罰處理措施加以規定,適用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但現行刑法對賠償可否作為量刑情節沒有明確規定。近年來的刑事司法實踐中,賠償的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司法實踐的做法一方面考慮現實需要,另一方面有來源于自1999年到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或準司法解釋作為依據。1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涉及賠償影響量刑的內容有三處:一是“關于破壞農業生產坑農害農案件”中提出,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時,要注意盡最大可能挽回農民群眾的損失。被告人積極賠償損失的,可以考慮適當從輕處罰。二是“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中提出,要適當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以避免數額過大而難以執行的判決引起的負面效應,被告人的民事賠償情況可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三是“關于盜竊案件”對盜竊犯罪的初犯、或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的,應當注意體現政策,酌情從輕處罰。我們可以把該紀要的上述內容簡單公式化為以下三種情況:①賠償——可以——從輕處罰;②賠償——可以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③賠償——應當——酌情從輕處罰。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其中第4條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規定》的上述內容邏輯上可簡單公式化為:賠償——可以作為——量刑情節。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一)提出,要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確保社會穩定,要“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對案發后真誠悔罪并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案件,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我們可將其公式化為:真誠悔罪+積極賠償——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二)規定,被告人案發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犯罪情節輕微,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不需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意見》二的上述規定可公式化為如下幾種情形:①積極賠償+認罪、悔罪(二者之間也應該是同時具備的關系)——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②被害方諒解——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限定案件類型為: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③被害人諒解的——可以從寬——直至可以免予刑事處罰,限定的案件類型為犯罪情節輕微案件。
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部分規定:“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其公式為:積極賠償+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被害方諒解+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從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臺文件的時間順序和相關內容,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對這一問題的態度變化。比較前后的規定,至少從字面上看,賠償正在經歷由可以獨立影響刑罰的酌定情節向與其它因素一道成為影響刑罰酌定情節的變化。隨著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發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大多制定了貫徹《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實施細則。該指導意見和各地的《實施細則》在規范賠償影響量刑的同時,老問題和新困惑也十分明顯,值得探討。其一,賠償影響量刑的根據是什么?其二,基準刑是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時,賠償可否作為酌定情節影響量刑?其三,哪些案件可以“賠錢減刑”,哪些案件不能“賠錢減刑”?其四,將“賠償”與“諒解”分別作為影響刑罰裁量的因素進行規定,并規定“同向相加”,是否合理?其五,如何把握賠償影響量刑的度?
2012年3月14日修正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盡管是將賠償損失作為獲得被害人諒解達致雙方當事人自愿和解的方式加以規定,但仔細閱讀其第270條、第277條之規定,可以整理出一個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賠償——諒解——和解——處罰上從寬的基本思路,可見,賠償對刑事案件處理的影響意義已經得到了立法層面的充分肯定。當然,《刑事訴訟法》主要是從程序法的角度就“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進行的規定,并且對所提“賠償”是在限定了適用的范圍即在可以和解的公訴案件范圍內規定的,因此,自然不能涵蓋賠償作為量刑情節影響量刑的全部情形,大量涉及賠償的刑事案件中,賠償可否以及如何影響量刑,仍然離不開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并且從賠償作為酌定量刑情節的角度來說,目前我國主要的依據仍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
二、賠償影響量刑的個案考察與分析
司法實踐中將賠償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的考量因素不算是新的做法,只是隨著最高人民法院對賠償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的不斷肯定,加之有多個省市出臺涉及加害人賠償的文件,“賠償”一詞在判決書中出現頻率更高,“賠償”的地位被提高,以至于一提到哪里發生了刑事案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犯罪人有沒有出錢賠償。
筆者對此曾做過調研,最近又去某基層法院翻閱一些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判決的時間從2006年到2011年都有,筆者隨機從中抽出10份,進行了閱讀比較。其中傷害案件8件、交通肇事案件2件。判決書將“賠償”作為影響量刑因素的表述模式有:賠償——諒解——從寬的1件2、賠償——悔罪——諒解——從寬的1件、賠償——悔罪——從寬的4件、賠償——諒解——悔罪的1件,賠償——從寬的1件,有一件是由于被告人認為受害人受害后果傷殘鑒定等級較高,表示自己經濟能力有限,無力承擔高額賠償,該案件的刑事附帶民事部分是通過判決解決的,所以沒有“賠償”影響刑罰的內容。另有一起案件是交通肇事案件,判決書中這樣寫道:“被告人×××未能及時賠償損失,可酌定對其從重處罰。”
隨后筆者又到該基層法院所屬市的中級人民法院調研,法院人員從2007到2010年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中,隨機抽出5份,其中,1份是搶劫案件判決書、3份是傷害案件判決書、1份是故意殺人案件判決書。在搶劫案件中,由于使用暴力手段致人死亡,所以對案件中被判處死刑的一名被告人,受害方表示放棄賠償要求,其他被告的賠償由于是通過判決而非調解解決的,所以判決書中未提及“賠償”對刑罰的影響,即量刑未考慮“賠償”因素。三起傷害案件中,一起是單獨作案且致人死亡,判決書認為“鑒于被告人認罪態度好,且積極賠償被害人近親屬的部分損失,具有悔罪表現,并取得了被害人近親屬的諒解,故可依法酌情從輕處罰”。另兩起是共同犯罪案件,其中對案發后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被告人從寬,對未賠償的被告人不體現從寬。在故意殺人案件中,盡管受害方家屬提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法院也根據法律作出判決,但由于判處死刑,賠償不了了之。
這里又要回到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及理解上來。依據字面規定,筆者在上文整理出不同的賠償與刑罰之間關系的“公式”,然而,是否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的涵義就是如此,還是作為辦案人員在解讀這些規定時就應該作這樣的“字面”理解呢?為此,筆者專門向法院的辦案人員了解,來自實務部門的看法和做法如下,由于現在沒有更好的評價“悔罪”的機制,加之承辦的案件多、工作量大,辦案中,如果被告人或其親屬在賠償上表現得主動,通常就把“賠償”視為犯罪人“真誠悔過”的表現,或者根據被告認罪態度和對事情的認識來認定其“悔罪”表現,判決書上顯示出來的就是“主動賠償”或者“積極賠償”、“有悔改表現”等一些套話。如果被害人請求賠償損失的要求得到滿足,特別是在基層法院,由于案件較輕,讓被告方進行一定的賠償,然后在刑罰適用上體現從寬,總體上不論是加害方、被害方還是周圍關注此事的民眾都是能夠接受的。當然實踐中也暴露出以下一些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在逐漸升級和擴大。一是有的被害人“得理不讓人”,抓住對方想換取從寬處罰和法官想案結事了、害怕上訪、信訪的心理,會提出非常高的賠償要求,如果對方或法官不滿足他的要求,就糾纏此事不放,影響案件正常程序的進行。二是被告方對賠償后從寬處罰的期望較高,在基層法院,有許多被告方提出適用緩刑的要求,并表示不適用“緩刑”就不賠。三是有的受害方只要重判不要賠償,特別是后果嚴重或者雙方過去積怨較深的案件。而對于突發性案件以及過失案件,受害方心里更容易接受賠償影響刑罰。四是有的案件,如果對判刑結果有預期,特別是可能判處1年以下刑期的案件,加上我國審前采取羈押措施的較多,扣除羈押期后,剩余的需要執行的刑罰已經不多時,律師會建議被告一方不用出錢賠償。五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進行攀比,沒錢賠償的往往與有錢賠償以獲得從寬處罰的被告人進行比較,心里不平衡。六是由于被告方、受害方的訴求不同,民眾心理上存在對“賠錢減刑”的不認同并由此質疑司法公正。因此,在有的案件中,法官很被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也不是、不調解也不是,要么是被告人或被害人不滿,要么是來自民眾的質疑。此外,法官還反映,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以及省級法院出臺的實施細則規定太細,有的邏輯上前后不相銜接,操作起來過于繁瑣。綜上,為解決賠償兌現率低而迅速發展起來的賠償影響量刑的制度設計和實踐,并不是平靜順暢的,而是正經歷著新的考驗。
三、賠償作為量刑酌定情節影響量刑的理論依據和現實需求
賠償是否可以影響量刑,賠償可否換來刑罰從寬考量?近年來,我國法律學者、司法實務人員、當事人、公眾以及官方等不同主體對這一現象的見解不盡相同,甚至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法律學者的觀點是大體上不排斥“賠錢減刑”的做法,不否認“賠錢減刑”存在的價值,同時主張不可擴大化,并需提防運作中損害法律正義的現象。司法實務界也多持肯定的意見。公眾的看法則表現出對“賠錢減刑”的討伐和強烈的質疑。個案當事人的反應不一。3
西方的思想家們很早就開始關注到了刑事損害賠償的問題。刑事古典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邊沁充分肯定犯罪補償即賠償對被害人的作用,他認為:“如果為了消除恐懼的情緒,補償應當和懲罰一樣,與犯罪形影相隨。如果對犯罪只適用懲罰,而不采用補償措施,那么,盡管許多犯罪受到懲罰,但很多證據證明,懲罰的效力甚微,并且,必然給社會增加大量的令人吃驚的負擔。”4他并強調補償即賠償必須是確定而完整的,不因被害人或犯罪人死亡而消失。刑事實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加羅法洛主張以遏制犯罪取代威懾犯罪,遏制的方法包括消除和賠償兩種形式。消除是將罪犯排斥出社會,方法有死刑、終生監禁、永久性驅逐出社會和一定權利的剝奪。強制賠償是遏制犯罪的一種新方法。“強制賠償的方法就可以適用于普通的偷竊行為、一定類型的欺詐行為、非法的破產行為、蓄意侵犯財產的行為、對莊稼和正在生長的樹木縱火的行為、在爭吵中的撕打和傷害行為、誹謗行為、使用侮辱性語言的行為以及輕微侮辱婦女的行為,等等。如果損害是可補償的,而且罪犯也愿意賠償,那么,消除就是不必要的方法,而且也是殘酷的方法。”5菲利主張將賠償損失作為一種社會防衛措施。他在一篇題為《論刑罰作為一種社會功能的合理性》的論文中寫道:“沒有人告訴我們民事賠償不是刑事責任的一部分。在付一定數額的錢作為罰金和付一定數額的錢作為賠償之間,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區別。不僅如此,我認為將民事措施與刑事措施絕對分開是一個錯誤,因為它們在預防某些反社會行為這一防衛目的上應當是一致的。”6
從當代各國立法情況來看,有的國家將賠償作為量刑情節加以規定,如《德國刑法典》第46條規定,法院在量刑時,應權衡對行為人有利和不利的情況,特別是應注意行為后的態度,尤其是行為人為了補救損害所做的努力。《德國刑法典》第46條a中規定:“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依第49條第1款減輕其刑罰,或者,如果刻處刑罰不超過1年自由刑或不超過360單位日額金之罰金刑的,則免除其刑罰:1、行為人努力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對其行為造成的損害全部或大部分予以補償,或認真致力于對其行為造成的損害進行補償的,或2、在行為人可以自主決定對損害進行補償或者不補償的情況下,他對被害人的損害進行了全部或大部分補償。”7《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61條規定:“減輕處罰的情節是:……(10)在犯罪之后立即對被害人給予醫療救助或其他幫助,自愿賠償犯罪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以及其他旨在彌補對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的行為。”8有的國家將賠償作為緩刑考察的內容或遵守的義務,賠償的表現直接影響緩刑的后果。《挪威一般公民刑法典》第53條規定,在緩刑期內,法庭可以責令犯罪人支付到期或者即將到期的賠償。緊接著在該法典的第54條將犯罪人的上述表現作為法庭可以停止或者延長緩刑期的條件,如果犯罪人嚴重違法或者多次違反法庭要求其賠償支付的義務,法庭可以通過判決決定全部或部分執行原判刑罰。9將賠償作為犯罪人緩刑期間應履行的義務進行規定的還有《丹麥刑法典與丹麥刑事執行法》、《瑞典刑法典》、《葡萄牙刑法典》、《法國刑法典》等。美國關于賠償是否影響刑罰的規定較為分散,舉例而言,其1984年通過的《美國聯邦犯罪被害人法》設專章規范被害人賠償事宜。該法規定:必須確定經濟損失是由犯罪行為引起的。被害人須提出補償要求和返還財產的要求,法庭須衡量被告人返還財產的能力,被告必須賠償其造成的損失;決定賠償款的數量和賠償方式時,法庭應考慮被告人的經濟來源和其未來的支付能力;法庭可以將該支付令作為對犯罪人宣判緩刑、假釋、免除處罰及其他附條件釋放的條件之一。補償令判決不妨礙被害人根據其他法律在民事訴訟中獲得補償。10
就我國而言,賠償從寬的功效突出地表現為兩點:其一,對于解決賠償執行難的問題,現實效果明顯。我國目前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判決得不到履行,因為,多數刑事犯罪的被告人處于經濟十分困難的狀況,沒有財產可供執行。而根據法律規定,民事賠償只能執行被告人自己的財產。對于貧困的被告人來說,如果賠償與否都難免定罪和判刑,甚至難免一死,賠償的主動性就無從談起。而如果在被害人或家屬同意的前提下,賠錢可能“減刑”,被告人賠償的積極性會發揮到最大限度,其親屬會主動代為賠償,甚至被告人和親屬會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來爭取賠償。這恐怕是“賠償”在我國近年來刑事司法中大有市場的現實原因。其二,可以減少刑事案件上訴上訪的數量。在我國,刑事案件上訴上訪是多年困擾各級司法機關、政府的難題,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中,充分貫徹上述有關賠償的規定和紀要精神,對于減少上訴上訪,確實收到一定效果,可以說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四、“賠償”影響量刑的度的把握
前面分析了賠償影響量刑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我國現實需要的背景,完全否認它不符合現實,現在的問題是賠償如何影響量刑,賠償就從寬還是另有要求?什么案件可以影響,什么案件不可以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如何?理論上講,任何量刑情節對刑罰的影響都要最終歸結于它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影響及程度,如果引入新的恢復性司法理念的話,還應同時考慮對被害方損害的修復、犯罪發生后各方關系的修復等內容。
綜合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這兩個刑罰裁量的根據,兼顧恢復性司法所追求的全面的平衡,筆者將與賠償緊密關聯的因素與刑罰之間的關系做一下歸類,可以有很多情形:悔罪——從寬;賠償——從寬;諒解——從寬;悔罪——賠償——從寬;賠償——諒解——從寬;悔罪——賠償——諒解——從寬;賠償——不諒解——從寬;悔罪——賠償——不諒解——從寬;不悔罪——賠償——從寬等等。這些模式中,選出帶有“賠償”因素的組合,悔罪——賠償——諒解——從寬應為最佳模式。因為這一模式最符合刑罰根據和刑罰目的及恢復性司法的要求,所以“悔罪——賠償——諒解——從寬”可以說是“賠償”作為酌定情節影響量刑的理想的基準模式。另外,如果仔細研讀一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279條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一模式已經為立法所肯定。
因此,可以“悔罪——賠償——諒解——從寬”作為基準模式,確定一個大致的從寬標準,假定就依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定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的話,那么,然后應該再依“悔罪”、“賠償”、“諒解”等因素在組合數量、程度上的遞減,在從寬的把握上逐漸遞減。舉例而言,如果僅有犯罪人親屬的賠償,犯罪人并無真誠悔改的表現,那么,只能說實現了修復損害的功能,無法證明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降低,因此,這時的賠償對基準刑影響的比例不宜過高,如果加上犯罪人真誠悔罪的情節,則不僅修復損害的功能得以實現,同時說明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降低,所以從寬的比例應高于前者,以此類推。為此,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要判斷被告人是否真誠悔罪。就被告人而言,如果僅看賠償的數額,不看是否認罪和悔罪,那么,基于賠償而獲得從輕或者減輕帶給被告人的可能是犯罪后的深刻反思但也可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扭曲認識。如果是后者,不僅對被告人起不到懲罰和教育的作用,反而更容易激起受害方的心理怨恨。從社會民眾的角度而言,他們內心的公平正義的情感會有一種被傷害的感覺,民眾自然會懷疑裁判本身的公正性與合理性。為避免有害的社會效應的出現,要把被告人的“真誠悔罪”情節作為“賠償”影響量刑的重要條件。具體判斷中,要看其賠償的主動性、賠償能力、為賠償受害方的損失所做的努力。在由被告人親屬甚至朋友賠償的案件中,要重點查清被告人自己的態度,是同意、無所謂還是反對。
二是看犯罪人的賠償表現。依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定,在適用“賠償”這一情節時,要綜合考慮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可見,賠償表現不同,量刑從寬的度應有所不同:一方面要考慮賠償的數額。一般來說,賠償數額越多表明犯罪人悔罪的決心越大,其人身危險性降低程度越高,同時賠償數額越大,對受害人損害的修復效果越好,因此,從寬的度應隨之提高。另一方面要考慮賠償的能力。如果不考慮賠償能力,僅僅看數額,那么一個億萬富豪出100萬的賠償金和一個家徒四壁、東湊西借湊足5萬元的賠償款,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其所體現的內含并不相同。
三是根據犯罪的不同性質,掌握賠償影響量刑從寬的幅度。實踐中有的案件僅僅造成被害方的物質損害,特別是過失造成物質損害的,從寬處罰的度要放大些,原因在于,物質損害的屬性決定了其能夠被修復,同時,如果主觀上出于過失,那么說明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較低,特殊預防的必要性小,另外,毀壞財物的一般預防必要性本身就比盜竊等犯罪小,因此,可放寬從寬的幅度。而如果系故意殺人罪,由于犯罪性質嚴重,人死不能復生,修復僅僅是對受害人親屬的生活而言的經濟上的補償,因此,如果賠償在這類案件中影響刑罰幅度過高,會使罪行嚴重者所得量刑利益過大,很可能會給社會釋放一個不良的信號,即“花錢買命”。因此,犯罪性質不同,賠償即使作為酌定量刑情節,其影響量刑的幅度也應有所不同。
當然,盡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是針對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規定的,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7條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的公訴案件限定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這不等于說,賠償僅僅是有期徒刑以下刑事案件的酌定量刑情節,更不能理解為“賠償”僅適用于可以和解的公訴案件。而應該理解為,在無期徒刑、死刑案件中,賠償同樣是酌定量刑情節,只是有的案件即使考慮了賠償這一酌定量刑情節,仍不能影響對犯罪人判處死刑,或者仍不能因為犯罪人及親屬有積極賠償的表現就足以使得該案件的判決降低到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因為,犯罪的危害是不可量化的并且每個犯罪事實都有其特殊性,但刑罰的嚴厲性是有限的,比如基準刑同樣是死刑的犯罪,但其危害程度仍有不同。可見賠償是影響刑罰的從寬情節,但是未必因為有這一事由就一定是非常輕的宣告刑。就如同對一個罪犯應判死刑,并且憑幾個酌定從輕情節甚至法定從輕情節都不足以將其刑罰降低到非死刑的,那么就不能因為賠償免于死刑。
四是考察被害人諒解的自愿性。被害人表示諒解并出于被害人的真意,對于消解受害人遭遇侵害后的怨恨和撫慰民眾情感,都是有積極作用的。因為有時被告人以經濟賠償的方式來彌補因自己的犯罪行為而加諸被害人身上的經濟損失,并不能消弭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心理和社會公眾帶來的傷痛。通過真誠的悔罪和與個人身份和財富無關的足以表達誠意的致歉,取得被害人的諒解,不僅可以化解當事人雙方之間的恩怨,也使公眾不至于形成“花錢買刑”的感覺,對糾正公眾對于司法不公正和判決偏頗的印象也會產生積極影響,它能夠讓民眾明白,對被告人的從輕處罰不僅僅是因為他付出了經濟賠償,更是基于他誠懇悔罪和受害人的諒解。
為了使賠償對量刑的影響更加規范,對現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有必要進行整理。上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整理出來一系列“公式”,給人較為混亂的感覺:賠償可以從寬、諒解可以從寬、賠償加上諒解可以從寬、諒解應當從寬……。當然,從時間順序來解讀上述規定,應該說,最高人民法院在這個問題上越來越完善了。但由于在這方面各地各級法院的司法活動主要就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進行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對待自己的規定更應慎重、嚴謹,有必要進行重新整理。在對司法實務部門的進一步調研中,筆者了解到被害人諒解往往與賠償損失相伴,不賠償獲得受害人諒解的案件幾乎很難見到,而2010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將“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與“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情節分開,規定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20%以下不同的刑罰,并采取同向相加的方法來確定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實在令人費解,也與實踐不符。為此筆者主張:有期限和可量化的刑種可借鑒《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試行)》的規定:“在人身損害型犯罪中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被害人或其家屬的諒解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可以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從寬掌握。”對涉及其它不能量化的刑種,最高人民法院只需列舉出悔罪、賠償、諒解等因素,適用上的組合、適用程度應交給辦案人員具體情況具體把握。
注:
1依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賠償”不僅是影響量刑的因素,同時還是影響定罪的因素,本文重點探討“賠償”對量刑的影響。
2盡管有的判決書寫明“減輕處罰”或“免予刑事處罰”,但由于判決書中提到考慮案件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這樣的判決書并沒有將“賠償”單獨作為“減輕”甚至“免予刑事處罰”的情節,故仍使用“從寬”的表述,下同。
3參見王瑞君:《賠償與刑罰關系研究》,《山東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4[英]邊沁:《立法理論——刑法典原理》,李貴方、陳興良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5[意]加羅法洛:《犯罪學》,王新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04頁。
6[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會學》,郭建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頁。
7徐久生、莊敬華譯:《德國刑法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
8黃道秀譯:《俄羅斯聯邦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
9馬松建譯:《挪威一般公民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10趙可:《犯罪被害人及其補償立法》,群眾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