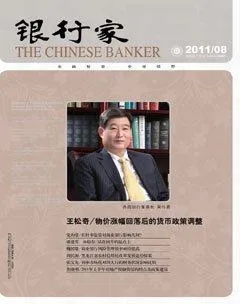那是中國商業的青春期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以戰敗國的地位,被迫與西方諸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這樣的歷史局面,從一個國家的地理意義上看,或者從一個守土為疆的天朝政府看,的確是再屈辱不過的事情。但從一個經濟體的商業貿易發展看,人們卻驚訝地發現,晚清的貿易水平卻由此扶搖直上,最明顯的局面發生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從19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之間,其市場結構、金融流動、貿易中心、航運物流,甚至包括商業組織的經營管理方式,都產生了一種近似于革命性的變化。晚清出現了一種以財產私有制、企業具有獲取利潤和競爭的自由,以及個人消費者具有選擇自由的區域性經濟制度。當這種制度以貿易而不是以工業為重點時,曾經出現在17世紀歐洲的“重商主義”、“重商資本主義”,開始在晚清的沿海地區發展。
有必要提到的一個事實是,晚清政府既不像明朝實行大面積的海禁政策,推行一種絕對意義上的經濟封閉政策,也不像后來的新中國推行嚴格意義上的公有制,用公私合營的方式徹底取消私人財產權。因此,簡單地認為晚清勃發的商業革命就是由于西方條約名義之下中西商業往來的結果,并不中肯。因為晚清沿海地區貿易的基本面,在此之前也有不錯的進展,只是規模不足以引起一個國家經濟體的轉型。事實上,就是在當時,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商業的確成為了人類生活的主旋律。就國內而言,中國在1683年滿族人統一國家之后,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繁榮階段,因此有所謂“中華升平盛世”之說。經濟廣泛發生,市場持續拓展,人口增加,地區之間的貿易劇增,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的手工業可以說是風起云涌。日后的人們總愛提到的所謂大國崛起,或者是所謂盛世中國,應該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之間的落差肯定是巨大的,雖然商業的旋律看上去有某種類似性。更為重要的是,晚清的商業,是一種基于農業的商業,而西方人的商業,已經大踏步走進了工業時代。但我們要強調的是,正是這種巨大的落差,催生了貿易的可能性,也讓一個古老的東亞帝國在貿易的層面上與躍躍欲試的西方人產生了巨大的沖突,只是這種沖突表面看上去是商業利益的訴求,但卻訴諸以血腥的武力。一個看上去四平八穩的天朝,終于經不住火藥和大炮的轟擊,不得不屈辱地坐在了西方人設定的談判桌前。
但是必須強調,當外部世界的商業潮流一浪高過一浪,當內部的商業力量也在不斷積累,中國人在商業領域的變革,就是一種必須。如果沒有一種主動的變革,那么外力就會毫不猶豫地推開我們的大門。長久以來,中國,這個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社會,一直在商業的層面,市場的層面封閉守舊,抵制人性對財貨的基本認識,進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發展出一種反市場、反經濟、反人性的社會格局。在儒家社會價值體系中,商人總是居于最底層,手工藝人稍微高一些,農民看上去不錯,但也沒有基本的產權保護,因此,所謂的士,就成為這個虛偽的社會里最醒目的、最有地位的人。
一個國家的商業轉型,竟然以一種戰爭的形式得以展開,這讓所有熱愛自己國家的人們不舒服。但有些商業的、市場的常識,也伴隨著這樣的格局產生,比如人口開始有規模地朝沿海城市流動,比如出現了專業化的分工,導致更多的人口進入商業系統。由此,市場經濟最為重要的基礎條件——私有財產和由此產生的財富以及收入的不平等,在“條約制度”的保護下,而不是在晚清政府的保護下,得以形成秩序。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的存款、利潤緊緊結合在一起,具有信貸作用的銀行開始建立。由此,資本、利潤等真正屬于市場經濟的概念,逐漸成為一種社會的共識,不僅在經濟發生鏈上,而且在道義上,都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才是中國企業家的啟蒙課啊!沿海的生意人,兼備了各種身份,他們有時候是貿易家,有時候是銀行家,有時候又是投資家。但無論哪種身份,他們的生意都完全建立在一個開放的市場需求上,整天圍繞著茶葉、絲和絲綢這些商品,而不是勞動力市場,他們最重要的貢獻,是改進了一個古老市場的交換機制,而不是直接投身工廠,在大量的外來銀行信貸的刺激之下,晚清的沿海一帶似乎成了亞洲最好掙錢的地方。
這么看起來,單向度地理解一個已經發生的歷史現象,幾乎是一件危險的工作。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強調了國家的地理尊嚴,卻忽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強調了意識形態力量,卻回避了市場的規律;強調了集體的優勢,卻遮蔽了個人的權利;強調了內心的落后,卻忽略了他人的發達;強調了自尊,卻不知道敬畏;強調了自力更生,卻回避了交流共享。這就是我們,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人的集體意識,這就是我們此時此刻的生活,我們的命運。
(作者為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