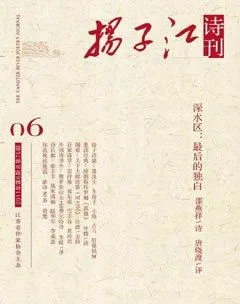詩性陳述背后……
寫孤獨和孤獨感的詩不計其數,而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所寫的《孤獨》,可以說是一首非常獨特的詩。此詩以一種陳述的方式呈現,用類似于電影的“蒙太奇”鏡頭,把若干片斷場景組織在一起。全詩并沒有涉及“孤獨”一詞,但是你在讀完全詩并悉心體味之后,就不能不心悅誠服于詩人的這種陳述和構思,是何等的匠心獨運,技藝高超。
粗略地閱讀此詩,或許會感到它是一首平淡得跡近乏味的庸常之作。它從頭到尾,似乎只敘述了一場即將發生的車禍以及脫險的過程。然而且慢。我們不妨在逐步進入詩人所設置的場景中,來探究其詩性構思和呈現的奧秘。
詩的第一節開宗明義,“二月的一個夜晚,我差點在這里喪生/我的車滑出車道,進入/路的另一側。”眼看著一場車禍即將發生之際,詩人的內心關注卻指向了“相遇的車”,他看到了“它們的燈——在逼近”。
這一節簡捷明快的陳述,它雖然暗含著一種戲劇性,可是在它開門見山的交待中,已經說明這是一次回憶性的陳述。在這種回憶中,“車滑出車道”固然是肇事之因,但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對“相遇的車”“它們的燈——在逼近”的描述。正是這種“逼近”提醒了我們,這絕不是簡單的回憶中的場景。它似乎隱含著某些生活經歷中的人生況味。
按照一般的敘述方式,接下來似乎應該是寫發生事故的瞬間,可是詩人卻出人意料地把筆鋒轉向了“意識流”:“我的名字,我的女兒,我的工作/松開我,默默地留在背后/在越來越遠的背后,我是匿名者——/像校園被對手包圍的男孩”。這種有意宕開一筆的緩沖之計,雖屬寫作上的技法,但在這里,似乎不是技法的運用,而是暗含著人生經歷中的辛酸的。說一個人在面對死亡威脅時腦際會浮現對自身和親人的瞬間關注,特別是在突發事件面前的那種慌亂時,這都屬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可是在這時候會想到“在越來越遠的背后,我是匿名者——/像校園被對手包圍的男孩”,這似乎只能解釋成這種場景曾經在他的內心留下深重的創傷。
接下來再看那“逼近的車輛射出巨大的光芒/它們照射著我,我轉動轉動著方向盤/透明的恐懼像蛋白滴淌/瞬息在擴大——你能在那里找到空間——/它們大得像座醫院的大樓”。如果說前面一節詩寫的是宕開的“意識流”,這一節詩就是現場感極強的瞬息感受了。這一節詩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對“透明的恐懼”的描述了。“像蛋白滴淌”而又“瞬間在擴大”,并且“能在那里找到空間”,這個空間則“大得像座醫院的大樓”,是驚恐中的幻覺,還是潛意識里那種對“醫院的大樓”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許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無論是幻覺還是印象,它們所指向的依然是一種無助或求助的茫然之感。
詩的四、五兩節,突然轉變成一種客觀敘述的姿態。在“被撞碎前”,“這里出現了一個支點:一粒援救的沙子”,“或一陣神奇的風”。因為“一粒援救的沙子”“或一陣神奇的風”而使得“車脫了險”,這看來實在有點不可思議,更使得人們產生一種神秘感和超現實的意味。而當“車脫了險/飛速爬回原道”之后,一根電線桿的斷裂并“在黑暗中飛走”,成為對這次車禍的最后描述。
我們從這種描述中,不僅感到有點不可思議,也有驚心動魄的震撼。“沙子”和“神奇的風”何以會成為“一個支點”,甚至改變了車的運行軌道;而一根電線桿的“橫空飛起”和“在暗黑中飛走”,似乎成了這一場車禍的最終見證人。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詩的最后一節:
四周已平靜。我仍系著安全帶坐著
等待有人冒著風雪
看我是否安然無事
這一節的呈現,說它是對這次車禍的最終定格,或者說它是在象征的意義上揭示了此詩的主題指向,我想都是符合實際的。
縱觀此詩,我們發現它雖然是以陳述性為特征的,但前三節與后三節的陳述視角是不同的。前三節詩是以我為核心的陳述。我的失誤,我的意識流,我的幻覺,這一系列以我為核心的主觀感受,構成了前三節詩的陳述方式。而在后三節詩中,視角的轉換使陳述方式改變為客觀性的描述。在第四節的開頭就寫道:“玻璃碎前/你幾乎能停下/喘一口氣”,一個“你”字就徹底改變了陳述的視角,從主觀轉換成客觀。值得探究的是,詩人為什么要作這種陳述視角的轉換?這也許牽涉到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表現方式和特色。他是一個在意象運用上非常著意于隱喻功能的詩人。我在前面分析其前三節詩時,特別注意到那逼近的燈,被包圍的男孩,以及那醫院的大樓,是因為我從中似乎讀出了在這些意象后面隱喻著他深藏在內心的孤獨和孤立無援的感受。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更深地知道他為什么在詩行中不涉及孤獨一詞,卻又把詩題命名為孤獨。因為他要表現和表達的,恰恰是一種在人生旅途上無時不在并可能隨時出現的境遇,以及這種境遇所呈現出的孤獨感。
如果說以上所分析的一切都只是屬于人的主觀感受范疇,那么,正當這種沿著原先的道路發展下去而使生命走向結束之際,又一個突然發生的事件,卻使事情的結局完全改變了。這種改變,因其神秘性和不可預測而令人茫然。這就是為什么在“你幾乎能停下/喘一口氣”時,那一粒“沙子”和“神奇的風”卻使“車脫了險”所暗含的有關人的命運中的玄機。這也就是為什么詩人要突然改變陳述視角的根本原因。
在詩人的內心深處,他或許就是認定人的命運是充滿神秘和不可預測性的。“車滑出車道”難以逆料,在逼近的燈和面臨滅頂之災時產生的臨終幻覺,是自己主觀意識范疇內的事,而因“沙子”和“神奇的風”而改變了事情發展的格局,則不是他主觀所能左右得了的,所以詩的最終定格的那一幕場景,他只能“等待有人冒著風雪/看我是否安然無事”了。即使是經歷了這一次脫險,詩中的“我”依然只能“等待”,而且是孤獨地等待。等待來的,并不一定是施救,而是“看我是否安然無事”。這是不是暴露和揭示出更深層次的內心孤獨感呢?特朗斯特羅姆被稱為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相結合的詩人,被譽為隱喻大師,而他自己則會公然聲稱“詩是神秘”。我們從這首《孤獨》中也大致能夠領略其詩歌藝術品位之一二。他先是以現實主義的陳述寫一場即將發生的車禍,以揭示人生道路上無時不在的潛伏著的危機;繼而又以象征主義的手法,表現一種因神秘的力量而左右和操縱著人的命運的“存在”。從事件發展的脈絡到最終的“定格”,“我”雖然行動著,從失誤到自救,而使他獲救的,卻是那一粒“沙子”和“神奇的風”。由此似乎證明著,人在這個世界上雖然行動著,自救著,而在關鍵時候改變他們命運的,卻往往是一種神秘而難以預測的力量。他是不是在這樣的陳述中,表達和表現一種他對人的終級命運的思考呢?當人對自身的命運感到因被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和操縱時,我想他一定會產生更為潛沉和更為深刻的孤獨感。這一定是他為什么把此詩命名為“孤獨”的心理機制。
據說,特朗斯特羅姆至今只寫了一百多首詩,而近些年幾乎每年都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沃爾科特甚至呼吁:“瑞典文學院”應毫不猶豫地把諾貝爾獎頒發給特朗斯特羅姆,盡管他是瑞典人。”我甚至由此而聯想到,如果諾獎的頒發地是北京,我們能夠如此“避嫌”地對待中國詩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