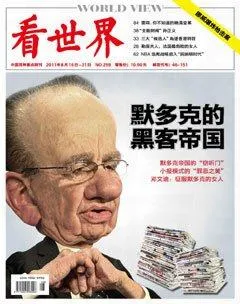雪珥:你不知道的晚清變革
2011-12-29 00:00:00王猛
看世界 2011年16期

雪珥,澳大利亞華人,職業(yè)商人,一直致力于收藏與晚清有關的海外文物,通過挖掘海外史料,運用國際關系理論,以國際化的嶄新視角、跨學科的寬闊思維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改革史,不僅十分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證,更重視思想的理性和寬容,及歷史研究成果的大眾傳播效果。著有《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國運1909》、《大國海盜》、《辛亥:計劃外革命》等。
史學界來了個生意人
雪珥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邁入大學校園,時值改革開放的激情歲月,帶著使命感與浪漫,畢業(yè)后他回到老家。然而,在最基層的單位,卻遭遇了困境: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所有人都有不滿,在種種利益的糾結下,善治的推行竟如此艱難。表面上看,每個個體都善良且向上,都具有理性,可組合在一起,卻如此盲目,甚至明知走在錯路上,也不愿改變。在“民意”、“正義”等大詞的裝點下,每個人都有充足的理由,都是那么的豪氣干云,然而,當共同的悲劇降臨時,究竟誰該負責呢?難道這一切,只是命中注定?離開了機關,雪珥下海經(jīng)商、當被告、在澳洲洋插隊、成了太平紳士……但曾經(jīng)的困擾縈繞不去,熱愛研究歷史的雪珥選擇了晚清政改作為其思考的開端。
“歷史拾荒者”雪珥進入這個領域時,國內(nèi)清末變革的研究狀況是這樣:史家往往以“皇族內(nèi)閣”的騙局和鬧劇作為結論,論證的過程充滿了荒誕氣氛。雪珥自2009年萌發(fā)了撰寫“石頭記”(摸著石頭過河,喻改革之意)的夢想,至今已撰寫出晚清變革三部曲。當《絕版恭親王》、《國運1909》、《辛亥:計劃外革命》在國內(nèi)相繼出版后,顛覆了許多人的觀念。有人說,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一個血腥腐敗的政權,居然主動地大力推行全面變革,積極地、冒險地擴大執(zhí)政基礎……也有人說,他的書比教科書更加可靠。因為誰也無法否定,雪珥的研究橫跨整個時代橫切面,著作中不僅引述了大量被國內(nèi)史學界忽略的國外文獻資料,還有當年大量震撼人心的圖片。
由于長久浸淫在單一的歷史敘述之中,國人對晚清的印象更多的是老邁與麻木,但在雪珥筆下,這個時期卻風云激蕩。可惜的是,一番又一番嘹亮的口號,迎來的是一次又一次慘痛的失敗。雪珥難以理解的是:難道這種種挫折,僅僅是因為出了幾個壞人,僅僅是因為少數(shù)人犯了錯誤?這一切,真的沒有我們自己的責任?
多研究些問題
雪珥寫史,抱持:以“人性”為中心,以“利益”與“權衡”為基本點,不傾向任何“主義”,只研究各種“問題”。利益是外在的砝碼與動力,權衡是內(nèi)在的行為與抉擇。
眾人皆知,任何變革,最重要的是警惕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才是變革最兇惡的敵人。皇權、紳權、民權,其實是三方博弈,其中的樞紐是紳權。在雪珥筆下的晚清變革中,紳權綁架了民權,將自己打扮成民權的代表,最終導致皇權失控,民權最后也沒有伸張。
就拿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四川保路運動為例,保路運動喊的口號是不讓路權流失給老外,實際上它真正和中央發(fā)生爭執(zhí)的是,民營的四川鐵路公司有200多萬兩資金被老總拿到上海炒股票虧了,他們要求中央在收回鐵路時,拿財政來補貼他們這個損失。四川公司和中央談不攏,就罵中央把路收回去是賣給老外,其實中央是借外資來推進鐵路國有。川路的股東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為自己的血汗錢著急,加之革命黨趁機搗亂,中央從武昌把端方的新軍調(diào)到四川去鎮(zhèn)壓,武昌空虛,起義成功。
結合康梁和孫中山等人在海外的所作所為,雪珥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典型的現(xiàn)象:在野者永遠將自己打扮成天使,將執(zhí)政者描繪成魔鬼,這是一種奪權的策略需要;同樣的,后世的執(zhí)政者也永遠把前代的執(zhí)政者妖魔化,以便證明自己是偉大的、正確的。自晚清以來,幾乎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那些摸著石頭過河的體制內(nèi)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責,摸不到石頭、摸錯了石頭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統(tǒng)統(tǒng)成為妖魔化和嘲弄的對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熱鬧、講風涼話、等待著時機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當然永遠正確了。指點江山太容易了,關鍵是怎么做。唾沫橫飛的批判者并不當家,其實并不關心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事務在他看來,無非是將當家人趕下來取而代之的“投槍和匕首”而已。
中國是個大國,而變革是一種利益調(diào)整,因此,在變革過程中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體系來支撐。雪珥認為,實現(xiàn)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一是穩(wěn)定,在穩(wěn)定狀態(tài)下尚且不容易達成的目標,是絕對不可能在動蕩中達成的。醫(y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等,這些問題還得靠變革,靠建設。
告別革命
晚清制度變革是必須的,關鍵在怎么改。任何變革,都應循序漸進,可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國人卻沉浸在浮躁情緒中,認為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變革時間長、見效慢,想在制度建設上強行超車,完全不顧基礎。戊戌變法時,皇帝和楊銳等四個小秘書(即“四小章京”)一下子推出了100多件詔書,很多是將日本文件翻譯過來一發(fā)布,就算改革了。這樣強行推動的體制改革,將張之洞、劉揆一等改革的操盤手都推到對立面上,怎么可能成功?這種浮躁心態(tài)愈演愈烈,到最后,清政府提出準備立憲期為9年,被一致批評為“假憲政”,只好改成6年,可日本憲政改革的準備期卻是30年。
雪珥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不應給群眾以幻覺,不能忽視改革的難度。用幾個口號調(diào)動起人們的激情很容易,但解決問題是另一回事。雪珥將國家比作一家公司,“革命”只能解決所有權的問題,不能解決經(jīng)營權的問題,必須將經(jīng)營權的問題和所有權的問題分開來看,不能一鍋飯沒煮熟,就把鍋給砸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思路。亨廷頓說過,變革的關鍵在于有效行使權力,但在晚清變革中,紳權卻綁架了民權,導致皇權失控,其實變革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官紳卻操控著實際的行政權,為一己之私,他們不惜上下?lián)芘罱K造成了大分裂。所以說“清亡于地方分離”,如果在變革時能加大集權,可能會少走彎路。不過,這個集權未必是中央集權,像日本變革,集權于議會,最終取得了成功。
清代的放權是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的。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中央讓曾國藩他們自己征兵、就地籌糧籌款,這就造成太平天國打完了,軍隊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財權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碼嚴重不足。到了1909年的時候,中央一方面繼續(xù)下放權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權,把司法權、立法權從原來的省長、市長手中分割開,在各個省建立咨議局,選舉產(chǎn)生一些地方領袖,來與地方官員形成制衡。各省咨議局成立之后,不斷與地方衙門出現(xiàn)矛盾。而當時中央政府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議會。地方的長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場上混到總督巡撫,那都是人中龍鳳,他們馬上就看明白了,紛紛向議會靠攏,憲政的旗子舉得比誰都高,民主的聲音喊得比誰都響。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權力越來越分散。
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權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沒有有力的行政資源去保障,改革措施如何推進?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權威資源的放棄,來換取改革的推進,最后事與愿違。中央放了很多的權力給地方,最終18個行省變成18個獨立王國。
于是雪珥得出一個結論:晚清的改革失敗,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最終導致失控。